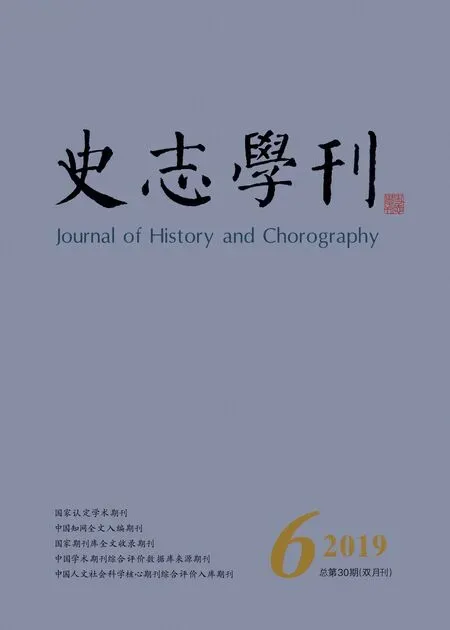關于時間視域下村志寫作的思考
張宗帥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一、鄉土時間觀念的生成及其坍塌
(一)鄉土時間觀念由農業生產活動所決定。農民群體以農業生產為導向,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鄉土生活的時間框架。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區別,除了地理空間差異,更根本地與捆綁在不同地理空間上的時間觀念有關。哈布瓦赫指出,生活中“家庭和土地非常自然地彼此緊密聯系在一起”[1](法)哈布瓦赫.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113),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既是以家庭為單位與相對固定的熟人網絡建立聯系的活動,同時也是與非人造對象(土地、農作物、動植物、山川河流等)在周期性的氣候環境下長期相處的活動,農民按照物候、節氣、歷法來開展田間勞動,這種生產勞動中的“時間”不是測量的時間,而是節奏的、循環的時間,如楊聯陞與梅歐金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鄉村人并不真正需要精確細微地安排時間,他們需要的是知道一年年循環往復的那些重要的日子”[2](美)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三聯書店,2009.(P227)。這使得傳統農業生活的時間觀念根本上不同于建立在機器大分工大合作基礎上的現代工業社會的時間觀念。如筆者曾調研的魯中傳統半工半農地區,解放前普遍沒有鐘表,人們靠煤礦汽笛掌握上班時間,去做工的農村婦女剛開始工作時,會突然放下生產線上的活計,跑回家去蒸饅頭。在她看來,面團發了,接下來“自然”要蒸面,這種“自然時間”必然會與工業生產的“人造時間”相沖突。再如筆者在貴州農村調研時,有些地方父母常因農業生產需要,給孩子請假,不讓孩子按時上學。對這些行為的道德判斷,很容易忽略時間觀念的多元性。農民被認為“沒有時間觀念”,事實上他們只是沒有“現代時間觀念”。楊懋春指出,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園工作中時“他們不時常計算一甲地的作物收成能賺多少錢,不以虧本或盈余為標準而考慮農業值得經營或不值得經營”[1]楊懋春.中國鄉村文化的特點.臺大社會學刊,1968,(4).。一旦農民在農業生產中計算時間成本,那么傳統農業生產必定會被拋棄。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鄉村工業的發展、大量的外出打工和電視的普及,使得以八小時工作制為代表的現代工業社會的時間觀念進入到鄉土社會中,不斷沖擊著傳統的以農業生產為導向的鄉土時間觀念,鄉土時間觀念經歷著坍塌,伴隨而來的就是土地拋荒,農民越來越傾向于進入到現代工業生產活動中去,或者進廠或者進城,因為接受了現代工業生產的時間觀念的洗禮后,農民群體開始從現代工業社會的時間效率上看待自己的勞動,工業生產的時間生產效率自然高于傳統農業生產的時間生產效率。
(二)鄉土文本承擔著鄉土時間觀念的再生產功能。傳統鄉村生活中的個體通過集體記憶的方式來感知時間,集體記憶承載著鄉土時間觀念并以鄉土文本的形式傳承下來,這些鄉土文本表現為大量諺語、傳說、習俗信仰等,鄉土文本反過來鞏固了農民的時間觀念,承擔著重要的鄉土時間觀念再生產功能。傳統鄉村社會中的農民群體不是直接以個體的方式對鄉土時間觀念進行體驗和感受,而是以群體的時間——集體記憶的方式來對時間觀念進行直接感知。因為,雖然在每個人都有他作為個體的時間感覺,但作為人類生活感知的基本范疇,個體所感知到時間之流的綿延并不等同于普遍的時間觀念。時間觀念是非個人的框架,“它不僅包含著我們的個體實存,也包含著整個人類的實存”[2](法)涂爾干.渠敬東,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商務印書館,2016.(P12),時間觀念是群體生活的一種節奏,它源于社會生活,是社會所有成員共享的一種集體意識和集體記憶,是一種傳統文化的遺存。如孟德拉斯所指出的那樣,農業勞動者生活于其中的時間并不僅僅是受到農作物自然生長周期和氣候紀律的影響,它同時也是傳統文化的遺傳,農業經營者雖然是自己時間表的主人,“但實際上卻要服從習慣的安排,他對這種安排的服從是很刻板的,就像他并非是自己時間表的主人一樣”[3](法)孟德拉斯.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P54)。集體記憶是時間流的“沉積物”,它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一種自覺的意識,而更傾向于一種自動化的無意識結構。要維持一種承載著時間感覺和時間觀念的集體記憶,需要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鄉村不斷地生成,例如農民按照共同的時間節律(節氣、氣候)在土地上展開勞作,收割的人不用協商,就在同一天割麥。同時這種同相同節律勞動還必須能夠實現代際傳承,即農民要和自己的子女長期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個農業家庭的土地能永遠耕作下去。
(三)鄉土文本的缺失與鄉土時間觀念的坍塌。近現代以來,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的集體記憶和鄉土知識生產(具體以鄉土文本的形式呈現)逐漸式微,現代城市文化主導的學校教育加速了鄉土文化的消失,鄉土時間面臨都市時間的全面取代。清末民初以來實行的“新式”教育,強烈地沖擊著鄉土社會的文化邏輯,并引發農村人才的“水土流失”(費孝通語),“新式教育的推行,促使鄉村在中國教育發展中逐步被疏離和拋棄”[4]饒靜,葉敬忠,郭靜靜.失去鄉村的中國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國鄉村——一個華北山區村落的個案觀察.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現代教育的教學內容以城市為導向,缺乏農村社會生活和農業生產的知識內容,承載著鄉村集體記憶的鄉土文本嚴重缺失。“鄉村教育堅決地摒棄鄉村經驗,一味地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進發,中國社會因此越發走向一種單面社會,這種社會因為缺乏多面向而將變得很脆弱。”[5]熊春文.文字上移:鄉村教育走向終結?社會學研究,2009,(5).農民把孩子送去城里的學校,教學點也被集中到中心城鎮,這使得即便是出身農村的學生,在學習內容和學習環境上都與鄉土隔離起來,這從根本上掐斷了鄉村集體記憶和鄉土知識的傳承。布迪厄與波特斯基指出:“現代學校教育加速了農民(包括鄉村的小商人和小手藝人)的孩子的文化斷裂過程。”[1](法)布迪厄,波特斯基.社會結構的變遷與教育需求的變化(1978).清華社會學評論(第5輯),2012,(6).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的農村子女,很難認同農村的生活方式,通過讓自己的孩子參與到城市導向的教育競爭中,往往造成農村出身的人對自己社會身份的厭棄和文化身份的不自覺。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越來越多的農民子女進城接受現代教育(通過將學校集中到中心城市,撤并農村小學),鄉村人才的流失,使得共同的田間勞動急速消失,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鄉村的消失,使得產生于其中的集體記憶也快速坍塌。
二、村志是承載鄉村集體記憶的重要文本形式
(一)保留鄉土時間具有重要意義。城市中國召喚一種多元性的文化邏輯的回歸,這對于應對全球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文化危機、生態危機具有重要意義。鄉土時間之于城市時間,絕非同一“時間線條”上的低級階段,而是具有不同文化邏輯的獨立類型,它具有豐富的文化價值。鄉土時間因村莊不同而不同,它具備包容性和多元色彩,以至于每個村莊都有其特點,這與同質性的現代城市時間截然不同。中國領土廣闊,氣候和水土條件有著極大的地域性差異,由此產生了特有的“風土”概念,“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2](元)王禎.王毓瑚校.農書·地利篇第二.農業出版社,1981.。在豐富的地域性差異下,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實踐經驗,在這種多樣化的“風土”條件下,鄉村生活呈現出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就沉積在與之相應的鄉土時間之中。這種多元性的時間觀念不同于都市生活中的整齊劃一的“標準時間”,它更具有人情味和親和性,對于緩解人在單一標準時間下的緊張和焦慮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人作為在時間中展開和存在,在現代大機器生產和全球市場資本流動的時間節奏帶動下,呈現出扭曲和迷失的狀態,人自身時間感覺的豐富性越來越脆弱。從現代人與自我和自然這兩個角度來看,多元性的鄉土時間,是具有糾正現代化偏失,實現人的自在狀態的作用。
(二)村志是延續鄉土時間的重要文本形式。鄉土時間觀念是無法直接重構的,它依賴鄉村集體記憶的傳承不輟,而既有的傳承方式,如口述傳說、民間儀式等等已面臨全面危機,目前亟需一種介入性的文化實踐來延續這種文化邏輯,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發明鄉土中國的文本形式,這種文本形式應該容納鄉土空間內的一切內容,一定意義上,實踐層面上他就是一部“村志”。中國歷來重視對“方志”編撰,它無疑對村志寫作具有啟發意義,但村志寫作與“方志”有巨大的不同,即前者自上而下,遵循嚴格的政治時間(古代為帝國時間,在近代為城市時間),后者是自下而上的,遵循村莊獨特的時間邏輯。并且,傳統方志是記錄性的,具有檔案價值,村志則是主動介入的,在知識層面具有鄉土教育的意義,在情感層面,村志具有文學的感化作用。“志”作為一種悠久的寫作傳統有其獨特優勢,重新激發這種文本類型所蘊含的構建地方集體記憶的活力,創造一種全新的村志文本,將賦予“志”以全新的時代精神。作為介入性的文化實踐,村志寫作試圖通過重建鄉村集體記憶來平衡全面現代化與普遍鄉愁的張力所制造的精神裂痕,它以村莊和村莊中的普通農民為主體,以農業生產、自然生態、鄉土日常為內容,以揭示鄉土生活人情味、重建人與自然(土地)的豐富情感關系為文本風格,從而在一定程度與記錄式的、崇尚權威、名人,非日常的方志傳統區別開來,村志寫作不僅承擔著發掘、探尋、保存鄉土知識的使命,還要呈現零散知識、獨立對象之間的邏輯和關系,它不是落滿塵灰的無機無趣的歷史檔案薄,而是具有可讀性的活在文本上的有機有趣的“文本化的鄉村”。
三、村志的歷史發展情況和現狀
(一)村志的歷史發展情況。“志”既可理解為一種文體規制的“志書”,也可理解為一種“志向”事業,在中國的書寫傳統中,以縣志為典型代表的志書是一個獨特而悠久的文體制式,但是以村為描寫單位的“村志”卻是一種非常近代的文體。村志在歷史上出現較晚,中國現存最早的村志文本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安徽池州的《杏花村志》和康熙五十七年(1718)上海閔行的《紫堤村小志》。另外值得注意的村志文本為清光緒初年(1873—1875)太平天國與捻軍時期,李鴻章為重建地方了解民情,因編纂《畿輔通志》的需要而作的地方普查報告:《深州村圖》《青縣村圖》《正定縣村圖》,這些村圖以村為單元,包含了河北各村的人口、土地、鄉紳等豐富信息。對于中國的不同地區,村志編寫情況也有較大不同,如山西最早的村志為光緒中后期的《祁縣谷戀村志》,民國時山西保留至今的村志有5種,其中《虞鄉縣第三區黃旗營治村志》(1945)是在虞鄉縣組政經軍統一行動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治村修志的情況下修成的,也是山西官方首次組織編寫村志。1963年毛澤東提出“用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P297),號召在廠史、社史基礎上加上村史、家史,作為推動“四清”運動、進行階級教育與革命傳統教育的工具,“四史”運動蓬勃開展起來。因為處于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下,這一時期的村志寫作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運動”。20世紀80年代,在編修地方志的熱潮中,也開始零星出現村志作品,但這一階段的村志作品數量不多。到了經濟發達的20世紀90年代,由于地方志編寫的制度化和正規化,村志的數量和“規范性”都較20世紀80年代有大幅的提高。根據已出版的村志文獻(還有很多村志文本是以非正式出版的形式存在)進行統計后發現,中國的村志寫作文本在21世紀以后開始大量涌現并在數量上占據了主體(相比于上世紀80年代),林麗娥也指出,“進入21世紀以后,村史志的數量呈井噴式狀態”[2]林麗娥.近三十年中國村史志研究.寧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總量在750本左右(可能會更多)。
(二)現有村志文本的特征。目前現有的正式出版的村志具有以下特征:從文本的寫作者的角度來看,村志文本的實際執筆人多為地方知識人,如本地作協成員、退休教師等本地鄉賢成員,以老年人為主,創作形式多為本村人集體創作,由家族中人擔任主編,同時設編委會、顧問委員會。從組織形態上,早期村志多為村民自發編寫,到了后期,鄉鎮志和村志的編寫被納入到各省市縣負責地方志工作的機構指導范圍,如河北滄州某地的鄉黨委政府專門成立了征編工作領導小組,下設專門辦公室,各村都成立了以村支書和村主任為正副主任的征編委員會,聘請了責任心強、文化功底深厚的人士為主編或主筆。從文本體例來看,村志基本上都是仿照縣志體例,內容不外建制沿革、自然地理、人口宗族、經濟社會(農業、工業,商業,農業側重合作化,工業側重鄉鎮企業)、政治(黨政機關組織)、文化風俗(教育、宗教)、人物(歷史人物、革命烈士、領導干部、讀書人),但與縣志體例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些村志專門開辟一章論述本村的獨特處,如特色企業產業、宗族譜系、物產資源等。從編寫村志的村莊類型來看,可以分為四類:(1)上世紀80年代以來因鄉鎮企業而發展起來的“明星村”,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蘇等這些村集體經濟發達的地區,如《王化村志》《謝田村志》。(2)沿海開放城市的城郊農村,主要分布在廣東深圳、東莞等地,大都因為經濟特區的城市化和引進外資企業而發展起來,村莊經濟發展主要靠房地產建設和物業出租,這類村莊多已轉為社區,名為村志,實際是社區城市化發展史,如《和平村志》《四村志》。(3)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物遺跡的村莊,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這類村莊的特點是,交通發達、資源豐富、文化古跡眾多,多為鄉鎮政府的所在地,名為村志實為鎮志,實際上是超級村莊,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普通村莊,如《賈村志》《王陶村志》。
(三)現有村志文本的局限性。本世紀以來的村志文本,從描寫對象上看,多為經濟發達、具有特殊性的“明星村”“超級村莊”,且多處于城鄉結合地帶的村莊,這類村志寫作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邏輯為導向的,而缺失了傳統鄉村社會生活和農業生產的層面,因此并不能很好地實現記錄鄉村獨有的文化邏輯和地方知識,尤其是鄉土時間觀念的功能,村志作為承載鄉村集體記憶,保留鄉土時間觀念的文化實踐職能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從體例上看,這一類村志文本在體例上大多模仿方志的體例,從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傳統方志文體的固有問題:明清以來所確立下來的傳統方志的文體制式,體現出一種中央-地方的分類體系,其中對于寫作格式的嚴格規定,在于追求一種“抽象的客觀性”[1]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新史學,十八卷二期(2007年6月).,在有意無意中,方志寫作成為一種分類系統和知識類型,如對地方“八景”的描寫呈現出程式化的特點,對“人物”只記載考取功名和忠孝之人。這種分類體系造成傳統方志文體形制的諸多限制,以至于它雖號稱博物全書,但大量對象是無法納入到它的分類體系之內的。這種知識分類也影響到村志文本,如現有村志文本中對地方風景名勝濃墨重彩,“人物”在這類村志中占據了較大的篇幅,村志中所重點書寫的人物為領導干部、大學生、教師醫生等,而極少將村中普通人物如農民、工匠、手藝人、邊緣人物等納入寫作范圍,其對人物、人才的入選是以行政頭銜、體制內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為標準。在對所記載的鄉村事件選擇上,也是惟政治事件、歷史事件馬首是瞻,地方普通鄉土景觀、普通民眾的生命情感(生老病死)、日常生活(飲食、器具)往往闕如。傳統方志體制上的局限性體現到村志文本中來,具體表現為鄉村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被忽視,如農事耕作(包括農作物的種植、生長、收獲,鄉土器具、玩具)、鄉土作物(包括谷物、蔬菜、果樹等)、鄉土動物(家養動物、野生動物、昆蟲等)、生活方式(生老病死、文化娛樂、民間儀式節日、食物制作等)、鬼怪故事等等,都無法納入到村志中,事實上這些被忽視的才是傳統鄉村時間的生成和展示場域,才是村志寫作所要承載的鄉村集體記憶之所在。
四、開辟新的村志寫作方向
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是人所賦予的,村志寫作就是一個構建和賦予價值意義的創造過程。在作者試圖描述鄉村社會的方方面面之前,首先要對現有各種鄉村書寫文體的洞見和遮蔽有一個深入的認識。除了在創造性、批判性地借鑒和運用傳統方志和現有村志文本的寫作方法之外,還要借鑒其他的鄉土文本類型,比如人類學的“民族志”和文學的“非虛構”等。
(一)創造性地借鑒運用傳統方志和現有村志的寫作方法。為了克服目前現有的村志文本的局限性,就需要在繼承傳統村志文本寫作中的積極因素的基礎上,探索一種新的村志文本寫作形式:首先要借鑒傳統方志中好的工作方式和寫作方法,依托現有的地方文化資源,我國八九十年代以來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地方史志編輯整理工作,設立了地方史志辦等專門的組織機制,留下了寶貴的地方文史資料,這一部分資料圈定的知識范圍為縣域,而一村必被包含在一縣之中,只有從宏觀上對一縣之人文地理、政治經濟有宏闊的了解,才能進一步對以一村為單位的村志書寫進行微觀的介入。除了注意搜集地方文史資料外,更重要的在于建立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聯系,縣一級的政協、文化館、圖書館、史志辦中的文化工作者,鄉鎮一級的各類藝術協會成員(如書法協會、音樂協會,多由鄉鎮退休教師、公務員組成),村一級的退休工人、退休教師、村兩委工作人員、家族長老、賬房先生等(這些人了解村中事務及村莊人際關系),這些人員組織構成了一個地方知識文化生態的“場域”,是地方文化生活的重要實踐者和村志寫作的重要幫助者。其次,傳統方志寫作中充分利用檔案資料、圖書資料(如報刊雜志、舊志書、史書、族譜、日記、賬本等)及口述材料(口碑、諺語、歌謠)、碑刻等實物材料的寫作方法也要在新的村志寫作中學習繼承下來,力求充分地占有材料,以記錄下農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識,實現一種接近于地方志“述而不論”的樸實記述的文體風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嚴守志書體例規范,而是要創造性、批判性地吸收其中的積極方面。前面所提到的傳統方志和現有村志文本的局限和問題,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如傳統方志和村志中嚴格遵循著“越界不書”的原則,超出本行政村即不予記錄。這種觀點忽視了一村必在一鎮之中,對于某一村之了解必建立在對其所在鎮之了解之上,即村志書寫不應只關注于某村,還應從鄉鎮一級的視角發現某村與其鄰村之交流關系,將某村放在其所在鎮的村莊關系網絡和人文地理界限中進行定位。
(二)借鑒人類學民族志的文本類型。在中國開創以一個村莊為單位進行詳細書寫的這種方法,受到人類學“民族志”的很大影響。人類學自傳入中國以來,就集中在鄉村社會研究上,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1899年出版的《中國鄉村生活》中指出:“中國鄉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1](美)明恩溥.午晴譯.中國鄉村生活.時事出版社,1998.(P1)這種認知心態使得西方的人類學家一直把鄉村社會作為中國人類學研究的重心,如荷蘭學者高延的《中國宗教系統》(1892)、美國學者葛學溥的《華南農村生活》(1925)。20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楊懋春、林耀華等有志于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人類學者,以村落為基本單位進行了大量的社區研究,寫出了《江村經濟》(原名《中國農民的生活》,費孝通,1939)、《金翼》(林耀華,1944)、《山東臺頭:一個中國村莊》(楊懋春,1945)等優秀的人類學著作。可以說,人類學對于中國以村落為對象的地方性知識的生產功不可沒。新的村志寫作與人類學民族志的共同特點在于對地方性知識、鄉村集體記憶的關注,對民間故事與風俗、地方文化傳統的發掘和研究,強調以一種在地的“當地人”眼光來認識鄉土世界,而非一種城市人的工業“文明”的眼光來看待鄉土生活,以“深描”的方法揭示出鄉土世界獨特的文化邏輯。同時,一種新的村志寫作與人類學民族志寫作的顯著區別在于:首先,人類學民族志不論是功能主義的田野調查還是文化闡釋主義的“深描”,都強調“問題”的優先性,受制于民族志的文體制式和學術規范,使得許多“多余”的材料無法進入到民族志寫作的問題域中,造成一種學科的盲視。其次,民族志書寫作為一種科學,遵循對象化的研究和客觀中立態度,這使得民族志文本缺乏與在地民眾的聯系,終究是一種學術寫作,很少和地方文化生態系統發生聯系。而一種新的村志寫作正是試圖克服民族志寫作中的局限,借鑒中國傳統方志“博物之書”的定義,將一方之萬物統納進來,而不是“問題先行”。同時,尋求將村志寫作的成果運用到在地的文化生活中去。
(三)借鑒文學和非虛構寫作的寫作方法。除了人類學民族志,近代以來的“鄉土文學”也是地方性知識的重要生產文體,如杜贊奇所指出的那樣“在漢語和日語中,20世紀前半葉流通于東亞的關于‘鄉土文學’及‘民族學’的符號標記常常可以互換”[2](美)杜贊奇.褚建芳譯.地方世界:現代中國的鄉土詩學與政治.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P23),而正是來自于弗雷澤等人的人類學著作和屠格涅夫等人的鄉土文學構成了現代中國關于地方話語的理論資源。作為一種地方知識生產的村志寫作與近代以來的鄉土文學都是圍繞著“家鄉”這一地域范圍展開敘述,但不同之處在于,鄉土文學偏重于文學性中想象虛構的部分,村志寫作的文學性并不體現在它的抒情性上、主觀性上(如近年來充滿著感傷色彩或浪漫主義的“返鄉體”),而是在文體上效法于《水經注》《洛陽伽藍記》《夢溪筆談》這類古代說明文、記述文,將寫作者的主觀情感都凝練在對描寫對象的描寫上文字本身上,不追求傳統文學敘述的故事性,而是試圖實現非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村志寫作以事實性的采訪、回憶作為素材,在此基礎上做輕度的“敘述”加工,但是這樣的“敘述”不是小說家那樣的推崇“想象力”,不是深度地提料加工,而是反其道而行,盡量地貼近事實性的素材,更像是一種現象學的“還原”。新的村志寫作在文體上還可值得借鑒吸收的是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 writing),非虛構寫作是基于“事實”前提展開的寫作活動,強調運用采訪、口述、文獻等材料,以接近新聞描寫的方式來還原真實的生活經驗。村志寫作與非虛構寫作的共同點在于:這兩種寫作都不是在密閉空間苦思冥想完成,而是要求寫作者進行扎實、詳實的采訪過程與繁復的資料研讀。但它們的不同點在于:一般的非虛構寫作多描寫當下現實情境和公共性議題,以時代社會的快速變遷為關注點,主題較為宏闊,而新的村志寫作則是面向鄉村“長時段”歷史時間和集體記憶的寫作,追求更細微的時間感覺,而非新聞性的社會歷史“事件”。
(四)村志寫作是參與鄉村文化保護的實踐過程。村志寫作是一個介入鄉村文化生活的實踐過程,村志寫作者根據自身的文化資源,以合適的方式和契機與縣鄉鎮一級的地方文化實踐者建立聯系,介入到地方文化“場域”中,積極動員起當地人的地方生活知識和人際資源經驗,為村志寫作收集豐富的地方文化知識資源。村志寫作所最終呈現出來的文本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結果,但村志寫作更重要的在于參與到地方文化場域的這個實踐過程,即以一種文化的身份返回到家鄉,以自身的文化特長和知識背景積極參與到地方文化生活中去。例如村志寫作者積極參與村級藝術協會[1]村級藝術協會是一個在黨的領導下的群眾文化組織,它是一個由村民及各類返鄉、退休有一技之長的熱心人員組成的,具有公益性質的服務鄉村文化社會生活的協會組織。的發展,調動村民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積極性、主動性、自覺性。對于村志寫作者來說,如能協助參與村級文化藝術協會的建立、運行,將極大地方便村志寫作工作的展開,如幫助村志寫作者動員鄉村群眾,組織座談、提供素材等。實現村志寫作的過程化,使村志寫作超越“寫作”本身,成為鄉村文化重建的一項參與式活動。村志寫作的成果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鄉村本身,以多種形式呈現村志寫作的成果。除了寫作村志文本,村志寫作者還應在發掘鄉村文化資源的同時,促進鄉村文化資源的轉化和展示,如組織書畫展、攝影展、非遺展演等形式,促進鄉村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村志寫作所生產出的地方知識將作為鄉土教育的教本,平衡過度以城市為導向的現代教育,村志文本將會成為本地鄉鎮中學最后的鄉土讀本和校本課程,同時,村志文本還應進一步以鎮級、村級文化活動室、文化館、博物館為依托,以各種鄉村記憶館、民俗博物館、名人紀念館為活動場所,以村級藝術協會為組織者,開展村志文化講座,實現村志文本的社會化,使村志寫作的成果——村志文本成為地方知識場域的一部分,成為未來可重寫、可再生的鄉村社會文化文本寫作實踐。
總之,由于地方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及寫作主體知識背景的差異,村志寫作實踐必然是多樣化的,它的介入形式和文體樣態也是多元和未知的。但這一點是相同的,即:村志寫作的目的在于,以一種開創性的文體風格生產出地方性知識話語,創造出鄉土中國的富于情味的文本形式;建構再生產出正在坍塌的鄉村人自身時間觀念和情感結構,塑造鄉村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共同體的社會集體記憶,開辟出鄉村作為自由精神之創造的可能性空間,借此彰顯鄉土社會獨特而豐富的文化魅力,進而為現代化、城市化所引發的文化困境,提供若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