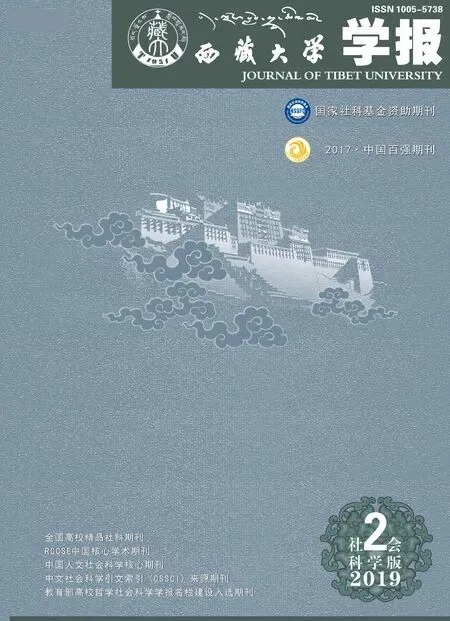論藏族文學中的生態美學意蘊
——以阿來《蘑菇圈》為例
王傳領
(聊城大學傳媒技術學院 山東聊城 252000)
時隔18年之后,曾經憑借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斬獲茅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阿來再度以中篇小說《蘑菇圈》榮獲2018年魯迅文學獎。作為國內最重要的藏族作家,阿來的文筆始終沒有離開藏文化圈,他對于藏區文化的炙熱感情和深刻理解,不僅構成了筆下引人深思的民族敘事和典型人物譜系,還向受眾展示了以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眼中所理解、所認知的藏文化形態。對于阿來而言,藏文化既是滋養其文學創作的主要源泉,更是塑造其文化身份的主要基因。因此,包括藏區環境、藏區民眾、藏區生活以及三者之間關系等一系列關涉藏文化因素的變化都會在阿來的文學作品中得以體現,并影響其作品的創作基調。自2015年起,阿來接連創作了《蘑菇圈》《三只蟲草》和《河上柏影》三部中篇小說,并被合稱為“山珍三部”。在這三部小說中,作家向我們展示了區別于《塵埃落定》隱秘敘事的另一種倫理情懷——藏區生態。這不僅反映出西藏這一公眾印象中遠離塵世喧囂的高原凈土同樣存在著人與自然的多重矛盾,也契合了當下生態美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在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生態文明成為共識的當下,有必要從生態美學角度對阿來的“山珍三部”,尤其是《蘑菇圈》中所呈現的生態倫理和美學問題加以再認識再思考。
一、人類中心與生態生存:《蘑菇圈》對于藏區生態美學的雙重折射
作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最具創新價值的理論建構,生態美學始終都被視為中國美學標志性的學理獨創。尤其是在上世紀初美學傳入中國之后,被西方美學理論和學術話語所困囿的中國美學界亟需尋找能夠被世界美學所認同、所重視的理論體系,并確立中國美學在世界美學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生態美學的提出和建構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長期以來中國美學話語的缺失,還在踐行“全球共同問題,國際通行話語”[1]這一學術準則中找到了建立學術自信的合理路徑。以上世紀80年代《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中將文藝與生態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為肇始,到徐恒醇出版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的著作《生態美學》,再到曾繁仁在《生態美學基本問題研究》中系統闡述其具有代表性的存在論生態美學構想,中國當代生態美學的話語體系在三十余年的研究拓展中得以初建。其中,最重要的建樹之一便是廓清了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之間的異同,并認為與國外環境美學研究相比,生態美學“力主一種將之調和的生態整體主義,或者是更加進一步的生態存在論”,因此,更加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生態整體論觀。以此為基礎,程相占提出了“生生美學”的概念,并認為生生美學是“以中國傳統生生思想作為哲學本體論、價值定向和文明理念,以‘天地大美’作為最高審美理想的美學觀念,它是從美學角度對當代生態運動和普世倫理運動的回應”。[2]總體而言,生態存在論美學與生生美學一起構成了當代中國生態美學的主要理論形態,事實上也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藝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阿來的《蘑菇圈》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除了反思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之外,《蘑菇圈》還折射出作家對于當代生態體系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問題和人類生態生存問題的反思,這兩點尤其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首先,《蘑菇圈》中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痕跡成為藏區生態之殤,這也是阿來在作品中反復描寫的重點。曾繁仁先生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對抗是當代生態美學向前推進的重要障礙,這不僅意味著人類與環境之間存在著鮮明的主次關系,還表明人與環境在事實上處于二元對立之中,“甚至‘環境’這個術語都暗含了人類的觀點:人類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圍繞著他。”[3]因此,生態美學的重要議題之一便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退場。只有這樣,自工業化以來人類以自我為中心所進行的對自然生態的壓制和破壞才能得以緩解,人類中心主義所帶來的“審美剝奪”(段義孚語)也才能真正回歸到具有非功利性特質的生態美學——“以生態人文主義為哲學根基所建立的生態美學是迥異于傳統的在人類中心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學形態的。”[4]而在《蘑菇圈》里所講述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故事中,作為主體的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的掠奪甚至摧殘卻成為始終的基調。縱觀整部作品不難發現,當1955年工作組第一次進駐機村,就開始宣傳所謂的“新的對待事物的觀念”,“這種觀念叫作物盡其用,這種觀念叫作不能浪費資源。”[5]基于這種觀念,機村的原始森林在十余年內被砍伐殆盡,這是以機村為代表的藏區生態第一次遭到大規模破壞。而當兩三年后工作組第二次進駐機村后,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甚至是“人定勝天”的思想得到了更深入的貫徹。工作組提出要把糧食產量提高一倍,因此,提高施肥量,最終結果便是“機村有史以來長得最茁壯的莊稼幾乎絕收。上面卻要按年初上報產量翻番的計劃征收公糧”。[6]由此造成了最嚴重的饑饉。不難發現,相比于過去“陽光朗照,草和樹,和水,和山巖都閃閃發光”、聽見布谷鳥叫而出現“一個美妙而短暫的停頓”[7]的原始生態,機村已經開始逐漸遭到嚴重破壞。除了原始森林被砍伐殆盡之外,隨之而發生的前所未有的大旱使得整個村子都陷入了絕望之中,最后只能依靠斯炯的秘密蘑菇圈勉強存活。作為有能力支配整個生態系統的特殊物種,人類源自自然、依賴生態的宿命似乎正被逐漸忘卻,取而代之的則是對自然的瘋狂掠奪、肆意踐踏以及未得到滿足時的強烈敵意。盡管作品并未特意強調“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但是人類站在崇高地位之上來俯視其他物種的種種表現,卻成為了藏區人們與生態系統和解的主要障礙。
借由機村在短短幾年內所發生的生態劇變,作家向我們展示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技術進步的作為主體的人,面對自然時的心態已然轉變,即由和自然的和諧共存轉變為將自然看作改造、甚至是掠奪式征服的對象,“地球作為養育者母親的隱喻逐漸消失,而自然作為無序的這第二個形象喚起了一個重要的現代觀念,即駕御自然的觀念。”[8]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不只是作為外來人的工作組,即使是機村村民也開始在貪欲的驅使下,破壞自然生態,無論是在災荒年男人進山偷獵,還是為獲得暴利而采摘松茸,都是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下對于自然這一血脈家園的審美異化,也是追求生理與倫理功利性的傳統藝術審美的典型特征。
其次,《蘑菇圈》中對于人的生態生存給予了特殊的關注,這不僅契合了生態美學對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重視,同時也是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的重要差異。當然,毋庸諱言的是,生態美學的提出和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環境美學的啟示,但是僅僅關注超越藝術哲學的、藝術周遭事物的欣賞顯然不符合當今紛繁復雜的審美形態,也沒有脫離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因此,難以為日漸豐富的文藝新形態和新批評提供審美支持。與此不同的是,曾繁仁和程相占所倡導的生態美學借生態倫理和生態知識之力,不僅超越了環境美學的傳統研究范疇(環境審美),還以生態整體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從而實現了對于作為生態要素之一的人的關注,尤其是給予了人的感性生命以更加多元的審視。“生態審美不應只強調它的適當性,也應強調它的感性體驗性。由此,生態審美應是一種感官的感性體驗,而不應是單純的對生態知識的認知或生態倫理的認同。”[9]由此可見,生態審美的重點不只在于對于生態倫理和生態知識的整合,也不只是對于環境美學的顛覆性重構,對于人的生態生存的關注才是其最終落腳點。就《蘑菇圈》而言,阿來著重描寫藏區生態在幾十年間遭到嚴重破壞的根本目的也是在于對藏區民眾的重新解讀。事實上,縱觀整部小說不難發現,由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所導致的生態災難也反過來給予了人類以沉重打擊,甚至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工作組第一次進駐機村就開始無節制地向村民索要牛奶和蔬菜,甚至在一個多月的羊肚菌季節里向每戶人家索要牛奶至少二十余次。不僅如此,工作組還提出了違背生態規律的將糧食產量翻番的設想,并直接導致不肯熟黃的麥子在霜凍之后絕收。如果說這些滿足個人口腹之欲的掠奪尚未對生態系統整體造成嚴重損害的話,那么,工作組砍伐原始森林所導致的溪流干涸則是大旱之年自然所給予人類的最嚴厲懲罰。當然,這種情形在80年代之后并未得到有效緩解,盜伐林木的年輕人被逮捕或者落懸崖,阿媽斯炯的蘑菇圈也被利欲熏心的人用釘耙毀壞……凡此種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功利性行為都忽略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自適應性。盡管對于生態的過度索求使得人類獲得了短暫的物質豐裕,但是,人的感性生命和感性體驗卻遭到了嚴重損害,因此,“走向生態觀、人文觀與審美觀的結合,實現人的詩意的棲居”[10]的理想也就絕無可能實現。
縱觀整部《蘑菇圈》不難發現,阿來對于人和自然的生態關系有著極為深刻且全面的認知,盡管他在作品中以非常克制的筆觸來展現生態破壞及其產生的嚴重災難,但是,他對于藏區生態的關切之心和感恩情懷卻始終溢于言表,這一點也在敘述當地民眾截然不同的生存體驗對照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僅如此,按照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阿來也將其筆下所塑造的人物進行了美與丑的區分。針對何為生態美學視域中的“美”,曾繁仁曾經做出這樣的判斷,“凡是符合系統整體性,有利于改善人的生態存在狀態的事物就是美的,反之,則是丑的。”[11]以此為標準,尊重自然、保護生態的阿媽斯炯顯然是最美的,而破壞自然、肆意掠奪的工作組則是丑陋的代名詞。總體而言,阿來筆下的機村,有著非常典型的存在論美學的意味,因此,從不缺乏對于人與自然之間生態關系的審視和判斷,也從未脫離生態整體主義的人文精神而存在。
二、消費社會與理性異化:《蘑菇圈》對于藏區生態美學的多維反思
作為一種新的審美方式,生態美學將美學和生態學進行了有機融合,并試圖以生態學的知識體系、倫理觀念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審美體驗和審美價值來突破傳統美學乃至西方環境美學的研究框架。它嘗試引導審美主體從生態和諧的視角來看待審美對象,并且將人類本身作為生態整體的組成元素,進一步消解了人在生態系統中的主導性作用。當然,生態美學的提出也是結合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生態文明建設被列為基本國策的當代現實所做出的深刻反思和積極應對,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情懷,因此,也就更具文化研究層面上的指導意義。而這也正是生態美學的革命性意義所在——“它從生態審美的角度,一方面嚴厲批判忽視生態健康的傳統審美偏好,另一方面努力揭示被納入資本運行邏輯的所謂的‘審美價值’的嚴重破壞力。”[12]若以此為基點來尋求當代生態問題的發生根源,那么,消費社會所帶來的“生產—消費”體系以及技術發展所導致的理性異化,則是破壞生態審美的最為重要的文化原因。這兩點在《蘑菇圈》中也有深刻反映。如果說作為邊疆地區的藏區生態系統是留給大眾想象原始之美的最后一塊圣地的話,那么,這塊圣地在消費主義思想和科技進步倫理之下所產生的生態問題則應成為警醒人類的最重要呼喊。從這一角度來看,與其將《蘑菇圈》視為對于藏區環境問題的揭露,不如將其看作是對導致生態紊亂的社會文化整體的反思。
首先,《蘑菇圈》展現了消費社會及其文化思潮對于生態系統整體的無限破壞力。一般認為,二戰之后社會整體便由生產轉向了消費模式,即進入了鮑德里亞所謂的“消費社會”,而消費社會及其文化思潮對于社會文化的影響則延綿至今,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的重要特征便是“商品的邏輯得到了普及,如今不僅支配著勞動進程和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欲、人際關系以及個體的幻象和沖動。一切都由這一邏輯決定著”。[13]盡管中國進入消費社會模式晚于西方社會,但是,作為邊疆的西藏地區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而這正源于消費文化所賦予稀缺資源的不合理規則,即“用某種編碼及某種與此編碼相適應的競爭性合作的無意識紀律來馴化他們”。[14]在《蘑菇圈》中,消費社會初露雛形是松茸商人來到機村收購蘑菇,高昂的價格使得所有人都為之瘋狂,寺廟甚至動用膽巴的力量以封山育林的名義壟斷松茸的收購和銷售,就連阿媽斯炯都因“三十二朵蘑菇就賣了四百多塊錢”而“眉開眼笑”。[15]而消費主義思潮真正開始展現它的威力是在2013年之后。丹雅為了找到阿媽斯炯的蘑菇圈,在她隨身的東西上裝備了GPS。而當斯炯絕望地問道這是為什么時,丹雅毫不掩飾地回答是為了很多錢。由此,開始營造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被徹底打破。“從生態存在論美學的視角看,審美的境域是此在與世界的關系,審美主體作為此在,所面對的是世界之中的對象。”[16]而一旦審美主體與世界的關系發生異化,那么,作為生態物種之一的人類的行為也就絕不可能有利于生物多樣和生態平衡。
顯然,阿來在《蘑菇圈》中對帶給藏區生態以極大破壞的消費主義思潮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雖然作者在作品中并未對其表現出直接的語言譴責,但憑借對于蘑菇圈的逐漸消失、阿媽斯炯的徹底絕望和受消費主義影響的人的貪婪等細節描寫,讀者仍能明顯感受到作家對于哺育自己成長、給予自己創作靈感的原鄉危機的極度憂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蘑菇圈》講述的是關于本土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故事,因此,盡管其發生在青藏高原,但由于相同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心理,讀者仍然能夠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作者想要傳達的獨特情愫。從這一意義上來講,《蘑菇圈》的出現不僅生動地呈現出當代中國——即使是邊遠地區——存在著的嚴重生態問題,并且有助于豐富生態美學的中國話語。只有找到了具有典型意義的研究對象,中國生態美學才能在強調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同時,走向世界美學,成為世界美學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論形態。
其次,《蘑菇圈》揭露了當代社會理性異化之下的人類的精神危機。作為“異化”一詞的提出者,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考察了勞動異化對于人本主義價值的扭曲,并指出:“在私有財產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生產勞動顯示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本質的特性被異化了、扭曲了,成為異化的勞動”。[17]在之后《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又提出:“雇傭勞動必然創造一個由自己轉化出來的統治力量——資本”。[18]與馬克思將異化與勞動和資本連接起來不同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盧卡奇進一步指出“異化”已經成為一種具有本體特征的社會存在,“異化普遍存在于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以人們自愿認可的形式對其實行普遍控制,進而成為人普遍存在的社會生活方式。”[19]除此之外,當代技術哲學家斯蒂格勒也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考察人被異化的過程,并指出當代技術的發展造成了正反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技術系統展現出的巨大活力;另一方面,卻是‘技術主導一切’所導致的人們平靜生活的瓦解。”[20]事實上,勞動、資本、生活方式和技術進步,毫無疑問都是當代社會生活中導致理性異化的典型手段,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將社會整體納入所謂的符號化、扁平化的“異化”體系之中,并最終實現整個社會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的所謂“發展進步”,而生態系統的存在狀態和人的感性精神卻并不作為有效評價指標而被重視。在《蘑菇圈》中,蘑菇作為生態系統中的普通因子,其所經歷的命運變遷恰恰就是當代社會理性異化的縮影。在相對原始的生產環境中,機村人一邊聆聽布谷鳥的鳴叫,一邊用牛奶烹煮羊肚菌。與生態融為一體的機村人盡管并不富有,卻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與滿足。而當外部世界的人、工具、思想闖入機村之后,以蘑菇為象征的生態資源便具有了更加現實的理性意義。它們可以滿足人的口腹之欲,也可以作為仕途晉升的重要砝碼,還為機村人打開了難以抵擋的財富之門。然而,當機村人以摧毀生態系統為代價變得越來越富足之時,他們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有人為了找到蘑菇圈跟蹤阿媽斯炯,有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盜伐森林,即使是孝順的膽巴也滯留于工作崗位而并未兌現過幾天請假來接母親的承諾。
三、結語
由上述分析不難發現,隨著資本、技術和生活方式等的異化作用,越來越“理性”的機村人在放棄生態和諧的同時,也拋棄了自己原本富足和諧的精神家園。對于擁有濃烈原鄉情結的作家阿來來說,這不僅是對于現實生活中藏區生態的真實寫照,更是“直指當代人的生存處境與精神危機,其在審美內驅、現實指向、終結關懷等層面均規定著生態文學創作的起源與發生”。[21]盡管從現實語境上來看,阿來對于精神危機的追問似乎并不合乎時宜,但也恰恰反映了藏人阿來所仍然保有的良知和對于藏區未來發展的遠見。面對正在遭遇生態失衡、文化消逝的藏區社會,阿來這樣的創作姿態也是其作為一位少數民族作家對于自己所應承擔的重要職責的呼應。
作為“山珍三部”的代表作,《蘑菇圈》對于藏區生態的書寫,不僅滿足了讀者的獵奇心理,其作為重要標本,更是警醒所有讀者都不應作為旁觀者而忽略自己對于周圍生態的關注,尤其是要厘清生態系統中各要素之間互相依存、和諧共生的平衡關系。正如曾繁仁所指出的那樣,生態美學作為當代美學的重要拓進,“它以人與自然的生態審美關系為基本出發點,包含人與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是一種包含著生態維度的當代存在論審美觀。”[22]盡管生態美學和環境美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更加關注人類生存體驗的生態美學,顯然更加適應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要求。從這一角度來說,《蘑菇圈》正是藏族文學中較為罕見的生態美學文本。由于帶有極為獨特的民族文化氣質且反映的又是受關注度極高的青藏高原的生態問題,因此,《蘑菇圈》的出現既是反映人們追尋精神家園的美好愿望,也是新時代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人文精神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