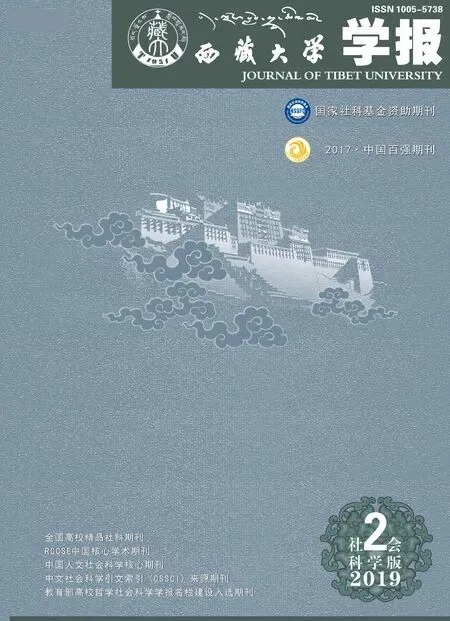西藏史前考古前沿動態及其研究方法
——訪著名考古專家李永憲教授
夏吾卡先
(西藏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 西藏拉薩 850000)
李永憲先生是原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主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中國巖畫學會副會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以及中央民族大學巖畫研究中心、西藏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臺灣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和全國寶鋼獎優秀教師。曾應邀赴徳國、法國、美國、日本、東埔寨、蒙古國、俄羅斯、孟加拉、加拿大等國高校及科研機構學術交流。1980年起,在四川大學從事考古及博物館專業教學與研究,曾在四川、重慶、陜西、河南、山東、西藏、青海等省區及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主持或參與50余項田野考古工作;1990~1992年在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西藏考古、美術考古、史前考古。發表論著100余篇(部),代表著作《西藏原始藝術》獲得首屆藏學研究“珠峰獎”。
筆者:李老師您好!我受《西藏大學學報》編輯部的委托,向您請教有關西藏史前考古前沿動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學術問題,非常感謝您在西藏大學講學期間撥冗接受我的采訪。首先,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在西藏考古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主要學術成就。
李永憲教授:我對西藏考古的學習和實踐,是從1990年參加西藏第二次文物普查(簡稱“二普”)開始的。其后一段時間,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關于西藏細石器的討論。“二普”期間,發現最多、最不好解決的問題就是眾多的石器地點,它雖不像遺址那樣有可分析的地層,但卻是發現石制品最多的地方。當時研究西藏細石器的人很少,除了后來擔任西北大學文博學院院長的段清波老師當時用碩士論文專門研究西藏細石器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未到過西藏的人的研究文章。后來,我寫過幾篇關于西藏細石器的文章,分別在《考古》《西藏研究》和某考古學《文集》上發表過。主要觀點概括起來,我認為西藏細石器主要是新石器與卡若文化、曲貢文化、林芝類型時代相距不遠的區域性遺存,我稱之為“藏西北類型”,西藏的細石器可能是在更早的石葉技術或長石片技術(1990年我們在仲巴有過發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不一定是其他文化傳播的結果。
第二是關于卡若遺址的再研究。卡若遺址1978~1979年發掘以后,出版了單行本考古報告。這份報告和一些研究文章都認為卡若文化晚期發生了生業形態的變化,其中,細石器數量增多、磨制石器減少就是早期的狩獵業進入“畜牧業”的標志,但我不這么認為。卡若文化晚期已有粟作農業,同時也有狩獵、捕撈采集等生產活動,而細石器、磨光石器這時出現的變化,反映的是生業活動的多樣化,同時也可以說是生活資源的多樣化,因為昌都一帶地處全球生物多樣性最好的地區之一(橫斷山區),與西藏很多地方不一樣。后來,我們在2002年、2012年再次作了兩次小規模發掘,在卡若遺址不僅發現了粟(小米)、黍(黃米),還有小麥以及捕魚的證據,動物種類也很豐富,這些特征與我先前主張的“生業活動多樣化”是相吻合的,并不是出現了所謂的畜牧業。
第三是關于西藏巖畫的研究。1985年,張建林等國內學者首次在日土境內調查發現了巖畫,可以說是西藏巖畫科學研究的開端。之后,我們在西藏“二普”(1990~1992年)中發現了大量的巖畫遺存,大部分是琢刻巖畫,也有涂繪巖畫。當時,大家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巖畫的圖像上面,比如說這些圖像表現的是什么?我更關注巖畫的空間分布,希望知道西藏哪些地方有巖畫,這些地點連接起來有什么樣的區域性特征。所以,“二普”結束后我與霍巍老師合作,把當時所知道的巖畫地點作了統計分析和初步研究,以《西藏巖畫藝術》為書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這算得上是第一部西藏巖畫的研究性圖錄。后來,我寫《西藏原始藝術》時,才有機會把對巖畫的一些思考陳述出來。再后來,《中國巖畫全集·西部卷二》(新疆-西藏分卷)由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其中,西藏部分是我撰寫的。關于西藏巖畫,我做的工作不算多,但我希望西藏巖畫的發現和研究能夠繼續往前推進。
第四項工作是負責《中國文物地圖集·西藏自治區分冊》的編寫直至最終出版問世。這是耗時近二十年的大工程,它一是要“追舊賬”,要把“二普”乃至更早的調查結果統計和梳理出來,所以,到處找原始資料、規整資料。二來這又是個“向前看”的工作,因為它是全國統一標準和要求的“西藏分冊”,所以不能老說西藏的困難與不足,而是要拿出辦法來跟上其他省區的專業水平,記得光是我們去北京和其他省區聽別人的審稿會、終審會就不下十幾次。三來這是一部國家級的工具書,要對西藏文物的特點、性質、時代、命名、分類、分級、保護等都有個清晰、標準的交代。最后,還要在地圖上標出來,標圖也是難事,太精確又怕被壞人利用,太模糊又缺乏科學性。所以,這項工作最大的“學術性”,就是將文物分類、分級、定名、定性等規范概念在書中用科學的文字反映出來。后來,以這批資料為基礎,以山南文物局局長強巴次仁為主,我們合作編撰了《西藏自治區文物志》(上、下冊),這一大工程的成果,終于前些年得以出版。以上這些工作,說不上成就,但從我個人來講,在過去的近三十年里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盡了一份力量。
筆者:請您介紹一下《西藏原始藝術》一書的撰寫緣由及其學術亮點?
李永憲教授:《西藏原始藝術》寫于1994~1997年,199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以“西藏藝術研究叢書”第二次出版,現在兩個版本都早已賣光了,因仍有讀者要書,有人建議第三次出版,我還沒答應,因為如果要再版,應該有修訂、有增補,但是我目前還沒有時間和精力來做這件事。為什么寫這樣的一本書?主要有幾點原因:第一,“二普”期間我們發現了大量考古材料、新文物點,拓寬了我們先前的視野,借助這些新材料可以探討一些西藏“史前期”(吐蕃王朝以前)的問題;第二,先前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著作中,有較大影響的是圖齊的中譯本《西藏考古》(譯自《穿越喜馬拉雅》)。書名和書中雖然都不斷出現“考古”這個詞,但圖齊受限于當時的種種條件,并沒有實施真正的“西藏考古”,中國學者應該有能力來彌補這個不足。第三,川大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早年曾在他的《西藏考古綜述》這篇文章中引用了俄國人羅列赫(當時譯為“勞瑞茨”)的一段話,大意是不能忘記“佛教的西藏旁邊還有一個游牧的西藏,還有一個格薩爾的英雄史詩的西藏”。這段話實際上是提醒人們注意,西藏絕不是從佛教傳入才有了所謂的文明史,還有更早的歷史亟待我們去研究。我是學考古學的,所以,希望能用考古學的的角度和材料去觀察西藏的早期歷史。為什么書名叫《西藏原始藝術》,這里的“原始”是相對于人們所熟知的西藏“佛教”時期來說的,是一個時代概念;所謂“藝術”是想依據考古發現實物材料,在探討古代西藏物質文化的同時,也力求涉及到人的精神活動。這本書說不上有什么“學術亮點”,但還是用了很大的心力把當時能收集的有關西藏吐蕃王朝之前的考古材料做了一個自認為是比較全面的梳理和討論。寫書不同于寫論文,是希望表達一種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
筆者:在關于大石遺跡的研究中,您的主要著眼點或關注點是什么?
李永憲教授:我在《西藏原始藝術》里有個章節專門討論過“大石遺跡”。我當時認為,“大石遺跡”是西藏早期歷史中表現人們精神活動(信仰意識)的一個物化遺存,稍微具體一點,它可能與畜牧/游牧文化中的祖先祭祀或神靈祭祀有關。
人類歷史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使得人們的行為及產品,沿著“功利性”和“非功利性”兩個方向發展,所以,“建筑”這類人工產品也有“功利性”(如住房、倉庫、牲圈等與生存活動緊密相關)與“非功利性”(如寺廟、祭壇等與精神活動緊密相關)的區別。我認為“大石遺跡”就是比較早的一種“非功利性”建筑,它不是人們的居所和生存建筑,它的“不可移動性”和結構樣式,一定體現了當時人們精神活動的某些概念,比如宇宙觀念、空間觀念等,還有“神界”與“人間”的關系,等等。“大石遺跡”中的石柱可能有與天神溝通的意義,它的不可移動性和建造位置、環境等,可能具有部落或祖先屬地的意義。記得才讓太老師的文章里提到,早期苯教是有“道場”的,名為“賽康”(音),雖然不能認定兩者之間一定有什么關系,但它提示我們要注意到一點:所謂早期宗教或神靈信仰這些精神層面的文化,很可能也會有某些物質遺存留待我們去發現和研究。所以,我覺得“大石遺跡”(現在一般稱為“石構遺跡”)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是早期精神活動的標志,而且它與那些可以移動的宗教物件、裝飾物件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不可移動性”,它是靠固定的位置地點、地勢環境與精神文化聯系在一起的。
筆者:請您介紹一下西藏史前即石器時代、早期金屬時代考古的研究現狀及其將來可能出現的學術熱點。
李永憲教授:西藏的石器時代起于何時、止于何時?這可能跟內地漢文化區有所不同,所以這項研究只能用西藏(或青藏高原)的材料來說話。西藏“早期金屬時期”是沿用童恩正老師的提法,西藏金屬器何時出現?現在也只是依據考古材料所做的一個大致判斷,也許今后會有修正。
西藏史前石器時代、“早期金屬時期”這兩大段時期的研究現狀及有什么樣的問題很值得關注。我想可能有三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什么時候西藏高原有人類居住?這里的“居住”是指“世代定居”,因為這關系到我們研究的一個起點。比方說,現在大家都知道高原缺氧不適合區外居民生活,可是藏族為什么就不缺氧?這種生理性的抗低氧能力需要多少年才能形成?所以,人類踏上高原以后,生存持續能力就是一個課題。西藏尼阿木底和青海都發現過舊石器時代的居住遺存,但還不足以讓我們了解到古人生存活動的方式或具體內容。不過有些基本的邏輯性問題我們可以思考,舊石器時代晚期現代人類已經擴散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區,那么,什么樣的人群適合到青藏高原居住?抗寒冷、抗低氧的能力是某個人群與生俱來的,還是定居高原之后逐漸形成的?再就是,青藏高原當時與它東西南北四鄰的文化(人群)是一個什么樣的接觸關系?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實物資料絕大部分就是石器,所以,我們必須以研究石器來探索人的生存樣態和文化接觸。
第二,農業何時在高原出現?農業的形成與發展對人群的規模、聚散方式有著重要影響。如定居影響到建筑發展和人口增殖,陶器等器具分類制作與居民分工、分群相關,人工產品及自然資源的多樣化導致分配權和群團內人群主次的劃分,物資交流和群團利益的鞏固如何統一,等等。總之,是農業的出現和發展更快地推動了西藏古代社會的復雜化、文明化。現在來看,雅礱部落為什么是在山南崛起?從經濟基礎看,無疑是農業經濟及其人口規模奠定了吐蕃王朝的社會基礎。
第三,就是牧業、游牧文化對西藏歷史的影響問題。農、牧業的二元結構對西藏高原文明的走向和特色都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我們從表面看,好像牧業、農業只是生產經濟的不同、景觀的不同,而在西藏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牧業文化特別是游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導遠程貿易、跨文化交流、領地擴張的重要動力。記得有人說過:早期“絲綢之路”交通路線的形成,源于游牧民的遠程轉場經驗。講的就是這樣的道理。
之所以提到這三個方面,實際上也是西藏史前史的三個重要節點(時間上)。從空間上看,這三個節點的發生區域似乎又都標志著西藏與不同方向文化的接觸:青藏高原已知的舊石器地點,全部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區,包括新發現的尼阿木底,過去發現的蘇熱、夏達措、青海江西溝等。它們與其他文化的接觸,有人認為是與廣泛的北方有關,有人認為可能也與西部有關系,但似乎與北方接觸的觀點更被人們接受。然而西藏農業出現的地域卻主要集中在高原東部(昌都卡若遺址),這里不僅有地理環境條件,也與黃河流域強大、歷史悠久的農業文化傳統有關。那么,牧業出現的空間節點在哪里呢?現在還不十分清楚,但可以梳理的線索是與高原西部“內亞走廊”傳播的“草原文化”有關聯,我們從金屬器、巖畫圖像、珠飾、早期宗教、墓葬形式等方面都可見到這種影響,甚至包括表類作物的傳播,等等。西藏牧業出現時,麥類作物在西藏基本普及,從此也有了現在的青稞。所以我覺得,從上面說到的“三個節點”可以衍生出很多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如果從這些方面下功夫,有關西藏史前史的研究將會有更好的進展。
筆者:您對人類進入青藏高原的“三部曲”或“三級跳”的假說有何看法?尼阿木底遺址的發現對上述假說是否具有挑戰性?
李永憲教授:我看過的英文資料很少(這類觀點最先是外國研究者用英文發表的),但我不太同意這個“三級跳”的邏輯,盡管它是個比較完整的假說。我認為人類文化出現空間、時間上的“跳躍”(突變),其原因是多樣化的,不外乎是平衡文化的常態因素被打破,這種打破需要時間的積累,必須擁有大量的考古證據才可能觀察到這種現象。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我們說中國現代史始于1848年(以前是“近代史”),但如果僅從物質文化的遺存上很難找到這個節點,你如何區分1848年前后不同的物質文化?是人們吃的食物或是使用工具不一樣了?如果說“三級跳”的理論或觀點是成立的,那么一定要能解釋“跳躍”的機制即原因問題。考古學上發現的只是事實的一小部分,用它來推導大道理、大理論需要非常謹慎,就像我們說尼阿木底遺址很重要,是西藏“唯一有地層依據、年代確切的高原人類的舊石器”,那么,尼阿木底是不是就是早期西藏高原人類的中心?恐怕沒人敢這樣說。
在我看來,尼阿木底遺址的發現是否對“三級跳”理論構成挑戰,這并不重要,我們應重點關注尼阿木底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尼阿木底遺址的發現,首先,提供了一個時間概念即3萬年(或3~4萬年);其次,是“長石片技術”。我們應去分析3、4萬年前亞洲文化與高原的關聯性,如通過石器技術分析來討論它與周邊文化的關系。
筆者:請您介紹一下史前青藏高原農作物和畜牧業研究的新進展及其意義。
李永憲教授:目前的新進展主要還是材料的新發現。2012年,在卡若遺址發現了3000多年前的麥類(以前說卡若農作物只有小米和黍),這是一個新發現。西部札達的格布賽魯墓葬中也發現了麥類(3000年前),這樣在高原的東、西部都發現了3000年前的麥類,所以可認為小麥進入西藏不晚于距今3000年,當然也可能會更早。可惜曲貢遺址當年發掘時沒有發現農作物,但可以肯定曲貢文化的農業是比較發達的。
青藏高原農業考古研究,目前主要還是在尋找農作物的發生時間和來源,其中粟類作物來源、時間是基本清楚的(黃河上游地區),但麥類作物的最早出現時間和來源還不是很清楚。青藏高原不是麥類作物的起源地(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都不是),所以,麥類作物的來源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化接觸問題。如果農作物(粟類、麥類)出現時間和來源問題,以及牧業出現的時間及地域這些問題都搞清楚了,那么,對西藏石器時代與“早期金屬時期”的分界,以及是哪些要素推動了牧業的出現和粟類、麥類的分化與替代(即大麥類青稞取代粟類成為主產作物)等問題的研究,都將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對西藏吐蕃之前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文化的觀察就會更有依據。
現在的問題是不能完全都靠考古發現來解決,需要有多學科、多領域的互動研究意識。牧業研究進展更緩慢一些,例如牲畜馴化物種孰先孰后等問題也并不清楚。以現在的常識來說,人們總認為羊的馴化應該比牦牛早,但是這并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在整個青藏高原巖畫中的動物,牦牛遠多于羊屬,這和中亞草原及新(疆)蒙(內蒙古)地區巖畫不一樣,那些地區的確是羊的圖像很多。現在大家公認麥類作物是從西亞傳播而來的,主要基于出土麥粒的遺址年代早晚鏈接起來的傳播方向,但是如何傳播也并不具體。最近我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流域的塔克西拉參加了中國考古隊的發掘(哈拉帕文化遺址),在那里我們發現了麥類(大麥、小麥)、稻類和粟類作物(粟、黍),其中最多的是大麥(包括青稞)。差不多與此同時,西藏農牧科學院的專家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合作,在《科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們根據遺傳基因逆向分析結果提出,西藏的青稞可能來自巴基斯坦北部地區,這表明高原西部與印度河上游地區可能發生過粟類作物/麥類作物的交互作用,當然這也是文化的交互作用。所以,很多研究通過開放合作是可以取得更有意義的進展。
筆者:高海拔以及寒冷的氣候等自然條件,對高原文明的形成產生了哪些影響?
李永憲教授:高海拔、寒冷氣候是地理環境的概念,綜合起來就是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它可以導致文化上的隔離性,或者叫文化的特殊性。凡是地理環境特殊的地方,其文化自然有它的特殊性,古代很多地方都用車,例如在北方草原地區的巖畫中有很多車的圖像,但青藏巖畫中車的圖像就較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在古代是不宜車行的。據文獻記載,西藏歷史上與蒙古政權之間有個很著名的“涼州會盟”,薩迦班智達要去今天甘肅這么遠的地方也是騎馬去的,因為,高原上騎行要遠遠快于車行。因此,環境總是會使文化特殊性顯現出來。有人問我,既然卡若文化已經有了農業,那為什么還要出去狩獵?我說因為古代高原人需要動物皮毛御寒,青藏高原不產棉花也少有麻,所以冬天就需要獸皮,需要獸皮就得捕獵,人與動物關系就顯得與其他地區不同了,這也是環境導致的文化特色。
環境會影響人的行為和意識。青藏高原在佛教之前具有“薩滿”性質的早期宗教(一般認為就是“苯教”)之所以盛行,也與高原環境有關。高海拔地區夏季短、冬季漫長,經常發生各種自然災變(現在三月間還常有雪災導致大量牲畜死亡),因此,人們自然信仰“萬物有靈”,相信世界是由“神界”和“人間”構成的。但關于高原環境的認知,我們應該盡量向科學研究看齊,比方說很多人一看到西藏古今之間的差異或變化,就會立刻說“是不是古代地勢沒有那么高啊”?所謂人類史的起始最早也不過幾百萬年,而幾百萬年之前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與今天最多也就是幾十米的差距,幾千年前與今天幾乎毫無差異,所以,古今變化也不都是海拔高度變化造成的。有人把古格王國的衰落跟氣候變化掛鉤,其實也是缺乏科學依據的,不足千年的氣候變異屬于小變化,很難影響到一個文化的變更。
筆者:您對史前高原文明幾大板塊的形成及其相互影響,有何看法?
李永憲教授:高原史前文明幾大板塊是個模糊的并不確切的說法。西藏高原或青藏高原的四周地形有別,會影響到人類文化相互間的交流接觸,但我更關注高原的東、西兩端在文化交互影響中的作用。青藏高原東、西兩端都是大江大河的發源地,或稱河源地帶。不同的是東部江河是向東流經中國境內的,西部大河則是向西北流向境外(印度河的河源段)。高原山區河流跟平原河流不一樣,就是在人類歷史時期不會出現河流“改道”(地理學上的概念),對早期人類活動來說,它更易成為交往通達的路線或方向引導。加上高原東部、西部相鄰的文化之間是有差異的,高原東部的甘青地區是馬家窯等文化影響最大的地區,是很有活力的農業文化區,農業文明把彩陶及粟類作物向西帶到了西域、中亞、南亞北部甚至更遠,同時,又從西邊接受了麥類作物和青銅器等文化因素,所以,東部史前時期的卡若等文化接觸到的主要是黃河流域的文化。高原西部,從古到今一直都是非常活躍的不同文化的薈萃之地,從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西藏的“早期金屬時期”),既有來自中亞草原文化的影響,也有來自西亞等地區的文化因素。它們對西藏高原文化的發展都產生過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但很難說它們已經在高原文明中形成了所謂不同的“板塊”。
筆者:您對西藏各種石器有一定的研究,那么,請您簡單概括一下西藏石制品總體器形、分類、組合,以及從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信息。
李永憲教授:石器的器形、分類、功能、組合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人類行為等,跟陶器研究是有所不同的。研究陶器的人很多,而研究石器的人較少,主要在于石器研究有它自己的特性。石器研究基本上是以形態研究和制作技術研究為基礎,現在知道西藏是有“長石片”技術的(藏北尼阿木底遺址,距今3~4萬年),其實1990年仲巴縣城北也發現過硅質巖原料長石片石制品,形制要小一些,但沒有年代數據。西藏早期的長石片技術的來源在哪里?它的發展能不能產生典型的細石器,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它與西藏石器時代人類的來源和流向問題有關。還有“手斧類石器”的問題,呂紅亮已經發表了很好的文章,他把西藏西部的“手斧”跟印巴次大陸北部文化聯系起來,所謂“莫維士線”也正好劃過這一地帶,這會改變我們的研究視野。石器時代沒有歷史時期的政治地理概念,所以,應有更寬的視線。
西藏東部新石器時代流行的條形磨光石器,是與黃河上游甘青地區、川西、滇北一帶的文化有關系的,但在西部阿里幾乎沒有見過這樣的石器,所以,這就是石器的技術傳統差異,而技術傳統就是文化的標志。石器制作也能反映人們的精神活動和群體意識,按照某種既定形態制作出形狀相同的產品,其實就是文化認同的表現。
筆者:請您對西藏史前陶器的總體器形、分類、組合,以及從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信息作個介紹。
李永憲教授:西藏的史前陶器的“總體器形”很難指認,要知道幾十年來考古發現的陶器只是古代真實情況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甚至可能是百萬分之一,這是考古學的局限性。不過從已經發現及獲知的陶器中,我們可以試作一些簡單的歸納:西藏史前陶器的器底形態主要有平底和圜底兩種,拉薩及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吐蕃時期一直是以圜底陶器為主,西部阿里一帶也基本如此,但東部、東南部的史前陶器則以平底器為主。器底形態反映的是陶器的功能,也體現了一種生活方式,即如何置放陶器、如何對陶器進行加熱(用火)。平底器好理解,在北方黃河流域史前文化中都是以平底器為主,圜底器不宜平放,要有三個支點(石頭或陶支架)。圜底器很多又是小口、長頸或帶流(嘴),說明主要用于盛裝液體,這與飲食習慣有關系。新疆的陶器與西藏阿里的陶器相似,也說明兩地有相類似的食物類型和飲食習俗。但西藏東部與西藏中、西部陶器,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歷史時期都有差異,這種器形上的差異與生業模式、生活習俗的不同都有關系。研究陶器的形態,最終是要回歸到器形背后的人的行為、人群的文化特征上來。
筆者:您最近關注比較多的是巖畫研究,請問西藏巖畫研究有哪些新的進展?它對高原文明史的研究可提供什么線索?
李永憲教授:目前,我比較關注巖畫在青藏高原的分布問題,遺存的分布狀態是資料的自然屬性(不可移動性),也是研究的基礎。至今我還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張明確標明青藏高原(所有已知)巖畫分布的地圖,如果連這個都不清楚,那么你的研究資料就有自然屬性的缺陷。為什么說分布圖很重要?比方說印度河上游巖畫和西藏西部巖畫的關系,不能用今天的國界或政區界線來劃分,必須要看與自然環境(如河流、山脈)的關系,要看歷史地理的關系,要標在同一張圖上。又比如近年大量發現巖畫的青海玉樹地區,巖畫沿通天河及兩側支流河谷分布,這可能就與人群的移動方式有關,但我們要看分布地圖才能發現和明白這些特點。
巖畫的“不可移動性”與墓葬遺址一樣,離開了位置環境,你分析的深度就十分有限,所以,巖畫研究絕不是只分析圖像。古代遺存的不可移動性,代表著古代人群生存與行為的地點位置,這就是歷史留下的文化信息,你只有把行為發生的地方搞清楚了,才能分析判斷可能是什么樣的人群有過這樣的活動。巖畫研究始終離不開背后的人群和地域文化的研究,結合人群的不可移動性才能讀懂巖畫的內容,比方說圖像的組合表現了某種古代人群的生活,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他們屬于農人還是牧人?他們有沒有使用金屬器?有沒有宗教活動?先了解了巖畫表現的生活內容,才可以討論圖像風格等問題。風格是一個區域文化的特性,青藏巖畫中的所謂“中亞動物風格”,實際上就是涉及兩個區域文化的問題。但風格并不是我們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西藏巖畫雖然在農區和牧區都有發現,但主要還是以牧業文化為標志,這就是它的不可移動性的重要意義所在。西藏巖畫中,雖然存在著少數駱駝和車的圖像,但它們并不是高原文化的主體標志,而是代表著西藏牧業文化具有的遠距離文化接觸和文化影響,但西藏巖畫中公鹿圖像突出的表現,則是一種本土文化的特征(與早期宗教、“薩滿信仰”有關)。巖畫的分布是個重要問題,從中可以看到區域的特點,西藏巖畫基本上呈東西方向的“帶狀”分布,見于從青海玉樹到藏北、阿里、印度河上游,主要分布在高海拔的牧區,表現為東西方向的流動,這個分布帶與早期游牧文化的流動就有關系。
筆者:針對巖畫斷代存在的一些爭議,可否介紹一下您認為比較科學的巖畫斷代方法?
李永憲教授:巖畫斷代不是存在“爭議”,而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大多數研究者公認的可以廣泛應用的斷代方法。但是,這不表明我們無需去做有關巖畫斷代的工作,針對青藏高原巖畫的斷代,我認最值得做的首推“實驗考古”,我也曾建議過某位研究生去做這樣的工作。所謂巖畫斷代的“實驗考古”就是用逆向的思路去模仿、復原古代巖畫的制作過程,在此過程中積累巖畫制作的原始證據。比如,針對不同的巖畫刻痕,我們用石、鐵、鋼、銅、鹿角、骨等不同質地、不同刃端形狀的工具在巖面上進行敲、琢、刻、磨等不同方法和不同時間長短的制作,看最后哪一種工具、方法、時間能制作出與古代巖畫最接近的圖像?進而反復比較嘗試,從中分辨各種工具質地、形態對不同巖石的作用和區別,由此可得到一系列的實驗數據,成為我們判斷古代巖畫刻痕最直接、最科學的證據。用這樣的方法并不是就能直接得到巖畫的時代,而是通過判斷制作方法,去推斷什么樣的技術、資源、社會發展水平可以為該制作方法提供條件。針對顏料涂繪的巖畫,也可用類似的方法去研究顏料的合成、用量、工具及來源等。
筆者:您對西藏巖畫的分布狀況和時代有何具體看法?巖畫對高原文明意味著什么?
李永憲教授:青藏巖畫的分布我剛才已經講了,現在看來主要是東西向的帶狀分布,這是很突出的一個特點。相對來講,西部發現較多,尤其是高海拔區和傳統牧業區發現得多,我個人認為可能西部巖畫相對較早,東部可能相對較晚。說西部可能偏早,是西部巖畫體現了圖像造型技能的“精英”水平,圖像組合的“格套化”也比較明顯。古代任何區域化的圖像制作,包括后來的佛教繪畫,都有所謂“范式”“粉本”傳承和發展,因此,圖像模式、“規矩”的創立,先都是人群中的“精英”所為,后來者、追隨者便遵循著“精英”模式發展成具有區域、時代特征的“風格”。
巖畫對高原文明意味著什么?首先,我覺得巖畫是畜牧、游牧文化的代表,他的傳播和分布都是牧業文化的表現。因此,由巖畫反映的文化交流、物質產品、技術水平、社會狀況等,都是以畜牧文化為主。其次,青藏高原在史前時期是自然地理一體化的,所以,不宜把青海巖畫和西藏巖畫看作是兩種巖畫。古代沒有青海、西藏這樣的概念,巖畫的文化影響和文化意義是整個高原性的。第三,巖畫是特殊的史料,它與遺址、墓葬一樣具有“不可移動性”。但它又與歷史文獻、文物器件不同,它不靠文字表意,它所記錄、保存、釋放的歷史文化信息都是“圖語”式的,需要專門分析研讀。第四,青藏巖畫的制作,出現在新石器時代之后,從時代上講,它是西藏早期歷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形象化史料。
關于西藏巖畫推斷時代的方法,我認為還是要從材料本身中找證據,就是用巖畫的內容來推斷時代。比方說巖畫的人物圖像中出現了專門的巫師、專門的武士、部落首領等,那么,我們可以分析這樣的社會階段大致應出現在什么時候?又比如,巖畫中的牧人有騎馬的、有駕車的、有大量牲群、有金屬武器用于狩獵、有輔助狩獵的鷹和犬等,那么,我們分析這是什么階段的經濟生產類型?如此等等。還有就是巖畫的共存遺跡分析,與巖畫共時、共地的其他遺存如墓葬、遺址、石構遺跡等,都可以作為推斷巖畫時代的參考。
筆者:西藏史前考古文化中的地方元素和外來元素如何區分?有哪些好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李永憲教授:分辨一個時代的文化中有幾種元素,一是用成份比較的方法,就是比例(比重)分析法;二是文化的源流分析,即一種文化元素的源頭和流向來自哪里?去向何方?如西藏佛教文化中哪些是漢地元素?哪些是南亞元素?這應該都比較容易分辨。但是,什么是本土文化的元素?除了成份分析,還需要有一個長時段的觀察、多地點的比較才能確認。例如,我們分析西藏史前文化時,總在想什么是西藏本土元素的代表?經過比較長期的觀察和比較,現在可以基本認為以曲貢遺址、昌果溝遺址、邦嘎遺址為代表的陶器最具本土特征。另外,青海宗日遺址發掘時,開始認為基本上都是馬家窯文化元素,后來西北大學陳洪海老師從成分比例、陶器形制、人骨特征、遺存地域分出了“宗日類型”,也就是后來說的“宗日文化”。當然,具體做起來并不是這樣簡單,這里說的是方法,也就是思路方向,西藏的曲貢文化和卡若文化都本土特色很明顯,但卡若的后續文化并不清楚,難以見到它的流向,可能今后會發現,所以說需要長時段的觀察。
筆者:史前高原先民以畜牧業(游牧)為主,還是以農耕產業定居為主?
李永憲教授:我個人認為,就整個史前時期來說,很難說以誰為主,因為,這有個時間先后問題,從發生時間上看,青藏高原是先有農業,后有畜牧業。沒有農業的支撐,牧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所謂單獨存在的牧業,是指區域性的,而不是時段性的。牧業發展的基礎當然是牲群(牲種),但牧民的生存目標是擴大牲群規模,增強和提高牲畜的附加值(皮、毛、奶、油等),并非大量宰殺牲畜,天天吃肉就可以生存發展下去。牧業人群所需的糧食、工具、生活用具、交通工具、建筑材料和構件等,都需要與農業人群進行交流貿易來獲得。
考古證據顯示,西藏5000年前始有農業(卡若),但那時并沒有形成畜牧業,所以,那時影響人們的產業經濟是農業。當牧業出現后,牧業文化中有些東西可能反過來影響到農業人群,比方說,西藏早期的金屬器,金屬器的制造者可能并不是牧業人群,但它被長距離活動的牧業人群(游牧民)傳播到了不常移動的農業人群所在的河谷地區。游牧民可以到達很遠的地方,大大超過了農業人群的移動能力,西藏巖畫中的那些來自遙遠中亞草原圖像文化元素,也只能是游牧文化傳播的產物。
筆者:西藏卡若文化、青海宗日文化以及青藏史前文明之間有何聯系?發生聯系的主要途徑又會是什么?
李永憲教授:青海宗日文化和西藏卡若文化的相關性(大于馬家窯與卡若文化的相關性),是近十年來提出的觀點。在我看來,具體主要表現在陶器器型(罐、盆為主)、陶質及制作(手制)、器表紋飾(紋樣)等方面。此外,還有體質人類學的分析(宗日墓葬中的人骨與馬家窯不同,應是高原土著人),認為文化時代相近或相同,文化分布地域和地理環境(海拔高度等)接近……整個青藏高原,石器時代以來就有了土著的高原人群,他們當然遠達不到今天的人口規模。但到了新石器時代,在海拔較低的高原東部地區可能已有一定規模的定居人群了,近年來在青海玉樹地區就發現有七、八千年的遺址。所以,高原東部地區因地理位置原因,最先受到了來自黃河上游的粟作農業文化的影響,但因缺少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他們必須同卡若文化一樣同時兼營捕獵、采集、漁撈等。史前考古研究是需要打破現行的行政地域界限,要有自然地理的概念。就目前青藏高原史前研究而言,研究青海的學者似乎不太關注西藏,研究西藏的學者似乎對青海的關注也不夠,需要打破這種以政區劃為主的研究領域劃分法,應當把青藏高原作為整體來研究。青海的齊家文化在藏東也有影響,也應該值得研究者關注。
筆者:巖畫中的“巫師”像與西藏早期宗教或苯教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李永憲教授:巖畫中的“巫師”,是研究者參考民族志等相關文獻對這類圖像的一個“身份推斷”,可以看作是巖畫中有關早期宗教的表現,但不宜把這類圖像說成是苯教里的巫師。因缺乏文字記載,西藏早期宗教(與巖畫同時期的宗教)究竟叫什么名稱我們無法確認。“苯教”是創制藏文之后出現在相關文獻里的宗教名稱,這些文獻相對巖畫而言是晚期的。我覺得巖畫中的“巫師”,主要具有“薩滿”的特征,而“薩滿教”則是起源很早的流行至今的一種很廣泛的宗教形式,它可能與早期的“苯教”有關系。例如,青藏巖畫中“巫師”的擊鼓姿態、披掛羽毛、身邊的鷹和鹿都是被重點刻畫的對象等現象,可能與后世文獻記載的苯教巫師“騎鹿通天”等描述相對應。蒙古國巖畫中也有所謂的“鹿師”,可以斜身飛入天空。所以,我所說的巖畫與“文獻苯教”的共同特征,主要是指描述的現象上,而不是指名稱上。
筆者:作為年輕一代的學者,在研究歷史特別是史前史時,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或者說,您對年輕一代的學者有什么樣的期望?
李永憲教授:第一,研究歷史一定要關注文獻,但不要依賴文獻、盡信文獻。關注文獻是要研究文獻,而且最好能研究不同語種(文字)的早期文獻,研究西藏早期歷史,僅掌握藏文是不夠的,有必要關注高原周邊地區用不同語言文字記述的青藏高原。
第二,要以研究對象所在地域的材料為主,其他地區的材料為輔。比方說,你要研究三星堆,最好用四川成都平原的材料來說話。你要研究西藏,如果用蒙古地區的材料來解釋青藏高原,那肯定是靠不住的。如果你研究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光靠西藏的材料也是無法解讀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第三,要注重“遺存性史料”的潛在意義。考古發現的遺址、遺物、遺跡都屬于“遺存性史料”,它最大的特點是材料本身是“絕對真實”的,但需要研究者從中“讀出”真實的歷史信息。所以,有意義的問題多是源于材料本身,而不是源于某個已有討論的“概念”。
第四,學術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研究過程中的學習和提高。如果說有一個研究目標,那么,為此目標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有意義的,不要太期待所謂驚世駭俗的結論,做研究,過程的科學性更重要。
筆者:非常感謝李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專訪,祝您貴體安康!萬事順心!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