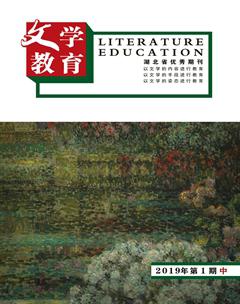北島詩歌《觸電》的一種解讀
李宇涵
內容摘要:北島《觸電》一詩發表于1985年,深受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詩人綜合運用通感、視角轉換、蒙太奇、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手法,表現出了一種悲喜劇意識。目前對北島《觸電》一詩進行闡釋的文章大多都采用“傳記式批評”或“印象式批評”。本文旨在通過借鑒新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批評方法對《觸電》所體現的藝術手法及目前讀者對其作出的闡釋進行分析。
關鍵詞:北島 《觸電》 藝術形式 文學接受
一.前言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于北京,做過建筑工人、編輯和自由撰稿人。其詩歌寫作始于1970年,1978年在北京創辦地下文學雜志《今天》,擔任主編至今。自1987年起在歐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
《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詩歌卷》中評論北島的詩歌藝術是這樣說的:“北島堅持了詩的獨立品格,以現代詩學意識改造被腐化的中國詩學,將西方現代藝術的蒙太奇、變形等手法納入詩學范疇,推進了中國現代詩在沉睡30年后的復活與繁榮,豐富了現代詩的表現手法,為中國現代詩重返世界文學格局提供了積極的努力,北島是20世紀中國現代詩承上啟下,走向未來的有力的一環,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張同道等:《獨自航行的島》,載《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詩歌卷》)。
北島詩的“質地”是堅硬的,是“黑色”的。他的詩有強烈的否定意識和批判精神。洪子誠先生認為,北島之深刻不僅在于對所處環境的懷疑和批判,更是因其涉及人自身的分裂狀況。以北島的《回答》為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冰川紀過去了,/為什么到處都是冰凌?/好望角發現了,/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競?/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北島早期的詩歌流露著一種否定的、宣言式的詩情,堅定的、不妥協的意志。這貫穿在這個時期北島的很多作品里。
北島80年代以后的詩作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而不同于其早期作品。北島說:“詩歌面臨著形式的危機,許多陳舊的表現已經不夠用了,隱喻、象征、通感,改變視角和透視關系、打破時空秩序等手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試圖把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詩中,造成意象的撞擊和迅速轉換,激發人們的想象力來填補大幅度跳躍留下的空白。另外,我還十分注重詩歌的容納量、潛意識和瞬間感受的捕捉。”[1]
北島的這種藝術主張充分體現在他80年代后的創作中。詩人運用多種藝術手法,“使他的詩在朦朧的底色上更呈現了錯綜、奇詭、撲朔迷離的味道。”[2]發表于1985年的作品《觸電》正處于北島詩歌創作的轉型期,綜合運用了通感、視角轉換、蒙太奇、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手法。而目前對北島《觸電》一詩進行闡釋的文章大多都采用“傳記式批評”或“印象式批評”。本文旨在通過借鑒新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批評方法對《觸電》所體現的藝術手法及目前讀者對其作出的闡釋進行分析。
二.《觸電》的藝術形式
觸 電
我曾和一個無形的人/握手,一聲慘叫/我的手被燙傷/留下了烙印/當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聲慘叫/他們的手被燙傷/留下了烙印/我不敢再和別人握手/總把手藏在背后/可當我祈禱/上蒼,雙手合十/一聲慘叫/在我的內心深處/留下了烙印
我們首先用文本細讀的方法闡釋此詩。全詩共三節,呈遞進式結構。三節內部各由屬于過去時間的動作形成瞬間連鎖反應。第一節,由“我”和“無形的人”握手導致“我”慘叫、被燙傷、留下烙印;第二節,由“我”和“有形的人”握手導致“他們”慘叫、被燙傷、留下烙印;第三節,由“我”雙手合十導致慘叫、內心深處留下烙印。縱向來看,第一節“我”與“無形的人”握手到第二節轉為“我”和“有形的人”握手再轉為“我不敢再和別人握手”;第一節我的手被燙傷留下烙印,到第二節他們的手被燙傷留下烙印,再到第三節我的內心深處留下烙印,三次重復和轉換使意義得到延展。
我們或許可以把“握手”解釋成接觸,接觸即意味著建構。人生而被建構,烙印即被建構的標記,來自于無形;“我”又將其施于他人,人為自己建構,為自身尋找存在的意義。每一次建構,無論源于無形,亦或施于有形,無論是無意識的,還是有意識的、自覺的,皆是一次重構,烙上一標記。
北島自身即注重用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法分析文學作品,他說:“英美新批評的細讀方法好處是“通過形式上的閱讀,通過詞與詞的關系,通過句式段落轉折音調變換等,來把握一首詩難以捉摸的含義。說來幾乎每一首現代詩都有語言密碼,只有破譯密碼才可能進入。但由于標準混亂,也存在著大量的偽詩歌,乍看起來差不多,其實完全是亂碼。在細讀的檢驗下,一首偽詩歌根本經不起推敲,處處打架,捉襟見肘。故只有通過細讀,才能去偽存真。但由于新批評派過分拘泥于形式分析,切斷文本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最后趨于僵化而衰落,被結構主義取代。”[3]
(一)整體與通感
《觸電》這首詩具有強烈的構成性,是整體與通感的。通感一般是把分屬于不同“感覺域”的詞或詞組,通過特定的語法手段組合在一起,使核心意象的詞義發生變化——感染上其他“感覺域”所特有的色彩,從而形成通感意象。
詩歌的題目“觸電”就給讀者以強烈的感官刺激。所謂觸電,就是當發生人體觸及帶電體時,或帶電體與人體間閃擊放電時,或電弧波及人體時,電流通過人體與大地或其它導體形成閉合回路。人體觸電時,電流通過人體,它的熱效應會造成電灼傷,它的化學效應會造成電烙印和皮膚金屬化;會對人體產生刺痛和痙攣;會干擾中樞神經的正常工作,造成呼吸停止、心室震顫。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會自然地把觸電的感受帶入其中,而如電流般的詩句也自然會給讀者帶來觸電般的感受。
詩中“有形的人”或“無形的人”訴諸視覺,“握手”訴諸觸覺,“一聲慘叫”訴諸聽覺,“燙傷”訴諸觸覺,給人以痛感的想象。北島將幾組意象并置,給人不同的“感覺域”以觸電般瞬間的刺激,最終刺激感由肉體進入靈魂,通過讀者的想象深入內心,增強詩歌對讀者感官的沖擊力。
(二)三重角度
朱光樹先生曾對此詩的三重角度做出過闡釋,他認為,“我曾和一個無形的人/握手,一聲慘叫/我的手被燙傷/留下了烙印”是從“我”對外界事物的感覺寫的。“當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聲慘叫/他們的手被燙傷/留下了烙印”是從外界事物對“我”的感覺的角度來寫的。“可當我祈禱/上蒼,雙手合十/一聲慘叫/在我的內心深處/留下了烙印”是從“我”對“我”的感覺的角度來寫的。三種不同的角度:“我”、“無形的人”、“有形的人”雖然感覺的方位不同,但實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留下了烙印”。從而表現了自我與環境、自我與別人、或自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4]我同意朱光樹先生對此詩的三重角度做出的闡釋。但是,我還以為,這三重角度最終還是指向了“我”的自在矛盾,“我”、“無形的人”、“有形的人”被燙傷都是由“我”來感知的。感覺的方位不同,實質也并非一樣,烙印由“我的手”轉向“他們的手”,最終轉向“我的內心深處”,即感覺由自身的表層向外擴展,最終進入內心。這三重角度既是并置,也是遞進,先擴張進而內化,層層深入。
(三)蒙太奇:組裝意象
蒙太奇(montage),原是法語建筑術語,意即裝配、構成,后來借用到電影領域,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剪輯,組接鏡頭的意思。蒙太奇是電影所特有的敘述方法,它是“借助于電影藝術而發展到極完善形式的分割和組合方法”。將蒙太奇運用于詩歌創作有利于更好地組合意象,以強化詩的強度和密度,使之產生審美多層次和多空間,造成意象的撞擊和迅速轉換,激發人們的想象力來填補大幅度跳躍留下的空白。
洪子誠先生認為“鏡頭”即詩的意象,從而對北島早期詩歌中的意象群展開分析。他提出了兩組基本的意象群。一個是作為理想世界、人道世界的象征物存在的,如天空、鮮花、紅玫瑰、橘子、土地、野百合等。另一個帶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如網,生銹的鐵柵欄,頹敗的墻,破敗的古寺等,“表示對人的正常的、人性的生活的破壞、阻隔,對人的自由精神的禁錮。”[5]北島早期的詩意象的涵義過于確定。到了《觸電》這里,我們會發現其意象的設置與北島早期詩歌有明顯的不同。《觸電》中的意象,如“握手”,所指不明,與日常生活和傳統意象都有距離和阻隔,只給讀者一模糊的感知,卻難以找到詞語明確地與之對應。
三組鏡頭呈現三個瞬間。三個瞬間不斷出現手和手的接觸、慘叫、烙印的反復。三組鏡頭的并置,就可以產生一種不同于它們單獨存在時的涵義,也就是產生一種獨特的新的質,從而使詩具有獨特的深度和強度。此外,蒙太奇通過將核心意象集中于瞬間鏡頭,使意象產生瞬間性,再加以反復呈現,使意象處于高度密集的狀態。這瞬間的感受往往是詩人對生活的高度忠實,是一種內化的真實。
(四)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的部分方法是把不尋常的性質歸于平常的事物,使明顯無關的事物、概念或詞語互相遇合,以及任意使事物和環境的位置發生錯亂。首先,我們先區分一組概念。約翰遜把玄學派奇喻(conceit)定義為“被強力枷在一起的……性質迥異的思想”。奇喻之有奇喻效果,正是依賴貌似異質的思想之間可以表明的而又符合邏輯的聯系。他辨別出了感覺與感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對應或類似,并隱喻表達這一無形的關聯浪漫主義意象因而斡旋在獲得了靈感的知覺和傳達這一直覺真實的需要之間。它是一種折衷的方法——表達無法表達事物的方法。但對于超現實主義者來說,意象不是不可名狀之物。超現實主義作家不是獲得了靈感,而是獲得了激發靈感的東西。意象不是代表某種思想狀態或強化的感覺。它是通過兼為手段與目的的那種跳板。正如勒韋迪在1918年所說:“意象純系精神的創造物。它不可得自比較,而可得自兩種或多或少相去遙遠的真實的遇合。這兩種被結合的真實的關系愈疏遠,意象就愈強烈——它就將具有更多的情感力量和詩歌真實。”[6]
《觸電》一詩中的意象,即得自這種“相去遙遠的真實的遇合”。“握手”、“雙手合十”這種手與手的接觸與“燙傷”、“烙印”在現實中的關系很遠,但正是由于這兩組意象“真實的關系疏遠”,給讀者以強烈的感官沖擊。但北島的詩與超現實主義作品不同的是,超現實主義追求的是無秩序的自由想象而北島的創作仍是基于理性。
(五)標點的使用
標點符號作為一種語言事實,參與到現代文學的構建之中,卻常常被忽視。北島《觸電》一詩中,只存在三個“逗號”,卻隱去了其它標點。我以為,詩人并非故意地不用標點,而是有意地運用標點。在前兩節中,詩人兩次將“握手”分離出來,置于下一行之始,與“一聲慘叫”并置,以逗號隔開。通過這種有意的安排,“握手”這一行為以及此行為導致的結果“一聲慘叫”得到突出,使觸電時電流通過體內的瞬間之感得以呈現,并因此將“握手”與“觸電”聯系起來。在第三節中,詩人將“上蒼”分離出來,置于下一行之始,與“雙手合十”并置,以逗號隔開。從文本呈現出的對“上蒼”一詞的突出,并將其與“雙手合十”并置,我看到了一種反諷。當與他者的接觸被“我”否定,我以“雙手合十”這樣一種祈禱的姿態訴諸“上蒼”,訴諸一種形而上的價值,卻是更深的痛苦,“在我的內心深處/留下了烙印”。
三.對《觸電》的文學闡釋和接受
(一)闡釋學
傳統闡釋學力求使解釋者超越歷史環境,達到完全不帶主觀成分的理解,而把屬于解釋者自己的歷史環境的東西看成理解的障礙,看成誤解和偏見的根源。赫施的客觀批評理論就主張一切闡釋以作者原意為準。實際上目前對北島《觸電》一詩闡釋的文章大多都是“傳記式批評”或“印象式批評”。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闡釋不只是一種詮釋技巧,他把闡釋學由認識論轉移到本體論的領域,于是對闡釋循環提出新的看法。在他看來,任何存在都是在一定時間空間條件下的存在,即定在,超越自己歷史環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的歷史性決定了理解的歷史性:我們理解任何東西,都不是用空白的頭腦去被動的接受,而是用活動的意識去積極參預,也就是說,闡釋是以我們已經先有、先見、先把握的東西為基礎。這種意識的“先結構”使理解和解釋總帶著解釋者自己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成分,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闡釋的循環。在海德格爾看來,“理解的循環并不是一個任何種類的認識都可以在其中運行的圓,而是定在本身存在的先結構的表現”,它不是一種惡性循環,因為它是認識過程本身的表現。換言之,認識過程永遠是一種循環過程,但它不是首尾相接的圓,不是沒有變化和進步,所以,“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并不是擺脫這循環,而是以正確的方式參預這循環”。[7]
對于《觸電》的闡釋,讀者大多會將其指向“文革”,將文本中的“我”與北島本人聯系起來。誠然,詩人北島是在“文革”中生長的,他的創作自然源于他的社會經驗和生命體驗。文革的創傷對北島影響之深遠,從他的詩中即可見到。
“即使年輕的憤怒和偉大的進軍已成記憶,但依然沒有離詩人的生命遠去,革命的傷口依舊會刺痛詩人的夢境,傷口就是革命在身體上所留下的烙印,而傷口上的鹽依舊會加深這種記憶的疼痛。”[8]讓我們來看一種較為普遍的闡釋:
第一次握手對象“無形的人”似為虛指信念和理想。和理想“握手”后之所以會發出慘叫聲,顯然是十年浩劫信念被摧毀后產生的強烈痛苦情緒,即“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的反映。第二次握手對象“有形的人”則是現實社會及社會中的人。相對“無形的人”來說,“有形的人”似容易接觸、親近,可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年月,現實顯得丑惡而冷酷,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乃至仇恨,無關心人、愛護人的情感可言,所以“握手”后發出的仍然是“慘叫”聲。之所以寫“他們的手被燙傷”而不寫“我的手被燙傷”,一來是為了不和上句重復,使語句有變化,另方面“我”在那個年代里,也不可能超時代不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在群眾斗爭中很可能傷害過別人。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我”只好向神靈禱告。禱告時“雙手合十”,所發出的也仍是慘叫聲。這反映了“我”內心矛盾無法克服的痛苦,以及由痛苦帶來的孤獨情緒。[9]
《觸電》的情景確實可以與現實形成對應,北島在他的散文集《城門開》中回憶道:
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地派系沖突中,這恐怕和我上的學校有關。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開始時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學校。我剛進校就趕到氣氛不對,那是“四清”運動后不久,正提倡階級路線,校內不少干部子弟開始張狂,自以為高人一等。“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公開信就是四中的幾個高干子弟寫的,后來四中一度成為“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一個極端的老紅衛兵組織)的大本營。我們也組織起來。和這些代表特權利益的高干子弟對著干。
但上述闡釋中,仍有幾點疑問,“無形的人”與“有形的人”所指不明,“握手”意象是否就可以與表示親近關聯,“我”祈禱的對象是什么,又為何要以“神靈”填充空白?讀者在闡釋過程中是一定要找出與之對應的詞語。這種闡釋文本是由詞語構建的,讀者自身以及詞語的限制最終會導致闡釋的差異。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受意識的“先結構”所制約
(二)接受美學
波蘭哲學家羅曼·英伽頓認為文學作品的本文只能提供一個多層次的結構框架,其中留有許多未定點,只有讀者一面閱讀一面將它具體化時,作品的主題意義才逐漸地表現出來。英伽頓分析了閱讀活動,認為讀者在逐字逐句閱讀一篇作品時,頭腦里就流動著一連串的“語句思維”,于是“我們在完成一個語句的思維之后,就預備好想出下一句的‘接續——也就是和我們剛才思考過的句子可以連接起來的另一個語句”。換言之,讀者并不是被動地接受作品本文的信息,而是在積極地思考,對語句的接續、意義的展開、情節的推進都不斷作出期待、預測和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讀者不斷地參預了信息的產生過程。而激發讀者的想象,就靠本文中故意留出的空白。
伊塞爾認為文學作品有兩極,一極是藝術的即作者寫出來的本文,另一極是審美的即讀者對本文的具體化或實現,而“從這種兩極化的觀點看來,作品本身顯然既不能等同于本文,也不能等同于具體化,而必定處于這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讀者的作用根據歷史和個人的不同情況可以以不同方式來完成,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本文的結構允許有不同的完成方式”。“暗含的讀者”作品本文的結構中已經隱藏著一切讀者的可能性。[10]
我認為以伊塞爾的介于兩極之間的觀點看待對北島《觸電》一詩的闡釋是合理的。《觸電》文本至今的闡釋之所以大多指向文革也是由于闡釋者與文本產生的間隔不長,文革作為民族的創傷還在隱隱作痛,人們通過回憶來感知傷痛。但文學作品之能超越時代,不僅在于其對特定時代的反映,還在于時代的傷痛逐漸消褪后,文本所剩余或增生的意義。
四.北島與現代主義詩風
北島為中國新詩的現代轉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新詩自誕生以來,先后有象征主義和諸種現代主義的引入和實驗,但大多仍是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抒寫。建國以后,50、60年代“頌歌”風行,文學藝術價值不高,“文革”期間,詩人食指的出現盡管對一代青年產生了深刻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還是在思想、心理層面上的。食指的詩基本沒有脫去浪漫主義的基調。“在《今天》派諸詩人中,應該說,只有北島才是最早步入現代主義詩歌的軌道,并以其無可懷疑的現代詩歌的創作實績開啟了現代主義的詩風的。”北島詩歌中的現代主義因素源自荒誕年代對詩人現代主義意識的激發以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
北島盡管是“朦朧詩派中最早具有現代主義特色的詩人”[11],但是北島的詩并非是對西方現代主義的簡單移植,與西方現代主義的詩歌有明顯的不同。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曾對這二者做過比較:“現代詩從坡的時候起即被理解為‘純詩,照雨果·弗里德里希的說法,它是獨立的、自成一格的,與其它事物無關,它首先是語言而不是對外物的描摹。然而這些定義都不適合北島,因為北島筆下或者以‘我,或者以‘我們為面目出現的抒情主體,都帶有強烈的道德化傾向,都在追求人和社會的真理,在整理自己掩埋在文革中的經歷,并對這段歷史的本質進行著思考。”[12]這表明,北島是立足于中國這塊土地而進行創作的,他從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中引入某些因子,而非亦步亦趨地模仿。
參考文獻
1.北島:《時間的玫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2.北島:《履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3.北島:《城門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4.北島:《談詩》,老木編《青年詩人談詩》,1985年.
5.畢光明,姜嵐:《藝術之光照徹心靈——北島謝冕會談記》,《批判的支點 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注 釋
[1]北島:《談詩》,老木編《青年人談詩》,1985年,第2頁.
[2]趙敏俐,吳思敏:《中國詩歌通史 當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337頁.
[3]北島:《時間的玫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5頁.
[4]宗鄂:《當代青年詩100首導讀》,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
[5]洪子誠:《北島早期的詩》,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第18卷.
[6]比格斯貝:《達達和超現實主義》,周發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89年.
[7]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93頁.
[8]吳曉東:《文學的詩性之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273頁.
[9]古遠清:《海峽兩岸朦朧詩品賞》,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100頁.
[10]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96-197頁.
[11]趙敏俐,吳思敏:《中國詩歌通史 當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
[12]趙敏俐,吳思敏:《中國詩歌通史 當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