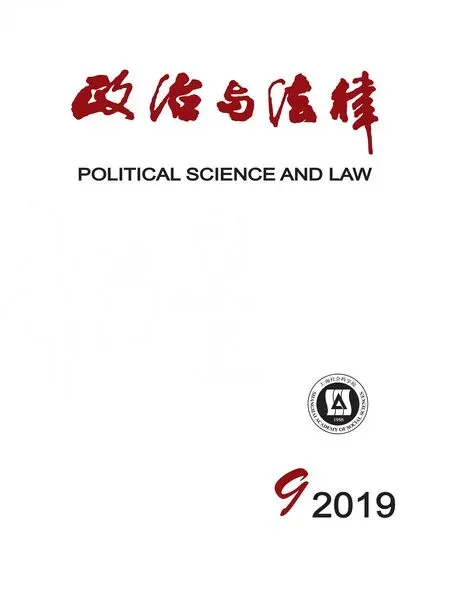論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藉由行政行為(Verwaltungsakt),國家與公民在個案中形成了公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行政行為的效力通常及于個案中參與行政程序的行政機關和相對人。然而在理論和實踐中,行政行為常常超越個案,進而拘束作出機關以外的其他行政機關和法院。那么,決定個案權利義務關系的行政行為何以能超越個案拘束并未參與行政程序的其他國家機關呢?
一、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理論與問題
在我國傳統(tǒng)行政法理論中,常用公定力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解答。在德國法上,由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Tatbestandswirkung)理論對此問題進行解答。(1)也有學者將Tatbestandswirkung譯為“事實要件效力”。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臺北),第446~447頁。我國學界目前對于行政行為公定力的討論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描述,并未發(fā)展出精致細密的理論體系,遑論適用。與此同時,公定力所拘束的主體不僅包括其他國家機關,還涵蓋個人。與公定力相比,構成要件效力的指向更為明確,因此更便于探討行政行為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
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近年來被部分學者引入國內(nèi)學界,并展開了初步研究。(2)國內(nèi)相關研究最早約始于2001年。參見沈軍:《論具體行政行為之構成要件效力》,《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由于相關行政程序法規(guī)定付之闕如,故而我國對行政行為效力的探討主要委諸理論。理論上對于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最為系統(tǒng)的介紹來自趙宏教授。趙宏教授對構成要件效力的由來、概念、依據(jù)與范圍等問題進行了全面闡述,奠定了國內(nèi)相關研究的基本框架。(3)參見趙宏:《法治國下的目的性創(chuàng)設——德國行政行為理論與制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305頁。之后,章劍生教授也將構成要件效力納入行政行為效力理論之中。(4)參見章劍生:《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拘束效力——基于民事、行政訴訟的交叉視角》,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98頁;章劍生:《現(xiàn)代行政法總論》(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6~157頁;章劍生:《現(xiàn)代行政法基本理論(上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頁。然而,既有研究對于構成要件效力某些問題的認識存在爭議,例如在章劍生教授看來,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指其他行政機關、法院等國家機關應當把具有形式確定力的行政行為當作一個既定的構成要件,在作出行政行為或者作出裁判時,應予以承認和尊重;趙宏教授卻認為,行政行為自生效之時起即具備構成要件效力。不僅如此,現(xiàn)有研究對于構成要件效力的依據(jù)、界限以及具體拘束效果等理論上的問題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如何對其加以應用尚不清晰。在構成要件效力理論產(chǎn)生的德國,相關討論更是意見龐雜,部分問題并非十分明確,對此也有詳加甄別整理的必要。因而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這一主題仍然具有繼續(xù)研究的價值。
除此之外,在當下中國的行政法制實踐中,行政與民事、刑事的交叉問題向來引起諸多爭議。理論上并未達成相對一致的見解,也未見有較為權威的學說。以行政行為作為民事訴訟的先決問題為例,長期以來,學界對該問題的解決方案大體可分為兩種進路:一是從行政行為及其效力出發(fā),通過對行政行為相關效力理論(特別是公定力)的研究以求擺脫此類困局;(5)參見劉菲:《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效力研究》,《北方法學》2011年第6期。二是立足于行政訴訟法,通過尋求具體的訴訟規(guī)范以解決此類爭議。(6)參見何海波:《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力》,《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在以上兩種進路中,前者致力于通過行政行為效力的基本理論連結行政救濟法,以求從根本上為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指導。第二種進路是我國學者目前關注的重點。持第二種進路的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應“打破對行政行為效力的迷信”,(7)何海波:《兩點澄清,一點質(zhì)疑——答韓思陽》,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頁。“行政行為效力理論提供了一種討論問題的視角,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8)同前注⑥,何海波文。固然,訴訟法的視角以權利救濟為出發(fā)點,通過訴訟程序的安排解決民行交叉爭議,頗具實踐意義與本土化價值,但這種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卻可能忽略行政行為基本理論所具有的統(tǒng)攝功能,使得緣此路徑下所產(chǎn)生的解決方案會缺乏行政法體系性的關照,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可能有助于問題解決的構成要件效力本身,理論界卻缺少足夠的關注。
綜上所述,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無論是在理論抑或實踐中都具有較為重要的價值。本文通過對于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理論輪廓作出較為清晰的介紹,藉此以完善和豐富我國的行政行為效力理論,同時希冀對相關民行交叉、行刑交叉等法律爭議的解決有所裨益。
二、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形成
構成要件效力最初僅指民事判決所具有的法效果,隨后為行政行為模仿和借鑒,從而成為行政行為的法效果。
(一)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
“構成要件效力”一詞最早由阿道夫·瓦赫(Adolf Wach)提出。瓦赫運用這一語詞主要想解釋下列情形:除具有既判力外,民事判決有時也可作為法律的構成要件,從而成為其他法律效果的前提。(9)Vgl.Adolf Wach, Handbuch des deutschen Civilprozessrechts Bd.I, 1885,S.626;Dagmar Unger, Adolf Wach(1843-1926) und das liberale Zivilprozeβrecht, 2005,S.206.為避免語詞誤解,格奧爾格·庫特納(Georg Kuttner)于1908年已經(jīng)意圖用附隨效力(Nebenswirkung)去取代瓦赫所提出的構成要件效力。庫特納所謂的附隨效力或構成要件效力意指民事判決的存在事實作為特定法律效果的構成要件,此種效力的存在與當事人的請求權無涉。(10)Vgl.Georg Kuttner, Die privatrechtlichen Nebenwirkungen der Zivilurteile,1908,S.4 ff.在庫特納論述的基礎上,弗里德里希·施泰因(Friedrich Stein)在1912年的著作中設專章討論構成要件效力。施泰因主張,包括民事判決、刑事判決以及行政行為在內(nèi)的所有國家行為都可因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而作為構成要件,從而具有構成要件效力。(11)Vgl.Friedrich Stein, Grenzen und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1912,S.94 ff.在現(xiàn)代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法理論中,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仍得以保留。“判決是調(diào)整私法后果(‘私法的副作用’)或訴訟后果(‘訴訟副作用’)的法律規(guī)范的事實構成要素。”(12)[德]奧特馬·堯厄尼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7版),周翠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頁。因而,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指由于法律的規(guī)定,民事判決的存在這一事實成為法律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并與特定的法律后果相連接。由此可以看出,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并不依賴訴訟兩造或法院的意志,而是基于法律的規(guī)定而自動產(chǎn)生,且與判決的存在密切關聯(lián)。正是因為如此,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也被稱為基于法律而產(chǎn)生的反射效力、附隨效力甚或是偶然的附隨現(xiàn)象。如依據(jù)《德國民法典》第775條第1款第4項,債權人取得要求保證人履行義務的可執(zhí)行判決,是保證人向主債務人要求免除保證責任的構成要件。(13)《德國民法典》第775條第1款規(guī)定:“保證人受主債務人委托而提供保證的,或者因提供保證,根據(jù)關于無因管理的規(guī)定,對主債務人享有委托人的權利的,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保證人可以向主債務人要求免除保證責任:1.主債務人的財產(chǎn)狀況明顯惡化的;2.在承擔保證后,因主債務人的住所、營業(yè)場所或者居所發(fā)生變動致對主債務人的權利追訴發(fā)生重大困難的;3.主債務人遲延履行債務的;4.債權人取得要求保證人履行義務的可執(zhí)行判決的。”經(jīng)由實定法與學說,源自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自然可以擴展至行政與刑事判決。在此語境中,行政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指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行政判決本身成為法律的構成要件,從而使得行政判決與特定的法律后果相聯(lián)系,其他國家機關應將行政判決作為裁判或決定的構成要件。(14)Vgl.Clausing, in:Schoch/Schneider/Bi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34.Aufl., 2018,§ 121 Rn. 38;[德]弗里德赫爾穆·胡芬:《行政訴訟法》,莫光華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7頁。如我國《公司法》第46條是有關刑事判決構成要件效力的規(guī)定,因貪污被判處刑罰,執(zhí)行期滿未逾五年的人員不能擔任公司的董事、監(jiān)事與高級管理人員,特定的刑事判決是公司特定職位從業(yè)資格的否定性構成要件。
雖然被稱為“效力”,但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在性質(zhì)上卻是基于法律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附隨的法效果,并且這種法效果試圖將判決的拘束力擴張至第三人。(15)參見[日]中村英郎:《新日本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林劍鋒、郭美松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頁。與既判力和形成力相比,構成要件效力既不是法院審理和判決的標的,也非判決的必然屬性,并且法院的判決主文無意發(fā)生此種效力,其存在與否和法律規(guī)定直接相關,其本質(zhì)是源自法院受法的拘束。(16)Vgl.Gerhard Lüke, Die Bindungswirkung im Zivilprozess, JuS 11(2000), 1046.
(二)構成要件效力在行政實體法領域的引入
以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理論為基礎,構成要件效力得以在行政實體法領域漸次展開。自科曼在1913年將構成要件效力引入行政法并對其進行界定以來,構成要件效力逐漸被行政法學界接受并得以進一步完善。實際上,早在1910年《法律行為性質(zhì)的國家行為體系》一書中,科曼即已塑造了構成要件效力的原型:國家行為具有拘束性(Verbindlichkeit),(17)科曼所稱的國家行為(Staatsakt)不僅包括行政行為,也包括司法行為。所謂拘束性是指國家行為將其所欲發(fā)生的法律效力表現(xiàn)于外部的能力。(18)Vgl.Karl Kormann, System der rechtsgesch?ftlichen Staatsakte: Verwaltungs-und prozeβre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allgemeinen Theil des ?ffentlichen Rechts,1910(Manuldruck 1925), S.199.國家行為所具有的這種概括的拘束性不僅及于受行政行為影響的相對人,也及于作出行政行為的國家。只要國家行為尚未被撤回或撤銷,包括法院在內(nèi)的所有國家機關必須視其為既存事實并且不可無視其存在,但是科曼所述的拘束性卻明確排除了單純的確認行為。(19)Karl Kormann, a.a.O, S. 200.此后在1913年,通過借鑒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科曼將構成要件效力界定為國家行為由于其存在這一事實而具有的效力。(20)Vgl.Karl Kormann,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 J?R 7(1913),14.與瓦赫、庫特納以及施泰因相比,科曼顯然不是在附隨效力的意義上使用構成要件效力,因為科曼主張,構成要件效力是所有具有法律性質(zhì)的國家行為所固有的屬性——國家行為一經(jīng)作出,只要并非無效,無論合法與否,均具備構成要件效力。這種構成要件效力的概念以行政行為的存在事實作為效力產(chǎn)生的前提,其他主體因為無法否認行政行為的存在,所以得受其拘束,從而將已存在的行政行為作為自身決定的基礎。本質(zhì)上,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屬于前述的拘束性。科曼也明確了不同類型行政行為在構成要件效力上的差異:形成性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展現(xiàn)了行政行為所具有的變更權利的效力;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僅在確認判決的存在成為法律構成要件時方可存在。(21)Karl Kormann, a.a.O, S.14 f ;Karl Kormann, Besprechung von Friedrich Stein, Grenzen und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 A?R 30(1913), 256.也就是說,惟有形成性行政行為才具有構成要件效力,確認性行政行為原則上被排除在構成要件效力的范圍之外。
經(jīng)由科曼引入與轉義的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與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產(chǎn)生了明顯的差異。其一,科曼補充和拓展了原本狹義的構成要件效力,構成要件效力不再是依附于法律規(guī)定的附隨效果,而是與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密切相關。只要行政行為有效存在,構成要件效力無須法律規(guī)定即可產(chǎn)生。其二,科曼區(qū)分了構成要件效力在行政行為類型上的差異,只有形成性行政行為才具有構成要件效力,此時構成要件效力實際上更接近對世性的形成效力。科曼從行政行為的存在推導出其他國家機關應受行政行為內(nèi)容的拘束,這種推演一方面表明科曼并不(明確)區(qū)分行政行為的存在與內(nèi)容,另一方面也隱含著行政權的先驗優(yōu)越性與自我確證效果。源自民事判決的構成要件效力被科曼賦予了嶄新的內(nèi)涵,從而奠定了德國有關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基本理論框架,科曼也因此被稱作“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之父”。(22)Franz Kn?pfle, Tatbestands- und Feststellungswirkung als Grundlage der Verbindlichkeit von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en und Verwaltungsakten, BayVBl 8(1982), 226.
(三)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內(nèi)涵
盡管科曼僅承認形成性行政行為具有構成要件效力,但此后無論是弗萊納、瓦爾特·耶利內(nèi)克抑或是福斯特霍夫等學者,都將構成要件效力視作所有行政行為的效力。(23)Vgl.Fritz Fleiner, Institution des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3.Aufl.,1913,S.18 f ; Walter Jellinek, Verwaltungsrecht, 2.Aufl.,1929, S.16 ff.; Ernst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I, Allgmeiner Teil,10.Aufl.,1973,S.105 f.雖然最初實踐中有法院否認這一概念,(24)BVerwGE 10,209 (211ff.); 11, 249 (251ff.).然而現(xiàn)今構成要件效力已為行政法主流見解,并成為德國行政行為效力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
1.構成要件效力的兩種含義
理論上對構成要件效力的討論頗為豐富,但同時也極具爭議。(25)Vgl.Max-Jürgen Seibert,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1989,S. 69 ff ; Gerhard Sehnert, Die Bindungswirkung der Einkommensfeststellung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tr?gers, NZS 9(2000), 439.一般認為,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指其他國家機關應該尊重有效的行政行為,并將其作為自身決定的既定構成要件(Tatbestand)。(26)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9.Aufl., 2017, § 10,Rdn. 20.除無效行政行為外,即使行政行為存有瑕疵,在有權機關撤銷之前,法院和其他行政機關均應受其拘束,(27)Vgl.Eisenmenger,in:Wolff/Bachof/Stober/Kluth,Verwaltungsrecht I,13 Aufl., 2017,§ 20,Rdn. 53.并將行政行為的存在與規(guī)制內(nèi)容(Regelung)作為自身決定的前提,而不得就行政行為是否正確、(28)Vgl.Kopp/Ramsau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17.Aufl., 2016, § 43,Rdn.19.是否合法進行審查。(29)Vgl.Erbguth/Guckelberg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und Staatshaftungsrecht,9.Aufl.,2018,§ 13,Rdn.3; Schemmer, in: Bader/Ronellenfitsch,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mit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 und Verwaltungszustellungsgesetz, 2.Aufl., 2016, § 43,Rdn. 29.簡言之,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是指行政行為以其存在事實及其規(guī)制內(nèi)容對其他國家機關以及其他公法主體的拘束作用。
在界定構成要件效力時,諸多理論事實上并不明確區(qū)分行政行為的存在及其規(guī)制內(nèi)容,所以通常討論的構成要件效力實際上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行政行為的存在事實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狹義的構成要件效力);二是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對于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廣義的構成要件效力)。(30)不過也有少數(shù)學者主張,行政行為的存在與規(guī)制內(nèi)容幾乎難以區(qū)分。Vgl.Ruffert,in:Erichsen/ Ehlers(Hrsg.),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4.Aufl., 2010, § 22,Rdn. 19.前者契合構成要件效力在訴訟法中的最初意義和效果,行政行為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后果產(chǎn)生的要件,此種效力并非依據(jù)管轄權限秩序或行政機關的意圖產(chǎn)生,而系依賴法律明示性或隱含性的規(guī)定。(31)Vgl.Kopp/Ramsauer (Fn.28), § 43,Rdn.24; Max-Jürgen Seibert (Fn.25), S.71 ff; Wolfgang L?wer, Funktion und Begriff des Verwaltungsakts, JuS 1980,805(806); Fritz Ossenbü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Verwaltung, JuS 1979,681(683).行政行為的作出或存在亦是法律事實,即使沒有法律依據(jù),其他國家機關也應將行政行為視作事實加以尊重,進而作為自身決定的基礎。對事實予以尊重的理據(jù)實際是源自于其他國家機關依職權對事實進行探知的義務。然而行政行為的效力本身卻是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所產(chǎn)生的,所以多數(shù)學者所討論的構成要件效力實際上是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行政行為所欲發(fā)生的法律效果)對于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其涉及的是行政行為的宣示(Ausspruch)所具有的先決效力。鑒于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兩重含義,有時為了避免相關語詞的混淆,也有學者使用拘束性(Verbindlichkeit)、(32)Vgl.J?rn Ipsen, Verbindlichkeit, Bestandskraft und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Kl?rung, Die Verwaltung 17(1984), 176 ff.重要性(Beachtlichkeit)、(33)Vgl.Michae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1992), 37; Sachs, in: Stelkens/ Bonk/ 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9.Aufl., 2018, § 43,Rdn.137 ff.決定性/基準性(Maβgeblichkeit)、(34)Vgl.Franz Kn?pfle (Fn. 22), S.228 f.實質(zhì)拘束力(materielle Bindungswirkung)、(35)Vgl.J?rn 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0.Aufl., 2017, § 10, Rdn.714c.實質(zhì)存續(xù)力等來指涉行政行為以其內(nèi)容對其他國家機關所產(chǎn)生的拘束作用。在行政許可領域,有的學者甚至運用“合法化效力”(Legalisierungswirkug)來取代構成要件效力。(36)Vgl.Jürgen Fluck, Die Legalisierungswirkung von Genehmigungen als ein Zentralproblem ?ffentlich-rechtlicher Haftung für Altlasten, VerwArch 79(1988), 408 f;Franz-Josepf Peine, Legalisierungswirkung, JZ 1990, 201(208 f); Jannis Broscheit, Rechtswirkungen von Genehmigungsfiktionen im?ffentlichen Recht, 2016,S.99.
2.行政行為效力體系中的構成要件效力
行政行為的效力一般可區(qū)分為存續(xù)力、構成要件效力和確認效力(Feststellungswirkung)。存續(xù)力包括形式存續(xù)力與實質(zhì)存續(xù)力,其中形式存續(xù)力與不可訴請撤銷性(Unanfechtbarkeit)同義,表明行政行為的救濟期限已過,相對人或第三人不可通過復議、訴訟等正式救濟方式對行政行為訴請撤銷。實質(zhì)存續(xù)力由于其內(nèi)涵爭議較大而被稱為“觀點的迷宮”。(37)Ernst Forsthoff (Fn. 23),S. 253.相對主流的觀點如毛雷爾將實質(zhì)存續(xù)力理解為通過形式存續(xù)力得以強化的拘束力,即受限制的廢除可能性。(38)Vgl.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Fn. 26), § 10,Rdn.17 ff.有些學者運用實質(zhì)既判力代替實質(zhì)存續(xù)力,認為只有功能及作出程序與判決類似的行政行為才具有實質(zhì)既判力。(39)Vgl.Korte,in:Wolff/Bachof/Stober/Kluth,Verwaltungsrecht I,13 Aufl., 2017,§ 50,Rdn.12.除此之外,實質(zhì)存續(xù)力有時也會被用以類比司法判決的既判力,這種效力是指行政行為規(guī)制內(nèi)容的決定性,特別是行政行為在后續(xù)程序中對于行政機關和法院的拘束,即禁止偏離(Abweichungsverbot)。(40)Vgl.Detlef Merten,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JW 1983,1993(1996 f ).如果據(jù)此將實質(zhì)存續(xù)力的主觀范圍不當擴張至其他國家機關,那么實質(zhì)存續(xù)力就是以形式存續(xù)力為基礎的禁止偏離,在這種意義上其與構成要件效力——不以形式存續(xù)力為基礎的禁止偏離——較為接近。(41)德國聯(lián)邦行政法院在2010年的一則判決中甚至將構成要件效力與實質(zhì)存續(xù)力等同:訴訟期限經(jīng)過的行政行為的存續(xù)力不僅包括形式存續(xù)力,也包括實質(zhì)的(構成要件)效力,即行政行為作為其他國家機關決定的基礎。Vgl.BVerwGE 136,119.為避免混淆,筆者于本文采用較為通行的行政行為效力體系,即形式存續(xù)力(不可訴請撤銷性)與實質(zhì)存續(xù)力(受限制的廢除可能性)指向行政程序的參與主體,(42)Vgl. Harald Kracht, Feststellender Verwaltungsakt und konkretisierende Verfügung: Verwaltungsakte zur pr?ventiven Regelung, Konkretisierung und Durchsetzung gesetzlicher Rechte und Pflichten, 2002,S.167 f.構成要件效力與確認效力則對應判決既判力中的決定性,(43)參見前注③,趙宏書,第288~291頁。并且是以后續(xù)決定程序中的其他國家機關為拘束對象——構成要件效力是以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主文)對其他行政機關和法院所產(chǎn)生的拘束力,而確認效力則是作為行政行為規(guī)制內(nèi)容基礎的理由部分(事實認定與法律上的判斷)對其他機關所具有的拘束力。以此可以看出,與存續(xù)力和確認效力相比,構成要件效力在拘束主體、拘束內(nèi)容等方面有其獨特性,因而有獨立存在的必要。
三、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依據(jù)
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依據(jù)由理論依據(jù)與實定法依據(jù)組成,主要解決行政行為對其他國家機關為何會產(chǎn)生拘束力的問題。
(一)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理論依據(jù)
理論上之所以承認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主要是基于國家的權限秩序分配,特別是憲法維度的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以及行政系統(tǒng)內(nèi)的權限分配與行政秩序的一體性。
1.憲法維度的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
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拘束源自憲法層面的權力分立(分配)原則。十八世紀以來,權力分立與制約構成了立憲主義的基本原理。以權力分立與法治主義為基礎,現(xiàn)代意義上的行政法得以產(chǎn)生。權力的“分立”與“制約”是主權性權力劃分的兩個面向,但近世的憲法基于反專制王權的需要,往往強調(diào)權力之間的區(qū)隔與制約,特別是凸顯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活動的控制與監(jiān)督。然而,一方面,權力分立的程序組織原則與法治國以及民主的本質(zhì)要求聯(lián)系密切,“權力分立之法治國面向是強調(diào)分立與監(jiān)督機制在保障自由上之效用”,“而民主面向則強調(diào)特定組織在政治形成上之適當性”;(44)[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體系建構》,林明鏘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另一方面,權力分立還需考慮不同國家組織在任務分配上的差異性,從而實現(xiàn)任務分配的適當化與最佳化。也就是說,權力分立除了能達致民主、實現(xiàn)對于行政的控制外,還要面對國家目的功能的實現(xiàn)。而基于行政和司法的本質(zhì)及其制度設計差異,行政與司法機關從憲法中獲得國家事務的不同分配,這種分配的基準為功能適當原則,即為了確保國家決定的盡可能正確,國家應依功能適當?shù)臉藴蕦沂聞辗峙浣o組織結構、組成、功能及決定程序等均具備最佳條件的機關來行使。(45)BVerfGE 68,1(144).有關功能適當原則的介紹,參見許宗力:《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以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學裁判為中心》,載許宗力:《法與國家權力(二)》,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臺北),第291~339頁;張翔:《我國國家權力配置原則的功能主義解釋》,《中外法學》2018年第2期。
由此,權力分立意味著權力的合理分配與相互制約,同時,立足于憲法秩序的統(tǒng)一性,不應全然忽視權力之間的相互承認與尊重。因為憲法自身應被理解為意義統(tǒng)一的系統(tǒng),為此應竭盡可能減少抵牾、避免權限重疊與漏洞。(46)Vgl. Franz Kn?pfle (Fn.22), S. 225.憲法的統(tǒng)一性同時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統(tǒng)一性,這要求其他行政機關和法院受有效行政行為的拘束,以創(chuàng)設與體現(xiàn)國家活動的一致性。(47)Vgl.Andreas Kollmann, Zur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D?V 5(1990), 192.各憲法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彼此協(xié)作、相互尊重對方所作的行為和決定,這種互相考慮、忠誠合作的立場又被稱作機關忠誠(Organtreue)。作為相互分立的國家機關,除法律另有規(guī)定或法院對行政行為具有司法審查權外,法院與行政機關應對彼此的決定或判斷相互承認與尊重,因此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也具有約束法院的作用。這樣,盡管原則上享有管轄權的法院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可對行政行為的法律與事實兩個層面進行全面審查,但在法規(guī)范設定的形成、裁量、評價余地以及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情形下,也可例外地承認行政行為可以拘束法院。(48)BVerfGE NJW 1982, 2173; BVerfGE 83, 182(198); BVerfG NJW 1987, 577(579); BVerwG NVwZ-RR 2017, 229(230).
2.行政系統(tǒng)內(nèi)的權限分配與行政秩序的一體性
行政行為對其他行政機關的構成要件效力,旨在維持憲法和法律對不同行政機關事務的管轄分工與權限分配秩序。(49)參見李建良:《行政處分對行政機關的構成要件效力》,《月旦法學雜志》(臺北)第79期(2001年12月)。與此同時,將不同的權限事務與機關結構等資源加以結合具有現(xiàn)代行政組織科學化的實踐意義。(50)參見[德]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三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59頁。由于不同的行政機關在專業(yè)能力、組織機構、管轄事務領域等方面存在差異,立法者基于功能適當原則賦予各行政機關不同的權限和管轄事務。權限分配意味著,對于事務的分工不僅要求專業(yè)化,而且也需要在分工履行中實現(xiàn)協(xié)調(diào)。(51)[德]齊佩利烏斯:《德國國家學》,趙宏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頁。各機關間也有彼此合作、相互忠誠的義務,以維護一體性的行政秩序。機關間的權限分配追求排他性,即原則上只有一個機關對于特定的問題進行拘束性地判斷。在行政法領域,以功能適當?shù)臋嗔Ψ至⑴c機關忠誠原則為基礎,國家的行政事務得以具體與有效地分配,由此形成統(tǒng)一的行政組織與事務管轄體系。這種權限與事務管轄分工理應得到其他行政機關的尊重與承認,否則,基于事務管轄差異而劃分的不同行政機關就失去區(qū)分的必要,而由立法者所形塑的行政(管轄)秩序也會隨之紊亂。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正是通過賦予行政行為拘束其他行政機關的法效果,借助多樣化的權限分配實現(xiàn)行政的統(tǒng)一性,從而確保行政機關的事務管理權限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的侵蝕,同時又能保障國家活動一致性地面向公民。因此,行政機關應當受已作出行政行為的拘束,否則將會破壞行政系統(tǒng)內(nèi)部的權限分配秩序。
(二)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實定法依據(jù)
德國通說向來認為,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無需具體的實定法作為依據(jù)。(52)Vgl.Adolf Rebler, Zur Tatbestandswirkung und Festellungswirkung von (rechtswidrigen) Verwaltungsakten, DVBl 20(2017),S.1279; Kopp/Ramsauer (Fn. 28),§ 43,Rdn.23.之所以承認構成要件效力主要是依據(jù)上述不成文的權限分配秩序,這一立場也得到了司法實踐的背書。(53)BVerwGE 60, 111(117).無需具體實體法依據(jù)、逕直賦予行政行為以拘束其他國家機關的“效力”是超越實定法、承認行政權先驗優(yōu)越性的體現(xiàn)。以依法律行政原理為基礎的法治國實際上排除了行政權的“專斷”,(54)BVerfGE 10, 264(267).要求法院對行政活動進行審查。作為必須恪守依法律行政原理的行政機關,僅憑自身作出的行政行為即可拘束其他國家機關,無疑是賦予行政機關可對其他機關“立法”的權能,這本身就意味著對依法律行政的行政法原理的突破,因而,除了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理論基礎之外,還應在實定法中為構成要件效力尋找具體妥當?shù)囊罁?jù)。
在實定法上,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款和德國《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第43條可以作為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依據(jù)。(55)Vgl.Jannis Broscheit (Fn.36),S.90;Daniela Schroeder, Bindungswirkungen von Entscheidungen nach Art. 249 EG im Vergleich zu denen von Verwaltungsakten nach deutschem Recht,2016,S.285 f;Daniela Schroeder, Zur Dogmatik der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D?V 6(2009),S.224;Paul Kirchhof, Der bestandskr?ftige Steuerbescheid im Steuerverfahren und im Steuerstrafverfahren, NJW 1985, 2977(2983);Franz Kn?pfle (Fn.22),S. 225; BVerwG, Beschluss vom 25.06.2007 - 4 BN 17.07;VG Hamburg NJOZ 2010, 2476(2477); BauR 2007, 1712;BVerwGE 117, 351(355) = NVwZ 2003, 742(743).也有少數(shù)學者否認第43條作為規(guī)范依據(jù)。Vgl.Stephan Becker,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im Schnittpunkt von Handlungsformenlehre und materiellem ?ffentlichen Rech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s gestuften Verfahrens im Atom- und Immissionsschutzrecht,1997, S.83 f. 對于這兩個條款作為構成要件效力規(guī)范依據(jù)的相關質(zhì)疑與批評,也可參見詹祐維:《行政處分對行政機關及行政法院的拘束效力——兼論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碩士學位論文(臺北),2015年,第69~72頁。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款規(guī)定,行政權與司法權受法律與法的拘束。行政行為是行政機關依據(jù)法律授權而作出的個案決定,是實體法拘束性的具體化實現(xiàn)。因此,行政行為的法律效果實質(zhì)上并非產(chǎn)生于行政行為自身,而是源自法律的有效規(guī)定,在無審查權的情形下,其他國家機關自是應將行政行為視作法律的具體化即法秩序的組成部分而受其拘束。(56)Christian Bumke,Verwaltungsakten,in: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βmann/Andreas Voβkuhle (Hrsg.),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Bd.II, 2.Aufl., 2012,§ 35,Rn. 215.然而,因為行政行為顯然不具備“法律”的形式,而且也有違法的可能,所以為了補強論證,有些學者對于該款規(guī)定中的“法律與法”進行了擴張解釋:拘束行政權的不僅有行政實體法與行政程序法,而且也包括憲法規(guī)定的權限秩序;正是權限秩序才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義務——將之前的決定作為實體法拘束性的具體化加以尊重并且將其內(nèi)容作為自身活動的基礎。(57)Vgl.Harald Kracht (Fn.42), S.177 f.根據(jù)德國《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2款之規(guī)定,行政行為只要未被有權機關撤銷、撤回以及以其他方式廢棄或因期限經(jīng)過或其他原因而完成,均一直有效,那么其他無權廢除的其他國家機關當然也就無法否認其效力。德國《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的這一規(guī)定以法的安定性原理為依據(jù)確認了行政行為的“有效性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行政行為的有效性與合法性之間的分離。行政行為對法律進行具體化并形塑安定性,從而確保法律關系可以依據(jù)其規(guī)制內(nèi)容穩(wěn)定存在,這種穩(wěn)定性需要以長時間確保行政行為的效果存續(xù)為前提。(58)Vgl.Hans-Uwe Erichsen/Ulrich Knoke,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VwZ 1983,185(188).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所描述的,正是行政行為在后續(xù)其他國家機關決定階段的存續(xù)性及其決定性,以此可以避免生活事實在法律上不斷被重新處理以及由此所產(chǎn)生的不同國家機關決定間的相互矛盾。(59)Vgl.Franz Kn?pfle (Fn.22), S. 225.因此構成要件效力背后所矗立著的無疑是法治國原則中法的安定性:個人依據(jù)自身意愿進行形塑的自由要求法秩序提供可靠性的保障,(60)BVerfGE 60, 253(267ff.).這只有在穩(wěn)定的法律狀態(tài)中方可實現(xiàn)。對于行政行為而言,只要并非無效,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應盡可能地使其存續(xù),在其他機關的決定過程中,也應將其作為給定的基礎。
我國目前的憲制安排并不承認西方意義上的三權分立,而是根據(jù)憲法與相關組織法構筑了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權力分工與制約模式。我國《憲法》第3條第1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依據(jù)該條第2款和第3款,(61)我國《憲法》第3條第2款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jiān)督。”該條第3款規(guī)定:“國家行政機關、監(jiān)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對它負責,受它監(jiān)督。”人民代表大會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亦須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具體而言,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包括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機關,并對其進行監(jiān)督;各國家機關產(chǎn)生之后,依據(jù)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對屬于機關自身職權范圍內(nèi)的事務獨立進行處理,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干涉。(62)參見韓大元、胡錦光:《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頁。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方面當然包括對行政機關(或行政系統(tǒng)內(nèi)的行政機關)獨立權限的保護,另一方面強調(diào)立法與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制約與監(jiān)督。其中,前者是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存在的依據(jù),后者則為構成要件效力劃定了作用的邊界。此外,機關忠誠原則所體現(xiàn)的各機關負有維護憲法秩序統(tǒng)一性的義務作為憲法秩序的基本要義,也可在我國憲法中找到相應的規(guī)定。(63)如我國《憲法》序言規(guī)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此外還包括我國《憲法》第5條與第140條的規(guī)定。
上述憲法維度的權力分立和行政系統(tǒng)內(nèi)的權限分配,意味著對行政行為效力或法效果的否認一般也須由法律規(guī)定的主體作出。行政行為的效力或其所形成的法效果得以在此后的程序中延續(xù),除了由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外,其他國家機關不得否認其效力,此即日本法中所謂撤銷制度的排他性管轄。(64)參見[日]鹽野宏:《行政法總論》,楊建順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3~100頁。林錫堯認為,構成要件效力可以在公定力的內(nèi)涵中得到表達。參見林錫堯:《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臺北),第305~310頁。雖然我國實定法中并無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用語,但是法規(guī)范卻建構了行政行為的法定撤銷制度。所以從解釋論的角度出發(fā),可以從我國《行政復議法》第2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46條以及我國《行政訴訟法》第70條等為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提供部分實定法依據(jù)。
本質(zhì)上,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源自權力以及權限分配的法治國原理,目的在于展現(xiàn)并解決不同國家機關的管轄權與相互行為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從理論的發(fā)展脈絡來看,自科曼至福斯特霍夫的諸多學者對于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探討主要是從司法與行政關系的角度所切入的,(65)Vgl. Antonius Kreft, Die Bindung des Zivilrichters an Verwaltungsakte, Dissertation G?ttingen 1928, S. 54; Walter Jellinek(Fn.23), S.16 ff.; Ernst Forsthoff (Fn.23),S.105 f.直至現(xiàn)在,部分著作也會同時在權力分立與行政行為效力兩個部分中討論構成要件效力。Vgl.Eisenmenger (Fn.27),§ 20 Rdn, 53 ff, § 48,Rdn.40.之后這一概念才逐漸轉移到行政行為的效力理論之中。職是之故,作為“不同機關管轄權與機關行為交錯之編碼”的構成要件效力,旨在維護行政機關藉由行政行為對法規(guī)范進行具體化與形塑的權限與責任。(66)J?rn Ipsen (Fn.32), 169(177).此外,立足于個人權利保護的立場,構成要件效力同時也對個人的正當期待進行保障,即行政行為所確定的權利義務不得被第三方機關無權變動或撤銷。(67)Vgl. Meinhard Schr?der, Verwaltungsrecht als Vorgabe für Zivil-und Strafrecht, VVDStRL 50(1991),S.222.基于此,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對行政機關所具有的“權限保護”所預防之對象既指向行政系統(tǒng)(其他行政機關),(68)參見林佳和:《行政法與私法:私法形成之行政處分、合法化效力與構成要件效力》,《月旦法學教室》(臺北)第151期(2015年5月)。也針對司法系統(tǒng)(法院),其最終目的正是法安定性的確保。
四、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構造
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構造是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得以適用的前提,主要包括構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及其界限等。理論上對于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和行為類型等界限上存有爭議,這些爭議延伸至司法實踐領域,進一步形塑了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制度樣態(tài)。
(一)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
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構造首先涉及的是拘束效果。為此需要明確,行政行為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是禁止對行政行為予以廢除還是禁止自身決定與行政行為相矛盾。
1.拘束:禁止廢除與禁止偏離
行政行為的“拘束”主要在兩種意義使用。一是禁止廢除(Aufhebungsverbot),相關主體對于有效的行政行為,不得排除或僅在特定條件下才容許排除其存在。二是禁止偏離或禁止矛盾(Widerspruchsverbot),這是指相關主體有義務接受已存在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將其作為自身決定的基礎,不得偏離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或與之相矛盾。雖然禁止廢除與禁止偏離相互獨立,但事實上,只有行政行為存在,才會有禁止偏離的問題。只有禁止偏離存在,禁止廢除才有意義,因為允許矛盾決定的出現(xiàn)實際上否定了行政行為的法效果,這無異于間接廢除該行政行為。所以禁止偏離的存在使得排除現(xiàn)在應被偏離的行政行為成為必要。(69)Vgl.Daniela Schroeder (Fn.55), S. 219 ff.正是借助禁止廢除與禁止偏離,行政行為對于現(xiàn)實生活的調(diào)整才得以真正實現(xiàn)。
對于國家活動決定主體的國家機關而言,行政行為的拘束是指國家機關在決定過程中是否以及在何種范圍內(nèi)受到有效行政行為的拘束。在此情形中,禁止廢除并不是立足于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或第三人權利救濟的角度,而是意味著相關決定主體不得恣意廢除行政行為,從而確保行政行為的存在免于被排除。因此禁止廢除是對行政行為可廢除性或可變更性的限制,其對象僅是主管廢除的國家機關,因為僅對其才可保障行政行為免于被排除,其余的決定主體由于缺少廢除權限而必然受到行政行為的拘束。行政行為的廢除存在著兩種可能性——由復議機關或法院予以撤銷,以及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依職權撤銷或撤回等。因此禁止廢除的對象不僅包括復議機關與審理行政訴訟的法院,也涉及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針對前者,形式存續(xù)力是禁止廢除的反射,構成了禁止廢除形成的觸發(fā)要素;對于后者,由于作出機關原則上可依職權撤銷或撤回行政行為,所以禁止廢除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機關遵守撤銷或撤回的條件與程序。與之相對,禁止偏離意味著其他國家機關處理事項已被行政行為所調(diào)整時,須受到已存在行政行為的拘束,不得偏離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進而作出與之相悖的判斷,從而確保法律行為之間沒有矛盾。
2.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以禁止廢除為基礎的禁止偏離
如前所述,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意味著其他國家機關應承認和尊重有效的行政行為。其具體效果在于,對于其他國家機關而言,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已經(jīng)由有權機關作出(先決性)或者在事實與法律狀況未變動的條件下,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又成為程序的標的(決定標的相同),則其他國家機關不得重新對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進行處理或與之相矛盾,并將其作為自己決定的基礎,從而避免矛盾決定的出現(xiàn)。然而禁止偏離的前提是行政行為的存在,所以毋寧如前所述,只有行政行為存在才會有是否偏離的問題。由于構成要件效力所針對的主要是無權廢除機關,所以通常不會存在行政行為被排除的問題,故而爭點主要集中在禁止偏離之上,即其他行政機關和法院必須將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作為自身決定的基礎并且不容許偏離。(70)Vgl.Jannis Broscheit (Fn.36),S.89 f.構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正是以禁止廢除為基礎的禁止偏離。首先,構成要件效力的前提是,對行政行為無廢除權限的其他國家機關和法院無權對其進行撤銷。其次,基于法秩序的一致性,只要行政行為并非無效,由于相關程序標的已經(jīng)被有權機關預先決定,則其他國家機關只得尊重其有效存在,將其作為自身判斷和決定的構成要件。因而其他國家機關既不必重新審查已決定的問題,也不得作出與既存行政行為相矛盾的判斷或決定,這也有程序經(jīng)濟的考慮。(71)Vgl.Sachs (Fn.33), §43,Rdn.41;Matthias Ruffert (Fn.30), § 22,Rdn.17.
(二)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界限
前述行政行為拘束效果須在其構成要件效力的界限內(nèi)展開。構成要件效力的界限具體是指何種類型的行政行為以何種內(nèi)容、在何時、對何種主體產(chǎn)生拘束效果。其他國家機關原則上僅受行政行為規(guī)制內(nèi)容的拘束,只有存在法律規(guī)定的例外情形時,才能承認作為行政行為規(guī)制基礎的事實和法律理由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確認效力)。(72)BVerwG NVwZ 1987, 496 f.以下探討的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界限主要包括時間界限、主體界限以及行為類型界限。
1.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時間界限
時間界限涉及行政行為何時具有構成要件效力。對此,在理論與實務中大體存在兩種立場:一是主張,構成要件效力自行政行為生效時產(chǎn)生,形式存續(xù)力的缺失對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并無實質(zhì)影響,這是多數(shù)學者觀點;(73)Vgl.Hans-Uwe Erichsen/Ulrich Knoke,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VwZ 1983, 185(189);Jan Ziekow,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3.Aufl., 2013, §43,Rdn.4; Kopp/Ramsauer (Fn.28), § 43,Rdn. 23;Adolf Rebler (Fn.52),S.1279.二是認為,形式存續(xù)力是構成要件效力的必要前提。(74)Vgl.Detlef Merten (Fn.40),S.1997;Fritz Wihelms, Zur Tatbestand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NJ 8(2005), 343; Sachs (Fn.33), § 35,Rdn.106.支持此說的中文相關見解,參見林騰鷂:《行政法總論》,三民書局2012年版(臺北),第486頁。司法實踐有時似乎更傾向于認為,在具備形式存續(xù)力后,構成要件效力方可對其他國家機關產(chǎn)生拘束效果。(75)BVerwG NJW 1976, 1987 (1988);BVerwG NJW 1987, 1713(1714); BVerwG NVwZ 1995, 170(171); BGHZ NJW 1991,700(701); BVerwG, Urteil vom 10.12.2013 - 8 C 5.12;Daniela Schroeder (Fn.55),S. 290.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需要以形式存續(xù)力為前提有側重維護后續(xù)行為穩(wěn)定性以及法安定性的考慮:行政行為惟有具備“不可訴請撤銷性”,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或受其影響的第三人也就無法通過撤銷制度來攻擊行政行為,以該行政行為為基礎的后續(xù)行為似乎具有較強的確定性;仍可訴請撤銷的行政行為無法提供法的安定性,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犧牲依法律行政原理。然而問題在于:其一,可訴請撤銷性與行政機關在法律上的判斷權限無關,(76)Christian Bumke,in: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βmann/Andreas Voβkuhle (Hrsg.),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I Informationsordnung·Verwaltungsverfahren·Handlungsformen, 2.Aufl., 2012,§ 35,Rn.214.如果以此作為行政行為構成要件的時間限制性條件。自然無法正當化地對權限秩序予以突破,在救濟期限經(jīng)過之前,行政機關的規(guī)制權限無法得到保護;其二,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會導致矛盾行為的出現(xiàn),這本身就是對法安定性的破壞;其三,以法的安定性優(yōu)先于實質(zhì)正義為由將形式存續(xù)力作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前提預設了行政行為違法的判斷,但如果行政行為合法,則否認構成要件效力明顯無充分理由;(77)Vgl.Veronika Schweikert, Der Rechtswidrigkeitszusammenhang im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recht, 2013,S.88 f.其四,行政行為可訴請撤銷并不意味著可以否認行政行為及其拘束效果,否則行政行為可撤銷與無效之間的區(qū)隔將會消失;其五,如果行政行為具有第三人效果或利害關系人尚未知悉行政行為,那么行政行為的法律效果在后續(xù)程序中將會長時間處于未定狀態(tài),法的安定性也無法得到確保;其六,縱使救濟期限經(jīng)過,行政行為仍然可被撤銷或撤回,即便該行政行為被具有既判力的判決所確認。(78)Vgl.Kopp/Ramsauer (Fn. 28), § 43,Rdn. 21.這些廢除條件以及行政機關的廢除權限實際上與形式存續(xù)力并無關聯(lián),從而也蘊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因僵化地將形式存續(xù)力作為更高安定性的保障手段并不妥當,(79)Vgl.Max-Jürgen Seibert (Fn.25), S.180 ff.其會造成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延宕。故而,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自行政行為生效時即已具備,其不僅與是否經(jīng)過爭訟期間、是否具有形式存續(xù)力無關,也與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并無必然聯(lián)系。(80)BVerwGE 4, 317(331);BVerwGE 59, 310(315);BVerwGE 140, 311 = NVwZ 2012, 707.如果在行政行為存在生效附款時,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則相應延后。(81)Vgl.Kopp/Ramsauer (Fn. 28), § 43,Rdn.23; Schemmer (Fn. 29),§ 43,Rdn. 28.
2.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界限
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界限是指何種主體受行政行為的拘束。該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指向其他國家機關,包括其他行政機關和法院。其他所有國家機關通常都得將既存的行政行為作為構成要件,但特定情形下,行政行為對某些主體并無拘束力。這些主體主要是指對行政行為有審查權的主體。
(1)復議機關
概念上,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中的“其他行政機關”應包括復議機關,但在行政復議程序中,復議機關通過行政自律性控制手段當然可以撤銷或變更違法的行政行為,故而復議機關當然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根據(jù)我國《行政復議法》的規(guī)定,復議機關有權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與適當。復議機關在復議程序中既然具有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權,那么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范圍自然不包括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否則,行政復議作為行政自我監(jiān)督和行政救濟的制度功能將喪失殆盡。在并非以行政行為作為程序標的的其他程序中,復議機關仍得受構成要件效力的拘束。
(2)對行政行為具有審查權的法院
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能否拘束法院,應視具體情形而定,如若系爭行政行為屬于法院的審查標的,則法院對行政行為具有審查權,并得就該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此時法院并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如果系爭行政行為并非法院的審查標的,或不屬于法院的審判權范圍的,法院應承認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82)參見李建良:《行政處分的構成要件效力與行政爭訟》,《月旦法學雜志》(臺北)第86期(2002年7月)。并將其作為自身判斷的既定構成要件,即在無權撤銷行政機關的命令時,只要高權行為并未被廢除,那么法院——與所有其他第三人一樣——應當接受和尊重行政機關已存在的高權行為。(83)Eisenmenger (Fn. 27),§ 20,Rdn. 52.
(3)對行政事務真正享有管轄權的機關
對于侵犯其他機關管轄權而作出的行政行為,對行政事務真正享有管轄權的機關不受其拘束,即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對這些主體并無拘束作用。這是基于行政系統(tǒng)內(nèi)權限分配得出的必然結論。行政法意義上的管轄權是指行政任務在行政機關之間的分配。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活動時,應遵守作為“行政機關活動的基礎和范圍”的管轄權的界限,而越權管轄的出現(xiàn),突破了國家的權力分配和管轄權限的排他性。在管轄權被侵犯時(職權僭越),真正享有管轄權的行政機關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無須待其撤銷即可自為判斷和決定,這正是構成要件效力所具有之“權限保護”功用的體現(xiàn)。
(4)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
行政機關是否受其自身于先前程序中所作行政行為的拘束,涉及構成要件效力的主體范圍能否包括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有學者另以行政行為的跨程序拘束力(verfahrensübergreifende Verbindlichkeit)或自我拘束效力(Selbstbindungswirkung)對該拘束作用予以說明。(84)Vgl.Sachs (Fn.33), § 43,Rdn. 135.之所以要承認行政行為對作出機關在后續(xù)程序所作行政行為的拘束效力,主要是為了避免矛盾決定的出現(xiàn)、尊重相對人的既得權益、同時為避免行政機關規(guī)避行政行為廢除的相關規(guī)定,(85)參見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臺北),第516~517頁。因而其更類似一種指向作出機關的自我拘束效果,而構成要件效力則主要是對其他國家機關產(chǎn)生的拘束作用。所以無論是在拘束主體抑或制度目的方面,兩者均存有較大差異,故而有相互區(qū)分的必要。因此,筆者于本文不用構成要件效力來指行政行為對同一機關在后續(xù)程序所作行政行為的拘束效力。
3.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行為類型界限
構成要件效力的行為類型界限是指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否是所有類型行政行為所共同具有的效力或者只是形成性行政行為所特有的法效果。(86)筆者于本文所采取的是廣義形成性(狹義形成性行政行為與命令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的二分法,也有形成性、命令性和確認性行政行為的三分法。就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上述分類的差異并不具有實際意義。討論行為類型界限的意義主要在于探求法院所受行政行為的拘束是否會有類型上的差異。早期由于以科曼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將構成要件效力與形成效力混同,因而學說多主張只有形成性行政行為才具有構成要件效力。(87)Vgl.Max Layer, überprüf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durch die ordentlichen Gerichte,VVDStRL 5(1928),S.153 ff.依肯定者之主張,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是除無效行政行為外,所有行政行為的共同特征。因為“行政機關的確認決定和形成決定,都是行政機關的任務,既然法律進行了授權,就不應認為二者之間有任何區(qū)別”。(88)同前注③,趙宏書,第299頁。然而只有否定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才契合行政與司法的權限劃分。理論上一向認為,之所以區(qū)分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主要是立足于行政與司法、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核心差異——終局性的確認在法原則上屬于司法權的專斷范圍,從而確認性行政行為不具有構成要件效力。(89)Vgl.Stephan Becker (Fn.55), S.59 f, S.66; Norbert Achterber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Aufl.,1986, § 23, Rdn.42. 有學者進一步將確認性行政行為區(qū)分為創(chuàng)設性確認行政行為(konstitutiv-feststellende Verwaltungsakte)與宣示性確認行政行為(deklaratorisch-feststellende Verwaltungsakte),并排除了后者的構成要件效力。Vgl.Michael Randak (Fn.33),S.37 f.部分學者持相似的觀點,認為法院只受狹義形成性行政行為(不包括命令性行政行為)和創(chuàng)設性確認行政行為的拘束,排除了宣示性確認行政行為。Vgl.Eisenmenger, (Fn.27),§ 20,Rdn. 54 ff.如耶施主張,行政的功能是面向未來,具有積極、形成的作用,形成性行政行為是行政的典型形態(tài);對法律關系的確認卻并非行政的固有領域。司法與行政的任務分工表明,對真實法律狀態(tài)進行權威性、終局性的確認權原則上應當屬于法院。如果行政程序和法院一樣足以保障行政的決定正確時,也可例外地承認行政機關的最終決定權。因此,民事法院不受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拘束,其有權也有義務去審查法律狀態(tài)并且決定由行政機關所判斷的先決問題。(90)Vgl.Dietrich Jesch, Die Binding des Zivilrichters an Verwaltungsakte,1956,S.108 ff.
不可否認,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均是行政機關將抽象的法律在個案中予以拘束性具體化的產(chǎn)物。雖然嚴格區(qū)分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并無可能,因為所有確認性行政行為多少都變更了法律狀態(tài),都包含形成性要素,同樣,形成性行政行為都包含一定的確認性要素,(91)Vgl.Max-Jürgen Seibert (Fn.25), S.94.但這不能掩蓋兩者之間的核心差異:沒有行政行為,法律狀態(tài)是否存在就失去了基礎。(92)Vgl.Max-Jürgen Seibert (Fn.25),S.100 f.具體而言,形成性行政行為所包含的意思表示之目的在于創(chuàng)設行政法中尚未存在的法律狀態(tài)或效果。在這種意義上,形成性行政行為產(chǎn)生了法律狀態(tài)的變化并且改變了公民與行政機關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沒有行政行為就不可能存在此種法律狀態(tài)。確認性行政行為旨在藉由國家權威對于某項權利或者法律關系進行確認,即使沒有行政行為,法律狀態(tài)依然存在,即既存的法律狀態(tài)并不依賴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說,確認性行政行為僅包含程序法上的意思表示、只涉及程序法上的法效果——對法律進行拘束性的具體化,作出確認性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對于既存的法律狀態(tài)只是進行確認。然而正如科爾曼(Kollmann)所言,在個案中拘束性地確認何為法原則上僅屬法院的司法權事項,由于法院對于法律關系的判斷具有終局性的確認權,所以確認性行政行為自然也就無法拘束法院。(93)Vgl.Andreas Kollmann (Fn.47),S.194 f.此時確認性行政行為只是由行政機關對法規(guī)范進行首次具體化,在訴訟中通常僅具有權利證明的效力。由于撤銷權的配置問題,對于行政行為的廢除只能由有權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禁止廢除)。在法律有明確規(guī)定時,也可例外承認確認性行政行為對于法院的拘束作用。與之相對的是,形成性行政行為既是程序法也是實體法上的意思表示。在程序法意思表示之外,形成性行政行為還依照法律授權形成了原本不存在的實體法律效果,正是這種額外的實體法規(guī)制要素才導致了兩者的根本區(qū)別。(94)Vgl.Harald Kracht (Fn.42),S.64 f,S.105 ff.形成性行政行為是行政法律關系變動以及實體法律效果產(chǎn)生的效力依據(jù)。法秩序將這種法律效果的形成權僅賦予行政機關(發(fā)生爭議時,為審理行政訴訟的法院),法院也就只能受其拘束。因此在禁止廢除外,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也不得被偏離(禁止偏離)。立足于行政權與司法權劃分的權限秩序才能夠解釋為何只有形成性行政行為才具有構成要件效力,為何唯獨法院而非其他行政機關才可否定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拘束力。
在具體的制度實踐中,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往往會受到諸多限制。其一,在權利濫用的場合,如以欺詐的方式獲得許可,往往要否認構成要件效力的存在。(95)Vgl.Kopp/Ramsauer (Fn.28), § 43,Rdn.18.其二,在法規(guī)范賦予行政機關以終局決定權的情形下,可直接肯定和認可行政行為對于其他國家機關的拘束,但此種終局決定權由于排除了法院的審查通常應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其三,在國家賠償訴訟中,法院僅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但并不觸及規(guī)制內(nèi)容的有效性,(96)Christian Bumke,in: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βmann/Andreas Voβkuhle (Hrsg.),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I Informationsordnung·Verwaltungsverfahren·Handlungsformen, 2.Aufl., 2012,§ 35,Rn. 222.此時無關禁止偏離。即使行政審判未就該行政行為作出判決,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也可自行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也就是說,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無法排除公民的國家賠償請求權。(97)BGHZ NJW 1953, 862(863); Leiner-Egensperger, in:Mann/Sennekamp/Uechtritz(Hrsg.),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Groβkommentar, 2014, § 43,Rdn. 39.
五、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運用: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
構成要件效力的價值主要在其具體運用,特別是體現(xiàn)為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拘束。除無效外,無論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法院得受行政行為的拘束。構成要件效力所維護的是法的安定性,而司法則旨在進行權利救濟、維護實質(zhì)正義,這兩種價值之間本身就存在張力。行政行為對未參與行政法律關系的法院是否產(chǎn)生拘束,主要應由立法者來確定何種價值具有優(yōu)先性。由于任務目的的差異,不同部門法所接收的行為指令不必相同。在此意義上,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拘束一定是類型化的,需要針對民事、刑事訴訟等不同訴訟類型、結合具體情形對沖突價值進行權衡,以判斷構成要件效力是否存在及其具體射程。(98)有關刑事訴訟中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問題,參見王世杰:《論行政行為對刑事審判的拘束》,《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6期。也可認為,構成要件效力只有在具體的情形中才能獲得切實的形態(tài)。以下僅以行政行為對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民事審判)的拘束為例展現(xiàn)構成要件效力的具體運用。
(一)行政行為作為民事審判的先決問題
在行政法與民法的聯(lián)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民法以行政行為為前提的情形愈發(fā)普遍和頻繁。行政行為作為民法的前提是指行政行為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件,在發(fā)生爭議時,行政行為就成為民事審判或民事訴訟的先決問題(Vorfrage)。先決問題是作為案件主要問題或本案爭議前提的法律問題。在訴訟實踐中,先決問題是審理本案爭議,繼續(xù)推行本案訴訟的事先步驟。一般而言,先決問題屬于其他法院或其他訴訟途徑的管轄范圍,但基于全面審查的原則,法院對于先決問題通常可以附帶裁判。
如果行政行為成為民事審判的先決問題,那么行政行為對審理民事訴訟法院是否具有構成要件效力,行政行為能否拘束法院呢?這里所謂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拘束,并非禁止而是限縮法院的審查權:法院只要確認行政行為有效即可,因為無效行政行為在法律上并不存在。(99)Vgl.Fritz Nicklisch,Die Bindung der Gerichte an gestaltende Gerichtsentscheidungen und Verwaltungsakte,1965,S.38 f; BVerwG, Urteil vom 27.11.2014-4 C 31.13.除此之外,法院既不得進行合法性審查,也無權撤銷行政行為,(100)Vgl.Schenke/Ruthig,in:Kopp/Schenke,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23.Aufl., 2017,§ 40,Rdn.43.更不得偏離行政行為而自為判斷。在德國,不僅理論上對于構成要件效力的構造內(nèi)容爭議較大,而且行政行為拘束民事法院的實踐問題也并未形成標準的見解。雖然構成要件效力原則上得到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的承認,但也有少數(shù)判決認為,行政行為只受經(jīng)過行政法院審查的行政行為的拘束,這無疑意味著否認民事法院受行政行為的拘束。(101)BVerwG NJW 1986, 1628(1629).
(二)我國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拘束的理論與實踐
關于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我國的情形較為復雜。為此需要判斷理論和實踐在何種程度上承認行政行為對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具有拘束效果。一方面,面對民行交叉爭議,立法者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態(tài)度。正是基于現(xiàn)實情境的復雜性,從訴訟便利、解決爭議與防止矛盾判決的情況出發(fā),才出現(xiàn)了行政附帶民事的訴訟制度。從最初的行政裁決案件,到涉及行政許可、登記、征收、征用的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均可申請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102)參見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8]1號)第137條至第141條。這種總體解決思路撇開了理論上的諸多爭議,頗有“快刀斬亂麻”的效果。在法規(guī)范尚未變動的情形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雖然能解決部分民行交叉爭議,但是也僅限于在行政訴訟中采用。承認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適用無異于間接否定民事訴訟制度,因而所有的交叉爭議通過行政訴訟制度進行一并審理既無現(xiàn)實的可能,也無規(guī)范的依據(jù),所以不具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guī)定,如果民事訴訟須以行政訴訟為依據(jù),而行政訴訟尚未審結的,應當中止訴訟。據(jù)此,對作為民事訴訟先決問題的行政行為,如果以行政行為為系爭對象的行政訴訟正在進行、尚未審結,則民事訴訟應該中止。此時,訴訟中止實際上是將行政行為的法效果懸于行政訴訟程序,進而成為構成要件效力的法定阻斷機制。如果有關作為先決問題的行政行為并未被提起訴訟,由于法院必須對案件進行處理,因而法院如何對待作為先決問題的行政行為自然成為無可回避的問題。現(xiàn)階段,我國理論與實踐所呈現(xiàn)的相對穩(wěn)定的基本立場是原則上承認行政行為的拘束作用,但否認確認性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
1.原則上承認行政行為的拘束作用
在民事訴訟中,我國的理論和司法實踐經(jīng)常借助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承認行政行為的拘束作用。也就是說,即使行政行為存在瑕疵,也得承認行政行為對法院具有拘束效果,法院不得在民事訴訟中對行政行為的效力進行爭議。盡管早期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比較搖擺,(103)如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9條、1994年《關于企業(yè)開辦的其他企業(yè)被撤銷或者歇業(yè)后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的批復》以及2001年《關于審理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移交、撤銷企業(yè)和與黨政機關脫鉤企業(yè)相關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3條均否認行政行為對法院具有拘束作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聊城市柳園供銷公司法人資格認定問題的復函》則承認法院受生效行政行為的拘束。但現(xiàn)今不少法院的做法則相對明確。在“魏昌蘇訴魏昌南排除妨礙糾紛抗訴案”中,法院認為,對于有效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必須在民事訴訟中予以尊重和認可,即在民事訴訟中法院不得徑自否定其效力或者不采信,如要否認具體行政行為的預決力,也必須經(jīng)行政訴訟程序予以撤銷或者變更”。(104)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浙民再抗字第21號民事判決書。在“曾言安訴中國太平洋財產(chǎn)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中,法院主張:“認定駕駛證是否有效,應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出認定。本案原告的駕駛證是行政機關核發(fā)的,并且在有效期內(nèi),應當有效。……原告1997年申領駕駛執(zhí)照時有年齡上的瑕疵,但期間原告的駕駛證經(jīng)過年審合格,其他條件也符合駕駛條件,應認定其仍有駕駛資質(zhì)。”(105)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qū)人民法院(2007)龍泉民初字第175號民事判決書。換言之,作為先決問題的行政行為即使存在瑕疵,只要其有效且并未被撤銷,仍得拘束其后的民事行為,法院不得偏離該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
2.否定確認性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
針對某些特定類型的行政行為,我國法院不承認行政行為的拘束作用。對此,理論上較有影響力的學說認為,應當區(qū)分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是采取形式審查還是實質(zhì)審查:對形式審查的行政行為,法院可直接否認行政行為的效力,逕直重新對民事行為進行審查;對實質(zhì)審查的行政行為,法院應直接承認行政行為的效力,不得對其審查。(106)參見方世榮、羊琴:《論行政行為作為民事訴訟先決問題之解決》,《中國法學》2005年第4期。對形式審查與實質(zhì)審查區(qū)分標準的批評,參見成協(xié)中:《行政民事交叉爭議的處理》,《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這種劃分以“國家意志對民事基礎關系和基礎事實的滲透和介入”程度為標準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具有拘束法院的效力。根據(jù)這一標準,行政行為可分為決定私法效果、促成私法效果以及確認私法效果的行政行為,(107)參見羊琴:《企業(yè)設立登記行為的性質(zhì)及其在民事訴訟中的效力》,《人民司法(應用)》2011年第9期。其中決定私法效果和促成私法效果是指以變更法律地位或法律關系的私法形成的行政行為,后者為僅對私法效果予以確認的行政行為。由此,所謂形式審查與實質(zhì)審查的本質(zhì)區(qū)分標準在于:行政機關是對私法效果或民事關系進行確認(確認性行政行為)還是形成私法效果或民事關系(形成性行政行為)。因此上述理論實際上也就否認了確認性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這一做法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承認。
在2004年的“香港綠谷投資公司訴加拿大綠谷(國際)投資公司等股權糾紛案”(以下簡稱;香港綠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將行政行為區(qū)分為兩種:一是形式性行政行為,即行政行為作為形式性要件,即使無行政行為,民事行為本身并非無效;二是實質(zhì)性行政行為,即行政行為作為實質(zhì)性要件,無行政行為,則民事行為無效。對前者,由于行政行為僅是確認私法效果,即使無行政行為,民事行為本身并非無效。既然如此,法院當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判決結果直接或間接地”對其進行變更。對后者,行政行為對于私法效果進行實體形成,所以沒有行政行為,民事行為本身歸于無效。在此情形中,即使行政行為存有瑕疵,法院也不得加以變更,只得通過法定的行政復議或訴訟程序予以否定。(10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四終字第14號民事裁定書。香港綠谷案區(qū)分了設定、變更民事法律關系的行政行為(形成私法效果的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民事法律關系的行政行為(確認私法效果的確認性行政行為)在民事訴訟中對法院拘束的差異:在民事訴訟中,法院不受確認私法效果的行政行為的拘束,可對其基礎的民事關系進行審查,并通過判決作出與行政行為規(guī)制內(nèi)容不同的決定;形成私法效果的行政行為則可以拘束法院,此類行為即使存有瑕疵,法院的決定也不得與之相矛盾,對于該類行政行為的撤銷與變更應通過行政訴訟或復議程序。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肯定這種做法,對于屬于確認行政行為的抵押權登記而言,法院應當就作為登記行為基礎的民事法律關系進行實質(zhì)審查,抵押權登記“不是當事人取得物權的根據(jù),其并非對物權進行確權的唯一和最終依據(jù),不能脫離物權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行為及其效力,必須與實質(zhì)的權利狀態(tài)相符合。一旦有證據(jù)證明物權的登記與實際的權利狀態(tài)不符合,真正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涂銷錯誤的登記”,“登記僅具有權利推定效力,至于該登記是否在實質(zhì)上亦屬真實有效,則應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作出司法判斷”。(109)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70號民事判決書。相似的立場,參見最高人民法院( 2017)行申8483號行政裁定書。否認確認性行政行為的拘束作用在下述情形中也得到證實:確認性行政行為有時也被法院視作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guī)定的民事訴訟的證據(jù)(書證)。在“陳淑德訴譚家軍等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侵權案”中,法院認為“(確認使用權屬的)行政確認行為一經(jīng)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公信力和公示力,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得撤銷。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對上述權證作為證據(jù)僅作形式與來源上的審核,認可其公定力、公信力,認定其作為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證明效力較高。”(110)湖北省興山縣人民法院(2007)興民初字第190號民事判決書。審理該案的法院將作為先決問題的行政行為當作民事訴訟的證據(jù),法院對這種特殊證據(jù)僅作形式與來源上的審核。與其他證據(jù)相比,確認性行政行為僅具有較高的證明效力,如若存在相反證據(jù),法院當然應否認行政行為在民事訴訟中對法院具有拘束作用。因此即便行政行為存在,但只要有相反證據(jù)足以反駁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也可突破行政行為的拘束,(111)參見王遠明、唐英:《公司登記效力探討》,《中國法學》2003年第2期;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終114號民事判決書。并作出與行政行為相悖的決定。換言之,法院雖然不可撤銷該行政行為,然而卻可以偏離既有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這實際上意味著法院不受行政行為內(nèi)容的拘束。然而在形成私法效果的行政行為中,即使行政行為存在瑕疵,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既不得撤銷行政行為,也不能與行政行為相矛盾。(11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64號民事裁定書。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無論物權變動采取的是債權形式主義還是物權形式主義,都不影響行政登記僅是對某種民事效果(當事人就物權變動所達成合意)的確認。在商事活動中,股權轉讓登記并非設權性登記,而是對股權變更這一民事法律關系進行確認的宣示性登記。(11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終字第32號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行申1286號行政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浙民申2685號民事裁定書;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皖民終116號民事判決書。“即使是具有實質(zhì)影響的商事主體資格登記也是確認建立商主體的私法行為(如合伙協(xié)議、公司合作協(xié)議等)的效力。”(114)石一峰:《論商事登記第三人效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同樣在親屬法領域,婚姻登記是對成立法律婚姻關系合意的確認與公示。因此,只要行政行為是對已存在私法效果的確認,最終對于該私法效果的終局判斷權都屬于法院而非行政機關,法院雖然并無撤銷權,但法院可以不受行政登記的拘束而獨立自為判斷,當然也就容許法院偏離行政行為。
綜上所述,對于民事訴訟中出現(xiàn)的行政行為,我國法院實際上區(qū)分了形成性行政行為與確認性行政行為。對于確認性行政行為,法院不僅可以附帶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也可對基礎的民事關系進行審查,進而當事人可以依據(jù)判決對行政行為規(guī)制內(nèi)容進行變更或否定,此時法院可不受行政行為的拘束,但不得撤銷該行政行為(禁止廢除、容許偏離)。對于形成性行政行為,由于行政機關實質(zhì)上設定或變更了民事關系,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既不能審查基礎的民事關系,也不可對行政行為進行直接變更或否定,只得受其拘束(禁止廢除、禁止偏離)。以上我國的理論與實踐可以表述為:在民事訴訟中,除確認性行政行為外,原則上承認行政行為對法院的構成要件效力。在具體的訴訟實踐中,毋寧應根據(jù)行政行為的性質(zhì)選擇救濟途徑:針對形成性行政行為,當事人可直接提起行政訴訟;針對確認性行政行為,由于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不能撤銷確認性行政行為,但卻可以偏離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所以當事人首先應提起民事訴訟就行政行為的基礎關系進行爭議,進而依據(jù)民事判決變更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
六、結 論
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本質(zhì)上是指行政行為的規(guī)制內(nèi)容在何種程度上被其他國家機關承認與接受,所以這一概念觸及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關系和任務分配。此外,由于行政行為的權利侵害可能性,故而它也與公民權利保護以及不同法律救濟途徑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有關。如果說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區(qū)分是訴訟途徑特殊化以及提升各訴訟制度處理能力的必然要求,那么承認構成要件效力、主張審理民事訴訟的法院受行政行為的拘束則意味著逾越具體的訴訟系統(tǒng)界限。(115)Vgl.Hans D.Jarass, Verwaltungsrecht als Vorgabe für Zivil- und Strafrecht, VVDStRL 50(1991), S. 257 ff.這在限縮法院審查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個案正義,從而對公民的權利保護造成威脅。正因如此,公民應及時通過行政救濟對于違法的行政行為進行防御,否則須容忍行政行為成為其他國家機關決定的基礎。面對存有違法之虞的行政行為,審理民事或刑事訴訟的法院可以通過釋明和教育敦促公民對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也可以借助訴訟中止以緩和不同國家機關決定之間的沖突風險。
承認構成要件效力本身就是對法秩序一致性、法安定性以及實質(zhì)正義等不同價值予以權衡的產(chǎn)物,這種不同價值或法益之間的沖突性在構成要件效力的構造爭議中已然顯現(xiàn)。因此僵化地為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劃定普適的標準缺乏可操作性,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的制度模式需要依據(jù)實體法的規(guī)定,結合具體的訴訟情形進行類型化的分析。長久以來,學界對民行交叉、行刑交叉爭議解決方案的尋求主要落在訴訟實益的考量之上,從而人為地割裂作為體系的行政法。本文的論述試圖說明,借助行政行為的效力解決行政與民事、刑事的交叉爭議不僅可能而且必要。作為最近十年才引起理論界關注的“舶來品”,行政行為構成要件效力能否在我國的行政法理論中得以自洽、能否從當下的行政法實踐中得以總結和抽象進而具有更加廣泛的解釋力,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