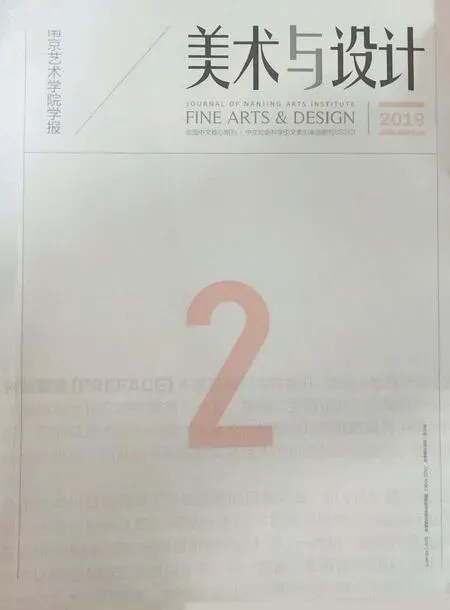《宣和書譜》成書問題考辨
劉 義(南京藝術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宣和書譜》(以下簡稱《書譜》)是北宋徽宗時期由官方主持編撰,現存最早對宮廷所藏歷代書法作品進行著錄的著作。全書20卷,不著撰人名氏,其中歷代帝王書一卷,正書四卷,行書六卷,草書八卷,八分書一卷。各書體前有敘論,述及其淵源、發展及其選錄標準等。書法家則依次為小傳、評論,后列御府所藏作品目錄。各卷有分目,人各一傳,共立傳197名書家,立目1344件作品,不錄文。該書雖然在傳世作品鑒定上不夠審慎,但在當時確實是體例精善,評論精當,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資料,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對于此書撰者及成書時間歷來眾說紛紜,史無定論。各家觀點多為零星見解,且往往論而不證,或證而不全,失之于疏。本文擬通過對各家觀點進行梳理和考辨,進一步厘清編撰者和成書時間等問題。
一、編撰者考辨
(一)宋徽宗御撰說。《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卷九曰:“《書譜》一函二冊,宋徽宗御撰。”清初著名史學家萬斯同《群書疑辨》卷八曰:“自歐陽公分楷隸為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書譜》,竟劃然分為二體。”卷九“題《書譜》”又曰:“此譜岀宋徽宗親撰,乃御府收藏眞跡。”俞紹宋亦說:“謂此書為宋徽宗御撰,不為無因。書中稱‘我神考’者凡三見。”[1]并將之與唐太宗為《晉書》作陸機、王羲之兩文相比,認為陳景元傳、王荊公傳、蔡京傳或為宋徽宗親撰,且謂前已有例可循,稱為御撰,并無不可。此說甚為不妥。一者,即使三篇小傳為宋徽宗御撰,但據此斷定全書版權歸屬,恐有未當。所謂前朝先例,也僅是個案,不能作為學術研究的慣例和規律。二者,陳景元傳雖稱“神考”,但徽宗不可能親自為陳景元作傳。雖然他曾一度寵信道教,但政和末年,他漸漸對道教失去了信任。宣和元年(1119),道教神霄派領袖級人物林靈素被放歸溫州,此后道士逐漸失寵。宣和二年(1120),他更是下詔罷道學,將儒道合二為一,不在專設道學。三者,《書譜》稱,京“奠九鼎、建明堂,制禮作樂,與賢舉能,其所以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其力焉。……于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無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為太平宰相”。[2]如此阿諛稱頌,豈是人君對臣子所能言者?理所未當,固不宜然。當代學者矯紅本在博客中撰文亦贊成“御制說”。他從宋徽宗具備編撰能力、“瘦金書”之尚在《書譜》中的諸多反映以及編撰者語氣和編撰體例中體現的心態等方面作了論證。[3]但其論多為可能性推測,并不能作為必然性的論斷。
(二)宋蔡絛撰說。清代目錄學家、藏書家周中孚認為,《書譜》稱蔡京“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懷之,又稱其書為本朝第一”“若在他人敘述,恐未敢如此肆無忌憚”。[4]并引《鐵圍山叢談》蔡絛語“以宣和癸卯得見內府書目,因備述其所藏之多”為據,認為作者當為蔡絛。[5]周中孚前言甚有道理,是書編撰受朝局和大臣影響不言自明,但據此認定為蔡絛所撰,恐為不妥。蔡絛在此書中又言:“知是譜所載,蓋亦精為簡汰,故止千二百幅。”[5]“知”表推理或接受性判斷,“蓋”表推測。如是蔡絛所撰,豈有不知之理?或曰此為掩飾之辭,故作是語。《鐵圍山叢談》乃蔡絛被貶途中所作,于其父之人之事多所辯護,議者評其人品卑劣。但絳為人子,為尊者諱,直書父罪與情不合。若論后世留名,將《書譜》歸在自己名下,豈不便當?蔡絛未冒此貪天之功為己有,亦自知不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也。
(三)明吳文貴編撰說。《衍極并注》卷三劉有定注《書譜》云:“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裒集宋宣和間書法文字,始晉終宋,名曰:《書譜》,二十卷。”[6]清末藏書家陸心源據此認為《書譜》為吳文貴所撰集,并云“《書譜》出于文貴,則鄭枃所目擊也”。[7]對于此種觀點,俞紹宋從文體繼承、行文內容、以及北宋書家選取標準等方面一一予以駁斥,認為吳文貴生當元時,不可能仍按宣和時人之政治立場、當時臣子或皇帝口吻編撰此書,所論甚當。[1]447但其“言文貴作是書出于劉有定注”,[1]447所言與事實不符。“裒”,聚集、輯集者也。《舊唐書》有云:“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于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余篇,天寶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8]《新唐書》云:“代宗語縉曰:‘朕嘗于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9]上兩例相較,足證劉有定注云“裒集”者,非所謂撰集之意也。陸心源誤解字意,故有此說。元王芝《宣和書畫普后序》曰:“及圣朝混一區宇,其書盛行。好事之家轉相謄寫,中間品目甚多,薦更遷徙,往往散佚于人間。……明年竣事南歸,適吳君和之將刻二譜于梓。余嘉其有志乎古也,因為書于篇末。先時紕謬絕多,君能廣求他集,與同志參校,遂為最善本。”[1]447-448清著名藏書家丁丙、民國俞紹宋也認為,吳文貴曾對《書譜》進行校刊和編輯,[10]與王芝說法相同。此據亦從反面證明,撰者并非吳文貴。
(四)蔡京、蔡卞、米芾、蔡攸編撰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書譜》云:“書終于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於?芾、京、卞書法皆工,芾尤善于鑒別,均為用其所長。故宣和之政無一可觀,而鑒賞則為獨絕也。”[2]此之觀點歷來備受質疑,現綜合各家所說并加以補證。米芾,北宋書法家、畫家,精鑒別,曾任校書郎,崇寧二年(1103)任書學博士,崇寧五年(1106)任書畫學博士。潘運告認為:“宋徽宗征召米芾為書學博士,值御前書畫所,可能就是要他幫助編撰此兩書(指《宣和書畫譜》)。”[11]但米芾卒于北宋大觀元年(1107),離《書譜》成書時間還有13年之久(成書時間詳見下文),說《書譜》由其所定,幾無可能。《書譜》米芾條言載:“然異議者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2]117與其字頗有異詞,米老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米芾作為書畫院博士,此前參與內府所藏書畫的鑒別則可確定無疑。蔡卞(1048-1117),政和七年去世時年近70,且其晚年仍居高位,考察其官職變化,幾無可能參與編撰工作。今人陳傳席認為應是蔡京所撰,主要根據是書中不載“元祐黨人”,且對與蔡京關系密切的王安石、童貫等人,恭維有加,甚為推重。[12]其實,王安石傳的內容較為客觀,童貫傳的內容確有阿諛奉承之嫌。但以童權傾一時的氣焰,吹捧他們的大有人在。蔡京(1047-1126)曾四度為相,尊稱太師,說他主持或主編是書,極有可能,但據此認定他為編撰者恐不能令人信服。俞紹宋謂:“亦無編集古人名跡,而將己書列入,自為抑揚之理”。[1]450俞先生胸懷坦蕩,博雅通理,但蔡京何許人也?以君子之心推小人之腹,恐有失真。謝魏及其他一些學者認為撰者為蔡攸,[13]對此,陳谷香在《<宣和畫譜>之作者考辨》中給予了否定性論證,[14]茲不再述。
(五)臣工集體奉命編集說。明王紱《書畫傳習錄》:“宣和間《畫譜》,不著撰人姓名,前人或以為宋徽宗所撰,非也。……其他大都冠冕形似之詞,層見疊出。即品題標別之處,必系眾手之所雜作,或經后人之所竄易,吾無取焉。”[15]此說甚是。一則內府所藏書帖數量巨大,列目規整、辨偽存真、去劣品優及編纂成書決非一人可當。二者從《書譜》敘述口吻來看,有為臣者、有為君者,撰者自是不一。趙構《翰墨志》有載:“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僣偽,其間法書名跡皆歸秘府。先帝時又加采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贗,紙書縑素,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褾裭、白玉珊瑚為軸,秘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后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儲于外秘。”[16]趙構乃徽宗之子,是當時北宋末年宮廷、官場和重要文藝等活動的目擊者和見證人,作為南宋的第一個皇帝,他的這段論述有相當的可信度。楊慎在刊刻《宣和書譜》序言中也說,書畫二譜乃“君臣?盱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所作。[17]對比考察《宣和書畫譜》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北宋所有書畫名家均只在《書譜》或《宣和畫譜》中單獨出現。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宣和書畫譜》的編撰絕對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統籌規劃,精密組織,由團隊集體編撰而成的,主編很有可能就是蔡京和梁師成,至于具體的編撰人員,今天可能無法一一考證了。但當時為宮廷服務的書畫鑒賞家們,包括一些宦官,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這一藝術盛事。
二、成書時間及其他
關于《書譜》成書時間,歷來研究較少。元以前文獻無載,后世雖有提及,或語焉不詳,或避而不談。今人馬龍根據《書譜》“蔡京傳”及所選蔡京、王黼等人書法作品的寫作時間推斷,認為該書應成于宣和六年(1124)正月至十二月之間。[18]對于此種論斷,吾甚疑之。
《書譜》王黼名下著錄有其進呈的“唐代三誥”,《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記載:“宣和六年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世南書《狄仁杰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18]文中雖有“宣和六年正月”,但下文轉曰“先是”,具體指向的時間年份已無法推斷,所以不能據此認為,徽宗設置書藝所和王黼進呈唐代三誥時間比較接近。再者馬龍論證《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和《顏允南母商氏贈告》實為“一告”,“商”“張”之別為聲近而誤,實與成書時間關系不大。艮岳,原名萬歲山,建成于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宣和六年(1124)九月更名為壽岳。如根據蔡京書法作品創作之時間,以及《書譜》言京“前后三入為相”“頃解機務”諸語等認定,《書譜》成書時間當在宣和六年,乍看似乎顛撲不破,但細細推想,卻令人疑竇叢生。
《書譜》載,蔡京書法作品多達77件,而同時期與其關系密切的書法家,米芾為2件,蔡卞2件,蔡襄3件。米芾書法獨絕一時,自不待言;蔡襄書法也多次被蘇軾推為“本朝第一”。他們時代相同,年代相近,為何被選錄的書法作品數量差距如此之大?此疑一也。從《書譜》所錄蔡京作品來看,事關皇家之作多達六成,其心昭昭,意在宣揚。其中至少有7件作品與艮岳有關,分別是:《萬歲山記》《游艮岳祝壽詩》《游艮岳詩》《艮岳噰噰亭題記》《題絳霄樓詩》《蕭閑館題名》《擷芳園記》。綜觀《書譜》全文,其他諸人作品幾無此種選法。或曰書法家晚年方達到藝術的巔峰,多錄一些后期的作品也無不可。但就一個主題選擇數件作品者歷來未有,何況蔡京艮岳作品多達7件。此疑二也。張其鳳認為,《宣和畫譜·序》明言其作于庚子年即宣和二年(1120),是書當成于此年無疑。[19]歷代學者對此亦多無異議。元王芝在《宣和畫譜序》、吳文貴在《宣和畫譜跋》、明朱存里在《宣和畫譜跋》中都將書畫兩譜并列并說,后世學者也多認為,書畫本為一集,后各單行。書畫兩譜,當是同時而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亦持此說,其成書時間前后差別應該不大。[20]
筆者認為,《書譜》于宣和二年(1120)首次成書后,寶藏于宮內并未外傳;蔡京在宣和六年(1124)四度為相前后,可能以補完校正為名,對該書進行篡改和增補。這一借口史有其載:“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詔……乃命建局,以‘補完校正文籍’名,設官綜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庶成一代之典。”[21]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言:“吾以宣和歲癸卯(1123),嘗得見其目”,“其目”當指《書譜》,“至于圖錄規模”中“圖錄”則應指《宣和畫譜》。[22]《天祿琳瑯》載:“(《書譜》)在宋時僅為內府秘籍,并未流行,見之者少。當時有書畫兩譜。”[23]阮璞說:“竊謂《宣和書畫譜》二書自其成書殺青之年,至其刻書行世之日,中間藏之內府,初與外界全然隔絕,寂然無聞者垂二百年。……茲事與宋代帝王著作秘藏內府之制度極有關系。考宋代累葉帝王之著作,必建閣以秘藏之,不使其流傳于世,久已形成定制。”[24]此說亦與趙構《翰墨志》所言相符。《書譜》作為內府秘籍,首次成書后,當時外界未曾流傳。可以推想的是,徽宗應曾御覽過宣和二年(1120)的書畫譜,但宣和六年(1124)篡改后的《書譜》他卻不曾審閱。一是蔡京不想讓他看到,也不能讓他看到;二是時事艱難,戰事紛擾,他也沒有心情和精力來管這些藝術文章的“瑣事”了。竊以為蔡京篡改的內容主要應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我美化,語稱:“休功盛烈,布在天下”,非臣子所能稱者(前文已有議及)。論蔡襄書法為本朝第一,卻又說自己“可與方駕”,而“飄逸過之”;又言:“喜寫紈扇,得者不減王羲之之六角葵扇”,阿諛過譽,言過其實。二是大幅塞充自己作品。其如上文言艮岳作品是其一也。三是貶低同時期與自己關系密切的書法大家,如上文論米黼之言,論蔡卞又言其“圓熟未至,圭角稍露”,借以襯托自己書法水平之高大瑰偉、不可超越。四是偽托徽宗親撰,論蔡京、王安石、陳景元則語稱“神考”,其他少許稱“仁祖”者,亦皆此地無銀、欲蓋彌彰,個中信息恰恰透露出改編者的倉促和拙劣。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編撰者是以臣子身份替皇帝捉刀,所以出現了角色的變化。至于其他《書譜》中宣和二年以后增補的內容此中不再一一論列。正是由于有了這些“篡改”和“補編”,宣和二年成書的《書譜》和原有的序言是不可能重見天日了。但《宣和畫譜》序言的存在,卻恰恰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明。
《善本書室藏書志》載:“嘉靖庚子楊慎有《宣和書畫譜》總序云:‘《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一帙,傳播無絕。’”[25]另宋人《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宋志》俱不載此書,可知《書譜》當時未曾流行。宣和四年(1122),北宋攻遼失敗;宣和六年(1124),金對遼的戰爭節節勝利,西夏對金稱臣;宣和七年(1125),金滅遼后分兩路攻宋。《書譜》在蔡京篡改后塵封于秘府,后為金人所掠,固南宋人多不知。近人葉啟勛述其于庚午冬月巧購宋版《書譜》一事,記其書云:“前后無序跋,全書歐體絕精,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黑線口,版心左上方間記數字,黑魚尾下書書譜卷第幾,書中對玄、匡、胤、貞、讓、桓、恒、構字皆缺筆,而慎、敦字不缺,蓋宋建炎、紹興間刻本也。……間尚留有墨釘,似是刻成后尚未加以洗刷者,的是宋刊宋印無疑。”[26]韓剛對此刊版之事有較為詳盡的考證。[27]果如其言,亦證《書譜》當為秘府珍藏,刊而未行也。此書今不可見,錄而存之,聊備一說,以待后之有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