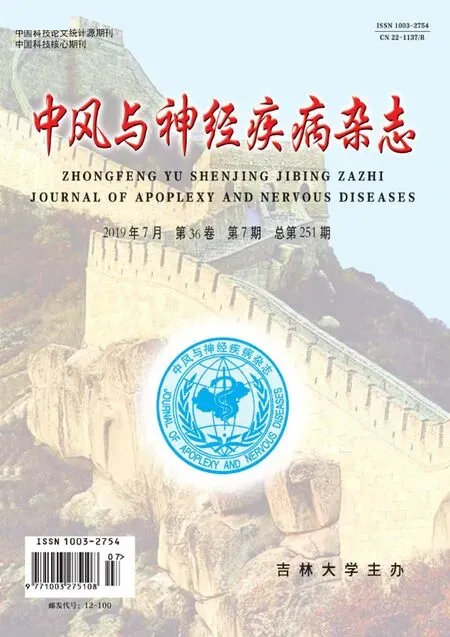發作性睡病研究進展
張蕊蕊, 張紅菊,2
發作性睡病(Narcolepsy)以白天不可抗拒的嗜睡、猝倒、睡眠幻覺、睡眠癱瘓、夜間睡眠紊亂為主要臨床特點,是一種慢性神經系統疾病。與“睡不著”-失眠相比,“睡不醒”-發作性睡病有更大的危害,可嚴重影響患者的工作學習生活,甚至造成意外事故危及生命。發作性睡病是一種終身性睡眠障礙疾病,主要發生于15~30歲的青少年,不同國家人群發病率不同,國人發病率為0.04%[1],由于其發病率低,加上臨床醫生對其認識不足,易造成漏診和誤診。本文就近年來發作性睡病的研究進展予以綜述,以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1 病因及發病機制
近年來,人們對發作性睡病的神經病理學、神經回路、神經免疫學等方面有了較多的了解;然而,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大多數的研究都在圍繞著1型發作性睡病(Type 1 narcolepsy,NT1),對2型發作性睡病(Type 2 narcolepsy,NT2)的病理機制知之甚少。NT1是由于下丘腦分泌素(hypocretin,Hcrt)神經元選擇性缺失、Hcrt含量減少所致。NT2下丘腦分泌素水平通常為正常,可能是由于Hcrt神經元的適度丟失或一個完全不同的過程[2]。Hcrt神經元調節許多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促進清醒和抑制快速眼球運動(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3]。若Hcrt丟失,發作性睡病典型的嗜睡和猝倒癥狀隨之而來。
發作性睡病與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具有高度相關性,尤其是HLA-DQB1*06:02,在人類各族發作性睡病患者中均有較高的陽性率,達88%~100%[4]。已知HLA與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關,如多發性硬化癥、類風濕關節炎、重癥肌無力、毒性彌漫性甲狀腺腫、系統性紅斑狼瘡。這導致了許多猜測,發作性睡病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遺傳學、流行病學和實驗數據均支持NT1是一種T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損傷 Hcrt神經元[5]。最近在發作性睡病患者的血液樣本中檢測到以Hcrt為靶點的CD4+T細胞,并證明識別Hcrt的CD4+T細胞對2009/2010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血凝素蛋白具有免疫交叉反應[5]。Latorre等研究發現與HLA-DQB1*06:02-陽性健康供體相比,NT1患者體內Hcrt特異性CD4+T細胞的頻率升高,反應活性增強[6]。T細胞可分為兩類:CD4+輔助性T細胞和CD8+殺傷性T細胞,兩種類型的T細胞的反應都是通過T細胞受體來觸發的[3]。研究表明細胞毒性CD8+T細胞,而不是輔助性CD4+T細胞,可以殺死Hcrt神經元[7],一種可能的情況是,CD4+T細胞啟動疾病過程,CD8+T細胞來執行組織損傷[8]。
發作性睡病是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疫苗接種、鏈球菌感染均可增加發作性睡病的風險,感染可以通過多種機制誘導自身免疫,包括分子擬態、表位擴散、旁觀者激活和超抗原,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病原體可以引發發作性睡病[9]。鏈球菌感染可使發作性睡病風險增加,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65%近期發作的發作性睡病患者血清抗鏈球菌抗體升高[10]。鏈球菌作為一類超抗原,可能通過廣泛的免疫應答激活或自身免疫反應性T細胞、炎性介質、發熱,造成血-腦脊液屏障通透性增加而使發作性睡病風險增加[11]。研究顯示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可以導致動物發作性睡病,甲型H1N1流感病毒本身可能包含誘發免疫反應的抗原,該抗原與Hcrt受體存在交叉抗原,從而誘發自身免疫反應[4,12]。為預防甲流而接種的Pandemrix疫苗(含AS03佐劑)在接種后的表位可通過分子模擬的方式誘導Hcrt受體抗體,導致發作性睡病的風險增加[13]。
有研究報道殺蟲劑和除草劑與發作性睡病有關[14],亦有報道頭部腫瘤、卒中與發作性睡病有關[15],可能是影響了Hcrt水平。此外,攜帶有T細胞受體 α 基因和G蛋白偶聯嘌呤受體P2Y11基因均可增加發作性睡病的風險[16]。
2 臨床表現
發作性睡病是一種無法治愈的中樞性嗜睡障礙,盡管其并不常見,但它幾乎總是對受測者產生嚴重且潛在的致殘影響,尤其是超過半數的受測者將在16歲之前出現癥狀[17]。其最常見的特征是白天不可抗拒的嗜睡發作,可發生于吃飯、行走、與人交談時,外界刺激少的情況下更易發生,短暫小睡后即可恢復精力,但不能維持太久。約70%的患者合并有猝倒發作,表現為突發的部分或全部肌張力喪失,常由面頸部開始,逐漸發展到軀干、四肢,常由積極的情緒誘發,如大笑;發作時患者意識清醒,發作后可回憶全過程。大多數發作性睡病患者可伴有REM睡眠異常,REM睡眠是一種獨特的睡眠狀態,其特點通常是做夢和肌肉麻痹,阻止一個人把他們的夢付諸于行動[3]。REM睡眠可以發生在某天的任何時間,插入到清醒時可表現為猝倒,插入到入睡或起床時,可表現為睡眠幻覺或睡眠癱瘓。睡眠幻覺多在入睡時發生,可以為視、觸或聽幻覺,也可以為夢境樣體驗;睡眠癱瘓是患者從REM睡眠中醒來時出現的一過性的不能言語和全身不能活動,常伴有恐怖樣體驗,可自行終止,也可被外界刺激所終止。
其他令人不安的癥狀還包括肥胖、夜間睡眠紊亂、精神情緒異常。肥胖在嗜睡人群中非常普遍,許多患者食欲控制失調,承認對食物有嚴重的渴望,通常是在晚上,尤其是對甜食的渴望,導致暴飲暴食[18],也有研究稱他們攝入的熱量和活動水平大致正常,可能是由較低的代謝率引起[3]。夜間睡眠紊亂可以是患者的主訴之一,其特征是頻繁夜間醒來導致睡眠片段化和睡眠質量下降。青少年發作性睡病患者多伴有抑郁癥狀,這些癥狀與夜間睡眠質量差、日間過度思睡和閑暇時間運動少有關[19],也可能與Hcrt能神經元喪失導致獎賞通路的活性不足有關[3]。抑郁癥狀通常始于青少年時期,其特征是隨著青少年向成人過渡,其體內的激素、神經系統、行為和社會心理發生顯著變化,如果不加以治療,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19]。
3 診 斷
發作性睡病的診斷除根據臨床表現外,還需結合夜間多導睡眠圖(nocturnal polysomnogram,nPSG),多次睡眠潛伏期試驗(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MSLT),腦脊液Hcrt檢測,血清HLA分型等。患者行MSLT的前夜需常規行nPSG,以保證充足的夜間睡眠,還有助于發現共患的其他睡眠障礙,以鑒別診斷;nPSG多表現為夜間易醒,睡眠片段化,REM睡眠潛伏期縮短,約50%的患者nPSG顯示夜間入睡后15 min內出現異常的REM睡眠,診斷嗜睡的特異度高達99%[20]。MSLT試驗前可佩戴1 w體動記錄儀并記錄睡眠日記,有助于確定是否存在睡眠不足、倒班工作或其他晝夜節律紊亂,從而更好地判讀MSLT結果。發作性睡病患者MSLT結果顯示平均睡眠期≦8 min,出現兩次或兩次以上始發的REM睡眠,夜間起始15 min內出現的REM睡眠可替代MSLT中的一次始發REM睡眠。腦脊液Hcrt的測定已成為發作性睡病診斷的“金標準”和分型依據,2014年頒布的《睡眠障礙國際分類》第三版將發作性睡病分為1型和2型,即伴(1型)和不伴(2型)Hcrt降低的發作性睡病。發作性睡病與HLA-DQB1* 06:02 基因高度相關,攜帶此基因者發病風險增高 200 倍[21],但由于特異性不強,亦有12%~38%正常人群攜帶此基因[22],已不再作為篩選和診斷指標。
發作性睡病起病隱匿,早期癥狀不典型、加上臨床醫生對本病認識不足,部分醫院缺乏診斷所需設備,導致該病易誤診和漏診。據報道,從癥狀出現到診斷的平均時間通常超過10 y,但隨著對該疾病認識的提高,時間延遲可能會減少[23]。
4 治 療
絕大多數發作性睡病患者將受益于藥物的對癥治療,可能還會伴隨生活方式的改變。如養成良好的作息,合理安排日間小睡,避免選擇高危職業。盡管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藥物獲得了臨床監管批準,但發作性睡病的治療涉及到多種生化靶點和神經回路,增強兒茶酚胺的有效性和藍斑去甲腎上腺素神經元的活性可能是這些藥物治療的核心[24]。
發作性睡病的藥物治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精神興奮劑治療日間過度思睡、抗抑郁藥改善猝倒癥狀以及鎮靜催眠藥治療夜間睡眠紊亂。鹽酸哌甲酯是治療兒童多動注意缺陷綜合征的主要藥物,也是世界上治療發作性睡病處方量最大的藥物,主要改善患者嗜睡癥狀,價格便宜,但不良反應較多。莫達非尼為治療發作性睡病的一線用藥,但促醒機制不明,可能與抑制多巴胺再攝取有關,對哌甲酯耐藥患者,莫達非尼仍可取得良效,且不良反應小,它的主要限制是不能改善猝倒。文拉法辛具有抑制腎上腺素能及5-羥色胺再攝取的雙重作用,在低于抗抑郁的劑量時即可發揮強的抗猝倒作用,同時還具有輕微的促醒作用,已成為治療發作性睡病的一線藥物。許多發作性睡病患者的夜間睡眠受到足夠的干擾,值得治療。羥巴酸鈉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準的唯一一種既能緩解睡眠/覺醒障礙又能緩解猝倒的藥物,大量證據表明,羥巴酸鈉可以通過增強慢波成分鞏固睡眠[25],也可以減少85%的猝倒以及提高白天的警覺性[26]。2016年,一種新型促醒劑匹托利松被用于治療發作性睡病,作為一種逆組胺受體(3型)激動劑,它通過提高下丘腦組胺水平提高清醒[27]。
人類發作性睡病中Hcrt神經元的缺失表明,補充Hcrt可能逆轉這種疾病的一些癥狀。最近一項針對嗜睡犬的研究表明,靜脈注射Hcrt可迅速逆轉發作性睡病癥狀,增加活動水平,減少日間嗜睡,減少或消除猝倒癥狀,鞏固夜間睡眠時間[3],在嚙齒類動物模型中也存在一些中樞給予Hcrt有益作用的證據,考慮到有前景的動物研究和人類患者的早期臨床試驗,Hcrt的替代治療可能很快成為一個可行的選擇[28]。然而,將動物模型應用于人類通常是不確定的,給藥途徑成為這種補充治療的主要問題,在現有的可能性中,鼻內給藥是最實際和可容忍的,靜脈注射和腦室內途徑受血腦屏障穿透性的限制[29]。基因治療和干細胞移植提供了唯一的因果治療方案,但也面臨一定的挑戰性,一是侵入性的顱內傳遞,二是載體基因表達的持久性以及移植細胞的存活率[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