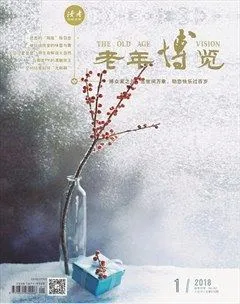亂世佳人蘇青
頂真的鼻子,無(wú)可批評(píng)的鵝蛋臉,俊眼修眉,有一種男孩的俊俏,面部的線條雖不硬而有一種硬的感覺……這是胡蘭成眼中的蘇青。張愛玲則用了這樣一句“張氏比喻”形容閨中密友蘇青的臉:“像從前大戶人家有喜事,蒸出的饅頭上點(diǎn)了胭脂。”
蘇青的老家在寧波城西一個(gè)叫浣錦的小村莊。這個(gè)早在19世紀(jì)中葉就開埠的商城,是浙東到上海的門戶。100多年來(lái),寧波人就有了那么一種熱辣、現(xiàn)實(shí)、不陳腐的新興的市民氣象。蘇青的現(xiàn)實(shí)與爽利,應(yīng)該也其來(lái)有自。朋友們都說(shuō):那真是個(gè)喜歡說(shuō)話的女人啊,說(shuō)起話來(lái)脆生生的,語(yǔ)氣連珠炮般快捷,不陰暗,也不特別明亮,就給人平平實(shí)實(shí)的那種快樂。
這個(gè)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孩大學(xué)才讀了一年,就早早地結(jié)婚去了。丈夫跟她中學(xué)同學(xué)時(shí)就訂了婚,當(dāng)時(shí)在東吳大學(xué)上海分部讀法律。為結(jié)婚而中途輟學(xué),在親戚朋友看來(lái)都是理所當(dāng)然的,在她而言卻總是有些不甘心。然而她又明白,女人終究是嫁了的好。時(shí)代是這樣的亦新亦舊,自己又能怎樣?
這樣的新婚家庭,在上海只能過(guò)最低水平的日子,連傭人也不可能雇,幸虧她母親安排周詳,讓家里的林媽跟她到了上海。
每天早晨,服侍丈夫吃罷早餐出門之后,還是有許多事好做:去四馬路的各個(gè)書店翻翻書刊,去公園的樹蔭下讀《良友》畫報(bào)。回來(lái)時(shí)在街角的一家店看中了喬其紗衣料、印花竹布,就暗暗地記在心里,預(yù)備著哪天再去買。半日將盡,踏著梧桐葉間漏下的碎碎的陽(yáng)光帶回家的,不是香糯的糖炒栗子,就是沙利文的糕點(diǎn),預(yù)備當(dāng)消夜或第二天的早餐。下雨天,就宅在家里,翻翻最新一期的歐美流行雜志,嗑嗑瓜子,聽聽百代公司的各式唱片。興致好的話,就織織絨線衫。柔軟蓬松的絨線纏在手里,有一絲微醺,一絲慵懶。周末的夜晚,兩個(gè)人去國(guó)泰、大光明看一場(chǎng)電影,各有各的所愛,或者阮玲玉或者胡蝶,或者顧蘭君或者王人美……
時(shí)代是這樣的半新半舊著,新的女人舊的男人,要改變都不是那么容易,不甘心又如何呢。然而洗洗刷刷、湯湯水水的日子里,人不免被捂得發(fā)芽,再加上女兒一個(gè)接一個(gè)地出生,手忙腳亂,把鹽瓿當(dāng)作糖缸,心浮氣躁,這樣一個(gè)少奶奶她也當(dāng)不下去了。于是先是分居,后來(lái)又協(xié)議離婚。
從家里搬出來(lái)過(guò)一個(gè)人的日子,其間的辛苦、悲喜也只有自己去體味了。那個(gè)時(shí)期的她有一句名言:“家里墻上的每一根釘子都是自己釘上去的。”語(yǔ)氣是傲嬌的,卻也無(wú)可奈何。
后來(lái)還要一邊帶著一串孩子,一邊在筆頭上討生活。坐在電燈下一手寫文章,一手還要替孩子們打扇。更要命的是望穿秋水,稿費(fèi)遲遲不來(lái)。
一個(gè)人的日子,照樣要紅塵滾滾。她不漂亮,只有中人之姿,但一個(gè)有才情、有熱情、有著端莊還可以說(shuō)有幾分秀麗的外貌的單身女作家,怎可以少了一則則綺麗的故事?

蘇青走出家庭之后的生活,我們可以從她家庭影集似的自傳體小說(shuō)《結(jié)婚十年》和《續(xù)結(jié)婚十年》中看到:一個(gè)單身的職業(yè)婦女,是那個(gè)時(shí)代一種比較稀有的動(dòng)物。她身邊走來(lái)一個(gè)又一個(gè)男人,他們欣賞她,引她為紅顏知己,和她談文學(xué)人生,談著談著談上了床,“結(jié)果終不免一別”。一個(gè)個(gè)亦正亦邪的男人,一場(chǎng)場(chǎng)愛情逐水而來(lái)又逐水而去,到頭來(lái),終究是“十二姻緣空色相”。
她不是古典小說(shuō)里那些為破碎的愛情守節(jié)的標(biāo)本。她要男人,要他們給她的一份內(nèi)心的瓷實(shí),要男女在一起過(guò)日子的興興頭頭。還是個(gè)女孩的時(shí)候,外祖母就說(shuō)過(guò)她太貪,貪世間的繁華。虔誠(chéng)禮佛的外婆說(shuō),大千世界的一切都是夢(mèng)幻泡影,而她喜歡的偏偏是這個(gè)世界的實(shí):街上的燈火,廚房的油煙味,剪子在新買的布匹上的咔嚓聲,男女的歡樂……實(shí)在的、可以觸摸的世界多么好啊。夜晚一個(gè)人躺在床上,暗數(shù)一個(gè)個(gè)皮影一樣從眼前走過(guò)的男人,她會(huì)問自己:我是個(gè)貪婪的女人嗎?
山河破碎,好男人不知都跑哪兒去了,紅塵滾滾中似乎只剩下勞工階級(jí)、小市民、舞男和漢奸。女人的夢(mèng)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下愈發(fā)成了小菜一碟,可有可無(wú)的。張愛玲的30萬(wàn)日元券都挽不住一個(gè)男人的心,女人在浮世中要抓住一點(diǎn)實(shí)在的東西還真是不容易。可是蘇青還是要強(qiáng)的,是那種心掉在泥淖里還要怦怦跳動(dòng)的強(qiáng)。她抓住了文字,希望它們還是影子一樣地忠實(shí)。那個(gè)報(bào)業(yè)興隆的年頭成全了她,她在報(bào)紙的邊角談著穿衣吃飯、侍夫育兒,也毫不避諱地談性,叫喊著“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于是似乎很風(fēng)光了,掙下個(gè)“大膽女作家”的名頭。
她談男女倒也罷了,談飲食,還真是樸實(shí)可喜。看她細(xì)細(xì)碎碎地說(shuō)早餐、說(shuō)熬粥的火候、說(shuō)盛點(diǎn)心的鍋碗不要與燒菜盛羹的混用,你會(huì)覺得,她在那么簡(jiǎn)單的物事中也那么講究,真是有著一顆在現(xiàn)世中過(guò)活的心。
一如她小說(shuō)中的女主角,她天真、感性、瑣碎、軟弱,渴望愛與依靠—盡管臉上有看透一切的諷刺的笑容。她沒有找到安慰她的人,倒是有許多人等著她安慰、幫襯:孩子、母親、妹妹、近房遠(yuǎn)房的親戚。她一直是很中國(guó)的女人。所以張愛玲說(shuō),中國(guó)風(fēng)格的房屋一明兩暗,她是明的那一間。
佳人處亂世,真?zhèn)€是沒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