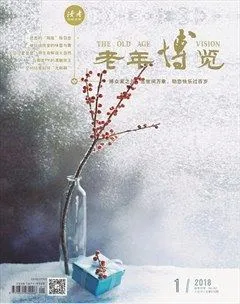被抗戰改變的味蕾與胃
胡辣湯是西安市民離不開的早餐,已經與肉夾饃、羊肉泡饃共同成為這座城市的風味名片。這鮮香濃郁的胡辣湯究竟從何而來?“獨立起源說”與“豫湯西遷說”各有擁躉,爭論激烈。對生活在西安的“道北人”來說,胡辣湯就是來自故鄉河南,而傳來的原因也很明確—抗日戰爭。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社會,也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味蕾與胃。
舌尖上的鄉愁
作家梁實秋籍貫浙江杭州,但素來以北京人自居,談起羊肉時說它“是北平人主要的食用肉之一。不知何故很多人家不吃牛肉,我家里牛肉就不曾進門”。任教青島期間,梁實秋托人專門從北京定制了一具烤肉支子,用北京烤肉宴客。離開北京40年后,梁實秋還在懷念:“我離開青島時把支子送給同事趙少侯,此后抗戰軍興,友朋星散,這青島獨有的一個支子就不知流落何方了。”
對梁實秋來說,故鄉風味僅僅用來懷念。對隨著抗戰爆發而逃難流亡的民眾而言,家鄉小吃卻是安身立命、養活全家的手藝。1938年6月花園口決堤,大批黃泛區民眾逃到鄭州,把金水河北的老墳崗變成了家鄉風味美食城,“牛家火燒、王家豆沫、白家燒雞、李長庚羊肉湯、馬大胖胡辣湯等,逐漸形成了字號”。1942年大饑荒期間,幾十萬河南人向西逃難,在西安道北聚居,把胡辣湯等河南小吃也帶到了陜西。
在西安人看來,西安胡辣湯和道北胡辣湯的區別在于肉丸肉丁,河南人卻能從中吃出更多不同。有的攤位大加花生、面筋,顯然是開封風味;有的攤位能吃出一塊塊燉肉,當是舞陽北舞渡胡辣湯一脈;多粉皮的攤位大約來自魯山;多粉條的攤位也許源于汝州。多少辛酸淚,都被一碗胡辣湯的五味雜陳承載。
與河南小吃相似的還有安徽菜。早在晚清時,徽菜就隨淮軍和徽商遍布各大商埠,舉凡武漢、南京、杭州、蘇州,每座城市總有二三十家徽菜館。在上海,徽菜更成為一景,租界內外每條大街都有一兩間徽菜館子。作家王定九為《上海門徑》寫《吃的門徑》時,稱上海是“徽氣籠罩”的城市。上海淪陷后,“徽氣”也隨著撤向后方,深入湘、鄂、川、滇等省份。

隨著東菜西遷、北食南下,后方兩大都市—高層聚集的重慶和駐有西南聯合大學的昆明,成為八方菜色薈萃的美食之都。
據統計,1943年重慶餐館多達1789家,其中既有頤之時、蓉村這樣的老牌川菜,也有龍王廟湖北飯店、白龍池口粵香村、都郵街冠生園這樣的館子,甚至還有國際飯店、俄國餐廳之類的西餐館。昆明也是如此。市民李瑞回憶,這座城市的餐館在戰前“并沒形成體系,規模也達不到品級”,但抗戰爆發后,餐飲業包羅萬象,“昆明食客坐地便可品嘗全國美食”,逃難而來的各地學子,也可以靠食物一解鄉愁。
吃肉的奢侈
“徽氣”蔓延到后方,安徽人馮玉祥卻沒什么感覺。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回憶錄,一句也沒提安徽菜。
這倒也不奇怪。一方面,和浙江籍北京人梁實秋相似,安徽籍的馮玉祥自幼生長在河北保定,對徽菜的感情遠沒有對北方菜深。另一方面,與自稱“牛肉不曾進家門”的梁實秋相反,馮玉祥心中只有牛肉。1928年,馮玉祥戰勝吳佩孚,在保定大宴袍澤,一連幾天都吃牛肉罩餅,直到部將們吃膩才作罷。各色人等回憶抗戰期間的馮玉祥,經常提到他吃飯的主菜是牛肉,諸如紅燒牛肉(據警衛王贊亭)、牛肉燒芋頭(據秘書馮興亞)、涼拌牛肉配豆芽(據舊縣完小教導主任張伯齊)等。部將宋聿修也說,馮玉祥“在重慶時,年事已高,除蔬菜外,也吃一些牛肉、雞蛋之類”。
馮玉祥畢竟位高權重,有牛肉吃不足為奇。對身在前線的抗日將士而言,吃肉就變得奢侈了。第73軍連長陳振在回憶錄中寫道:行軍趕路時,排長問“弟兄們餓了渴了,怎么辦”,擔心完不成任務的陳振要求“過了時間趕不上船就不好辦了,現在你們到池塘邊去喝點水,馬上走”。到了駐地,從干糧袋里拿出大餅,一折就成兩半,其干硬可想而知,陳振卻“毫不客氣地接過,大口大口地吃”。戰斗失利時,第一頓飯是每人一捧米飯加點鹽菜邊走邊吃,第二頓只煮了些稀飯,第三頓還是稀飯,添些紅薯,便“又香又甜”了。

身在相對富足的南方,野戰部隊吃肉都很困難,在貧瘠的華北吃肉更成為一種難得的享受。綏遠五原戰役期間,董其武曾在友軍那里吃到一頓“糜米飯和羊肉煮山藥蛋”,40多年后寫回憶錄時,這位上將依然對這頓肉食念念不忘,感嘆“在當時這真是一頓豐盛的美食”。
軍官尚且如此,士兵想吃肉就更困難了。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第54軍任排長,最擔心的便是“士兵們從村民處偷來一只狗,放進鍋里煮,整只吃干凈”。黃仁宇擔心的不是軍紀問題,而是怕士兵吃壞肚子,導致生病甚至死亡,那樣的話不僅裝備要別人背,補充員額更是遙遙無期。
和前線軍人一樣對吃肉趨之若鶩的還有學生。昆明西南聯大附近有個“西南食堂”,特別受大學生歡迎,熱門菜包括回鍋肉、大頭菜炒肉、宮保肉、紅燒肘子等。學生們喜歡這里是因為“價錢公道和菜內油多”,縱使有不衛生、食材不正的問題,但在“一元多可吃飽”的情況下,也就無人在意了。當然,這還是身處昆明。如果像浙江大學一樣遷到貴州,有錢也沒得吃。學者丁文江就曾抱怨,貴州有種小飯鋪只有兩種東西下飯:一碟鹽巴,一碟干辣椒。
前方吃緊,后方緊吃
國民政府軍政部曾在1935年制定了《陸軍戰時給養定量標準》,規定每名士兵每天要配給大米22兩(舊制,1斤=16兩)或面粉26兩、罐頭肉4兩、干菜2兩、咸菜2兩、食鹽3錢、醬油4錢,臨時加給燒酒2兩或白糖1兩。以抗戰爆發后的物質條件而論,這個標準根本無從達到。據貴陽軍醫院院長楊文達觀察,“總的來說,軍隊的伙食費采購米是夠的,菜卻不夠,尤其油脂及蛋白質更是不足”。
吃米不愁,還是抗戰初期的事。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與郵政儲金匯業局編印的《重慶物價專刊》顯示,如果以1937年上半年糧價指數為100,那么1939年12月糧價指數就漲至182.1,1940年12月猛漲到1004.5。在這種狀況下,前方一旦傳來吃緊的消息,后方民眾便要抓緊多吃一點,不然就真吃不起了。
這種背景下,糧食變得“保量不保質”。連中央大學的食堂,供應的也是摻雜了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殼、稗子、老鼠屎和小蟲子的“八寶飯”。第54軍軍長黃維曾經因大米質量太差,幾次把領到的壞米用小袋寄到軍政部去投訴。飯都吃不飽,菜當然就更少。士兵多面有菜色,體力下降,“列隊稍久,就有人暈倒”。
在糧錢兩缺的痛苦中,伴隨著“八寶飯”和幾乎沒有肉的三餐,中國人靠鐵胃堅持到了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