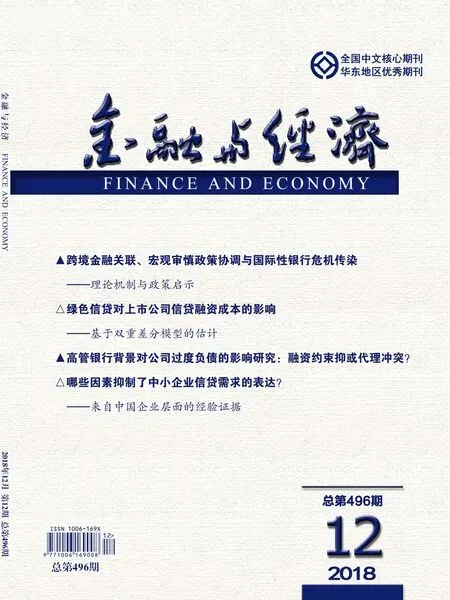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陳 鋒
當前,我國征信領域異議、投訴和訴訟三類糾紛解決渠道各有長短,尚難以覆蓋各類征信糾紛,影響了征信糾紛的處理效率和效果。應借鑒國內外相關經驗做法,構建征信領域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著重明確機構設置、管轄范圍和條件、調解效力等方面的規則。
隨著信息主體權利保護意識的日益增強,社會公眾充分利用各種渠道維護自身權利。當前,《征信業管理條例》規定的救濟渠道主要有三種,即異議、投訴和訴訟。然而實踐中,這三類救濟途徑在解決征信領域相關糾紛時,各有長短,尚難以覆蓋各類征信異議糾紛。因此,有必要在借鑒國內外經驗基礎上,探索構建我國征信領域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
一、當前我國征信領域糾紛解決機制的現狀
根據《征信業管理條例》第25條與26條的規定,當信息主體認為其信用信息不準確或認為其合法權益被侵害的,有權通過征信異議、投訴或訴訟三種渠道尋求救濟。但實踐中,還存在不足之處。
一是個別異議事項具有復雜性,增加了解決處理難度。征信異議主要針對的是信用信息不準確、不完整、不及時的情形,在征信機構、信用提供者和信息主體之間,能夠核實清楚,確認屬實的前提下,異議事項一般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但在實踐中,部分征信異議涉及基礎信貸關系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雙方就基礎信貸關系的確認產生很大爭議,各執一詞,導致征信糾紛難以在異議處理環節得到解決。例如,江西某礦泉水有限公司否認其名下一筆于1992年發放、1994年到期的30.30萬元貸款逾期的征信記錄。經過調查發現,該筆貸款主體為原某國營企業,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企業主體發生變更,導致貸款繼承到該公司名下。但時間間隔20多年,工商、質監、銀行等部門留存資料不全,難以核實兩者是否存在延續關系,異議久拖不決。
二是征信投訴渠道執行效力不足,影響了解決力度。《征信業管理條例》僅賦予人民銀行對征信業進行監督管理的權力,在處理信息主體投訴過程中,對于信息報送機構與信息主體之間的具體爭議(尤其是基礎信貸關系中的糾紛),只能從中協調,要求金融機構調查反饋,尚難直接做出有約束力的裁定。因此,在雙方各執一詞的情形下,徹底解決問題的手段和方法有限,即便在投訴處理過程中雙方就解決方案達成了一致,倘若一方事后反悔,并無相應制約機制,影響了征信糾紛的有效解決。例如,江西某集團與九江某小貸公司征信異議糾紛,涉及復雜的擔保代償關系,雙方發生多起訴訟,期間企業投訴征信信息與事實不符,但因一直處于訴訟(或上訴)狀態,爭議得不到解決。
三是訴訟具有較強的程序約束,限制了解決效率。隨著信息主體法律意識和信用權利保護意識增強,涉及征信的訴訟案件也時有發生。實踐中,法院審理要遵循嚴格的法定程序,從起訴受理、舉證質證、開庭審理、法院宣判到可能發生的上訴程序,案件審理的耗時較長,尤其在一些基礎信貸關系相互交叉、舉證質證較為困難的案件中,審理期限可能進一步延長,大大增加了訴訟雙方特別是信息主體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可見司法救濟途徑在某些情況下并不適合征信糾紛處理對效率的追求。
二、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概念及意義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也稱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該概念最早源于美國,是各種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替代性(Alternative)”,即對法院訴訟程序的替代。目前,國內外最常用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為調解機制,我國亦將調解機制視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核心內容,將其確定為司法改革的重要領域,最高人民法院曾經先后印發多個文件,推進調解機制的完善和深化。本文討論的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也主要圍繞調解機制展開。具體到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尤其是調解機制)因其內在的優勢和特點,能夠有效解決現有征信異議、投訴和訴訟渠道的各種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效率。征信爭議有一個典型特征,即對爭議解決的時效性要求較高。征信業務實踐中,許多信息主體是在貸款申請受到不利影響時,才發現信用報告中的異常現象,并通過相關渠道尋求解決。征信糾紛解決的效率,將對信息主體的切身利益造成巨大影響,這也是《征信業管理條例》分別為征信異議和投訴設定20日和30日的核查處理期限的原因。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首要特征是當事人有權通過自愿協議的方式自由處理爭議,即當事人選擇何種ADR程序完全處于其本人意愿。程序上的非正式性,使當事人可以自由地設計他們認為合適的程序,具有簡易性和靈活性,因而省時。
(2)低成本。實踐中,如果信息主體通過法院訴訟程序解決征信爭議,應當承擔敗訴而可能產生的訴訟費用,并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對于大部分情況下急需解決征信爭議、獲得相關貸款的信息主體來說,經濟負擔將進一步增加。而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能實現以更低的成本解決爭議,如澳大利亞金融督察服務機構對于其調解的金融糾紛,不對金融消費者收取任何費用,其運營費用來源于會員(主要是金融機構)。所有會員都應繳納會費,會費標準取決于其業務規模的大小。同時,結合會員單位發生糾紛的數量和糾紛處理流程的復雜程度收取附加費用,調解次數越多,流程越復雜,則費用越高,以此激勵金融機構提升糾紛處理效率。
(3)不公開。當今,司法公開已成為“深化司法改革、建立公開透明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的重要內容,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征信糾紛,可能將面臨更多的公開透明要求,并給社會公眾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恐慌,也可能給被動陷入應訴狀態的征信服務和管理部門帶來負面影響。而調解機制可以通過不公開的形式解決爭議,如《人民調解法》第23條規定,當事人在調節活動中有權要求調解公開進行或者不公開進行。因此,調解機制不公開的特征,有助于消除征信糾紛帶來的不良社會影響。
(4)促和諧。目前,社會對征信領域高度關注,個人信息保護意識日益提升,若糾紛處理不當,可能形成不良的社會影響。訴訟方式是一種正式性、嚴肅性的糾紛解決方式,貫徹辯論原則,無形中增加了爭議雙方的對立性,并使一方在舉證不能時承擔敗訴后果。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相比訴訟方式,更能體現一種平和狀態,雙方通過第三方居中斡旋,促進平等協商,并通過妥協與退讓達成一致,對抗性大大減弱,真正實現“以和為貴、定紛止爭”。此外,法律規范本身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當靜態的法律條文與動態的社會經濟發展不一致時,通過法院依法判決,并不能很好地得出雙方均信服的結果。在該方面,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靈活性特點能發揮重要作用。
(5)專業性。征信是相對比較專業的領域,需要對征信系統的運作、征信體系內各方權利義務關系等全面了解,才能做出妥善的裁決。此外,征信糾紛常常與基礎信貸關系交叉,也需要裁決者在金融、征信及法律等方面都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能集中各個行業的專家,提升爭議處理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如日本金融行業非訴解決機構中的委員由從業5年以上的律師、從事10年以上的銀行工作人員以及消費生活咨詢員等專業人士擔任。
綜上,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引入,能為快捷有效解決征信爭議提供全新途徑,并且能夠進一步豐富征信救濟體系。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39條規定,當前我國消費者權益糾紛可以通過協商和解、請求調解、投訴、仲裁和訴訟五種渠道解決。因此,構建我國征信領域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也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要求。
三、我國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法律框架設計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在國外諸多國家已逐漸成熟,如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據初步統計,全球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建立了申訴專員制度(Financial Ombudsman)。國內,在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的指導下,上海市金融消費糾紛調解中心(以下簡稱“上海調解中心”)于2014年12月16日成立,四年來已形成諸多寶貴的制度框架和經驗做法。我國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法律框架構建,應重點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
(1)機構設置問題。根據國內外的經驗,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均為獨立于政府部門和市場機構之外的第三方機構,而且機構內部治理相對獨立,履職立場也相對中立。機構設置的獨立性與中立性,是確保其解決征信糾紛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其不是行業協會,也不是金融機構利益的維護人和代言人,而是為信息主體提供獨立中立、快速便捷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渠道。另外,在諸多國家的實踐經驗中,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還應對主管行政機關保持獨立和中立,如日本金融ADR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盡可能地以國家權力不參與的方式解決金融糾紛”。鑒于此,我國征信領域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可以考慮獨立建立,也可以考慮與地方現有的金融行業調解中心合作,但原則上該機構與監管部門應無隸屬關系或管理關系,監管部門可以就征信法律政策提供指導意見。同時,為凸顯征信糾紛調解機制的中立性,在機構設置和案件辦理方面,應賦予征信糾紛調解機構充分的獨立性,在調解員的確定方面,應充分吸收高校、研究機構、律師事務所等各領域的專業人士,適當控制金融機構及監管部門人員的比例。
(2)管轄范圍問題。征信領域爭議由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解決,已有先例。如英國2006年《消費信貸法》(Consumer Credit Act)第59條規定,信息主體與信用服務機構所發生的相關征信糾紛,可以在自愿的基礎上提交金融申訴專員(英國金融領域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處理。在我國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構建中,為充分發揮其獨特的優勢和功能,應通過制度安排確認其對各類征信爭議管轄權,包括與此相關的基礎信貸關系爭議等,以促進征信糾紛高效、徹底地解決。此外,對于信息主體與非金融機構(如法院、公積金管理中心等數據報送機構或接入機構)之間的征信爭議,若雙方自愿提交調解,亦應賦予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管轄權,使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成為征信領域普遍適用的糾紛解決途徑,更好地維護征信市場秩序。
(3)管轄條件問題。在各國的立法和實踐中,以調解機制為代表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均已自愿原則為前提。我國《人民調解法》第3條也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應遵循自愿原則。”基于該理念,征信異議調解機制應以爭議雙方的自愿為基礎,不得因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客觀優點和獨特功能,盲目擴大其管轄范圍和條件,甚至剝奪爭議方(尤其是信息主體)提起訴訟的法定權利。上海調解中心的管轄條件值得借鑒,其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爭議雙方自愿提交其調解的案件,二是根據與法院的訴調對接機制,法院也可經當事人同意,將爭議案件委托或委派上海調解中心調解。此外,因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通常具有低成本的特點,容易導致被濫用的風險,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中,可以考慮將征信異議和投訴作為調解機制的前置程序,先充分利用征信體系內部的救濟手段,再尋求外部第三方解決。
(4)調解效力問題。根據我國法律,目前通過調解機構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法院判決所具有的法律約束力,其效力僅等同于民事合同,爭議方有權請求另一方履行,但無法直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為了支持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增強調解協議對當事人的約束力,我國當前主要采取兩種模式。一是立法模式,如《人民調解法》第33條規定,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協議后,雙方當事人可以共同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法院對調解協議進行審查后,進行效力確認。經法院確認后的調解協議,當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二是協議模式,如上海調解中心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協商建立“金融消費糾紛訴調對接工作機制”,上海調解中心做出的調解協議,可申請法院司法確認,經確認的調解協議,也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在征信領域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設計中,為提高處理結果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可通過立法模式或協議模式,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