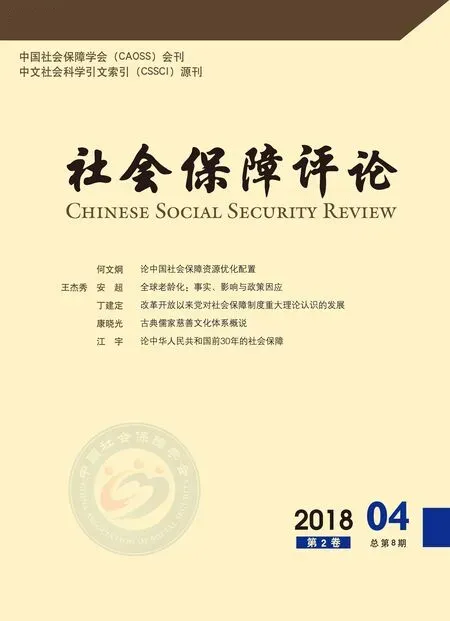中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
張奇林 宋心璐
一、引言
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是傳統經濟學的一個主流命題,對于這一現象的探討可以追溯至18世紀早期經濟學家關于政府債務減少投資和消費的思想,盡管在當時這一名詞未被確切提出aMichael Hudson, "How Economic Theory Came to Ignore the Role of Debt,"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1,57(6).。現代經濟學中,擠出效應主要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所導致的私人投資和消費可能出現減少的現象。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是指政府在慈善領域的支出引起私人慈善降低的現象,即公共慈善對私人慈善的擠出。擠出的路徑有多種,主要包括直接降低慈善捐贈者的捐贈、通過降低慈善組織的募捐意愿和能力而減少私人捐贈總量以及通過減少慈善資金的最終流向來減少捐贈。研究公共支出對慈善捐贈的擠出,是觀察和實證檢驗政府與慈善互動關系的重要方面,同時也是制定有效的慈善促進政策的重要依據bJerald Schiff, "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 out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5, 38.。
從17世紀濟貧法時代開始,到二戰后福利國家的建立,政府對民生等社會事務的干預越來越多,政府直接支出a被稱作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稅惠政策,是一種間接支出。對于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也引起研究者越來越多的關注。關于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理論形式推導出擠出模型,第二類則是利用國家間、國家內部或某一地區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Warr是較早提出慈善捐贈擠出效應模型的學者。該理論的關鍵假設在于效用的共用性,即當一個人的消費或效用進入另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時,收入的轉移將有益于兩者。那么,只要捐助者的數量大于等于兩個,當個別捐贈者用盡了從他們的自愿捐贈中可獨立獲得的效用時,任何其他增量轉移都能進一步實現額外收益,每個捐贈者也都可從這些額外轉移中獲益。在這種分析中,轉移具有了公共物品的特性,但“搭便車”(Free-Rider)問題也就會出現。因此,如果政府增加財政再分配,捐贈者對增量做出的反應是將自愿捐贈減少相同數量,從而從整體來看,并無法實現資源的凈轉移,也就是不可能存在帕累托改進。如果想要實現凈轉移,可能的途徑只有增加財政再分配直至私人捐贈減少為零,也即完全由公共部門提供此處的公共效用,或者通過激勵捐贈的邊際財政措施實現凈轉移bPeter Warr, "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 and Private Char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2, 19(1).。Robert也認為,政府支出對慈善捐贈的擠出是完全的。他假設私人慈善捐贈完全是出于利他主義以及政治均衡過程會通過收入分配的調整來獲得包括窮人和富人在內的最大的政治支持率,由此他得出了類似于Warr的結論:私人捐贈對政府公共轉移支出增加的減少力度是一比一(Dollar for Dollar)的;在政治均衡中,相比利他主義者的捐贈,政府收入再分配總是過度提供的,公共轉移將逐漸把私人捐贈“逼迫”至零。Robert還研究發現,這種公共轉移將私人捐贈逼至零的現象正是從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背景下美國實行大規模財政干預政策開始出現的cRussell Robert, "A Positive Model of Private Charity and Public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4, 92(1).。
但是Warr和Robert提出的完全擠出模型基于非常嚴苛的假設,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對于完全利他主義產生了質疑。因此,在不斷試圖放寬原有假設的基礎上,慈善捐贈完全擠出理論也很快得到了許多學者的修正和擴展。Bergstrom等認為原理論中假設捐贈主體是外部恒定并不合理,他們放松了這一假設,得出了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支出部分擠出私人慈善捐贈的結論,并進一步指出,只有政府大刀闊斧再分配財富時,個人提供公共物品的行為才會有較大改變,從而改變整個公共物品供給的均衡狀態;如果政府的再分配力量不甚巨大,個人慈善行為并無太大變化dTheodore Bergstrom, et al., "O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6, 29(1).。但是有大量學者認為,在每一個人的效用函數中,他人的捐贈和政府支出可以被視為一種對自己捐贈的完美的希克斯替代(Hicksian Substitution Effect),在這樣的模型中,擠出效應預測在邊際和方向上都變得模糊和不明朗,政府支出對于私人捐贈的效應可以是擠出,也可以是擠入,效應大小的絕對值甚至可以大于1,而且這種模糊是固有的,即使政府支出被看作是個人捐贈的不完全替代,且在所有商品都是正常商品的情況下,仍然可能產生各種不同的效應eRichard Cornes, Todd Sandler, "Easy Riders, Joint Production, and Public Good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4,94(375); Jerald Schiff, "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 out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5,38; Richard Steven Steinberg, "Voluntary Donations and Public Expenditures in a Federalist Syste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1); James Andreoni, "Giving with Impure Altruism: Applications to Charity and Ricardian Equival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6).。
關于政府支出對于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實證研究伴隨著理論模型的建立而同步展開。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研究都表明政府支出對于慈善捐贈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但是究竟是何種政府支出對何種慈善捐贈以怎樣的機理產生多大程度上的擠出作用,研究者們并未達成較為一致的認識。Abrams和Schitz是實證檢驗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早期研究者,他們的分析結果顯示,政府相關公共支出每上升1%,私人慈善捐贈則下降0.2%,政府支出對慈善捐贈有部分擠出效應aBurton Abrams, Mark Schitz,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Governmental Transfers on Priv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Public Choice, 1978, 33(1).。后來他們進一步研究發現,美國州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每增加1美元將導致慈善捐贈減少30美分,而且當他們將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關支出作比較時,發現捐贈者對于聯邦政府的公共服務支出的敏感性更高bBurton Abrams, Mark Schitz,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Governmental Transfers on Priv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Cross-section Evidence,"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4, 37(4).。Jones對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的研究也表明,政府總體支出對慈善捐贈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cJones Philip, "Aid Char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83, 10(2).。
但是,不同的政府支出項目和支出水平對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并不相同dJyoti Khannaa, et al., "Charity Donations in the UK: New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 56(2); Daniel Hungerman, "Are Church and State Substitutes? Evidence from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11); Christopher Horne, et al., "Do Charitable Donors Know Enough—and Care Enough—about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Affect Private Giving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5, 34(1); Jonathan Gruber, Daniel Hungerman, "Faith-based Charity and Crowd-ou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5-6); Thomas Garrett, Russell Rhine, "Government Growth and Private Contributions to Charity," Public Choice, 2010, 143(1-2).。Schiff將政府支出類別進行細化,結果顯示,唯有純貨幣轉移和地方政府支出對慈善捐贈具有顯著的擠出,其他類型的政府支出對慈善捐贈的擠出并不明顯,甚至有擠入作用eJerald Schiff, "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 out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5, 38.。但Chung等人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健康和社會服務的支出對慈善捐贈有負向影響fChung Ming Wong, et al., "Contribu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98, 25(1).。而Brooks研究發現,個人慈善捐贈與政府支出之間的關系呈拋物線形狀,個人慈善捐贈首先會隨著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到達頂峰后隨著政府支出的繼續增加而減少,直至為零,而慈善捐贈與政府支出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效用的峰值則處在慈善捐贈的下降區間內gArthur Brooks, "Public Subsidies and Charitable Giving: Crowding out, Crowding in, or Both?"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00, 19(3).。當然,亦有研究基于對數據的不同認知和處理,認為政府支出對于慈善捐贈并沒有顯著的擠出作用hWilliam Reec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New Evidence on Household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9, 69(1).。
綜上,國外對于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主要發展出了早期完全擠出模型以及后來的不完全擠出模型、模糊效應、非一致趨勢效應等多種理論架構,并使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調查數據和統計數據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雖然得出的結論不完全一致,但多數研究認為擠出效應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慈善領域。
相比國外的研究,國內對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比較有限。有學者對慈善領域擠出效應的形成機理以及可能出現擠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理論分析,但其依據來源于部分慈善新聞或慈善案例,缺乏說服力。僅有的幾項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大都認為我國政府用于教育、衛生、科技、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支出會“擠入”慈善捐贈a林琳:《政府支出與慈善捐贈之間的效應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2期;顏克高、彭西妍:《慈善領域的擠出效應及對策探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4年第3期。,相應的解釋是,政府行為對慈善捐贈有“引領”作用b曹洪彬:《我國捐贈的公共經濟學分析》,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王輝:《慈善捐贈、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遼寧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政府支出作為一種“信號”,能夠引起民眾對某類問題的關注,進而民眾以捐贈的方式給予“響應”c汪大海、劉金發:《政府支出與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研究——基于2003—2010年中國省市面板數據》,《中國市場》2012年第50期。。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我國現階段慈善事業發展的某些特點,在慈善捐贈方面政治動員和政治投機的色彩較濃,這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也能找到佐證。如張奇林認為,我國慈善捐贈的波動性大,事件性特征比較明顯,與動員性和攤派性募捐有一定的關系d張奇林:《〈慈善法〉與中國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江淮論壇》2016年第4期。;戴亦一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換屆后,企業慈善捐贈的傾向和規模都會顯著增加,而政府換屆之后的慈善捐贈確實能為民營企業帶來融資便利、政府補助、投資機會等多方面的經濟實惠,由此,他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慈善捐贈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為建立政治關系而付出的“政治獻金”e戴亦一等:《中國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政治獻金”嗎?——來自市委書記更替的證據》,《經濟研究》2014年第2期。;賈明等也研究發現,企業高管的政治關聯容易促進公司慈善行為,具體表現為具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參與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f賈明、張喆:《高管的政治關聯影響公司慈善行為嗎?》,《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但是這些得出“擠入”結論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以總體的政府支出(主要是公共服務支出)為因變量來進行研究,這種處理略顯簡單和粗糙,不太符合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現實。從我國目前慈善捐贈的流向來看,慈善捐贈的主要目的是緩解貧困和救濟災民g用于教育救助、減災救災、扶貧、醫療救助等的捐贈資金占捐贈總額的一半以上。參見楊團:《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這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慈善捐贈不盡相同,后者將大量的慈善資源投入到了前沿科技研究、私立大學建設、公共和社區福利、文化藝術以及宗教發展等方面,用于緩解貧困的捐贈其實并不多。以政府總體支出為解釋變量來研究我國政府支出對慈善捐贈的影響,往往不得問題的要領,容易產生誤導性的結論。鑒于此,我們抽取公共支出中的社會救助支出為自變量,考察和檢驗我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慈善捐贈是否存在擠出效應。
當然,除了政府支出外,影響慈善捐贈的因素還有很多,包括宗教、地域、家庭背景、教育水平、職業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及人口因素等,學術界都給予了高度關注,這些研究為我們設置和考察相關變量提供了依據和參考。
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論,通過回顧國內外有關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成果,明確變量的含義及其之間的關系,為后續的研究做理論鋪墊。結合中國慈善捐贈的特點以及現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以社會救助支出為自變量,檢驗我國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設想。第二部分為實證分析,根據既往的研究和我國的實際情況,構建實證模型和省級面板數據,使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及隨機效應模型分析社會救助支出和慈善捐贈之間的關系,并用LM檢驗、Hausman檢驗等方法篩選出最優模型,并得出實證結果。第三部分是結論與建議,根據實證結果,進一步給出理論解釋,并針對我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減少這種擠出效應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設置
根據既定的研究思路及對相關文獻的回顧,我們構建了一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期在盡可能考慮到其他相關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定量分析和實證檢驗政府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charityit,是省級慈善捐贈水平指標,用各省每年人均慈善捐贈額表示;解釋變量soci_assisit,是省級政府救助支出水平指標,用各省每年人均社會救助財政支出額表示,待考察系數為α1;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系數系列為β',我們將這些控制變量分為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文化教育狀況、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發展狀況以及人口自然狀況等4類,詳細的變量設置和操作方式見表1;εit為隨省份與時間而改變的擾動項,μit表示不可觀測的省份特殊效應。

表1 各個變量的名稱、含義及具體操作方式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1997a目前所能看到的較完整的分省份社會捐贈統計數據始于1997年,因此,本文的面板數據從1997年開始統計。—2015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相關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1998—201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5)》、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國家民政部網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jb/sjsj/?)、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網站(http://sara.gov.cn/zjjbxxcx/)、EPS全球統計數據/分析平臺(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http://www.epsnet.com.cn/)等。為了消除物價變化的影響,在具體操作中,包括各地區實際人均GDP在內的所有涉及到價格水平的指標,
均以1997年為基期進行了“消脹”處理。表2報告的是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結果。

表2 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結果
從表2可知我國總體人均慈善捐贈為6.33元,最低時僅為0.12元/人,最多為92.2元/人。而政府財政中社會救助支出的人均水平為40.5元。
圖1和圖2展現了1997—2015年我國人均慈善捐贈水平和社會救助支出水平的地理分布。自1997年以來,各省的人均慈善捐贈呈波動上升狀況,尤其是在重災年份,如1998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以及2008年和2010年發生特大地震災害,捐贈活動異常活躍。其中,北京、上海、江蘇及浙江等地人均慈善捐贈水平較高。
而政府社會救助支出方面的情況則與慈善捐贈水平不同。比較圖1和圖2可知,社會救助支出平均水平高的省區與慈善捐贈較高的省區相左。在社會救助支出方面,西藏、青海、甘肅及新疆等地的支出數額增長很快,并在近些年超越多數東中部省份,位列全國前列,這一方面與西部地區人少地廣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國家扶貧政策大幅向西部地區傾斜的事實。另外,還可以發現,人均社會救助支出水平遠高于人均慈善捐贈水平。人均慈善捐贈僅有少數年份的少數省份突破人均50元,最高也未超過100元,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均社會救助支出水平在近兩年已達60—80元,有些省份近兩年的人均救助水平已超150元,最高達300元左右。

圖1 1997—2015年我國分省份人均慈善捐贈水平(元)

圖2 1997—2015年我國分省份人均社會救助支出水平(元)
四、實證結果
我們采用靜態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實證分析我國政府救助支出對于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第一步以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三種基本模型進行估計;第二步以F值檢驗和LDSV法比較混合OLS模型與固定效應模型;第三步采用LM檢驗和Hausman檢驗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中進行篩選,以求得靜態面板數據下的相對最優模型解。
(一)靜態混合OLS、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及模型篩選
靜態混合OLS、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下的實證結果見表3。從表中可見,雖然三種模型的實證結果均表明,我們所關注的系數α1均小于零,也即政府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具有擠出效應,但唯有固定效應模型下呈現顯著。從本文的數據結構和類型來看,此面板數據也可能更適合固定效應模型,但為保精確,我們將進行檢驗,以篩選出最適合的靜態模型進行分析。

表3 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POOLED-OLS、FE和RE模型)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在表3中,固定效應已經給出了檢驗一般固定效應是否顯著的F統計量和相應的P值,其中,F值=5.07,P值=0.0000,說明固定效應非常顯著,優于混合OLS模型。但是此處的一般固定效應采取的是普通標準誤,我們再利用LDSV法aLDSV即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法(Least Squares with Dummy Variable),屬于固定效應模型的一種。與一般檢驗使用普通標準誤不同,LDSV法采用的是考慮到異方差條件的穩健標準誤,比普通標準誤更為保守。因此在N相對不大的情況下,使用LSDV可以用來進一步確定固定效應模型是否會優于混合OLS模型。進行估計,從而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之間進行更精確的比較。
LSDV法下的各系數以及以年份作為虛擬變量的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可見,在更保守的穩健誤差作用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仍呈現出顯著的擠出效應,且顯著性提高至1%的水平上,同時以年份作為虛擬變量均在1%的水平上表現顯著,因此可進一步確定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OLS模型,且采取LSDV模型優于一般的固定效應模型。

表4 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LSDV模型)
我們已根據普通標準誤以及基于穩健標準誤的LSDV法比較了混合OLS和固定效應模型在本文中的切合性,并得出了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OLS模型的結論。接下來,我們將比較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效果。我們采用LM法單獨檢驗隨機模型的顯著性,再利用Hausman檢驗來比較兩者。
表5報告了LM法的檢驗結果,不難看出,隨機效應模型并不適用于本文中探討的政府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擠出效應的研究。

表5 隨機效應模型的檢驗(LM法)
在我們運用Hausman檢驗對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篩選時,結果顯示,p值在1%的水平下顯著,同時,chi2(13) 值=109.71,由此基礎上得到的Prob>chi2值= 0.0000,且sqrt(diag(Vb-VB))不存在缺失值(見表6),進一步排除了模型設置存在諸如重要變量遺漏、模型形式不切合實際等問題,因此可以判斷,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

表6 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篩選(Hausman檢驗)
最后,為了檢驗模型的內生性問題,我們用動態面板模型,將因變量滯后一期作為IV進行再次驗證,實證結果與前面一致,雖p值不顯著,但社會救助支出微弱擠出慈善捐贈的方向一致。同時,用J統計量進行Sargan檢驗,p值=0.00018(見表7),說明檢驗原假設過度約束正確,模型設定有效。

表7 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動態面板GMM模型)
(二)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一般固定效應模型和LSDV的實證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
我們最關心的系數α1,即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的作用,在固定效應模型皆為負值,且在相關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我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于民間慈善捐贈存在較為顯著的部分擠出效應。具體從數值上來看,一般固定效應模型顯示,我國政府對人均社會救助支出每提高1%,會導致民間慈善捐贈下降0.02%,也即擠出0.02%的民間慈善捐贈,并在10%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根據LSDV法的實證結果顯示,這一擠出達到了0.0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從模型分析結果看,我國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于民間慈善捐贈的擠出效應是顯著的,但擠出的力度非常小。這一結果表明,盡管社會救助和慈善捐贈的瞄準對象重合率比較高,主要集中于老弱病殘、急難人員、低收入群體等,但是兩者都還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擠出效應十分弱小。我們將在后文對此結論作進一步的探討和闡釋。
除解釋變量社會救助水平對被解釋變量慈善捐贈的效應以外,一系列控制變量中亦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結果和發現。
首先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慈善捐贈水平的正效應。主要表現在固定效應模型下,人均GDP、人均收入變量對于人均慈善捐贈水平的作用顯著為正,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慈善捐贈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莫大聯系,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良好,其慈善捐贈活動亦更加活躍。正如圖1所示,我國京津、廣東、江浙滬等地的慈善捐贈水平就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以及許多中西部省區。這也不難理解我國較大規模的慈善組織為什么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
其次是教育發展水平對慈善捐贈具有正效應。本文以各省每年15歲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率作為一個地區的教育發展程度指標,實證結果顯示,教育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某地的文盲和半文盲率越高,其慈善捐贈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即一個地區教育越不發達,它所獲得人均慈善捐贈就越多,充分表明我國慈善資源流向有明顯的扶助落后、扶助教育趨向。
第三,社會組織的發展對民間慈善捐贈活動有促進作用。根據LSDV模型的實證結果,每十萬人中的社會組織數量增加1%,可促進慈善捐贈增加0.08%,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充分說明社會組織的迅速發展對我國慈善捐贈水平提高的重要作用。
第四,社會保險的逐步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亦對民間慈善捐贈活動有擠出作用。近些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斷完善,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為代表的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保障水平不斷提高,當居民年老或陷入疾病等困境的時候,健全的社會保險制度將會保障其基本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民間慈善活動a。本文的實證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一般固定效應模型的相關系數為-0.104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最后,自然災害往往是慈善捐贈活動進入高峰的“觸發機制”。在我們的實證模型中,將各省每年自然災害的受災人口數量設置為控制變量,這一變量的系數在包括混合OLS和隨機效應模型在內的所有模型中均為正,且在一定水平上顯著。說明自然災害越嚴重,對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越大,慈善捐贈活動便會格外活躍。現實也確實如此,如2008年我國遭遇汶川地震及南方雪災,引發了空前的社會捐贈熱潮,有人甚至將這一年稱為中國的“慈善元年”。
五、結論與建議
經過比較,采用固定面板數據模型,尤其是LSDV模型下能夠達到模型的最優化。實證結果顯示,我國政府在社會救助方面的財政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不過擠出效應非常小。在LSDV法下,這一擠出達到了0.0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也即政府救助支出每增加1%,我國私人慈善捐贈則相應減少0.04%。
這一結論與我國目前已有的類似研究相左a參見曹洪彬:《我國捐贈的公共經濟學分析》,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王輝:《慈善捐贈、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遼寧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導致結論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變量選取的不同。鑒于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現狀和特點,選取公共支出中與慈善捐贈的流向和目標人群較為一致且有一定競爭性的社會救助支出為自變量,對于探討慈善領域的擠出效應,可能更合理,也更有必要。
相比國外經驗研究的結果,本文得出的擠出效應的絕對值過小,擠出效應微弱。我們對這一差異的解釋是,我國的社會救助制度和慈善事業都處在蓬勃發展的“開拓期”,無論是社會救助支出還是慈善捐贈水平,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從貧困群體的總量來看,在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政策推動之下,近5年累計減少貧困人口6800多萬,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b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18)》,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uanti/2018lh/2018zfgzbg/zfgzbg.htm,2018年3月5日。,但目前尚有農村貧困人口3000萬左右c《中農辦:未來三年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18-08/20/c_1123313294.htm,2018年8月20日。。社會救助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舉措,有大量兜底保障的工作要做。當前我國城鎮低保水平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8%,農村低保水平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0%,不到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2017 年全國城市低保平均標準540.6 元/人·月,農村低保平均標準4300.7 元/人·年d民政部:《2017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民政部官網: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201708021607.pdf。,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e國家統計局:《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官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年2月28日。)。同樣,我國慈善事業雖然有了長足發展,慈善捐贈已連續幾年突破1000億,但與快速發展的經濟水平和不斷增長的居民收入相比,慈善捐贈水平仍然偏低,我國慈善捐贈總額占GDP的比重僅為0.16%,相比之下,美國慈善捐贈總量占GDP比重常年在2%左右f張奇林:《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0頁。。由于總量有限,我國慈善捐贈流入社會救助領域的資源比較少,因此,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對慈善捐贈的擠出程度自然就比較弱。
綜上,雖然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社會救助支出對民間慈善捐贈存在擠出效應,但在兩者均有較大提升和發展空間的情況下,如此低程度的擠出效應說明政府在社會救助領域占絕對主導地位,也意味著社會救助領域的慈善捐贈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為此,應堅決貫徹執行十八大提出的“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支持發展慈善事業”和十九大提出的“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的方針政策,促進社會救助和慈善事業在災害救助、貧困救濟、醫療救助、教育救助、扶老助殘和其他公益領域發揮積極作用,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慈善工作,統籌慈善和社會救助兩方面資源,更好地保障和改善困難群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