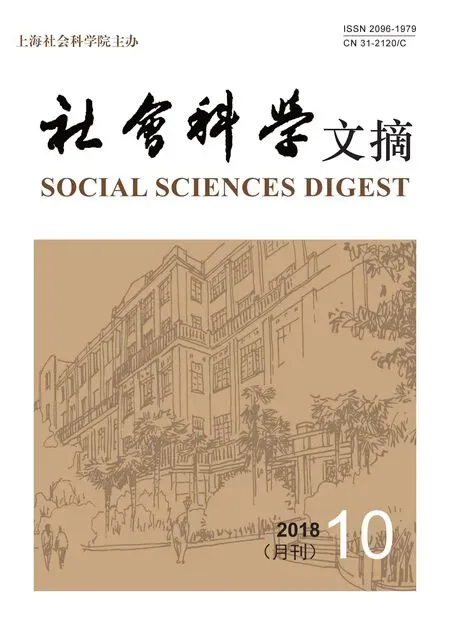關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幾個問題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只有在明確它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之后,才可能對其學術定位作出某種設想或建議。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研究的對象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是指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那些具有批評意識的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學人,針對史學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中所出現的意見、分歧、觀點互相討論、辯難的史學活動、史學現象,稱之為史學批評。史學批評個案的聯系,構成了某一時期或某一時代的史學批評史;不同時代的史學批評史,構成了連續不斷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研究的范圍,從縱向看,上起春秋時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以前);從橫向看,包括各方面學人對史學的批評。涉及的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學科定位應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從宏觀領域來看,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屬于“中國歷史”一級學科范圍;第二,從研究內容與特點來看,可能涉及理論上的分析,因此,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下的一個三級學科。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發展的面貌及其規律的歷史;中國史學批評史是研究中國史學史上存在于其間的一個最活躍的內部動因即批評與反思,包含批評的意識、批評的思想、批評的理論與方法及各方面成果。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發展大勢與主要問題
這里講的“發展大勢”,可劃為七個階段。
第一階段:開端(先秦秦漢時期)。孔子評晉國史官董狐以及孟子評《左傳》和《春秋》,揭開史學批評序幕。司馬談、司馬遷對《春秋》的評論,班彪、班固對司馬遷及《史記》的批評,是最重要的標志。劉向、劉歆校書對各類歷史文獻作出評論,寫出《別錄》和《七略》。荀悅《漢紀》為這一時期史學批評畫上句號。這時期的主要概念和觀念有:良史,書法不隱和史書三要素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論,以及立典五志論(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勛、表賢能)等。
第二階段:初步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于《史記》《漢書》的批評,開這一時期史學批評之先河;《三國志》的批評表明時人對它的關注。史學家們關于“史例”及國史“條例”的討論,推動了史書編撰形式的評論。史書內容和史家修養的各種批評,構成這時期史學批評主要部分。《文心雕龍·史傳》堪稱中國史學批評初步發展階段的標志性成果。這時期的主要概念和觀念是:信史,煩省,評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及由立典五志演變而來的書契五善論(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勛、旌賢能),和注史四旨論(以補其闕、以備異聞、以懲其妄、有所論辯)等。
第三階段:深入發展(隋唐時期)。《隋書·經籍志》史部,是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最早最全面的總結;“史才三長”學說的提出與“良史”觀念發展,增進了人們對史學主體的認識;治學宗旨的討論,凸顯了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史注家的史學批評意識,在《史記》《漢書》《后漢書》注中,均有所發揮。《史通》一書則是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這一時期的主要概念和觀念有:直書、曲筆、鑒識、探賾、疑古、惑經,以及史學功用論、史才三長論(才、學、識)、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論、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論、史官辨職論、編年紀傳論、師古與隨時(稽古與隨時)論、行狀不實論等。
第四階段:興盛(五代兩宋時期)。圍繞兩《唐書》、兩《五代史》修撰、比較而展開的史學批評,受到學人關注,《資治通鑒》直接促進史學批評的發展。綱目體、紀事本末體開始出現。鄭樵、李燾豐富了史學之“通”的觀念。《冊府元龜》國史部總序及各門小序,顯示了類書中蘊含的史學批評思想。《郡齋讀書志·序》體現了目錄學家、文獻學家之學術批評思想積累以至形成的歷程。歐陽修和趙明誠對金石學“考其異同”。類書、目錄書和金石之學中包含的史學批評,是這時期史學批評的幾個特點。宋代學人大量的史料筆記,是這時期史學批評走向興盛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時期的主要概念和觀念有:公正、議論、記注、疏謬、不實、非才、法世、會通,以及信史論、史家源起論、良史“四足”論(明、道、智、文)、紀事本末論、史法論、作史三原則論(事實、褒貶、文采)等。
第五階段:民族史學與史學批評(遼夏金元時期)。中國各民族史學發展遲速不一。這時期史學與史學批評既有中原文化影響,也有各民族的文化基礎。民族史學在史學思想、史學批評意識方面,在針對性和具體表述上存在一定差異,但本質上是一致的。這時期的主要觀念是:“史筆天下之大信”論、“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論、“自古帝王得失興廢,斑斑可考者,以有史”論、“事”與“道”關系論、文獻論、“理”(義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評判標準論、心術為修史之本論等。
第六階段:拓展與前景(明時期)。明代關于前朝正史的修撰與評論,顯示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之連續性。修撰本朝史過程中的評論,既表明對史學認識的深入,也表明存在各種歧見。辯證思維在史學批評領域也有突出的表現。《史通》的研究和評論形成第一個高潮,相關專書的問世,凸顯了批評之批評的活力。這時期的主要概念和觀念有:“人恣”與“蔽真”、“人臆”與“失真”、“人諛”與“溢真”,史權,平心,公議,公實,筆正,歷史評價無是非論,“經史一物”論,“六經皆史”論,評史著四旨(據、實、慎、忠)論,史家修養五要素論(才、學、識、公心、直筆),“務成昔美,毋薄前修”論等。
第七階段:高峰(清時期,1840年前)。這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集大成時期。顧炎武為清代史學批評確定了新起點;章學誠打開人們從史學視角評論經書的思路;浦起龍把《史通》研究推至新高峰。龔自珍“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啟示,可視為對中國古代史學成就最中肯的評論。這時期的概念和觀念有:史德、史釋、釋通、通史家風、別識心裁、記注與撰述、史法與史意、尊史,以及“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論、“史者,垂于來今以作則”論、“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論等。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所提出的有些問題,可能是具有普遍性或規律性的。下面這幾個問題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史學批評產生的原因何在?劉知幾認為:“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是著眼于批評主體而言。又說:“古之述者,或以取舍難分,或以是非相亂。”是著眼于批評客體而言。或許還有更復雜的原因,研究者不能不顧及這些因素。
第二,怎樣看待和分析史學批評主體提出問題的主要根源?如班彪、班固批評司馬遷及其《史記》,唐太宗批評眾家晉史,李大師、李延壽批評南北朝所修三部正史,是什么原因?這些原因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
第三,怎樣看待史學批評的成果及其思想的意義?這是研究者需要運用自身的研究加以說明的。如:《史記》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產生了何等重要作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等等。
第四,怎樣看待史學批評中出現的偏頗?如班彪、班固批評《史記》“是非頗繆于圣人”。劉知幾認為《魏書》“世薄其書,號為‘穢史’”。鄭樵極力貶低斷代為史。葉適批評司馬遷破壞了古之“史法”。吳縝批評《新唐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修書之初,其失有八”等。如有偏頗,則需要把主觀的、客觀的原因都要考察明白。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研究的方法和意義
史學批評史研究應當重視研究的方法和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于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和廣泛的指導意義。我要強調兩點,一是對歷史的基本認識,二是把所研究的問題置于一定的歷史范圍內考察。
關于對歷史的基本認識,恩格斯認為,人類歷史活動第一位是經濟活動,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得以建立和發展,因而也必須從經濟活動去加以解釋。史學工作者應當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從事歷史研究和史學活動。侯外廬先生指出,思想史研究應當以社會史研究為基礎。中國史學批評史研究同樣應當以對社會史的認識為基礎。
把所要研究的對象置于相應的歷史范圍內考察,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原則之一。這個“絕對要求”,就是強調歷史地看待歷史的方法。批評者批評的對象,大多是歷史上的存在;而研究者所研究的批評者,亦是歷史上的存在。對于前一種“歷史上存在”,不能對當時的研究者提出“絕對要求”;對于后一種“歷史上的存在”,研究者應當自覺遵循這一“絕對要求”。這正反映“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的原則。如果離開這一“絕對要求”,結果必然脫離認識歷史真相的路徑。
我們還要借鑒前人提出來的有益方法。如劉知幾重視體例而且善言體例。史學批評史的研究也要重視體例,一是判斷研究對象的體例和體例思想,二是要求我們自身在撰述中遵循既定體例,既要關注局部體例,也要關注局部體例與全局體例的一致性。劉知幾還提倡歷史撰述應堅持辯證思維的方法,在史學批評領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再如章學誠關于知人論世的思想和方法,同樣是值得借鑒的。他認為處在不同時期的人,一般都會有當時的認識和處置的方法。這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同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名家的認識相結合,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及意義就越發清晰和易于理解。
歷史和史學批評的現象都是復雜的。這就要求針對具體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比如:
——對同一批評對象有所肯定,有所否定。如班彪、班固父子評論《史記》,范曄評論《漢書》,肯定與否定都會促進人們對歷史、對史學的深入認識。《史通》和《十七史商榷》在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方面,顯得很突出。劉知幾的“商榷古今”是極可取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記》,在“正史”范圍內進行商榷,給后人留下了許多啟發和許多可以進一步研究、探索的問題。
——對同一批評對象的缺點,作有根據的否定。吳縝《新唐書糾謬》和《五代史纂誤》可視為代表作。不是說這兩部書沒有任何缺點,但吳縝所“糾”之“謬”、所“纂”之“誤”,大多可以成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對比較研究的對象作全面的、辯證的分析。明代王世貞比較國史、野史、家史的長短得失時,客觀地考慮到它們各自產生的條件及特點,并對此作了辯證分析。在史學批評的理論上提出了很有價值的結論。
當然,在史學批評中,也有一些不妥當甚至是錯誤的作法。如:
對進行比較的對象作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的評價。在中國史學史上,有的比較研究者陷于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的境地。如鄭樵對《史記》作絕對的肯定,對《漢書》作絕對的否定,給人留下了不少遺憾。
對同一評論對象從整體上作無根據的全部否定。《魏書》被斥為“穢史”,唐太宗全部否定當時所見十八家晉史,明代學人不滿本朝史學以至于說明朝無史學,等等。
還有必要提到章學誠關于“文辭”的見解。他引用春秋時期子產等人重視文辭而共同努力的典故,說這是“期于至善,不期于矜私”。不能看作是重文辭的表現。在今天看來,這種“集體式”的重視文辭,真正做到了“合眾力而為辭”,同樣是值得稱道的。白壽彝先生對文字表述提出一個總的原則:平實。具體要求是:明白,準確,凝練。一個學術群體,可以嘗試以平實為風格,以明白、準確、凝練為要求,探索一條“合眾力而為辭”的新路徑。
史學批評者的歷史命運及身后影響也是值得關注的。如劉知幾,有人“深重其書”。唐末柳璨則認為:“劉子玄所撰《史通》議駁經史過當。”經過明代學者郭孔延、王惟儉、清代學者浦起龍的撰述,《史通》的學術地位又逐步得到提高。
上述事例表明,史學批評家的“歷史命運”是曲折多變的。但凡有價值的史學批評,終究是站得住的。
探索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學科話語體系的建構
我們要努力探索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為中國史學批評史話語體系的建構作知識上和理論上的積累。
首先,是如何對待中國史學遺產問題。中國史學批評史,其話語體系必建構在中國史學遺產基礎之上。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重視史學遺產的研究,應是中國史學批評史話語體系建構中的第一個層面。
其次,從史學遺產研究中揭示出或提煉出與相關學科密切聯系的概念和觀念,是建構該學科話語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們先人會提出一些概念和觀念,后人可結合自身所處的時代,考察這些概念和觀念是怎樣提出來的,怎樣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狀況和人們的思想面貌。如《左傳》“趙盾弒其君”一事中提出“良史”和“書法不隱”。學者對這兩個概念的認識產生了分歧。只要把這一事件放到它所處的時代加以考察,董狐、趙盾、孔子的言行,都可迎刃而解,這個“刃”就是“禮”。“禮”是當時的社會倫理準則,董狐反駁趙盾是合于“禮”的,孔子贊揚董狐也是合于“禮”的,孔子惋惜趙盾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維護“禮”的。
再次,對史學批評史上有關的概念、觀念作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使之建構成合理的體系。第一,研究和闡述有關概念、觀念提出的社會條件與歷史根源。對于不同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下提出的概念或觀念,自應作同樣的研究和闡述,并關注此概念或觀念與彼概念或觀念的關系,以豐富概念或觀念的體系構成。第二,根據唯物史觀關于人的認識發展規律和基本原理,重點考察中國史學批評史上那些具有某種合理因素的概念、觀念,使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如前述劉知幾引用前人的觀點用以評論史書,包含了樸素辯證思想的觀念。又如杜佑在評論前人的有關爭論時,包含了樸素的歷史主義觀念。
在認識、解說、運用概念和觀念的同時,應當用學科發展的歷史以至于社會發展的歷史加以說明。如“信史”、“實錄”這樣的概念,反映了中國史學求真的優良傳統,但若認為“信史”絕無錯誤,“實錄”絕無不實之處,這就過于絕對了;反之,如若發現“信史”也有錯誤記載、“實錄”也有不妥之處,就認為無“信史”、“實錄”可言,就走向歷史虛無主義了。
關于中國史學批評史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們的認識水平自然也處于起步階段,它的深刻的意義和重要價值,都有待于作進一步的發掘、梳理和闡述。一方面我們在研究中要注意從宏觀把握史學批評的大勢,從中提出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也要重視對于個案的分析判斷。這樣可以使全局同局部相聯系、宏觀與微觀相聯系,庶幾才能寫出一部比較深入的中國史學批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