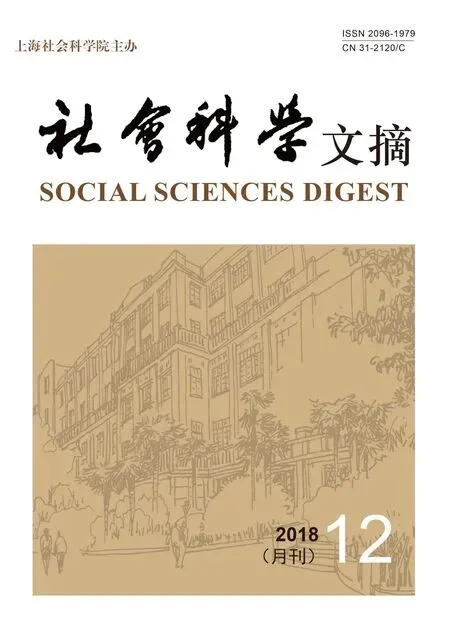中國近代“公益”的觀念生成:概念譜系與結構過程
研究問題與文獻起點
中文“公益”一詞在今天是常見用語,基本表示“公共的利益”,并常與“慈善”連用而呈現“公益慈善”的整體表達。據朱健剛的梳理,當代公益慈善研究主要由三股思潮構成:第一股是以慈善為主題的研究,在中國語境中多理解為慈心善念的驅動,具體表現為好善樂施與好人好事;第二股來自對民間組織的討論,研究對象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以及大量并未注冊或非正式注冊的志愿團體,學界對它們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市場-社會”關系的理論框架以及有關市民社會的種種可能;第三股則是政府建設“和諧社會”的思路,公益慈善既是政策的關注焦點,亦是政策法規的專門用語。
以上三股思潮中,第二股思潮的影響尤為顯著,故相關研究對于中國當代公益的理解也較多地參照西方學界對于“philanthropy”以及“public interest”的界定與闡釋。其中,對公民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的強調與第二股思潮的旨趣彼此呼應,逐漸形成以公益慈善領域探討當代中國公民意識與公共精神的研究脈絡。
與此相應和,歷史學界對于中國傳統慈善向近代公益轉型的研究亦與公共空間、市民社會等術語勾連對接,但基本認為明末以后的中國社會其實并未形成一個歐洲意義上的“公共空間”。那么,中國近代公益在其誕生之初究竟蘊含著怎樣一種新型的公共意味?這一問題始終模糊不清,因為學界對中國歷史語境中的“公益”具體何時出現及其話語構造的現代特性尚未展開充分研究。
目前對于中國近代公益的解釋大體呈兩種路徑。第一種即以當代公益觀念或西方“philanthropy”或“publicinterest”的理解來整合中國歷史上的諸多實踐,于是歷朝歷代皆有例可舉,多指建橋修路、圍堤筑壩、出資教育、賑濟災荒等關涉公共福利之事。但記載這些史實的原始文獻語境其實并未使用“公益”二字,而是多用“義行”“義舉”或“善舉”。
第二種則將“公益”視為中國整體發生近代轉型過程中一個子領域的轉型產物,基本沿用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分界進行論證,故將清末民初視作中國傳統慈善向近代公益轉型的發端,并從中闡發了慈善思想與觀念從“重養輕教”轉向“教養并重”、實踐主體與關懷范圍由富人精英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轉變為普通公民對廣泛社會議題的回應,以及籌款融資方式的多樣更新等“近代”特征。然真正與“公益”二字連用的事物究竟何時出現?它們具體所指何事?上述兩種路徑的研究僅零星涉及。研究者們發現,中文的“公益”概念似乎在20世紀初才開始出現。
如果中文“公益”概念果真自清末這一現代國體開始生成的時段出現并普及,那么“公益”語匯的內部構造必與當時國家話語的建構及其現實基礎有著錯綜復雜的邏輯關聯。因此,本文將從概念譜系與思想觀念的角度入手,嘗試回歸中文“公益”使用普及之初的時代語境,在其概念視野具體化的展開之中,進一步厘清中國“近代公益”的本土脈絡,探索晚清慈善領域內部諸種近代特征之間的結構聯系及其可能揭示的“新型公共意識”之實指。
中國本土的“公益”概念
學界基本認為中國“公益”的概念自日本舶來。劉珊珊的發現則將舶來時間從20世紀初提早到戊戌維新。至于“公益”一詞是否具有本土淵源,僅有一點模糊不清的蛛絲馬跡,讓人難以判斷。筆者進行了專門留意,發現“公益”二字的確在甲午海戰以前就已經連用,并且形成了至少三種主要的語義用法。
(一)經濟收益
第一種是作為金融語匯,表示共同的經濟收益。以目前的資料來看,“公益”二字與表示商行或金融機構的名詞連用大約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如“公益洋行”“公益當鋪”“公益匯利公司”,等等。作為金融語匯的“公益”主要表示集資者或參股人共同的經濟收益。
(二)地方公事
第二種用法主要表達涉足地方公共事務的士紳善舉。在1884年貢生馮驥聲為戶部四川司主事舉人陳尹東所撰寫的一篇墓表中,即有“公益”一詞。墓表歷數陳氏種種地方善舉,既有善待異母兄弟與組織建祠修譜等家族事務,亦有書院講學、贍養友人遺孤、救助貧困鄉親、排解糾紛和立定鄉約等家族之外的地方事務,最后全部歸結為“種種公益之舉”。由此可見,墓表語境中的“公益”之“公”是包含了家族事務在內的地方公事,其實踐主體士紳亦往往具有“族長、地主和道德(知識精英)三重身份”(金觀濤、劉青峰)。因此,這一語義所對接的現實空間,乃是以家族及其精英代表為本位的一種地方公共空間。
(三)國家利益
第三種是作為法律語匯,主要表達國際交往間的國家利益。這一用法始自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翻譯的《萬國公法》。該書譯自美國國際法學家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將惠氏原著與丁氏譯本兩相對照,可知譯文中出現的8次“公益”所對應的英文表達其實各不相同。具體可細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表達國際交往間的常例與習慣;二是表達與私人利益相對的國家利益;三是表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共有利益。由此亦可知,最早與西文進行對譯的“公益”更有可能為中文語匯,而非日語。
中國“公益”語匯的觀念資源
(一)思想觀念中的“公”
既往研究發現,中國的“公”觀念的兩組關鍵雛形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出現。第一組觀念成型于戰國中期,有通眾、普遍、平等、平均之意,經常與“平”連用,指涉范圍極廣,涵納普天之下的萬事萬物,故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經典名句,與表示“自環”“偏也,側面于人,掩匿其奸”的消極之“私”全然對立。第二組觀念源自甲骨文,形似王宮建筑,有祖先、尊長、國君、朝廷之義,春秋晚期以后,逐漸表示朝廷、政府和國家的公務,形成“國家之公”。其中,表達“天下之公”的第一組觀念勢力最強,貫穿整個中國的思想主脈及其在各個時期的不同流變。
(二)民間日常中的“公”
中國本土“公益”中表示“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觀念淵源已經比較清晰。那么,表達“經濟營利”的“公益”將作何解釋呢?溝口雄三曾專門指出,“天下”與“國家”這兩組基本的“公”觀念其實還只是對“士大夫、知識分子頭腦中醞釀和繼承下來的治世觀念、秩序思想”的梳理,它們與民間日常的“公”之間有明顯鴻溝,并不能直接反映“生民”的現實生活。對此,溝口舉了一個例子,即宗族內部的“公業”,但未做出具體解釋。
日本“公”的觀念相對單一,僅有中國“公”系統中的第二種類型,即以王權為中心的國家之公。這種結構性的差異,在溝口看來,直接決定了兩國近代轉型的深層走向。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動立憲,盡管改變了國家權力的構成,但并未從根本上突破其“公”觀念的最大極——國家,而是將王權與國家的關系作了調整。中國的情況與此完全不同,明末以后,“天下”作為“公”觀念的最大極,不僅逐漸壓倒了王權式的國家,還反過來成為賦予現代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資源。換言之,抽象的“天下”觀念需要轉化為具體的“國家”制度。于是,如何重構整套與之相適應的公私關系成為實現這一轉化的邏輯重點,其中個體、國家與地方關系的邏輯關聯與內在張力亦大體統攝了戊戌維新以后中國“公益”語義的重構格局。
戊戌維新以后的“公益”語義
在“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中搜索“公益”一詞,庫內出現的最早記錄是1903年,隨后頻率逐年上升,1908年以后成為高頻用語。此間,清廷主動實施新政,廢除科舉,預備立憲。與此同時,各地起義不斷,革命蓄勢待發,直至辛亥鼎革,帝制結束,可謂“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由此可知,來自日本的“公益”概念與中國“公益”概念的原有格局正是在這劇變的十年之間發生互構并得以普及的。那么,這一時期的“公益”主要表達了哪些內容?
(一)地方公事
首先,前述陳尹東墓表中所列“地方善舉”的語境依然沿用,以表達傳統精英對地方事務的承擔。同一時期,隨著新政施行,各地發起易風俗、興學堂、辦實業、治警察、行征兵以及地方自治等多項舉措,這些內容逐漸成為地方公益的重要組成。表達“地方公益”的語匯成分一方面繼承了原有的語義內容,一方面展現出與清末政治轉型密切相關的新生內涵,且新生部分所論及的公益實踐主體日益多元,既有傳統士紳,亦有志士、留學人士甚至普通鄉民。事實上,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和教育,使之具有權利觀念,明白國家乃“君與己共之”的道理正是新政的核心目標之一。
(二)啟迪民智
在當時,開設閱報社和舉辦演說會是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的常見途徑。1906年,《時事畫報》報道兩廣總督周馥路過江南地區,見到“東西各國報館林立,雖廝養走卒,無不閱報”,故而感到“人人明義務、知公益,而合乎立憲國之資格……”。1907年,四川洪雅縣的楊氏家族創立“公益書社”,開放家藏古今書籍,“任人閱抄,并添購時務書報多種,務期開通智識”。1911年,三位志士欲在京城會友軒茶館組織閱報社,《淺說畫報》稱他們“熱心公益”。與這一系列蓬勃實踐相同步的是當時風行的群學理論,旗手正是梁啟超。1902年,他創辦于日本橫濱的《新民叢報》告白即言:“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
(三)愛國合群
隨著群學理論的流行,強調愛國合群、戒除自私自利的“公益”用法也日漸成為主流。新政時期頒布的《大清光緒新法令》即將“公益學”列為大學堂的修讀科目,并附有專門解釋:“日本名為社會學,近人譯作群學,專講公共利益之禮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1903年,鄭貫公等人在香港創辦《世界公益報》,專門說明“本報為國民代表,乃社會之公器,而非一家之私言”。時人亦開始撰文討論究竟什么樣的實踐可以稱為“公益”。
(四)地方自治
與新民的塑造同步,培養民眾參與實際治理的政治實踐也自戊戌時期開始興起。成立于1898年2月的湖南保衛局和南學會可謂中國近代最早的地方自治組織。1903年,攻法子撰文闡發“欲養人民奉公之念,莫如使之從事于公共事務,使人民無(此處疑應為“有”——作者注)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則不至人人依賴國家,謀一己之私利而不顧國家之公益”的道理,明確指出自治乃“代議政治之基礎”。隨后,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孫中山等人亦紛紛撰文論述自治與憲政之關系,認為“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1906年,端方、劉直等人將地方自治作為預備立憲之基礎提上新政議程。同年,一些以“公益”冠名的自治團體開始出現。1908年底,清廷仿效日本《市町村志》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明確提出,“地方自治以專辦地方公益事宜,輔佐官治為主”。章程所列“地方公益事宜”包括本城鄉鎮之學務、衛生、道路工程、農工商務以及各種善舉,“公益”遂成為自治語境中的高頻用詞,同時引發了有關民間公益與自治公所管轄范圍的討論。這說明新政部門與民間公益團體的角色正在發生重疊,亦表明中國近代公益的開端即包含了地方共治的深刻意涵。
(五)鐵路利權
甲午以后,日本被允許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歐美列強“利益均沾”,亦先后在華修筑鐵路,開采礦山,展開利權爭奪,掀起瓜分狂潮。清廷雖意識到筑路之重要,卻苦于資金短缺,商界無力,只得借款筑路。1897年1月,清廷在上海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專門負責借貸洋款筑路。1898年8月,清廷成立礦務鐵路總局,改變思路,鼓勵鐵路商辦,但僅過一月,又會同總理衙門宣布鐵路建設由中央統籌規劃。反復之中,中國路權幾乎喪失殆盡,激起舉國公憤,收回利權運動遂于各地相繼爆發。自此,各省商辦鐵路公司次第成立,籌款宣傳之中,表示國家利益的“公益”成為高頻用語。鐵路語境中的“公益”經常游走在具體的地方利益與抽象的群體利益之間。
(六)經濟收益
最后一種“公益”沿用前述的金融語義,表達共同的經濟收益。此外,正如表達“地方公事”的語義在延續原有內容的同時還衍生出與清季十年政治轉型密切相關的新內容,“公益”的經濟語義也發生了相似的重構。1908年底,清廷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繳納“公益捐”者可以成為選民。自《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出臺后,“公益捐”作為地方自治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開始頻繁地出現在政府公牘與法律文書之中,一直沿用至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
結語與討論
本文從概念與思想的角度入手,爬梳中文中“公益”的語源流變以及與此同步的觀念再造和社會現實,從中形成如下三點主要發現和研究啟示:
其一,中國近代“公益”觀念實則是嵌入在明清之際公私問題與群己關系不斷重構這一漫長過程中的一項子過程。因此,它的具體生成涉及長時段的思想變動以及復雜多次的跨國互動,并非簡單地藉由維新風潮舶自日本。
其二,清末新生“公益”語義的現代特質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國家利益”被賦予了支持政體轉型的群學理論與變革實踐,另一方面亦承載了這一轉型過程中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實際張力。在此過程中,國家力量與地方勢力之間錯綜復雜的動態關系及其對“公”資源的爭奪,直接導致了新生“公益”語義呈現出趨向“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兩個走向。
其三,如果以中文“公益”的近代使用和普及時段作為理解傳統慈善轉向近代公益的一個面向,那么戊戌以來的維新人士以及后來擴大到各種身份的“志士”乃至商人、平民和女性基于公民意識而開展的非營利實踐,可謂中國近代公益的開端。這些個體盡管身份各異,甚至懷有不盡相同的政治主張,但他們所共享的群學理念其實極大地貫通了社會公眾與國家政府的共同利益。當時的“公益學”也因而等同于“群學”或“社會學”,既為“天下”向“國家”的轉化提供最為實用的“公”之資源,亦為培養現代制度的基層土壤提供學理依據。從這個意義上看,陳若水所言晚清“公益”所帶動的“新型公共意識”,之所以“新”便在于其對現代國體的明確意識與推動轉型的切實努力,但同時也包含了某種社會與國家的局部同構。這一同構在何種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國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脈絡中的歷史養成,或能為今天探討公益慈善與公共精神提供一種關注本土內生屬性的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