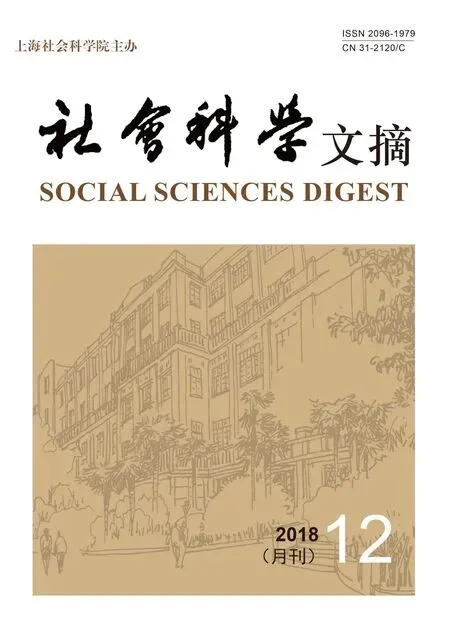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企業的退出與進入:政府與市場的作用
引言
合理有序的調控企業進入與退出是產業結構領域最為重要的話題之一。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著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大量僵尸企業尚未退出、新興產業供給不足、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升級的局面,經濟和產業發展更需注重質量。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判斷一針見血:“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習近平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對經濟增長有重要貢獻,目前產業的適度規模和退出機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產能過剩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為什么長期存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失靈和體制扭曲導致。2018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去產能的制度梗阻”,可以看到中央就產能過剩問題的治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許多文獻從不同視角分析了產能過剩的原因,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還有一些文獻測度了產能過剩程度。盡管從現實來看,產能過剩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行業層面以上的宏觀現象,但它歸根到底仍源于企業決策。產能過剩一直處于“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市場長效機制的缺乏,過往研究沒有給出理論化且可操作的企業退出的微觀機理,并缺少對產業政策進行評估的機制。那么在新常態下,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培育新興產業從而順利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關鍵是要從供給側的視角解決政府與市場協調的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更多地協同考量市場的作用,并且對政策的精準性及評估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較少有文獻能從理論上給出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協同作用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而這種混合機制下的理論框架和數值分析是保證宏觀經濟要穩、產業政策要準的重要議題。
在產業發展方面,政府與市場應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例如,張維迎主張廢棄所有產業政策,而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認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僅需要政府通過自身的改革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還要求政府在該新格局中更好地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中強調,“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大量國內外文獻分別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對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模式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的研究。Dixit(1989基于實物期權理論,討論了完全競爭情形,即市場中企業數量時,企業最優的進入與退出閾值,然而沒有考慮其它類型的市場結構。無論是完全競爭,還是寡頭或壟斷市場,都無法涵蓋所有市場類型,并且不一定符合市場的真實情況。Pindyck(2009)研究了在企業數量n較小時,沉沒成本及不同類別的風險如何影響企業的進入決策。然而,這些研究沒有討論企業數量n較小時,企業最優的退出策略,并且沒有文獻探討中國特有的體制扭曲與市場不確定性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導致企業過度進入和產能擴張的不合理性。現有文獻缺乏一個能夠指導新常態下緩和體制扭曲與市場失靈,特別是考慮企業有效退出的理論模型,無法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最為直接且有效的指導。
還有許多國內外文獻探討了產業結構中企業的投資或生產規模行為。其中,一些文獻從一定數量的企業面臨競爭和需求不確定的情形出發,探討了企業逐步增加投資的均衡策略,以及產業演化過程。上述文獻主要針對企業層面的最優產能,然而,對企業產量的過度限定或干預并不能解決我國產能過剩及僵尸企業的問題,機械式的行政命令無法發揮企業的能動性,甚至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針對企業的最優化決策,從企業數量角度出發,旨在研究政府和市場如何更有效地引導過剩產能退出和新興產業進入,這將更有實際指導意義。
基準模型
借鑒Pindyck(2009)和Bustamante & Donangelo(2017)的分析框架,通過允許企業退出,本文構建了一個基于期權博弈理論的市場動態均衡模型。企業可以通過支付一定的沉沒成本進入市場,而當市場條件變差時,企業也可付出相應成本實現退出。不失一般性,假設市場中的企業可以生產任意產量的同質產品,并服從古諾競爭。市場需求是隨機波動的,我們把它看作市場風險。而市場中每家企業也同時面臨著特質風險,即每家企業的固定成本是隨機的,并且也都面臨突然倒閉破產的風險。因而,企業退出與進入策略、市場中企業的數量以及市場均衡在很大程度上由退出與進入成本和不同類別風險決定。隨后,運用期權博弈理論,求解出在小n和大n兩種情形下,達到均衡時企業最優的退出與進入策略。
通過模型求解可知,企業的退出與進入策略主要與σ(市場風險)、λ(企業淘汰率)、E(退出成本)、S(進入成本)、n(企業數量)等因素有關。其中,退出閾值與退出成本E負相關,而進入閾值與進入成本S正相關,并且隨著企業數量n的增加,退出與進入閾值逐漸收斂于完全競爭時的情形。由于這兩種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響(如補貼等政策),因而本文把退出與進入成本視為政府因素。另外影響企業退出與進入的因素是市場風險及企業的特質風險,這兩類風險是市場結構中的基礎要素,本文把這兩類風險看作市場因素。
政府與市場如何影響企業退出與進入的閾值
隨后本文深入探討市場因素和政府因素如何影響企業的退出與進入。首先,簡要分析閾值、產業發展過程及企業價值。從市場中企業數量n與退出和進入閾值的關系可知,隨著企業數量n的增加,其退出和進入閾值逐漸收斂于n足夠大時的情形。當市場中企業數量n越大時,企業的退出與進入所需要的條件越低,速度也越快。而企業數量n較小時,退出與進入所需的條件較高,速度也相對較慢。
其次,我們給出市場因素與政府因素對閾值的敏感性分析。市場風險σ的增加,加劇了企業退出及進入的難度。因而當市場無法起到有效調節作用,或市場劇烈波動時,政府可以通過給予市場較穩定的預期或采取價格限定等手段來調節市場風險σ,其目的在于減少企業退出或進入市場期權的等待價值。行業中企業淘汰率λ也代表著市場因素,不同行業的λ會由其行業特質決定。在扶持新興產業時,政府可成立產業基金充當“孵化器”的作用以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并在企業財務危機時為其擔保、背書,通過相應政策降低該行業的淘汰率。而在引導過剩產能退出方面,對還未退出的僵尸企業,政府應采取向其減少“輸血”力度和銀行貸款等手段,以加速其退出市場。企業的退出成本E和進入成本S,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影響。退出成本E的增加(即退出“補償”減小)加劇了企業退出的難度。我國當前面臨著產能過剩嚴重,大量僵尸企業尚未退出的情形,因而政府應降低相應行業的退出成本,如完善企業退出機制、保障職工安置等,從而實現提升效率、優化產業結構的目的。進入成本S的增加提高了進入閾值,從而加劇了企業進入的難度。我國當前同樣存在著戰略性新興企業不足,產業結構有待優化的現象,因而政府應降低新興產業的進入成本,例如對新興企業給予財政補貼或專項資金支持,完善行政審批制度,降低其融資門檻、貸款利率和稅率。
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對于企業退出與進入成本的調控范圍有限,且成本很高,單靠該手段無法有效地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升級。尤其是在某些極端條件或市場失靈的情形下,如市場風險σ很大時,此時市場的劇烈波動會加劇企業退出以及進入的難度。此時政府可以一方面從退出及進入成本的角度著手調控,另一方面,可以從調節市場風險σ或企業淘汰率λ的視角出發,給予市場較穩定的預期或救助危機中的企業,從而實現“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互補充、協調與促進,以達到目的。而通過市場風險或企業淘汰率的手段來調整產業結構,成本可能會更低。因而在特定情況下,政府應該在深刻理解企業決策機制的基礎上,結合各種調控手段,穩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轉型中產業結構的調整。
最后,本文簡要討論市場風險σ及企業淘汰率λ對退出與進入成本的“放大”效應。通過數值模擬可以看到,市場風險σ的增加,加劇了企業退出與進入的難度,等同于放大了相應的退出與進入成本。而企業的淘汰率也會放大企業進入的成本,并加速企業退出市場。
產業發展、市場摩擦與政策內生機制
新常態下要保證宏觀經濟穩、產業政策準,就必須對不同政策下產業的發展過程進行定量化的分析,并刻畫出產業的演化路徑,這是目前國內產業政策研究急需解決的重要議題。在我國,當前許多產業政策存在著“朝令夕改”“急功近利”等情況,然而現實中,每一條政策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達到相應效果。首先,給定市場條件(如當前市場中有m家企業),來討論產業中有n家企業平均所需要的時間,以及一定時間T以后市場中企業數量的期望值。
緊接著,在理想條件下的市場動態均衡的基礎上引入市場摩擦。在本文,我們認為市場摩擦主要有以下兩類:第一,市場中存在信息不完全,如政府擁有的信息更加準確、完全,或掌握信息的方差更小;第二,假設政府站在更宏觀、更有戰略性的角度對某特定市場心中有其理想的企業數量或產量,若企業根據市場情形做最優化決策所達到的均衡與政府心中理想的狀態有所出入,形成摩擦。本文分別以信息不完全和政府目標與企業最優化決策不一致時的摩擦為例,簡要說明市場摩擦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并簡述了其引起的無效率問題。
最后,基于產業演化路徑來考察產業政策的內生機制,并給出政府與市場作用的對比。本文的理論框架緊抓企業的最優化決策和路徑,由于存在市場摩擦,我們通過政企博弈思想將產業政策內生化。具體來說市場動態均衡的結果可以看作政府與企業博弈的結果。政府進行總量控制,即政府給出政策或行動,企業是政策的接受者。企業觀測或預測到市場情形后,進行最優化的生產以及退出或進入策略從而達到均衡,該均衡下的企業加總數量、產量或價格等行為與政府政策相博弈。若市場的動態均衡與理想情形或政府目標有差異,政府通過干預手段不斷調整,不斷逼近和達到新的均衡。至于對政府具體內生決策的求解,可以借助蒙特卡羅模擬來反推。
隨后本文給出一個過剩產能退出(以煉鋼企業為例)和新興企業進入(環保儀器企業為例)的例子,通過產業演化路徑的數值模擬來對比政府在調節市場因素(市場風險σ和企業淘汰率λ)與政府因素(退出成本E和進入成本S)的效果,并借此簡要闡述產業政策的內生求解思路。兩個例子展示了不同政策下產業的發展和演化過程,這有利于政府在不同條件下對產業政策做出直觀和定量的判斷,并選擇最有效的手段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同時也可以依據上述思路,來解決產業政策的內生化問題,即通過蒙特卡羅模擬反推具體政策。恰當的產業政策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特定情形下,如市場劇烈波動或市場失靈時,政府應考慮適當調節市場因素,如市場風險或淘汰率。由于產業發展是長期動態的過程,產業政策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在多數情形下政府應該采取聯合措施同時調控以上幾個方面,以實現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結論、政策含義與貢獻
本文基于期權博弈理論,探討了政府與市場在企業的退出與進入、市場均衡及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兩者協同影響以及產業政策的內生機制。本文給出了從壟斷到完全競爭等一系列不同市場結構下,企業退出與進入市場的閾值,從而得到了包含退出與進入、小n和大n情形的完整市場均衡、產業發展模式。根據理論模型得出以下主要結論:第一,市場風險的增加,會加劇企業退出與進入的難度;第二,本文比較了市場因素與政府因素對企業退出與進入的效果,并具體計算出不同類別風險對于退出與進入成本的“放大”作用;第三,產業政策應該根據市場情形相應制定,當市場風險較大時,政府通過調節市場風險更為有效,尤其在短期,而在長期,調節退出與進入成本以及企業淘汰率相對更加有效;第四,本文給出了特定條件下,產業政策所需的時間、產生的效果、產業演化過程和政策的內生化機制,這為政府提供了直觀且定量化地評估產業政策的工具,從而回答了產業政策如何精準的問題,本文的結論對當前如何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在當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以上結論對于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化解產能過剩、引導僵尸企業退出以及培育新興產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府應深刻了解企業決策機制,明確自身的定位,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更多的需要協同考量市場作用,實現“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具體來說,第一,政府應該有效降低過剩產能的退出成本,以及新興產業的進入成本,引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第二,適度運用調節市場風險的方法,以達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例如,當市場風險波動較大或者市場失靈時,要適度穩定市場預期;第三,減小對僵尸企業的“輸血”力度,而當新興產業遇到危機,應該“出手相助”,有效降低新興產業的淘汰率,起到新興產業“孵化器”的作用;第四,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要有效評判該政策定量化的效果、產業演化路徑,并給予充分時間,避免“朝令夕改”或“急功近利”的情況;第五,充分了解政府與市場在市場均衡、產業發展中的定位和協同作用,合理利用市場機制更為有效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本文的貢獻及創新之處體現在三方面。首先,基于期權博弈理論,本文完善了企業數量較小的情況下,企業最優的退出策略,從而得到了包含退出與進入、小與大的完整市場均衡、產業發展的統一理論框架,這是對現有理論研究的擴展。其次,本文從供給側的視角探討了政府與市場在引導落后產能退出和新興產業進入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協同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根據市場情形制定有效的政策,從而給出了理論化且可操作的企業退出與進入的微觀機制,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可行的思路。最后,本文考察了特定條件下,產業政策所需的時間、效果、產業演化過程及政策內生化的機制,這為政府提供了直觀且定量化地評估產業政策的工具,回答了產業政策要準的問題,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