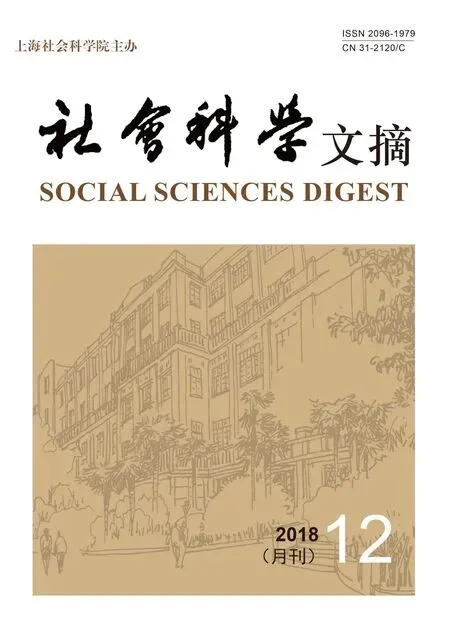論田野哲學的興起
——兼與張衛博士商榷
田野哲學興起的背景
張衛博士在《哲學在行動:當代美國“田野哲學”的崛起》一文(以下簡稱“張文”)中認為,“‘田野哲學’的興起與美國當今社會‘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與盛行有關”,“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語境下……‘田野哲學’即在此種語境下應運而生”。但本文認為,田野哲學興起的背景并非“新自由主義時代語境”,而是西方哲學危機的加劇。
(一)學科哲學與哲學的危機
當代西方哲學被看作是在學院存在的、僅僅與其他學科并列的一門學科,“如果哲學想在學院占有一席安全之地,它就需要有自己的獨立領域、自己的專業語言、自己的成功標準、自己的信息傳遞者和自己的專業化問題”。哲學愈發想在學院尋得安全,就愈發需要變得“獨立”、“專業”,愈發需要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專屬于“自己的”更加系統、獨特的學科特性。這是一個不斷深化的“學科化”的過程。當哲學學科化到形成“排他性的單一文化”時,就把自己完全限定在學科(或學院)的高墻深院之內,把自己完全與高墻之外的其他學科和生活世界隔離開來。這樣,哲學就純粹成了一種哲學同行們用特定的行話術語(通常是晦澀難懂的)為彼此或自己寫作的內部游戲。至此,哲學完全成了“學科的俘虜”(disciplinarycapture),哲學就只是學科哲學。
學科哲學,亦即當代西方哲學的這種內部游戲,由于其排他性的單一文化,而使其過度專業化和職業化。過度職業化的結果,可以借用梭羅的話來描述:“如今有許多哲學教授,但沒有哲學家。”過度專業化的結果,可以借用奎因的話來描述:“說到有機化學,我承認它很重要,但我對它沒有興趣,就像我不明白為什么哲學外行們應該要對我關注的哲學問題感興趣一樣。”過度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哲學只在學院存在,哲學家作為學科專家也只在學院活動。在哲學家曾經活動的生活場所再也不見哲學家的身影。這表明哲學脫離了日常生活,喪失了關注、批判現實世界的能力,更遑論改造世界了——哲學已經背離了它的本性,這造成了當代西方哲學的危機。
說當代西方哲學正在經歷的危機是學科哲學的危機,并不是說“學科哲學”本身就是危機,而是說學科哲學的排他性的單一文化造成了西方哲學的危機。當西方哲學經由學科化而成為學科的俘虜時,當西方哲學只是學科哲學時,西方哲學就背離了其本性和根本任務,就產生了危機。
(二)新自由主義時代與哲學危機的加劇
西方哲學的學科化仍在持續,它排他性的單一文化也仍在蔓延。在今天彌漫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西方社會,學科哲學的命運如何?
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由追求真理轉變為追求利潤,大學由學術自由主義轉變為學術資本主義。而且,大學形成了一種以結果為導向的“不發表,就出局”的研究審計文化,出版物成了“資本”的等價物,大學教師為達到預設的“目標”或“關鍵業績指標”。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淪為邊緣學科的哲學和人文學科出現了知識生產過剩現象,從而造成了一種學科繁榮的幻相。絕大多數哲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術出版物無人問津,更別說要產生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了。今天的哲學家已經背離了蘇格拉底賦予“哲學家”的“牛虻”的社會角色。
對這種知識生產過剩現象,政府和社會用新自由主義賦予的經濟理性思維方式(如成本/收益分析)去考量哲學的投入和產出——一如考量自然科學那樣。雖然哲學以“學科”的形式把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了,但外界(政府和社會)卻對哲學學科做出了反應:大幅減少資助、選擇不報考、嚴格控制教工數量等。然而,高校的哲學院系、學科哲學家們是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各種財政資助和學生的學費得以維持的。所以,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學科哲學模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哲學的知識生產過剩這種學科繁榮的幻相,其實是對哲學危機的一種遮蔽。哲學學科從知識生產過剩,到資助銳減、招生和學位授予數量下降、教工數量減少等的事實,反映了學科哲學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艱難境遇,也凸顯、加劇了西方哲學的危機。如果學科哲學繼續躲在高墻深院里玩與生活世界無關的內部游戲,繼續無視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要求,那么,長此以往,學科哲學便會終結。
面對西方哲學的危機及其加劇,美國學者羅伯特·弗洛德曼(Frodem an R.)、亞當·布瑞格爾(Briggle A.)等認為,哲學需要沖破學科化枷鎖,從學科的俘虜中解放出來,需要走向田野,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哲學家需要在書房和圖書館之外的場所工作,需要與科學家、工程師、政策制定者、公共機構及社區人群一起在項目層面上做哲學,需要在學科外的世界通過對社會需要的回應而增加工作價值。
田野哲學的內涵
張文認為,“‘田野哲學’是美國近來興起的一種從事哲學研究的新理念”,是“元哲學理論”。本文認為,“田野哲學”是一種從事哲學的新理念,但它更是一種哲學實踐。田野哲學充滿了濃厚的實踐性。田野哲學的內涵,需要從“規定性”和“機制”兩方面去把握。
(一)規定性
第一,定位。田野哲學的定位,是哲學家以盡可能開放的態度,從哲學維度參與現實的社會問題,從而充當“溝通學院哲學和無形的、不斷發展的技術化‘文人共和國’的橋梁”。弗洛德曼和布瑞格爾給“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用“技術化的‘文人共和國’”指代當代西方社會生產知識的校外場所,其邊界是可滲透的和不斷變化的。對于田野哲學家,確定某種理論、進行學術爭論或探求矛盾和意義是他們可能要做的,但他們必須要做的是介入具體的決策過程。哲學家保持開放的心態,把自己的視野不要限定在哲學學科內,積極應用哲學知識,運用哲學思維,通過發現、挖掘、闡明、討論和評估等方式去參與處理社會實際問題。這就是哲學家走出“學科”的高墻深院,走向“田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田野哲學家需要在學院哲學積累的哲學智慧、知識和技能,另一方面,田野哲學家要積極介入到技術化的文人共和國所關注、研究的社會問題中去,比如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全球化、新媒體以及人類基因組重塑的可能性等,所以,田野哲學充當著溝通學院哲學和技術化文人共和國的橋梁。如是,哲學便逃離了學科的俘虜,哲學也就不只是學科哲學,還包括非學科哲學,即田野哲學。
第二,研究方式。田野哲學主張包括跨學科、交叉學科、超學科,以及哲學學科在內的“多學科”或“后學科”的研究方式。“田野”就是多學科、后學科的實踐及作用的地方。田野哲學應用“跨學科”的、“交叉學科”的或“超學科”的研究方式,其實就是在“去學科化”。可見,田野哲學是在“破”“學科化”。另外,田野哲學要通過“破”“學科化”去“立”某些東西,但要“立”的東西并非“跨學科”。“跨學科”只是田野哲學所憑借的研究方式之一,是手段,并非目的。
第三,受眾。田野哲學的受眾由各種非哲學家群體構成。田野哲學家并非“公知”,而是從事具體社會實踐活動的“實干家”。“受眾”一詞能表明田野哲學實踐的多樣性:田野哲學家們不只是為非哲學家群體而“說”,還為其而“寫”、而“做”。更重要的是,“田野哲學家與非哲學家們共同合作生產知識”。與田野哲學家們共同合作的非哲學家們主要指“面對現實生活問題的非學科利益相關者”,雙方共同合作生產的知識“在使用的語境中產生”。
第四,制度配置。“田野哲學”作為一種新事物,目前還不具有成型的制度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去學科化哲學,田野哲學的制度配置不是現有的學院體系,或著說,不是學院體系的現有狀態。田野哲學的倡導者們認為,田野哲學“駐留在現有機構的邊緣,穿梭于學院和更廣闊的世界之間;但也在學術界和不同的實踐社區尋求自身的制度化”,“應該包括反思自身的制度現狀,確保有適當的標準和程序在適當的地方去評估非學科實踐”。這是對田野哲學的制度配置的大致構想。
第五,評價。由于田野哲學是“去學科化”的,所以,評價田野哲學的標準不能與評價學科哲學的標準完全相同,即不能完全靠傳統的文獻計量學來衡量。在整體上,學科哲學的標準是哲學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而田野哲學的標準是哲學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田野哲學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一種繼承。田野哲學家倡導一種由受眾定義的非學科指標方法——替代計量學。
(二)機制
田野哲學是在“中觀”維度運行的,即田野哲學家在項目層面上進行哲學實踐。田野哲學家的工作從非哲學行動者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開始,為問題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從哲學視角提供一種公正、文明的對話模式,尋求做出具有時效性的、根據多學科的標準而被認為是成功的貢獻。最初,“問題”是什么,其解決辦法是什么,都是由非哲學行動者界定的。哲學家會對此再進行周全的慎思,并與非哲學行動者就此進行進一步交流,以促成、推動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最終協商解決問題。在交流、對話中,哲學家通過鼓動、提示、追問、啟發和建議等精神助產方式,使利益相關者提出他們自己對問題的答案。哲學家不提供答案,提供答案的是專家和科學家。當然,哲學家有時候也提供答案,“但這應該服務于哲學的質疑功能”。這是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生成而非既成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哲學家的智慧、激情、技能與社會的需要相重疊,最終也會產生社會影響。在結束了一個田野哲學項目之后,田野哲學家會回到學院充電,準備開啟下一個項目。田野哲學家通過這樣的哲學實踐而確證自己的存在,同時也擴大了學院哲學的領域。
田野哲學是要“破”哲學的“學科化”,并不是要否定學科哲學。相反,田野哲學家們“堅決支持理論哲學、學科哲學”。田野哲學家參與解決項目問題的智慧、知識和技能主要來自學科哲學。他們在田野與書房之間、實際與理論之間、實踐與思想之間、實踐智慧與理論智慧之間無限地辯證循環。這是田野哲學家與學科哲學家、哲學家官僚的本質區別。“哲學家官僚”這個術語,是弗洛德曼和布瑞格爾受“哲學王”的啟發而創制的,指“雖然受過哲學教育,但卻離開了學院,永久工作在公共或私營部門”,且“致力于制度層面的哲學家”。他們認為,21世紀西方哲學的生態系統應該由三種不同類型的哲學家——學科哲學家、田野哲學家和哲學家官僚共同構成。這比當前學科哲學排他性的單一文化更健全和富有彈性。
對田野哲學的評價
張文認為,田野哲學的價值在于:“它是對古希臘哲學中蘇格拉底傳統和中國哲學中實踐精神的回歸,是對西方‘為學術而學術’傳統的超越。”本文認為該評價不夠中肯,田野哲學應享有下述兩份“殊榮”。
(一)田野哲學為哲學實踐爭取與學科哲學相同的地位
田野哲學不僅注重實踐,更注重田野哲學家們以何種形式進行實踐。個體形式的哲學實踐活動相對于學院體系來說是“例外”而非“例子”。田野哲學要在組織層面以哲學組織機構普遍、正式認可的形式運行。
哲學實踐早已有之,但真正意識到哲學實踐的制度配置問題,并努力進行制度化的,是田野哲學。“目前的情況是,非正統的實踐者(這是他們的自我認定)處于邊緣化,過著格格不入的職業化生活。”這里,“非正統的實踐者”指沒有制度歸屬的哲學實踐者。田野哲學倡導進行組織層面的哲學實踐,是要把田野哲學和田野哲學家從制度上納入學院哲學之中,從而獲得與學科哲學一樣的“正統”地位。
田野哲學的制度化是一項十分復雜且艱巨的任務,因為哲學的制度化“關系到哲學家的所有方面:如何寫、為誰寫,何為‘真正’的哲學工作;吸引什么樣的學生,如何培養他們;雇用誰,誰晉升為終身教職等”。在具體操作層面,大學現有的學科哲學的“學院”體系需要做出改變。從課程設置、學生培養目標設定,到教師工作考評辦法、終身職位晉升標準等,都需要改變。而且,這種改變需要在社會系統內發生。
在組織層面進行哲學實踐,積極追求哲學實踐的制度化,是田野哲學區別于其他一切類型哲學實踐的本質特征。田野哲學家要在組織層面進行哲學實踐,就如同學科哲學家在組織層面進行哲學研究那樣。田野哲學要把那些一次性的、個體的哲學實踐者,或者進行一系列一次性的哲學實踐的哲學家,通過制度化升級為穩定的、成熟的、富有更大影響力的哲學實踐共同體,要為哲學實踐建立穩定的制度文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田野哲學為哲學實踐爭取與學科哲學相同的地位。
(二)田野哲學為哲學在商業社會里尋找光明的未來
學科哲學宅在哲學院的高墻大院內,靠滲透(rickledown)模式或機緣巧合(serendipity)模式,等待哲學的學術價值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產生社會影響,或者等待社會組織、個人等“有緣”者自行、自由提取需要的學術成果,從而把其內含的學術價值轉化為社會影響。“影響從來不是有意要產生的,但它們總會產生。”于是,哲學便是“無用之大用”。田野哲學則不以為然。田野哲學家必須走向田野,在社會中積極搜尋、發現機會,并通過哲學實踐的方式,主動把學術價值轉化為社會影響。田野哲學家不僅要掌握、了解哲學知識及其學術價值,還要掌握如何實施和調配這些價值。如此,哲學便“有用”。
田野哲學更注重社會影響而非學術價值。它所注重的社會影響被稱為“更廣泛的影響”(Broader Impacts)。田野哲學家認為“更廣泛的影響”是“運用在學術價值方面所發揮的創造力,去闡明和確定研究結果對社會帶來好處和對實現不斷增加的社會需求的可能性”。田野哲學家所進行的田野哲學實踐項目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哲學項目”。在項目結束后,田野哲學家可能沒有發表一篇同行評議的學術論文。但沒有關系,田野哲學實踐項目的“結項”并不以學科同行的評議為準,而是以“更廣泛的同行”所受到的影響為準。在學術期刊發表同行評議的學術論文并不是評判田野哲學家工作的唯一甚至最重要的標準。田野哲學家的廣闊天地在田野,在田野他們會大有作為,會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更確切地講,田野哲學注重的是“更廣泛的影響”中的“好影響”。田野哲學家認為,許多研究、實踐所產生的影響在結果上都不全是好的,往往具有混合性。因此,他們認為“問責文化、更廣泛的影響制度或負責任創新都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什么是進步,即,什么是好的影響。”田野哲學家考量“好的影響”,并不是以某個利益集團或組織的利益為中心,而是盡可能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中心。田野哲學注重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中的好影響,這說明田野哲學注重社會的“需求側”,體現了田野哲學家更注重社會責任。這是在積極回應國家和社會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對哲學、哲學家的希望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田野哲學為哲學在商業社會里尋找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