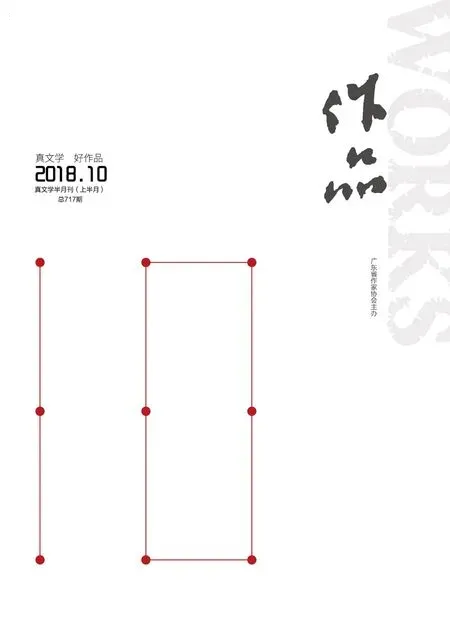一半陰影一半明亮
文 /小 乙
1
李大祥剛拐進石頭巷,街坊鄰居馬上認出他來。但沒人大呼小叫大驚小怪,反而都克制且友善地喚他,老李,精神不錯,真心替你高興哩;大祥,你兒子沒跟你一塊來?哦,在外地忙工程,搞勞務分包。好好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吶……眾人跟他家長里短地寒暄著,巷子一下熱鬧起來。四月春深,墻頭的幾叢三角梅開得繁花似火。老李一路回應,握手道謝,淚水好幾次要滾出來,又硬生生壓回去。他不問也知道,自己的事兒早在鎮上傳開了。
到了巷尾口,兩側各一間老瓦房,跟蒼老的動物一樣,靜默對立。夕陽從遠處斜照過來,滑下屋檐,投在青石板上,形成一半陰影一半明亮。陰影這邊是自己家,明亮那頭是陳老太的家。李大祥在分界線駐足,身影如同陰影的觸角,無聲地探到陳老太家的大門上。透過門縫,他瞧見從亮瓦射下來的光,像凌亂的雪花在飄。站了一會兒,老李聽到有拐杖聲傳出來。篤篤篤,篤篤篤,像鈍刀在案板上切菜。陳老太!老李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兒上。少頃,響動沒了。忽然門啪一聲關回去,耳光一樣打在他臉上。
半晌,老李回過神,心里冷哼一聲,開門進了自家屋。一抬頭,瞧見墻上的佛龕,閃動出一兩抹亮光。老李跪下來,不停地叩頭,眼睛一下濕潤了。
在失去自由的八年多里,老李經歷了四次定罪,三次重審。他跟圣斗士一樣,和兒子“里應外合”,不屈不撓地堅持申訴。出了獄,兒子把他接到縣城的新家住。接受過一次采訪后,他從此閉門謝客。遇上好天氣,就到公園逛逛,或者去影院看熱播片,甚至進酒吧聽音樂。他想,我現在清白了,愿意怎么過就怎么過。話雖這樣說,但賠償申請還在走司法程序,他已經閑不住了。老李以前開推拿店,現在決定回老家,重操舊業。
老李的推拿店,是用客堂改裝而成的,一個半月后萬事俱備。那段時間,他忙里忙外跑上跑下,免不了瞧見陳老太。老李掐指一算,她六十七了。這樣的老太,身板沒那么直了,慢性支氣管炎也更厲害了,經常走著走著,面朝泥墻,又咳又喘,好一會兒才緩過勁來。最大的變化,是她胖了不少。脖子上的筋拉著肉皮,水流一樣往下淌。老李猜測,這多半是她長年吃激素藥造成的。
而陳老太每次碰到他,臉上立刻呈現出青苔的陰性,瞪起巨卵般的眼睛,直直往前走。老李不卑不亢,不躲她也不惹她。倒是陳老太的孫子豆豆,每天放學回家,都要朝他店里瞧一瞧。大腦袋,小骨架,校服套在身子上,跟套在衣架上一樣空蕩蕩的。但他眼亮,眨巴時瞳孔里跳閃著光。店子開張那天,老李喚住他問,豆豆,讀幾年級了?豆豆說,三年級。聲音脆脆的,卻很怯生。老李抬抬下頜,招手道,進來玩嗎?豆豆走到門口,止步了。他歪著腦袋往里瞄了瞄,我阿婆說,里面有大毒蛇,是真的?老李沉默了幾秒,笑瞇瞇地說,我就是那條蛇,怕嗎?豆豆縮一縮脖子,沒答話。老李又問,認得我嗎?豆豆猛搖頭,老李低聲道,你阿婆沒給你說過?豆豆說,我回去問問。過了兩天,老李又喚他,豆豆拉一拉脖子上的紅領巾,扭頭就跑。
陳老太給豆豆下了啥迷藥?老李納悶。
2
推拿店的生意不溫不火,每天三五個客人光顧。這正合老李的意,他一邊兒給對方推拿一邊兒聊天,感覺日子舒坦又充實。而且他十分慶幸,這些年除開睡眠差了點兒,沒落下什么大毛病。要是像陳老太那樣,山珍海味也無福消受。
只是到了夏季,天氣一暖和,陳老太幾乎不咳不喘了,臉上漸漸透出陽氣。她喜歡坐在屋檐下曬太陽。老李進出店子,她囁嚅幾下嘴,像是有話要說,又忍住了。老李依舊不語,靜觀其變。沒多久,代理律師幫他落實了賠償金的事兒。周末又有記者來采訪,老李借口做生意,三言兩語把對方打發走了。剛清靜下來,陳老太愣起眼球,拄著拐杖,上門了。老李有點兒猝不及防,馬上站起來,腦子一片空白。
你該繼續坐下去,越坐越肥。
老李怔了怔,陳老太,法官都判了我無罪啊。
我認識報紙上的字,你騙不了我!法官說的不是你無罪,是無罪從疑。疑,懷疑的疑。
老太,你是瞎折騰,那叫疑罪從無。
都一樣,反正就是疑。法官都疑,我還能不疑?
老李的血氣一下沖上腦頂,老太,那你說咋辦?
我能把你咋辦!你奸殺我女兒,還能拿到一大筆獎金,我和豆豆現在全靠我侄子扶貧。你別高興得太早,我侄子現在支教去了,等一段時間回來,他會幫我討說法的……陳老太講到激動處,脖子上的“水流”一顫一顫地跳動,仿佛全世界的冤屈都注在那里面。
老太,什么都要講證據,不是討就討得來的啊。
證據?你能拿出證據,證明你沒罪嗎?
老李臉一下繃緊,顴骨凸成兩個小拳頭。他盯了陳老太片刻,忽地往椅子上一坐,懶得回應了。陳老太冷哼一聲,像大獲全勝的巫師,跺著拐杖,打道回府。老李望著她的背影,心里塞了團麻布,堵得難受。
夕陽落山后,老李的心情總算順暢下來。他去廚房弄菜,聽到外面有響動。抬頭一瞧,是豆豆,站在巷子對面,拿一把彈弓,朝店子的招牌射玉米籽。玉米籽很輕,在空中劃一道弧線,落進了店子里。老李穿過客堂,邁出大門。豆豆退縮兩步。老李走過去,一把奪去他的彈弓。豆豆嚇得趕忙掉頭,往屋里跑。陳老太正坐在天井邊,她母儀天下地站起來,目光跟老李對抗著。老李扯一扯嘴角,忽然沖豆豆笑道,你看好了。然后轉身,舉起弓,保持四十五度的角拉開弦,啪一聲放出去。又摸一摸豆豆的頭說,記住,要擺準角度,拿捏好力度,知道嗎?豆豆眼一亮,遞去一粒玉米籽說,你試一個給我瞧瞧。陳老太一跺拐杖,去做作業!弓拉得再好,能證明啥兒?豆豆一溜煙跑進里屋。老李知趣地放下弓,陳老太又嘀咕一句,我侄子馬上回來,會幫我討說法的。
老李心頭一顫,急步走了。
3
接連幾天,老李躺在床上,腦子里總會浮出那個他無法自證的夜晚。鬧鐘嘀嘀嗒嗒地響,聲音像鍘草,一刀刀鍘得他心慌。
老李離婚的第三個年頭,兒子不到二十歲,已經是出師的焊工,完全能自食其力了。那會兒,對面家的陳英死了老公,就把寡居多年的陳老太從娘家接來,讓她幫忙照顧豆豆。老李很快對陳英動了心思,陳英也中意,畢竟豆豆才兩歲,有男人愿意接手,是值得考慮的。但陳老太嫌他年齡太大,又是寒門家境,堅決反對。陳英左右為難,跟老李交往的大半年里,抵不過陳老太的唆使,跟其他男子有過接觸。兩人因此鬧了別扭。陳英失蹤的當晚,老李正在生悶氣,一個人窩在床上,把窗戶關得嚴嚴實實地看A片。哪能想到,第二天,在附近的枯井里發現了陳英的尸體。
老李一直活在世人的眼皮下,唯獨案發的關鍵時間,他不存在了,從所有人的視線里消失了。他的噩夢從此降臨。他始終無法證明自己當晚呆在屋子里,這是他心里的疙瘩。現在有人來碰它,不是別人,偏偏是陳老太。疙瘩仿佛惡化成了腫瘤,弄得他覺也睡不踏實。老李的兒子兩次打來電話問候,聽出他精神不好,追問原因。他想一想說,沒啥,店子生意好,太忙,一時半會兒不適應。
轉眼豆豆放暑假。他不玩彈弓了,整天就呆在家里看電視。陳老太呢,天氣越熱精神越好。她不蜷在屋檐下曬太陽,而改在巷口沐日光浴。有街坊鄰居進出,便拉著別人聊天。有時也趕場,老半天才回來。老李聽說,她前些日子跑過鎮上的法院、派出所,還有人大辦公室,結果如何沒人知道。但不管怎么樣,她不來店里“鬧事”了。
豆豆開學后,陳老太卻跟著“開工”。白天,只要店里有生意,她就拄著拐杖,站在店門口,跟佘太君一樣威風凜凜地說,我侄子馬上回來,會幫我討說法的。要是有顧客勸兩句,她就眼球一白說,我現在總算見識了啥叫墻頭草,風吹兩邊倒!
而老李每次聽到這些話,心里總有點兒發虛。律師跟他說過,“疑罪從無”一旦發現新證據,的確要重新歸案。老李當然沒殺人,按理不用擔心。但人生太無常了,會不會哪天忽然冒出一個對他不利的新“證據”,他真吃不準。五十歲的人,再召回去,折騰不起啊。要知道,當年陳英的案子只要一重審,陳老太馬上把她侄子從遂寧叫來,跑到法院鬧,甚至拉著法官跳樓。這樣想著,老李總感覺有一把刀如影隨形地橫在脖子上。在陳老太面前,他說話行事就比較克制,不想刺激到她。
那天,陳老太從巷口回來,又在店門口晃悠。剛巧客人離去,老李就挪出椅子說,老太,進來坐,有什么慢慢說。
沒證據,說什么都多余。陳老太向門口靠了一步。
兩人沉默著。時間似乎在陳老太那里多一些,她忍不住咳了一聲。老李又把椅子往門邊推一推,我說過很多次,那天晚上,我就在屋里看……看……哎,反正你不信,我不提了。
陳老太跨進門,厲眼瞟他說,法官也沒信,對不?
老李走到佛龕前說,我發誓,如果我是兇手,全家不得好死。
菩薩瞎了眼,讓我女兒替你們死了!
那你想咋辦?老李嗓子有點兒壓不住了。
我能咋辦?我侄子馬上回來,會幫我討說法的。死了人的不賠錢,白吃白喝白住八年多的,反倒發工資。陳老太忽然喘起來,只要這事……沒了,我……就是……死了,我侄子也不會……不會……
別急別急,你——你坐,我給你倒杯水。你那咳喘,得冬病夏養。你要樂意,我幫你按摩中府穴、肺俞穴,對慢性支氣管炎特別有效。要不辦張卡,七折,劃算?
等老李遞去水杯,陳老太已經緩過勁來。她又激動道,你邪了我女兒算了我女兒,現在還想邪我算我,沒門!說完,肺里拉起小風箱,像受重傷的巫師,踉蹌回去了。
吃過午飯,老李好幾次到她家門口聽動靜。沒任何聲響。門虛掩著,他從門縫里窺探,只探到天井下,有一柱灰塵在陽光里翻飛。推門,手伸出去又縮回來。整個下午,只要店里沒生意,他就坐在街沿邊,遇見街坊鄰居,馬上跟對方打招呼。他想,我必須存在!
黃昏時分,豆豆回來了。老李盯著他進門,心一下揪得緊緊的。過了一會兒,豆豆提一副鐵環,嘟著嘴出門說,吃面吃面又吃面,上周才吃了面又吃面,我家又不是開面館的。
老李的身子瞬間舒軟下來。他朝豆豆招手說,怎么不玩彈弓了?
豆豆走過去,一叉腰說,阿婆沒收了,說考試過關才還我。
哦,也好也好。對了,你問過阿婆,我是誰吧?
問過。阿婆罵我多管閑事兒,沒說,只讓我別理你。其實,我也不想理阿婆。她今天躺一下午,啥也不做,害得我又要吃面。不說了,我要去滾鐵環了。
你小子居然學會賭氣了。老李呵呵笑兩聲,拍了拍他的背。一層皮貼著肋骨,像紙糊的風箏架。老李心一凜,又想到了陳英。陳英不漂亮,但豐滿,屁股繃得褲子緊緊的,這讓他產生過無數次異常的想象。老李很懊悔,如果當初不跟陳英斗氣,她就不會出事,現在自己應該是豆豆他爸了。豆豆一定會長得跟他媽一樣,圓滾滾的。
短暫的沉默后,老李說,我冰箱里有雞腿,一會兒給你阿婆送去,讓她弄給你吃,行嗎?
真的?要搞快哦。
等豆豆溜出巷口,老李馬上取出雞腿,裝在盤里,送到陳老太家。陳老太聽了他的來意,嘴一撇說,別在豆豆面前賣乖,你有什么資格跑來挑撥離間!
不是這意思。老李把盤子遞她面前,豆豆說,你身子不太舒服……
不等老李說完,陳老太手一掀,咣當一聲,盤子掉地上,雞腿滾進天井的陰溝里。
晚上,豆豆跑來店里問,李叔叔,你說的雞腿呢?老李目光躲閃地說,你看我這記性,后來我才想起,雞腿昨天就吃完了。豆豆腮幫左鼓鼓右鼓鼓,又是一叉腰,走了。
4
秋老虎一來,天悶得讓人發慌。陳老太卻出奇地安靜下來。她大多時間縮在家里,即便出門,也壓根不往店里瞧。但她跟老李的后續“恩怨”,已經在小鎮炸開了鍋。這一來,很少人去光顧老李的推拿店。老李明白,別人未必真中了陳老太的蠱惑,只是不愿得罪她罷了。老李經常守著空店,老僧入定。陽光照在巷子里,依舊一半陰影一半明亮。陰影這邊是自己家,明亮那頭是陳老太的家。
過了幾日,老李實在憋不住了,他打電話給兒子,把悶在肚子里的苦水,一骨碌全倒了出來。兒子聽后說,依我看,眼不見心不煩,還是回我那兒住穩當。等工程完了,馬上來接你。老李動心了,他說,也好。不過我的推拿店裝修不到半年,家當也搬不走,你回來前,我先找個人接手。第二天,老李貼出轉讓啟事。不到半日,店里來人了,居然是陳老太。她說,我辦卡,打七折那種。
老李鞠躬道,老太,抱歉,我準備回兒子家住了。
我女兒的事一天沒了結,你一天也走不了!
兩下無話。這一次,沉默的時間在老李這頭多一些。他率先說,老太,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抵對門。你不用辦卡,只要來,我都給打七折,好嗎?
我就辦卡,憑什么別人能辦,我不能辦?
老李沉吟片刻,行行行,辦辦辦。
辦完卡,陳老太雙手拄著拐杖說,我現在就做推拿。
老李見她當真做,只好接招。他扶陳老太躺床上,翻過身,跟拍死豬一樣拍她幾下,然后敷衍地捏揉起來。甚至有那么一瞬間,他生出一個念頭,想往陳老太背部一壓,直接把她壓碎。而陳老太呢,好幾次有說話的傾向,最終卻清一清嗓子,啥也沒說。
陳老太隔三岔五來店里一次。老李悉聽尊便,每次都表現出十分自然的樣子。周一下午,老李正給她推拿,秋老虎忽然收山。太陽一掃而過,小鎮轉瞬暗下來。不久滾起雷聲,墻頭的三角梅被大風吹得晃來倒去,跟受刑一樣。接著下起大雨,雨點打地上,像熱鍋里的油,亂蹦亂跳。陳老太站在店門口,左右環顧,一臉焦躁。老李一下反應過來,老太別急,我……我幫你去接豆豆。
陳老太拄拐杖的手微微抖了幾下,老李拿起傘出門了。
豆豆跟老李坐人力三輪車回來,已經暴雨如注。巷道的水漫到街沿上,在門檻邊蕩來漾去。雷電劈下來,每次都把屋子劈得煞白一片。豆豆見狀,馬上緊捂耳朵。別怕,老李一把摟住他說。豆豆朝他身上靠了靠,頭往他懷里鉆。陳老太走過來,牽住豆豆的手。少頃,忽然停電了,巷子頓時暗下來,一片沉寂。
老李說,老太,要不這樣,我去煮點兒面條,湊合著吃。
陳老太沒表態。閃電劃過,她穩如磐石。
老李松開豆豆,摸出一支蠟燭,點亮,進廚房。豆豆馬上跟過去,老李拉住他的手,又說,別怕。
灶頭很快有熱氣騰出,把燭光罩成溫暖的霧氣。豆豆一直拽住老李的衣角,偶爾頑皮地用臉蹭一蹭老李的腰背。陳老太不知什么時候站在廚房門口,監視般地盯住他倆看。
面條起了鍋,陳老太不吃。她說,我不餓。聲音小,但芯硬。老李不敢多勸。豆豆卻吃得很香,吸溜吸溜連湯也喝干了。陳老太的臉松動了不少,老李故意問豆豆,好吃嗎?
豆豆說,好吃,但沒雞腿好吃。
老李一愣說,改天補上。
我叔叔年底接我去遂寧念書,阿婆也去,不回來了。
多嘴。陳老太瞪他一眼。
老李心頭掠過一道明亮的火花。
收拾好餐碗,雷雨還是沒有停下來的跡象。豆豆犯困,在沙發上打起盹來。老李給他蓋了一條薄單。等豆豆睡熟后,老李把他挪到寢室里。雷聲滾過,豆豆下意識抽一抽肩膀。再有閃電劃過,老李立刻捂住他的耳朵。陳老太守在床邊,嘴唇下掰,依舊不語。
到了深夜,雷雨漸收。陳老太要帶豆豆回去,老李說,別動了吧,明早我喚他就是。陳老太遲疑片刻,打道回府。剛到店門口,陳老太忽然一跺拐杖,不行,豆豆必須回去。語氣十分堅決。老李滾兩下喉嚨,賭氣似的回到床邊,輕輕抱起豆豆,送到陳老太家。剛放下,豆豆醒了,他又抓住老李的手。老李輕輕拍他,直到他重新睡過去。離開時,穿過漆黑的客堂,忽然有電筒光從背后直直射來。
老李沒回頭,急步跨出大門。但他心里無端端地長出幾根蔓藤,飄來飄去,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卻什么也沒抓住。
5
月底,老李的兒子打來電話,說工程初驗了,有些小整改。如果他著急,就先把他接過去。老李含糊道,快年底了,店子沒有人接手,估計一時半會兒也轉不出去,你先忙吧。
日子暫時恢復了平靜。天氣轉涼,巷子里又出現了陳老太的咳嗽聲,一天比一天厲害。陳老太來做推拿,老李不馬虎了。他在陳老太的脾胃腎膈肺穴上認真按揉,又用打滾法來回推。他期待陳老太有某種轉變,比如一個眼神、一句話。但啥也沒有,他耐心等待。
立冬時,陳老太忽然端來一碗面說,你嘗嘗,雞雜臊子,肯定比你做的好吃,也不比館子里賣的差呢。
老李捧過來,他覺得這一大碗面就是一大碗酒,酒盡言歡。放下空空的碗后,他一抹嘴說,老太,以后去了遂寧,常回來看看,到時還給你推拿哩。
你想多了。上次豆豆吃了你的面條,現在我們兩不相欠。
老李扯一扯嘴角。
我侄子馬上回來,一定會幫我討說法的。
老李眼睛瞪得比雞蛋大,面條在胃里,直感到一陣燒心。
老李還沒把面條完全“消化”下去,陳老太的侄子忽然“駕臨”。那個時候,離春節還有一個月。陳老師每天進進出出,一直沒跟老李打過一句招呼。據說他請了律師,重新梳理出案件的線索,向相關部門遞交了訴求書。
老李靜觀其變。說靜,其實哪兒靜得下來。當年這條線索那條證據,每一條都指向他套牢他。一想到這些事兒,他腦子就嗡嗡作響,整夜失眠。到了白天,眼皮沉重如木門,眨巴時都吱嘎作響。到了年底,陳老太一家子收拾行李,準備撤退。老李剛松一口氣,陳老師忽然上門,說找他有事兒商量。
老李緊張,不自在。
寒暄了一會兒,陳老師說,老李,我舅媽是很偏執的人。你出獄后,她每個月給我打電話,那口氣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似的。哎,扯遠了,說正事吧。現在她死活都不去遂寧,我差點兒給她下跪,但她非要留在這里,守住你,不讓你走。
老李擠出一絲笑,拳頭卻暗自捏緊地說,我可以不走,但你必須、必須跟陳老太說清楚,害死陳英的人不是我,天地作證。
陳老師目光深邃地看著他,仿佛透過長鏡頭看人。少頃,他深一口氣說,老李,我該怎么說呢?“疑罪從無”這個司法理念,我充分尊重充分認同。但對于我舅媽來說,一點兒用也沒有,她認定就是你。
既然這樣,抱歉,恕我不能答應。老李一下臉泛青色,目光聚成刺說,你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你,我,還有陳老太,特別是陳老太,遲早會見到陳英,見到陳英,到時候什么都一清二楚了。
陳老師趕忙握住他的手說,老李,別急別急,我想說的是,我舅媽一定要守著你盯著你,我為這事兒深感抱歉。希望你能理解她,別跟她一般見識。她人其實挺好,我們家族人丁不旺,她從小把我帶大。哎,又說遠了。現在最讓我頭痛的,是我答應了她的要求,打算給她請個保姆,可她堅決不要,說守住你就行。我真理解不了她對你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我想,我想你們就權當是緣分吧。
緣分?老李苦笑,這緣分不會是讓我照顧她吧?
陳老師連擺手,不是不是,肯定不會讓你伺候她,你沒任何義務這樣做,你該干嘛就干嘛。這么說吧,我舅媽只要發現你還在她眼皮下打轉,她似乎就安心了。我的請求很簡單,就麻煩你稍留一點兒心,用眼角瞄著她就行。我保證,無論她出現什么意外,都跟你無關,絕不會賴上你。你要不放心,我寫承諾書給你。不過,唯一需要你幫忙的,就是萬一我舅媽的病出現緊急情況,麻煩你通知一聲,我會第一時間趕來。
老李綠著臉,嘴唇碰兩下,又緊緊抿住了。
陳老師遞來一個紅包說,老李,請收下。哎,別推辭,我不知道該用什么形式來表達這份謝意。真別推辭,我知道你不在乎這錢。說著,他幾乎半跪在地上,老李,算我求你,真的求你了!
老李在原地怵了一會兒,一下癱軟在椅子上。
6
春去秋來,雨打風吹。墻頭的三角梅不斷折枝,又生出新芽。陳老太的病也隨著季節,去了又來。剛開始,老李采取的策略是,她不理,我不睬。但耳朵保持警惕,聽到咳喘聲,他歪著腦袋,往巷里瞄一瞄,僅此而已。
倒是陳老太,變得知趣了安靜了。炎癥厲害起來,馬上來店里推拿。老李給她揉背推穴,越來越有耐性。但他依然會無端無由地想起陳老太鬧法院的事兒,轉瞬沖動,恨不得一巴掌把她拍碎。拍碎是不敢,走神常有,不自覺下手就重了。陳老太任憑他“處置”,偶爾也向他發難,故意讓老李一會兒按輕些,一會兒推重一點兒,這個地方必須反復揉,那個地方需要反復按。語氣里夾著嗔怪,帶點兒宣泄。
陳老師幾乎每月來看望陳老太,豆豆也來。每次陳老師都給老李捎東西,水果、酒或茶葉。老李不收,他就不走。實在勸不通,就讓豆豆送來。有一次豆豆忽然跑來說,李叔叔,我才知道,你騙了我一件事,上次那個雞腿是阿婆打翻的,對不?半晌老李說,記不清了。
后來,老李勸陳老太少吃激素藥,開始幫她抓中藥、熬中藥。陳老太每次接過藥碗,總要捧上好一會兒,才慢慢喝下去。嘖嘖兩聲,不笑不皺眉,似乎藥很苦又很甜。記不清哪一天,陳老太喝完藥,對老李說了一句,這輩子我做錯了一件事。老李問啥事兒,她不語。
一晃兩年半,陳老太滿七十。她眼袋松垂,像青棗,老年斑則跟陽光穿過樹葉灑下的陰翳一樣,匍匐在臉上。最要命的,是她的咳喘一年比一年加重。老李給她推拿的時間越來越長,每次都累得腰酸背脹。
到了冬季,陳老太的病莫名好轉。她又給老李端來一碗面,雞雜臊子特別多。老李不安地問,老太,這碗面,又是因為啥兒?陳老太還是啥也沒說,只眼神干巴地望著墻頭的三角梅。三角梅的花早凋零了,但葉子依舊又綠又蓬。
隔了兩日,陳老太忽然臥床不起。老李準備送醫院時,這才發現她床頭擺了兩大瓶激素藥。送進重癥監護室,陳老太周身插滿管子。醫生說,她慢性支氣管炎并發出肺心病,引起心力衰竭。不到三天,下了死亡通知書。所有人圍坐床邊,守候她生命的最后時刻。等到回光返照,陳老太抓住老李的手,讓其他人出去。病室里一下肅靜得嚇人。
我死不瞑目。陳老太的聲音跟巖水一樣滯濁。
老太,你到底想說啥兒?
陳老太搖頭,搖了一會兒說,當年,我要不阻攔你們的婚事,我女兒,我們會很幸福的。說著,她手發抖,目光迅速黯淡下去。
老李閉眼,深吸一口氣。
陳老太再次抓住他的手說,你到底是不是兇手?你說,說……
老李木著臉,呼吸急促起來。
我—死—不—瞑—目。陳老太軟軟松開他的手,垂下眼瞼,蓋住深陷的眼睛,如同沉沉地拉下的帷布。
陳老太去世后,老李關掉了店子。兒子來接他那天,剛巧正午。陽光照在巷子里,依然一半陰影一半明亮,陰影這邊是自己家,明亮那頭是陳老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