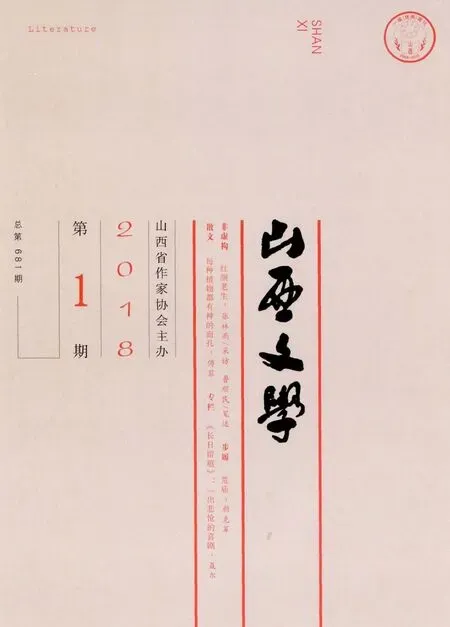紅顏老生(上)
—— 晉劇表演藝術家謝濤口述
張林雨 / 采訪 魯順民 / 筆述
頭一回面對觀眾哭了
我1967年6月4日出生在太原,我們兄妹共3人,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父親當時擔任太原戲曲學校的副校長,他的資格很老,是當年晉綏邊區七月劇社的老演員。母親則是太原市實驗晉劇團青衣兼老旦演員。
一方面來自家庭的熏陶,父母的遺傳,另一方面是環境的影響,每天耳邊是晉胡、二弦、打擊樂,每天都看叔叔阿姨們在排練場排練和舞臺上表演,可能很小很小的時候,戲曲的種子應該在我心里生根發芽了。所以自己后來從事戲曲藝術,已經不能用酷愛來表達,那真是沉淀在骨子里血液里的東西。
當時的太原市實驗晉劇院有“六大員”,過去的說法叫“角兒”。這些人對我的影響特別大,這個影響遠不止“六大員”。
所謂“六大員”,共六位,有郭彩萍老師,她是晉劇小生名家;有武忠老師,是晉劇老生名家;李月仙老師,晉劇須生名家,后來我磕頭拜其為師;后邊還有閻慧珍老師、高翠英老師。他們都是咱們晉劇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最后還有另一位白桂英老師。
實際上,優秀的演員還不止這六位,包括薛維義老師、唱花臉的戴占壽老師、薛玲花老師,還有我媽媽張翠英,他們是一代人。他們這一代人,是解放之后晉劇培養的第一代接班人。這一代人中間,也包括田桂蘭老師,還有調到省晉劇院的張友蓮老師。
我六歲上學之前,就是看他們排練和演出,那種影響和熏陶就很厲害了。院里孩子們在一起玩,也是照貓畫虎在那里演戲。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就是按照父母演什么角色來分配各自的角色。
我當時很不樂意啊!為什么呢?因為我媽媽唱青衣兼老旦,她演的最多的就是老太太,我一個小姑娘,不想演老太太。想演啥?演舞臺中間那個小姑娘,比方《紅燈記》里的李鐵梅,后來還有《朝陽溝》里的銀環,還有《苗嶺風雷》《平原作戰》《杜鵑山》里面的旦角,站在舞臺中央很漂亮啊。可媽媽不演這些角色,她演張大娘、杜媽媽、沙奶奶,就這些角色。
當時,院里的叔叔阿姨他們演的角色我照貓畫虎都會的,但他們總讓我演老太太。演就演吧,演老太太,我也并沒有覺得影響到我對戲曲這種藝術出自骨子里那一份喜歡。
這些記憶應該是三歲之后的事情了。三歲之前有記憶嗎?很小很小,我就想,什么時候我能夠像叔叔阿姨和媽媽那樣站在舞臺中間表演,讓那么多觀眾給我鼓掌,給我叫好!
盛夏時節的傍晚,屋里熱,人們就在大院里乘涼,點起艾草熏蚊子,一堆一堆的,叔叔阿姨們坐在院里聊天,聊家常,聊排練。我們一群孩子就在他們中間來回穿梭。記得我穿著爸爸的一個大襯衣,穿起來像裙子一樣。后來我問媽媽,我那時幾歲?媽媽說,那時候也就三歲出頭。
我們一群孩子們在大人中間瘋玩瘋跑,跑著跑著,就有叔叔阿姨一伸手逮住我,叫我小名:紅紅,來一段!這時候我特別高興的,好像也特別愛表現,大人拉住我的手,站在中間來一段,像模像樣。唱什么?當然是自己喜歡的那些旦角,《紅燈記》啦,《杜鵑山》啦。現在想想都特別甜蜜美好。
真正顯現出對戲曲的愛好與癡迷,應該是上學之后。
1974年9月,我上小學。上的是新建路小學,現在叫一校二校。當時就是一個新建路小學。新建路小學是一所戴帽小學,小學五年,初中兩年,小學和初中都有,是所謂的“七年制小學”。
其實,在上學之前,已經跟新建路小學有接觸。上學之前,院里有一個哥哥,大我五歲,叫陳亞平,我記得應該是五歲左右,他應該是在五年級的樣子。那一年“六一”兒童節,他跟我講:紅紅,我們學校過“六一”兒童節要演節目,你能不能給唱個山西梆子?
我說:能。
他說:你敢嗎?
我說:敢。
有什么不敢的?兩三歲就在院里唱,現在五歲了嘛!
他講:那你跟媽媽說,明天早晨化個淡妝,我帶你去學校。
當時我什么都不想,膽子也挺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和面對這么多觀眾。后來想想,師生合起來有一兩千人。舞臺由土堆起來,外頭再砌一些磚,很不整齊,而且也陳舊,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搭起來的,有三個臺階,當時我五歲,很小的個子,還是老師把我抱上臺上去的。
在上臺之前,學校的音樂老師拉手風琴,問我說:孩子,你唱什么?
我說:晉劇!
后來我知道音樂老師是裴老師。裴老師說:晉劇我不會伴奏,你就獨唱吧。
這樣我就被抱上臺了,那個話筒裝在一根桿子上,老師把它壓到最低,就那還在我的頭頂上。那天操場里面坐滿了老師和學生,一大片,老師把我放下之后讓我站在中間唱。當時高老師問我說你唱幾段,我說兩段,一段是《紅燈記》里鐵梅唱的《都有一顆紅亮的心》,一段是《平原作戰》中小英唱的《槍林彈雨》。就準備了這兩段。
他們給我報幕,我一上臺大家就開始鼓掌。現在可以理解,“六一”兒童節,把一個學齡前兒童請到臺上給大家唱,大家不很開心嗎?我一張嘴唱的晉劇,是山西梆子,平時大家聽得不多,小姑娘一唱,又覺得很好玩,唱完又鼓掌。我呢,就是這種人來瘋,他們一鼓掌,我覺得他們肯定是覺得我唱得好,這個勁兒就上來了,自己給自己報幕說我再來一段《平原作戰》小英的唱段。大家又熱烈鼓掌。唱完之后,大家更開心了,掌聲比上一段掌聲更加熱烈。這時候腦子就有點暈,有些膨脹,竟然還不想下臺。
老師一看我準備的兩段唱完之后沒有下去,就說:你再來一段。我點點頭,他問我:你唱什么?我說:《朝陽溝》。
我就唱《親家母,你坐下》,演倆老太太。五歲年紀,乳牙剛退,新牙還沒長齊,前面兩個大板牙長長短短不齊,我一說《朝陽溝》,先擺出那個老太太的動作,小板嘴一撇,那個效果可想而知了,大家哄然大笑。他們這一笑不要緊,我把第一句詞給忘掉了,怎么也想不起來。這下好,大家又開始鼓掌,現在想,大家的掌聲是善意的,鼓勵的。一個小姑娘擺出那樣一個姿勢,大家覺得更有意思或者更可愛,可我站在那里很尷尬,一聽到掌聲響起來,不樂意了,沖著那個話筒哇一聲就哭了。記得是裴老師,在臺下一看這個情況,趕緊上臺把我夾在他胳膊肘底下抱了下去。
為什么講這一段呢?后來我才知道,因為這一段,在新建路小學出名了。入學前去報名,兩個班主任搶著要我,說我們要這個孩子我們要這個孩子,就那個在“六一”兒童節在臺上唱了兩段不肯下來,最后在臺上哭了的那個孩子。
所以,上小學之后,老師對我特別好。我自己呢,學習也特別好,開始當班長,后來是中隊長,后面又是大隊委員,在大隊委里還擔任宣傳委員。擔任宣傳委員,自己是文藝骨干,這沒有問題,但也不全是這個原因,學習成績也特別好,尤其是語文作文,還有朗誦。11歲那一年,代表山西省出席全國普通話比賽。全省7名代表,有教師,有中學生,還有小學生,我是其中之一。
小學五年,過得特別快樂,除了學習用功成績特別好,也沒有離開過文藝。可能也是人來瘋,過年過節學校搞什么活動,積極參加積極表現,不單單唱晉劇,還跳《草原英雄小姐妹》之類的舞蹈,還有朗誦。上學的時候文藝活動也特別多特別豐富,文化館、少年宮都有。這樣,我其實已經不單單是新建路小學的文藝骨干,而是太原市青少年中的文藝骨干和文藝苗子。
小學五年,我覺得跟文藝的接觸更近了,在舞臺上更有表現自己的機會。
我要上戲校
小學畢業,面臨著升學。
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上戲校。
在11歲的時候我就知道戲校招生,那會兒叫太原市文化藝術學校,爸爸擔任主管業務和招生的副校長。為什么要上藝術學校呢?因為打心里喜歡當演員,當戲曲演員,喜歡唱戲,這個沒有辦法。或者說,這就是我的理想。
當年寫作文,曾經寫自己的理想是當個科學家,那都是違心的,特別違心。其實理想是做演員,唱戲。因為除了在學校讀書之外,課余時間的生活環境還是劇團,經常看叔叔阿姨們演出,尤其是節假日,放寒暑假,他們在長風劇場、和平劇院、山大劇院演戲,我都是要跟著去看的。那個時候就特別憧憬,心說啊呀,自己將來的職業就是演員嘛。這樣,對他們的工作狀態都十分熟,每天演什么什么戲,每天提前多長時間化妝,都很清楚。他們還經常下鄉演出,扛著行李卷,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很喜歡。
但上藝校并不順利。
首先是我的班主任張老師反對。為什么呢?因為我學習成績好,她希望我能順利上初中、高中,考大學。張老師是太原市和山西省的優秀班主任。上初中、上高中,順利考個好大學,是任何一個老師對好學生的期許。所以上藝校,張老師很不理解,也很不高興。現在張老師都七十多歲的人了,見了我都不說她改變了當初的主意。
有一次,師生見了面,張老師只是說:孩子,你現在唱戲唱得不錯,挺有出息啊。
她老公馬上阻止她:你別再說了,人家謝濤唱戲現在都得大獎了。意思是你應該夸人家呀!但張老師還是很固執,她講:她就是搞了別的也一樣有出息。
很固執的一個老太太。
老師不同意,媽媽也反對。反對得特別厲害。她知道我要報戲校,直截了當阻止:你不能學戲,你不能唱戲。
這個時候,我哥哥已經考入太原市碗碗腔劇團,媽媽實際是不樂意的,她一直阻止我,說:你得學習,你得學文化,將來考大學。
媽媽常年下鄉演出,一走就是兩三個月,家里管不上。她就跟我爸爸講:你不許謝濤去上戲校,不許謝濤考戲校,不許讓她唱戲。
我們這個家庭,是慈父嚴母。母親對我們三個孩子特別嚴格,雖然沒有打過我罵過我,但對我們特別嚴格,不許這不許那,她個性也很要強。相反爸爸對我們相對溫和,所以她下鄉之前再三叮囑爸爸來阻止我。
媽媽反對,要比老師不樂意來得麻煩。為什么呢?因為報名要戶口,媽媽反對,她不給你戶口怎么辦?但是,我還是偷偷取了戶口本報了名——戶口在哪個抽屜里我知道。不過,爸爸其實也是睜只眼閉只眼,他作為主考官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家的姑娘報了名?雖然他不參加初試這些過程,但他是知道我要做什么的,說明他贊成我的選擇,至少不反對。
這就考試了,當然同時也參加了中學的考試,現在叫“小升初”。結果,太原市文化藝術學校的通知發下來,同時也接到了12中的錄取通知。12中是太原市的重點中學。這就存在一個選擇的問題,那時候新建路小學已經取消了“戴帽”,變成完全小學。小學畢業,要么上12中,然后上高中,考大學,要么就去讀戲校,做我喜歡做愿意做的事情。其實也沒有怎么多想,把12中那個錄取通知給撕了。現在想想,那時候12歲的小孩子怎么會有那么大的主見?直接就撕了。回家之后,把文化藝術學校的通知書放在自己的小抽屜里,夾在一個日記本里藏起來。我們三個孩子每人有一個小抽屜。給家里人撒謊說自己沒考上重點中學。
這中間,媽媽回來過一趟,我就跟她聊,探她口風,說:媽,我要是考不上重點中學,你讓我上戲校。
媽媽回答很決絕:不可以,今年考不上,明年繼續考。她一口回絕,但我覺得自己一定能上成戲校,一點也不氣餒,有一種認準一條路一定要走下去的感覺。這可能就是我性格里的執拗,一根筋那種勁頭。我也不吭氣了。
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中間媽媽曾問我說誰誰誰家的孩子考上12中了,謝濤,你這通知書就沒拿到?我就搖頭。
可是這樣僵持也不是辦法,畢竟紙里包不住火。記得是8月底9月初,各學校的新生都開學報到了,那一天家里就我和媽媽,媽媽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大盆里架了搓板,在那里忙碌。這時候,我的小學老師找來了,她一進門就說:這孩子怎么回事不去報到呀?媽媽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說孩子沒有考上呀!
她們在那里聊,我一聽不好,不敢在院里待了,刺溜一下子跑回自己小屋子里躲起來。聽得老師在外頭跟媽媽說話,老師說謝濤考上12中了,人家都報到了,這孩子到底上還是不上?
我記得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一邊應著老師說:上上,一定上,我讓她去報到。一邊用那樣一種眼神找我,狠狠的那種眼神。我嚇得哪里敢出去?
老師簡單說了幾句就走了,這時候媽媽甩干凈手上的肥皂沫,擦凈手,左顧右盼找東西,結果找到一條馬鞭。是練功用的那種馬鞭。這時候哥哥已經開始練功,媽媽也有這些練功的東西,實際就是一根藤桿,上面的穗子都掉了,就剩下一個馬鞭桿。媽媽一把把我揪過來按到床上就抽,在屁股上抽了十幾下。真是很疼啊。晚上我摸腿,都是一棱一棱的鞭痕,在燈光下能看見好幾種顏色,青的黃的綠的紫的。現在想起來都很疼。
就那樣,我沒有哭。一聲都沒哭。媽媽打我抽我,我就咬著牙不哭。
這已經是將近40年前的事情,至今還像電影鏡頭一樣清晰,媽媽打完我,扔掉鞭子,抱著我哭。
我安慰她:媽媽你別難過,我肯定給你爭氣!
媽媽說: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唱戲有多苦。它還不是你身體的皮肉之苦,遠不止胳膊腿骨折那些閃失,主要是得靠多少人幫襯你才能成啊。
唱戲苦我理解,但是媽媽說的幫襯我當時真的不理解。媽媽是個要強的人,那會兒沒有出大名,觀眾也知道,也熟悉,也喜歡,但不是大角兒,我想媽媽可能有一種不得志,心里頭不服。出大名也好,做大角兒也好,可能就是命運或者人生。
現在想想,媽媽的話有許多道理,這一路走過來,多少人去推著你,幫著你,托著你做成一件又一件的事,你最后才能成為一個大家喜歡的好演員好藝術家。幫襯,是媽媽對唱戲這一行的理解。
但當時我是不理解的,12歲的孩子就是那么簡單的喜歡,就是喜歡唱戲。所以我對媽媽說,我一定給你爭氣。
挨了媽媽的打,實際上等于媽媽接納了我的選擇,我可以順利地上戲校了。
上戲校那一年是12歲,我們那一屆是78屆,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耽誤了一年。
入學是1979年的事情。
戲校春秋
戲校是粉碎“四人幫”之后恢復起來的,校舍在一座廟里,那條件跟今天的戲校不能比。那座廟很有名,后來成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叫竇大夫祠,離城二十多公里,老師從城里來上課,學校安排有一輛大轎子車,每天早上來,晚上回,一白天都在學校上課,學生則兩周回一次家。我們的學制是五年,我在這里待了整整三年,第四年就實習去了。現在想,所有的唱做念舞基本功就是在戲校里打下的,我特別感謝戲校的三年。
剛入戲校,我的基礎要好得多,并不是生茬子從來沒有接觸過戲曲,從小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不說,而且在上學之前就練過腰腿,從小叔叔阿姨經常把我兩個腳一提溜,兩個手就拖到地下,拿大頂倒立。這個從五六歲就開始了,雖然是斷斷續續的,不是每天練功,但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底子,相對其他孩子是有些基礎的。
那座著名的竇大夫祠是恢復戲校后的一個教學點,那個時候廟很破,很空,我們的教室和練功房就在廟里。那個地是磚漫的,老舊的磚大而長,但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我們練功跑圓場就在這個老磚地上,尤其是走跪步。現在練功房都鋪著地毯了,但那個練功場真還有它的效果,后來我跟同事們開玩笑,我說如果說我的跪步走得好,那都是在坑洼不平的磚地上練出來的。
環境雖然跟今天不能比,但戲校里集中了一批傳統戲曲表演很過硬的老師。這一批老師和我媽媽是一茬人,是晉劇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批傳承人。比方田翠蘭老師、呂鐵成老師、王玉珍老師、秦英環老師等等,這些老師跟武忠老師、郭彩萍老師,都是一茬人,后來因為方方面面的原因離開了舞臺,搞戲曲教育。他們肚子里有很多功夫玩意兒,所以我們這批學生很幸運,從他們身上學習和繼承了比較扎實的戲曲功夫。
進入戲校,一開始給我分配的是青衣行當,第一出戲學的是《女起解》,也就是《蘇三起解》。這出戲是我們當時的沈毅校長幫我排的,他是搞京劇的導演,整出戲是京劇打的基礎。同時輔導我的還有花艷君老師,她也是我媽媽的師父,晉劇華派的代表人物,她給我傳授指導《女起解》。學的第一出戲,我們叫做開蒙戲,我的開蒙戲就是《女起解》。開蒙戲很關鍵,基礎打得也很扎實。
《女起解》之后,我和一部分同學,大概有七八個人,都是所謂的“尖子”,被派到臨汾戲校學蒲劇。又學了幾出戲,《殺狗》《掛畫》 《雙鎖山》。跟張巧鳳老師學的 《殺狗》。《殺狗》它不完全是一個青衣戲,它糅合了潑辣旦、彩旦、花旦的一些東西,包括道白,都不一樣。所以這出戲無疑給我打開一條戲路。
學的第三出戲是《永壽庵》,這是晉劇正工青衣的一個戲,40多分鐘,一出場就唱,一直唱到結束。里面所有晉劇青衣的板式基本上都包含了,非常之豐富。
可能老師考慮到我的行當是青衣,就著意選了這么三出戲。但第四出戲《擋馬》則是我自己選的。《擋馬》跟青衣沒有什么關系,主角楊八姐是旦角里的刀馬旦,還要結合一些小生的東西,這個在晉劇里叫做“夾生旦”,或者反串。可能我這個性格起作用,好像天生就喜歡這個角色,就選了《擋馬》。
選這出戲也有意思。上學的時候,我還是很淘氣的,一副不務正業的樣子。每天路過另外一個教室,看見呂鐵成老師給其他同學排這出戲,就特別喜歡。那時候我正學《永壽庵》,已經學會了,心里有些煩,就想再學一個戲。
我去找教青衣的秦英環老師,跟她講我想再學一個戲。秦老師問我說想學什么?我說我要學《擋馬》。秦老師當然很吃驚了,她說:那不是你的行當。但我堅持說我想學,秦老師很好的,她想了想說:那我給你建議建議。
我們當時學什么戲,是由教導處統一按行當來安排的,所以她說給我建議建議。當時的教導主任是鮑云鵬老師,那是京劇的大武生,人很和靄。他知道我想學《擋馬》,就找到我們宿舍里,問我說:你干嗎不想學這個青衣戲?我也敢說,我說青衣戲就是咿咿呀呀坐在那里唱,從上臺就坐在那里一直唱,我想動。
他說:你想動,要學什么?
我說:要學《擋馬》。
他說:你能好好學?
我說:我能好好學。
很順利,他就把我推薦給呂鐵成老師。去了之后,人家那里已經有兩個楊八姐,兩個焦光普,我是個單的。呂老師就讓那兩個焦光普給我配。我學得很快的,學到什么程度呢?學得比他們原來教的學生都快,呂老師總讓我來當示范,教完我以后就招呼大家:來,你們跟謝濤走,謝濤走前面,你們在后邊。我學得很帶勁的。
這就是在戲校里學的四出戲。四出戲,四個樣子,風格完全不一樣,雖然當時只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但戲路拓得很寬,不單單是一個行當一個角色,嘗試了四種。所以在校戲三年,過得特別充實。學校里有那么多好的老師,他們都有如此高超的技術,有如此扎實的傳統唱念做舞功夫,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們,這是我們最初汲取到的養份。
改行當
在藝校上了三年,第四年就下團實習,那一年我15歲了,被派到太原市實驗晉劇團,也就是現在的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
當時太原市實驗晉劇團的實力很強,開始講的“六大員”像郭彩萍老師、武忠老師、李月仙老師等等,這些名家正在舞臺上。他們都在40歲左右,郭彩萍老師好像還不到40歲,這是一個演員藝術家最好的年紀,是藝術的黃金期,他們帶著團演出好多好多劇目。我們這些學生娃一來,就是給跑龍套,演丫鬟、扮才女,還有男兵女兵一類。下團實習,眼界一下子打開了,和我小時候看他們完全是另外一種感覺,感覺不一樣。小時候懵懵懂懂,歲數不大,只是喜歡模仿,戲校學了三年,有了一些唱念做舞的小基礎小功夫,一下子來到真正的劇團真正的舞臺上,眼界自然不一樣,打得很開。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們就像海綿吸水那樣,各種藝術營養在潛移默化過程中慢慢吸收,慢慢吸納。
進團之后,我分配的是旦角。那一年15歲,開始變聲,本來我的聲音在女孩子中就比較粗,變聲之后聲音變得更寬更厚了,身材呢,也隨著發育越來越結實。這時候我心里就琢磨,我唱旦角優勢并不大。
雖然那個時候還不是太明顯,而且我唱得也蠻好。在戲校的時候,學校要和周邊單位聯歡,或者有什么實踐的機會,我的《殺狗》《擋馬》兩出戲都是要出去的,算是戲校我們這茬學生的代表劇目吧。能出去演一兩出戲,大家都很羨慕。包括下團實習,老師們也要在我們這茬學生中選那么一兩出,像《打店》《擋馬》,包括我的《殺狗》,讓大家有鍛煉的機會。在一個臺口演出。我們臺口很長,比方到內蒙,一演就是五六天七八天,一天要演兩場,一場本戲就是3個小時,3個小時之前還要加半個小到40分鐘小折子戲,這些小折子戲就是鍛煉我們的。能演上這么一兩出小折子戲,應該是蠻得意的。
但這個時候,我開始變聲,聲音粗了,唱旦的時候還要捏著,身材越來越結實,也不苗條,長得也不算漂亮。自己就在底下琢磨,對著鏡子照,冷靜下來想,你到底適合什么行當?
可能沒幾個15歲的孩子會這樣想,這個與我成長的環境有關系,因為環境熏陶,就是在藝術圈子里長大,會比普通孩子想得長一些,遠一些。來到實驗團,打開眼界,發現,噢,有這么多老生。小時候看叔叔阿姨們演出,包括爸爸媽媽他們,更多的是現代戲,只知道是男唱男女唱女,后來上戲校,恢復了傳統戲,現在看就不一樣了。熟悉的阿姨像郭彩萍啊閻慧珍啊,都叫阿姨,還有李月仙老師,小時候叫她愛子姨姨,她們在舞臺上都是演男角的,如此瀟灑,如此豪邁,如此有氣勢。舞臺上女人是可以這么去演的,我要唱這個!我要演這個!
實驗團分為兩個演出隊,實際就是兩個團。郭彩萍老師帶一個團,李月仙老師帶一個團,我跟的是李月仙老師這個團。
決定要唱男角色,每天就看李月仙老師,像著魔一樣,她演戲,我在幕條旁邊看。她演完之后,我們幾個同學就在舞臺上模仿。她演《點帥》的楊六郎,我就演楊六郎,就讓其他同學演什么穆桂英啊楊宗保啊。天天就這樣子。
這個事情持續時間不長,讓我媽媽發現了。我媽媽那會兒也跟著李月仙老師這個團。
她說我:你瞎琢磨什么,你每天在臺上那是演什么!你是唱旦的,每天琢磨須生干嗎呀?楊六郎跟你有什么關系?
其實不獨是媽媽吃驚,團里的叔叔阿姨們也早看在眼里,他們跟媽媽講:你也管管你閨女,那在臺上是干嗎呢?那是她要唱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唱旦,下鄉演那么一出《殺狗》,效果還好。這就等于是起了風波了。
我跟媽媽講:我要唱須生。
媽媽馬上說:胡鬧,你知不知道,隔行如隔山?我們一茬一茬同事就是唱女的再改男的,最后改得不男不女,再也改不回來了,唱男的像女的,演女的又像男的,沒有徹底改好。你不要改。
媽媽苦口婆心,她講:我都起過這個意,我都改過。
事情是這樣的,當初丁果仙大師在他們這一茬演員里覺得我媽媽的嗓子特別好,而且給扮過戲。戴上髯口,她長的也是這種長臉,扮起來特別好看。但后來花老師,也就是我媽媽的師父舍不得讓她改,而且她自己也舍不得改,也就唱了幾出。當時花派戲也是小有名氣,舍不得改就改回來了。因此媽媽講:你千萬不要改,到時候改得會不男不女。
媽媽不同意,我還是那股拗勁兒,不管她,照樣每天還是老師演戲我去看,演完之后在底下瞎琢磨瞎折騰。也沒有人知道,沒有人告狀,就那么過了一段時間。
媽媽拗不過我,就正兒八經跟我談:這樣吧謝濤,我領你去見李老師你愛子姨姨,她如果說你唱須生合適,她教你,我就把你交給她,我不反對。如果說李老師也說你不適合,那你就死了那條心。
我點頭。
那時候也是在下鄉演出,媽媽拉著我去見李老師,是在一個大教室里邊, 李老師在那里織毛衣。媽媽拉我進去之后跟她說:你看孩子就跟著了魔一樣,就要學須生,我的話她也不聽,那你說吧,她適合不適合唱須生?
到今天也沒有問過李老師,也沒有問過媽媽,她們是不是提前商量過,通過氣?李老師抬起頭看一看就笑了。她是個特別文靜的那種性格,她笑完之后,細聲細語說:不要改須生,你唱青衣挺合適,唱須生不一定合適。可惜啊,不要改!
她就說了這么幾句,媽媽看看,說:走吧。
我聽了之后也沒有多沮喪,有多失落,心里頭只是想,不管你們誰說,反正我認定我要改。就這樣出來了。出來之后媽媽說:怎么樣?聽清楚老師跟你說的了吧?我點頭,她說:以后咱們還是唱旦角。我搖頭。媽媽就急了,開始數落我。她在那里數落我,我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不當回事。
這之后,原來是怎么樣還繼續是怎么樣,還看老師表演,還是瞎琢磨。時間大概是李老師談話過后沒超過三個月,大概就一兩個月,有一天李老師突然把我叫到她住的那個大教室,說:我看你每天看我演戲,你學會了沒有?
我說:學會了。
她說:你學會了什么?
我說:《三關點帥》楊六郎的唱。
李老師說:那就給我來兩句。
我一下就冒汗了,緊張得不得了,沒有任何準備啊。實際是真的學會了,真學會那么幾句了,但一緊張就有點蒙,我想唱“眼前落下金彩鳳”,就是楊六郎見了穆桂英唱的第一句。我邊唱邊想,眼前落下……想不起落下什么漂亮的鳥。但老師讓你唱你又不能停下來,就張嘴唱,“眼前嗯嗯嗯嗯唉落下金絲鳥”。李老師噗嗤就笑,說:還金絲猴呢,你把詞兒給我改了——好啦,不要唱了,你跟我學,我教你!
從這時開始,就跟老師改學須生。那時候還不到16歲的樣子。從開始琢磨自己要唱須生,到最后被老師接納,這個過程折騰了有半年多時間,這樣,真正跟老師學,也就16歲了。
老師教我的第一出戲是《殺驛》,《殺驛》這出戲特別要演員的功夫。什么功夫呢?做工技巧,帽翅也好,髯口也好,捎子也好,靴子也好,就是這些功夫。我覺得老師給我選的這出戲特別好,這些功夫你能拿下,以后唱老生唱須生跟這些有關系的戲就能拿下了。這出戲的難度非常非常大,它就是唱少一點,這個戲主要是技巧。老師教我這出戲,就是打下扎實做工的基礎。學這出戲我學得也挺難,因為我不是扎的須生的基礎,現在要演一個須生戲,即便你扎的就是須生的基礎,學《殺驛》也挺難,何況我的基礎是旦角,一下子跳過來,特別難。
比方臺步,旦角是夾著地,收著地走,而生行呢,它是放著地走。就是說走臺步時,胯得打開。唱呢,我那個階段就是以旦角的唱法去唱須生的腔,很難聽。
團里拉晉胡的張步昌老師,是我媽的同學。我媽還想給我吃偏飯,拉著我去找張老師,給我吊嗓子。我不是不唱旦了唱老生了嘛,去唱。張老師本來是端端正正坐著,給我拉著拉著身子就扭過來,腦袋扭得很痛苦,他是聽不下去了。他說不是這么個唱法!他告訴我媽:讓孩子改回去吧,唱這個不靈。
他當時沒有講出來,從我本身來講,唱的方法和位置都不對,他覺得挺可惜,因為張老師看過我的旦角。所以他說:還讓唱旦吧,不要唱生了,這個太費勁,而且改不好,將來也是不倫不類,男不男女不女。
老一代教師教你發聲,他們有他們一套方法,如果他一下子點不透你,就要走很多彎路。后來我知道,我的老師就是在她聲音壞掉之后,她找到一個我們稱之為“背躬音”(“腦后音”),不一樣的發聲位置唱出來的。這個音他們叫“救命音”,它是一個假音,真假聲結合,假聲大于真聲。我現在學了一些發聲方法,知道這個位置,當時真不知道老師是這么唱的,她找的音我找不到,只能用我自己的本嗓去唱,用青衣嗓去唱須生。
那個時候特別頭疼,只能在練功房里跑圓場。我們那會兒招了一批插班生,就是因為我們這一茬學生的基本功都好,但沒嗓子——實際不是沒嗓子,都是演唱方法不對,不會唱,大家就怵這個唱,都不唱,都是練功,搞表演這些戲。招來的十來個插班學生,個個唱功都非常棒,他們站在琴師跟前,一個人一唱就是四十來分鐘一個小時。我們一上午練功,三到四個小時,人家就在琴師跟前唱三四個小時,就那么幾個人。我們這一幫人在底下練功跑圓場,踢腿下腰,靶子功、身段功都練。
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在底下跑圓場,穿個靴子跑,練嗓子的就在臺上練。我想,我多會兒能站在那個胡琴跟前放開嗓子唱那么完整的一段須生腔就好了。
當時,我只有16歲。以后要走很漫長的路。但是,我憑著自己的堅持,憑著自己的一種喜歡,自己給自己拿主意,自己給自己一個選擇。16歲已經經過了兩個關節點,一個是撕了12中的通知書上戲校,一個就是放棄旦角唱須生。
這兩個關節點在16歲之前完成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