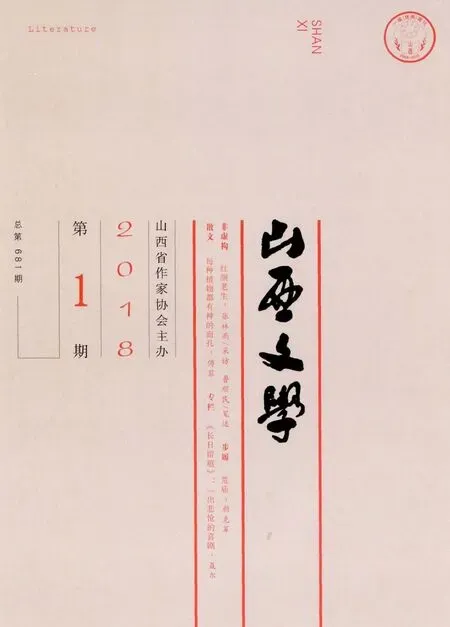《長日留痕》:一出悲愴的喜劇
聶 爾
《長日留痕》是石黑一雄于1989年摘得布克獎(jiǎng)的長篇小說,他時(shí)年35歲。然后,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了石黑一雄。他所獲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當(dāng)然不止這些。石黑一雄是在五歲時(shí),亦即1960年,隨著他的日本家庭移居到了英國。所以,雖然一般也將他視為是一個(gè)移民作家,但卻很難確認(rèn)他的身上究竟有多少日本文化底色,至少他的雙重文化色彩肯定不如納博科夫、康拉德和哈金他們來得強(qiáng)烈。石黑一雄的另一文化背景是現(xiàn)代音樂,他曾經(jīng)做過一個(gè)樂隊(duì)的打擊樂手。這讓我聯(lián)想到許多作家都具有的音樂背景,我所知道的最著名的有帕斯捷爾納克和昆德拉,其中青年帕斯捷爾納克從音樂、哲學(xué)和文學(xué)三條可能的道路中選擇了文學(xué);而昆德拉曾是一名爵士樂手,他自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如何根據(jù)音樂的原理來構(gòu)思的。相反的例子是納博科夫,這個(gè)文學(xué)鬼才幾乎是公開宣稱厭惡音樂的唯一的作家。總之,音樂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是一個(gè)令人遐思卻頗不易詳解的題目。石黑一雄的另一個(gè)來歷也必需被提及,那就是他曾參加過一個(gè)創(chuàng)意寫作班的課程學(xué)習(xí),這是一個(gè)與卡佛和哈金相似的背景,這是否可以證明文學(xué)寫作不僅是可以學(xué)到手的一種技藝,而且甚至可以學(xué)到一個(gè)大師的程度?這對于很多冀望于此的文學(xué)學(xué)徒應(yīng)該是一個(gè)好消息。
在石黑一雄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之前很久,我就“收藏”了他,準(zhǔn)備日后閱讀,但到真的打開他的書卻也是到了他獲諾獎(jiǎng)之后了。無論如何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都不是一個(gè)不重要的文學(xué)事件,連帶著它還提出了我們不得不正視的文學(xué)問題,顯見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會是他,而不是米蘭·昆德拉、北島、村上春樹、閻連科等許多作家和詩人中的一個(gè)?畢竟這個(gè)獎(jiǎng)是面向全世界的,而這個(gè)世界上的文學(xué)奇才何其之多呵。平心而論,假設(shè)在他尚未獲獎(jiǎng)之前我就已經(jīng)讀過了他的作品,由我來預(yù)測獲獎(jiǎng)人選的話,至少我不會把他列為首選。我的理由是,他的長篇小說《無可慰藉》和《黑暗降臨的村莊》(特別是后者)有較為明顯的卡夫卡式的東西在里面,這對于他作為一個(gè)作家的原創(chuàng)性有所損害;他的另兩部長篇小說《遠(yuǎn)山淡影》和《浮世畫家》所呈現(xiàn)出的文學(xué)世界都稍欠豐滿和厚實(shí),稍欠一點(diǎn)文學(xué)的說服力,這或許與他為這兩部作品所設(shè)定的日本背景有關(guān),也未可知。他的最好的、最具獨(dú)創(chuàng)性的、堪稱無懈可擊的長篇小說可能當(dāng)屬《長日留痕》。以上就是我已經(jīng)讀過的他的長篇小說中的幾部,其中并非每一部都讀到了真正的結(jié)尾。
但我又忽然意識到,也許我對石黑一雄的原創(chuàng)性的懷疑理由,也同樣是值得懷疑的,因?yàn)閼蚍潞突ノ恼菍儆诤蟋F(xiàn)代主義的技巧和特征。我得承認(rèn),在《無可慰藉》的浩瀚河水中,我在幾經(jīng)沉浮之后,懷疑慢慢地消失了,我慢慢地適應(yīng)了那里面的暗黑的性質(zhì),甚至還慢慢地產(chǎn)生了一種差不多可稱之為是眷戀的情感。閱讀就是對抗拒的克服,我居然真的克服了我的抗拒。我似乎體會到了放棄光榮抵抗之后的那樣一種順從的墜落的快感。我得承認(rèn),石黑一雄至少具有許多大作家都具有的那樣一種催眠般的語言魔力。(當(dāng)然,我看的是中文譯本,這樣說語言層面的問題我有點(diǎn)心虛,但卻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提到了后現(xiàn)代主義,這是因?yàn)槲乙庾R到戲仿是石黑一雄的一個(gè)主要的特征。我不說這是他使用的一個(gè)主要的技巧,而說是特征,是因?yàn)槲艺J(rèn)為當(dāng)一種技巧被發(fā)展為文本的一個(gè)支柱性的東西之后,它就從技巧的層面上升了,我甚至想說,這說不定是一種小說思想呢。昆德拉曾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小說是有思想的,而小說的思想并不與哲學(xué)和宗教的思想等同,因?yàn)樾≌f的思想閃爍在它的不確定性之上。戲仿正是表達(dá)不確定性的小說思想的一個(gè)方便法門。石黑一雄喜歡為他的每部小說設(shè)置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開頭。這讓不解內(nèi)情的讀者抱著一種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期待走了進(jìn)去,后來他才終于(有一個(gè)過程)明白,原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這是他應(yīng)當(dāng)調(diào)整他的閱讀態(tài)度的時(shí)候了,如果不愿調(diào)整,并且到此就作出了結(jié)論,那至少是不公平的)。回頭再看所來之處,他會明白(我就是這樣明白的),原來,所謂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無非也是一種幻覺而已。所以,石黑一雄小說的開頭亦可視為是對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種戲仿。戲仿這種手段,肯定有其妙用,絕不可以僅僅理解為是小說家對其文化淵源的一種致敬。所以,石黑一雄作品的卡夫卡味道,和他被稱為是“穿褲子的簡·奧斯汀”,都還有待我們?nèi)ド钊氲乩斫夂徒邮堋?/p>
戲仿亦是傳承之一法。實(shí)際上當(dāng)代文化中遠(yuǎn)不止小說,戲仿幾乎充斥于所有的藝術(shù)和生活的領(lǐng)域。完全的獨(dú)創(chuàng)性已經(jīng)成為一種癡想。甚至在政治領(lǐng)域我們也可以強(qiáng)烈地感受到這一點(diǎn)。我們知道馬克思曾說:“一切歷史事實(shí)與人物都出現(xiàn)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所謂喜劇,即是戲仿也。但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告訴我們的,似乎并非如此。在小說和其他藝術(shù)中,其涵義就變得更為復(fù)雜了。之所以如此,是因?yàn)楸瘎∑鋵?shí)是可以重復(fù)上演的,并且是作為悲劇而非喜劇的重復(fù)。這正是人所承受的歷史之重,歷史之黑,黑歷史。戲仿正是對于悲劇重復(fù)的一種藝術(shù)的阻擊。減輕歷史之重,揭開其暗面,如夜鶯一般歌唱,這不正是藝術(shù)的功能之一嗎?這當(dāng)然只是泛泛而論。
剛才還說到互文。石黑一雄在《無可慰藉》中寫“我”初遇酒店“年邁的迎賓員”的一幕,似乎就是為了與《長日留痕》形成互文性效果,而有意設(shè)置的(讀過這兩部小說并且注意到此處的讀者,相信會與我會心一笑的)。互文和戲仿是可以相互滲入和相互參照的。他對卡夫卡的戲仿,難道就沒有將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夢幻和關(guān)于夢幻的夢幻,夢與夢中之夢,加以互文的考慮嗎?他一定知道,面對如此明顯的卡夫卡元素,任何一個(gè)了解文學(xué)史的讀者都不會無動于衷吧?因此,互文和戲仿仿佛都是為了修復(fù)歷史斷裂,綴連文化碎片,療愈現(xiàn)實(shí)焦灼的手段。
《長日留痕》的主人公那個(gè)英國管家是多么可憫而又可笑,多么枯燥乏味但卻又多么生動有趣,多么像極了一套制服般的僵硬卻又包藏著多少打動人心的情感的力量,他鼠目寸光,全無一丁點(diǎn)歷史的見地,但他卻天使般地飄游在文化歷史的天空上。我們用所謂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原則是很難理解這樣一個(gè)形象的,用現(xiàn)代主義也同樣不能,因?yàn)樗粌H是一個(gè)人物形象,他是作家對傳統(tǒng)英國的一個(gè)文化符號的戲仿。他不是依據(jù)現(xiàn)實(shí)的創(chuàng)造物,也非出自想象,甚至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虛構(gòu),他是一個(gè)綜合的產(chǎn)物。他一方面應(yīng)合著某種關(guān)于歷史的想象,一方面同時(shí)就將這種想象加以了解構(gòu)。他是一個(gè)語言的化合物,同時(shí)又是語言和歷史互文的反諷之物。他是一個(gè)絕妙的形象,但真正的絕妙之處,是作家觸摸到了讀者心靈的某個(gè)隱秘的機(jī)關(guān)。這個(gè)心靈就是現(xiàn)代讀者的心靈,一顆長期以來被認(rèn)作是虛無主義的無可寄寓的物質(zhì)的冷漠之心,未曾想它的情感的機(jī)關(guān)是有的,只是很少有人可以觸摸到而已。
這個(gè)形象是從一個(gè)戲劇性的情境中向我們顯現(xiàn)的。我們覺得那依稀就是一個(gè)喜劇的情境。因?yàn)槲覀冏x者都已經(jīng)預(yù)先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diǎn)上,我們這些無所不知滿不在乎心神渙散的所謂讀者們,站在高處,看到下方的一個(gè)仿佛是人的黑點(diǎn)在移動,他果然是人,我們看見他臨淵而行,危險(xiǎn)至極,但他卻中規(guī)中矩,充滿自信,滿懷著忠誠,儀態(tài)萬方地向著終點(diǎn)而去。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他此行的終點(diǎn),那是一個(gè)失敗的,恥辱的,虛假的終點(diǎn)。這就是喜劇,喜劇人物總是被蒙在鼓里的。作家就這樣預(yù)先滿足了我們作為讀者的優(yōu)越感,于是我們就優(yōu)越起來了。但我們也越來越心里明白,我們所親眼目睹的,是人的失敗,是人的運(yùn)動軌跡,這個(gè)人他是自由的,他擁有自由的意志,職業(yè)的操守,可貴的忠誠,以及愛情和對愛的節(jié)制——愛因節(jié)制而可憫并且可敬,但他卻失敗得如此徹底。這樣,我們的憐憫之心被激發(fā)出來了。那么,這是一出悲劇嗎?顯然也不是,主人公一直彬彬有禮地走在命運(yùn)的塹壕里,未敢逾雷池一步,而且他既非英雄,也沒有受到什么磨難和挫折,他所引起的并非我們的崇敬之心。
他所做的都是瑣碎之事,他本當(dāng)被遺忘,只因他永遠(yuǎn)整潔的制服之下藏著一顆英國管家的心靈,他引起了我們對他長久的凝視。這個(gè)不曾也沒有能力思考命運(yùn)的人,引起了我們對所有人命運(yùn)的擔(dān)憂。這個(gè)拘謹(jǐn)刻板到可笑的人,觸發(fā)了我們這些無情之人的情思。這個(gè)由業(yè)已消失的文化符號戲仿來的文學(xué)形象,引起我們對文學(xué)和人的無法回避的思考。
注:《長日留痕》,石黑一雄著,冒國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017年12月5日于蘭煜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