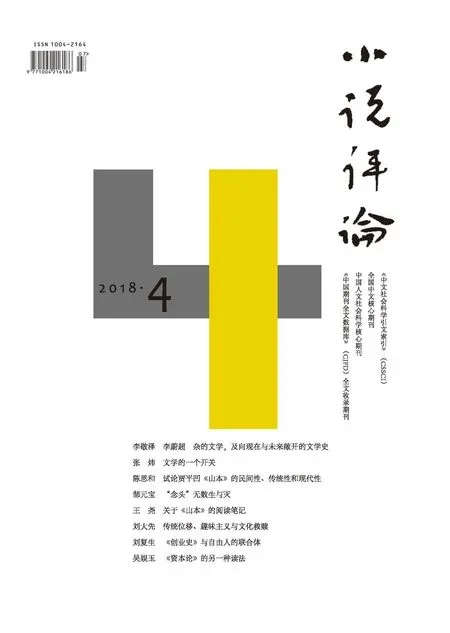經驗的貧乏及其并發癥
——論《平原客》《藏珠記》
呂東亮
李佩甫的《平原客》、喬葉的《藏珠記》都是2017年中國文壇值得注意的長篇小說。兩部長篇在經驗、結構與語言方面都呈現出相似的問題,值得作為一種寫作的癥候提出來討論。
一、經驗的貧乏
李佩甫的《平原客》講述的是由一起副省長殺妻案所牽連起來的人與事,作者對這些人與事的敘述貫徹了他一直以來對于平原人精神生態的關注,作者對人與地關系的理解也秉承了一直以來的“植物與土壤”關系的隱喻。圍繞著副省長殺妻案,作者傾力塑造了三個人物:副省長李德林、副市長劉金鼎以及刑案專家赫連東山。副省長李德林出身貧寒農家,憑借學業的優秀考入大學、出國留學、歸國任教、破格晉升,一步步成長為主管農業的副省長。快速成長的李德林并沒有快速轉變為妻子所期望的優雅的、精英化的成功人士,而是由于美國苦讀生活的壓抑、對家鄉父老的摯愛而變得不修邊幅,在家鄉故舊的包圍與纏繞中化解著內心的焦慮,享受著虛弱的自信和榮光,進而與作為城市大家閨秀的妻子離異,與鄉村女人徐二彩結婚并最終在劉金鼎、謝之長等人的幫助下殺害徐二彩,徹底陷入了鄉土關系構成的泥沼。李德林這個人物形象在李佩甫小說的形象譜系里是有淵源的,他也是一個從鄉村走入城市的平原客,如同李佩甫之前的《無邊無際的早晨》《敗節草》和《生命冊》中的男主人公一樣,斬不斷鄉土的臍帶,卻又為無法全面融入城市而惶恐焦慮,人物形象身上的歷史牽絆感如影隨形。小說對李德林形象的塑造是基本成功的,對其承載的社會歷史內涵的發掘也是深入的。但也必須指出,李德林形象還不夠飽滿,作者對這個形象的審視還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些描寫沒有貼近李德林的內心,沒有做到“理解之同情”。相對于李德林,劉金鼎、謝之長、赫連東山等形象則較為浮表化,劉金鼎出身花匠世家,其命運也因此帶有幾絲神秘色彩,從小說中對其幼年母親失蹤、少年輾轉求學等經歷的敘述來看,作者是有意把劉金鼎作為一種植物描寫其生長的,但隨著后來情節的吃緊,劉金鼎的成長實際上被擱置了,關于他的生命反思也消失了。赫連東山這個形象則流于一般,小說中關于他和兒子之間代際沖突的書寫較為生澀和概念化,沒有出人意表之處。小說中他唯一的較為動人之處可能是一句感慨:“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我的時代了”。謝之長形象也沒有生長起來,作為平原上的“跑事兒”的人物,他的復雜性以及所牽涉的社會經驗顯然沒有在小說中呈現出來,尤其是和李佩甫之前的中篇小說《寂寞許由》中“跑事兒”的郭守道形象相比就更加蒼白。整體看來,《平原客》存在故事淹沒人物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作者對故事的體驗不夠深入、認知不夠透徹。作者雖然試圖寫出時代對于人物的潛移默化的形塑,寫出那種“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平原生存之復雜奧妙,但呈現在作品里的卻是敘述的慌亂與人物的模糊,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平原客》的主要故事情節來自于十多年前發生在河南省的一個真實的副省長殺妻案,人物也大多有原型。在文學史上,依據一個真實的案件進行文學創作,并不鮮見。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名著《紅與黑》就是根據一個真實案件創作的。從社會案件到小說情節,關鍵的是實現事件從新聞性到人文性的轉化,將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社會案件中的人心人性中去。就《平原客》而言,從小說的敘述態度來看,作者對這一案件的探究興趣、書寫興趣是濃厚的,這一案件也刺激了作家理解新的社會經驗的創作欲,同時也對作家解釋新的現實的能力提出了挑戰。面對新現實、新經驗的挑戰,《平原客》作出的回應是不能滿足讀者對李佩甫這一茅獎作家的期待的。《平原客》中,作者對情節的敘述興趣過于濃厚了,有渲染之感,甚至有獵奇等黑幕式小說的傾向。盡管作者增加了一些頗有抒情氛圍的書寫用以烘托人物的心靈,但還是沒能遮蓋小說的通俗氣味,沒有提升小說的文學品質。總的來說,這些問題都緣于作者還沒有把新的經驗想透,作者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消化這些經驗。
喬葉的《藏珠記》如作家自己所稱是一部輕逸之作,尤其是和作者上一部長篇《認罪書》相比,就更加令人感到作品的隨性隨意,甚至帶有游戲的意味。《藏珠記》講的是一個千年不老的處女唐珠和一個出身名廚世家的官二代金澤的情愛故事。唐珠吞下波斯人所贈的寶珠從而千年不老,順利穿越到當世,結識并愛上金澤后便拋開不能交歡的禁忌,以正常衰老為代價與金澤歡愛并結婚生女。與此同時,唐珠走進了金澤的名廚家族,了解了豐富的飲食文化,并與金澤聯手,打敗了曾為金澤父親司機、后來成為金父腐敗同盟者進而成為見利忘義者的房地產公司老總趙耀。《藏珠記》的故事情節主要是三方面的:一是唐珠和金澤的愛戀,在這些故事中,唐珠和《認罪書》中的金金等喬葉小說中女主人公一樣,是一個具有強悍而熱烈的愛欲的女子,小說關于其愛欲的描寫一如既往地大膽暴露;二是關于飲食文化的內容,小說主要是通過金澤親族中人物的敘述呈現的,這些內容是小說中最為出彩的部分;三是唐珠、金澤與趙耀的斗爭,具有反腐敗的意味,但這些情節卻寫得較為模式化,沒有超出流俗的腐敗想象。三方面的情節雖然有所交集,但內在的聯系是松散的,根本原因則是這些經驗是碎片化的,小說對這些經驗的認知和表達也有媚俗的傾向。對世俗人情的體貼,對平民生存經驗和智慧的尊重是喬葉創作的一個特色,也賦予了其作品一種可貴的非精英化的姿態和品質。但這種平民化或世俗化也潛藏著一種危險,那就是對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趨附。在大眾傳媒日益喧囂的今天,真正平民經驗的表達日益變得困難,媒介文化中大眾已然成為被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裹挾的欲望主體,是馬爾庫塞所稱的“單面人”,他們面目模糊、主體虛幻,無法感知到真實的利益狀況,無法獲得一種集體感,只能以分子化的個體形式消耗能量、透支想象。被資本利益控制的通俗文化會源源不斷地向大眾提供廉價的、充滿快感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大多標榜快樂至上、娛樂至死,確實具有令人“沉醉不知歸路”的體驗。在這樣的文化場域中,喬葉的《藏珠記》因為其軟性的文化質地,很容易被歸并吸附到通俗文化的陣營中去,事實上也恐怕正是如此。《藏珠記》的一些套路化、雞湯化的內容,尤其是那些討巧的章節標題,是十分契合通俗文化的興奮點的。如果我們將《藏珠記》與喬葉的《良宵》《月牙泉》等作品相比,就會明顯發現什么是真正的大眾,什么是真正的平民經驗。因為作者太想走輕逸路線了,或者說過于任性了,《藏珠記》中很多有意味的內容完全可以生發出來,卻被作者有意無意地抹去了、撇開了,比如關于美食的書寫,盡管小說中有不少精彩之處,但還是不夠,小說完全可以借鑒陸文夫名篇《美食家》的思維形式,將圍繞著飲食而牽連的社會歷史意蘊表現得豐厚一些,而事實上,小說中關于“守山糧”的描寫就頗有值得深究的意趣。小說關于金澤形象的塑造也有可議之處。作為官二代、富二代,金澤的脾性有些抽象,其間的轉換也有些突兀,小說顯然沒有用心解釋這個人物形象,也就無法將之塑造得更為豐滿。對于富貴階層以及富二代、官二代的成功書寫,在當下中國文學中是較為少見的。這也是一種新現實、新經驗,對此喬葉和許多小說家一樣,沒有準備好。凡此種種,決定了《藏珠記》只能是一部倉促拼貼了諸般經驗的小說。
如上所述,兩部長篇小說都存在與時代真實經驗相隔絕的問題,不僅以往小說那種常見的“自敘傳”式的個人親歷經驗的敘述比較少見,而且經驗的渾然狀態也較為欠缺。這當然和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有關。我們所面臨的當下社會,是典型的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說的“景觀社會”。居伊·德波認為景觀社會所生產的景觀“是自我與世界的邊界的消除,通過世界的在場和不在場對自我進行擠壓,它也是真實與虛假的邊界的消除,通過表象組織所保障的虛假的真實在場,對所經歷的任何真理進行壓抑。”在景觀社會中,文化狀態則是媒介與資本高度共謀并進而牢籠一切的,在這樣一個狀態下,影像與現實、主體與客體、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是顛倒的、混亂的,新聞、廣告、娛樂畫面生成了不計其數的超現實的“景觀”,“景觀”代替了真實的生存經驗,并以消費文化為助力,成為社會經驗的主導性表達方式,甚至成為人們感知社會經驗的唯一方式。景觀社會里的景觀生產,當然是繁多且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優勝劣汰、花樣翻新,真正是“亂花漸欲迷人眼”。景觀社會中的小說創作,無疑要面臨講故事的難度。小說家作為現代社會“講故事的人”,也要應對新的經驗問題。關于現代社會小說與生存經驗的關系,德國猶太裔學者本雅明認為“長篇小說在現代初期的興起是講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他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闡釋道:“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驗,然后把這種經驗轉化為聽故事人的經驗。小說家則閉門獨處,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此人已不能通過列舉自身最深切的關懷來表達自己,他缺乏指教,對人亦無以教誨。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囿于生活之繁復豐盈而又要呈現這豐盈,小說顯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所指的“講故事的人”是指傳統的說書人之類的民間故事傳說的自然的講述者。在本雅明看來,除了“講故事的人”和社會生存經驗具有統一性之外,“講故事的人”所呈現的經驗還具有教誨性,對聽故事的人而言則是增加了一種人生經驗,而小說則只能傳遞并且鞏固現代人的孤獨感,彰顯“生命深刻的困惑”,因而也就面臨能夠為讀者提供教益的經驗的貧乏等問題。《平原客》和《藏珠記》,表面上講的是似乎也是來自民間的道聽途說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已經被大眾傳媒反復講述過,不僅喪失了吸引讀者或聽眾的能力,而且也不能提供教益,經驗只能處于貧乏狀態。在“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這一小說創作的維度上,三部小說也沒有顯出應有的精彩來,靈魂的深度、“生命深刻的困惑”是缺失的。問題還在于,三部小說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書寫時代整體經驗的抱負。就本雅明關于小說家和“講故事的人”的闡述而言,三位作家都是難以被歸類的,他們都想以“講故事的人”的身份創作小說,因而也就必然直面經驗的貧乏這一時代難題。
二、結構的虛弱
在《平原客》和《藏珠記》中,經驗的貧乏導致了結構的衰弱,而結構的衰弱進一步暴露了經驗的貧乏。在傳統的小說敘述中,渾融性的經驗往往自身會提供一個合適的結構,或者依托一個人的成長,或者依托一個重大事件的起承轉合,或者歷史時序本身就規定了結構的樣態。但這三部長篇小說,都無法再享用傳統小說的結構便利,作家只能耗費心力,去嘗試著搭建新的結構,然而這樣的嘗試由于實感經驗的貧乏都顯得較為勉強。
《平原客》的結構,是花開三朵、各表一枝。小說分別講述了副省長殺妻案中的副省長李德林、幫兇劉金鼎以及刑案的偵破者赫連東山的故事,三個人的故事因為刑案而交叉融匯。應該說,這樣的結構是符合事件本身的情理的。但在小說中,三人故事的黏連度是不高的,既缺乏通俗敘述所常見的環環相扣,又缺乏純文學敘述所應該達到的從容老到。當然,作為純文學作家,李佩甫自然不愿把副省長殺妻案敘述成一個坊間流傳的兇殺艷情故事,他之所以以三個人物作為三條線索敘述,就是想呈現平原的復雜性以及平原客的精神惶惑。在作者的設計中,李德林、劉金鼎、赫連東山乃至謝之長都是典型的平原客,他們敏感地意識到社會的變動,努力地去追尋成功,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意志,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時代的紛亂和內心的惶惑。小說一方面想完整地講述副省長殺妻案的全過程——這的的確確是令人震驚、引人深思的新經驗,另一方面又想深入探尋三個甚或更多平原客的內心世界,于是便出現了兼顧的困難。如前所述,李德林的形象相對成功些,但還不夠飽滿;劉金鼎的成長過程顯得有些跳躍,并且時斷時續;赫連東山的形象則顯得有些類型化。小說敘述常常要面臨“事”與“人”之間的矛盾,重視事件的完整敘述,就會壓抑人物形象的完美生成,而凸顯人物的性格心理,則會影響故事的推進、淡化小說的情節感。作者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平原客》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為了兼顧事與人而在敘述上所作的騰挪趨避以及其間的慌張,甚至有些情節更像是事后補充上去的,而這又造成了敘述的支離。在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情節是贅余的,游離于主線之外,而且對于人物的塑造也起不到助力,這無疑是令人惋惜的。在之前的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生命冊》中,基于對大時代經驗的書寫,李佩甫采用的也是復線結構。因為設置了第一人稱敘事人“我”來統率小說中豐富的情節片段,故而整部小說的敘述顯得從容不迫。《平原客》如果也設置一個具有統攝意味的敘述人,可能會彌補一下敘述的支離和結構的虛弱,至少可以使一些情節的補敘顯得自然一些,對于審視人物的內心而言則更加便利妥帖。但即令如此,《平原客》的結構可能還是存在離散性的問題。歸根結底,小說結構所建基的現實經驗還是太單薄了,這些現實經驗用以敘述整個案件是充分的,但用以探究案件中的人物則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作者沒有把這個案件背后的社會現實經驗想透,也沒有把副省長的生命經驗與劉金鼎、赫連東山等平原客的生命經驗在深層次上聯系起來,故而一進入敘述,小說不由自主地被刑案奇聞式的趣味所牽引,追尋人性之變異的旨趣為社會探秘的窺視欲所沖擊。
《藏珠記》的結構也是以唐珠、金澤、趙耀三個人物為線索連接而成。連接的機緣則具有巧合意義。唐珠雖然是從唐朝穿越而來的女子,行動具有自由性,但她結識趙耀和金澤,卻具有偶然性,而且她所舍身相許的金澤就是自己所要報恩的名廚世家的后人。喬葉的一些小說,情節的維系往往依賴巧合,雖然有“無巧不成書”的說法,但也難免為人所詬病。因為巧合背后如果缺乏世事情理的依托,就難免令人生疑。《藏珠記》因為設置了一個既是主人公又是敘述人的穿越者唐珠,所以就沖淡了小說的機巧之感,但也同時呈現了經驗的貧乏。一個按照現實邏輯行進的故事架構,卻接納了一個從唐朝穿越而來的千年處女,不正說明經驗的虛空以使得外在的敘述元素可以隨意嵌入嗎?從這個意義上看,設置唐珠這個穿越者,可能是小說的一個敗筆。當然,小說想以唐珠形象表達現代人的一個欲望困境,既想青春不老,又想盡情盡欲。這種困境也可以說是一種欲望夢想,即長久地、無風險地、高質量地滿足欲望。這種夢想在現實中也只能成為困境,小說中的唐珠、金澤、趙耀也都面臨這種困境。“食色性也”,《藏珠記》中,作者對飲食的書寫精彩紛呈,對愛欲的書寫也一如既往地大膽直露。對于欲望困境中的抉擇及其結果,小說也做出了為普羅大眾所認可的處理。小說以三個人的故事為線索,而且讓三個人分別作為敘述人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內心生活,呈現各自的立場,既可以見出利益格局中欲望的糾葛,又可以很好地把飲食文化、反腐敗、男女情愛等敘述元素連接起來。但問題在于,三個敘述元素的粘合度較低,對于欲望糾葛的描寫又太過簡單。飲食文化、反腐敗、男女情愛都是大眾文化所喜聞樂見的元素,作者統籌這三個元素的書寫,很明顯有取悅大眾的意味,但可能是因為太過于在意讀者的反應了,作者在寫作時對每一個文化元素都頗費心力,反而導致了總體上的離散感。就是說,單看反腐敗、飲食文化或男女情愛來說,都寫得相當不錯,可是三個文化元素的關聯性、有機性卻沒有呈現出來。飲食文化與男女情愛之關系的書寫顯得有些牽強,反腐敗與男女情愛之關系的書寫顯得有些疏離,而飲食文化和反腐敗之間的關系則著墨甚少。作者當然也意識到了這樣的缺失,所以在三個敘述人的講述中,分別作了彌補性的交代,其中一些感慨議論的文字也不乏見地,但整體上來說,這樣的彌補收效甚微,結構的虛弱無法得到大的改善。
三、語言的衰疲
經驗的貧乏也帶來了兩部長篇小說語言上的一些問題。李佩甫的《平原客》的語言總體上顯得有些生澀。這種生澀不是指作家的語言修養和功夫不夠,而是相對于語言所呈現的經驗而言的。相對于李佩甫之前的作品尤其是和《平原客》具有相似性的《生命冊》而言,語言的那種雍容之感就減少很多。在《平原客》里,具有力道的語言、富有抒情性的語言、靈動的語言也頗多,但似乎大多沒有契合小說敘事的節拍。語言的流速感覺太快了,太過慌亂了,缺乏那種讓人在閱讀中駐留欣賞進而回味無窮的魅力。既然小說主要是寫人,寫平原客,就不妨多一些抒情性的語言,經營幾幅典型性的畫面甚至幾個含蓄蘊藉的意象,如此可能會沖淡小說的那種新聞感,提升小說的文學品質。尤其是面對一些作家自己不太熟悉的場景時,比如赫連東山和兒子之間的沖突時,不妨少一些言不及義的場景描繪——這些場景描繪流于套路化,實在也說不上有什么精彩之處——多用一些語言描寫赫連東山的內心世界,充分寫出他內心的惶惑,進而寫出一代平原客面對時代變動的焦慮感。語言本身是有形象的,領會一種語言就是領會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狀態。巴赫金認為:“語言要成為藝術形象,必須要與說話人的形象結合,成為說話人嘴里的話語。”也就是說,小說的敘述語言自身會生成可以被感知的形象,這形象和敘述人以及敘述人所在的生活場域連接在一起,成為作品形象世界的有效參與元素。《平原客》中的故事是由一個全知型敘述人完成的。我們從敘述語言所生發的形象中可以窺測出,這個敘述人是惶惑的,內心的情緒是雜亂的,或者說這個敘述人的形象狀態是模糊的、破碎的。講故事的時候,這個敘述人時而表示了對新經驗的驚異,甚至有獵奇性的欣悅,時而又有不確定、不堅定的人生感悟,甚至連抒情也無處可抒了。這些大概都是經驗的貧乏所造成的。
《藏珠記》的語言流利嫻熟,如山中的小溪一般歡快地流淌。喬葉在《藏珠記》的后記中說:“這個長篇,我想讓它偏輕。”這輕首先就顯現在語言上,具體來說就是語言的軟性化、時尚化。因為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設置成敘述人,人物的自我言說同時也是情節敘述,所以小說的敘述語言并不多,語言形象和敘述人的形象、主要人物的形象是融為一體的。而這些主要人物及其關聯情節都是具有比較濃郁的大眾文化特征的欲望敘事,就不能不使得小說的語言向消費文化靠近。打開小說的目錄,我們會發現許多俏皮而帶有強烈當下感覺的小標題,小說正文的語言也是活潑有趣的。但俏皮也罷、活潑有趣也罷,都是在大眾文化的意義上被確認的,就創造有品質的文學語言而言,俏皮等等可能并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傾向。它可能恰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怠惰,因為襲用或化用流行文化中的語言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相對于根據自己的實感經驗創造語言來說。《藏珠記》第34節標題為“性感”,里面提到唐珠對金澤的感受,有這么一段:
不瘋魔,不成活。現在的金澤越來越用功,越來越專注,然而危險的是,他在我眼里也越來越性感,性感的地方簡直無處不在。他穿廚師服自然是性感的,穿上普通的襯衣則是另一種性感。夾克敞著懷是撒開來要擁抱的性感,拉鏈合住是內斂高冷帶點兒神秘的性感,卷起袖子是性感,把袖口的紐扣扣緊也是性感。他擦油煙機,擦地板,擦冰箱,擦玻璃,擦燃氣灶,換燈泡,通下水道,統統都是性感,而他在做菜時準確利落的一切:淘米,洗菜,揉面,煎炒烹炸,盯著鍋里的菜肴時目不轉睛的樣子……更是性感分值勁升到爆。
性感是大眾文化所熱衷的詞匯,文學作品書寫性感亦未嘗不可。但《藏珠記》中的這段關于性感的描寫,并沒有將其與大眾文化書寫區別開來,而是認可并引用了消費文化中的表述,并且幫助擴張了那種粗糙的卻是得勢的生存幻覺。其實,小說完全可以去展開分析、細細闡說金澤所帶給她的可以命名為性感、卻有著非同尋常的韻味的生存感覺,這樣一來,性感這個詞就脫離了大眾文化場域而得到了文學語言的救贖。《藏珠記》中的類似的段落很多,可惜大多語詞沒有被作者用文學語言救贖。喬葉早年寫作了大量的時尚美文,對流行文化機制、對讀者大眾心理了然于心,對大眾文化中的語言狀態也有著深入的體認,但這種體認應該作為作家更新語言的背景,而不應成為作家從中征用語言的便利。喬葉近些年的小說創作,在語言的把握上是好的,她有效地采用日常化的語言對平民生存進行體貼式的書寫,成功地抗衡了大眾生活中愈發強勢的時尚化語言表達而自立面目,實在是十分難得。但長期游走在大眾文化的邊緣,難免有所浸染而喪失文化警惕,進而認可大眾文化的快感原則而進行無難度的語言表達。這種傾向,也反映在《藏珠記》中。《藏珠記》中的經驗內容,尤其是一些美食文化和文史故事,寫成一些散文是比較合適的,一定要寫成小說,就必須用有力的語言去統合這些經驗,而熔鑄這種語言則需要更周密、更深入的思考。可惜的是,作者沒有如此功夫去熔鑄語言,只好借用大眾文化的語言來做情節的粘合劑了。
《平原客》和《藏珠記》書寫的都是當下帶有總體性意味的現實經驗,也都屬于正面強攻的現實主義寫作。面對當下變動不居的現實以及日趨膨脹的大眾傳媒,作家們的困境有增無減。李佩甫、喬葉如此,其他作家也一樣面對經驗的貧乏及相應的并發癥。余華的《兄弟》上半部寫改革開放前的生活寫得從容,下半部寫改革開放后的生活寫得慌亂;格非的《望春風》也是如此,小說的后半部分寫改革開放以來的生活時推進得明顯快一些,經驗的全面性也明顯不足。這大概都是作家沒有把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想深想透的結果。面對新世紀、新時代的經驗,如何想深想透就是一個更加讓人焦慮也更加讓人著迷的問題,而具有高峰意義的作品也將在對這個問題的卓越應答中得到誕生。
注釋:
①[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頁。
②漢娜·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99頁。
③李佩甫:《平原客》,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小說在第31頁寫道:“四年后,劉金鼎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已是主管農業的副省長了,那年他四十七歲。”無論從小說內部世界還是現實世界來說,這都是不合情理的。劉金鼎從大學畢業生到常務副市長,盡管有李德林的幫助,至少也要經過十多年的歷練,而李德林不可能做了十多年的副省長還被劉金鼎以為有提拔至中央的可能。小說在時序上的錯亂也是小說結構虛弱的一個表現。
④[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頁。
⑤⑥喬葉:《藏珠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頁、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