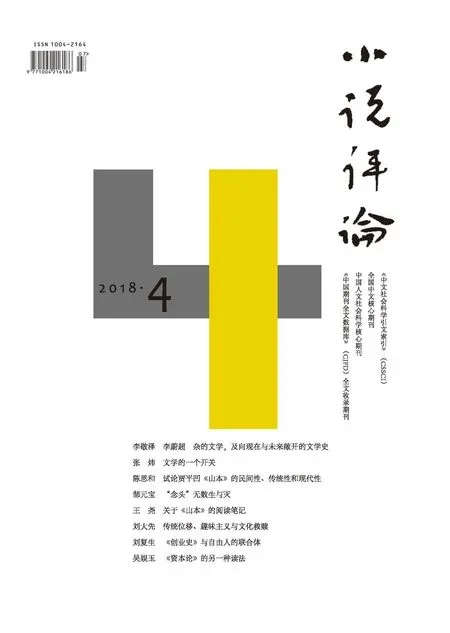文學版圖的新拓展
——談賈平凹長篇小說《山本》
陳思廣 李雨庭
賈平凹是當代文壇中少有的幾位橫貫新時期且至今仍勤奮追夢的文學大家,也是一位筆耕不輟、不斷創造文壇神話的文學奇才。也正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出版后都會引起文學界的強烈反響,也因之被稱為“賈平凹現象”。2018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步出版發行的長篇新作《山本》,是他奉獻給讀者的第16部長篇小說,也是他醞釀多年立志要寫的“秦嶺志”。小說的出版自然引發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不僅濃墨重彩地書寫了秦嶺這方水土養育的子民們平凡、神性而又略帶英雄色彩的山民性格,也細致入微地展示了秦嶺一帶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等奇異景觀,令人眼界大開。小說以亙古蒼茫的秦嶺深處一個叫渦鎮的地方為中心,以童養媳陸菊人的三分胭脂地為引子,以渦鎮梟雄井宗秀和女杰陸菊人“英雄愛英雄,叔陽愛管仲”的惺惺相惜又漸行漸遠的人生經歷和命運結局為中心線索,在歷史的動蕩與滄海巨變中,將普通人的大志向演繹成平凡人生與命運的多重交響曲,亦由之勾連起秦嶺腹地人事自然的紛繁變遷,顯示出作家非凡的藝術才能。而作家在這場動蕩的風云變幻中展現的秦嶺兒女所特有的性情和氣概,如陸菊人的睿智善良、郎中陳先生的圓融通達、地藏菩薩廟師父寬展的悲憫仁慈等,使小說在表現成王敗寇的永恒定律中透出一種人道主義的溫度和悲憫情懷。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與賈平凹同時代的作家開始逐漸由關注城市轉向回歸故土,并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鄉土小說,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張煒的“蘆青河系列”,葉兆言“秦淮河小說”,賈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其中賈平凹的商州書寫成為當代文學版圖中一道溫潤而古樸的文學風景。雖然商州只是秦嶺的一個點,秦嶺卻是橫貫中國中部且東西走向的大山脈,被尊為華夏文明的龍脈。受秦嶺庇佑的陜西人,更是自恃為龍脈的正統后裔。出生于秦嶺深處的賈平凹自然對這一龍脈及其風情情有獨鐘,也被他不斷地寫進《商州》《浮躁》《懷念狼》《秦腔》《古爐》《老生》《高興》等一系列作品中。通過對秦嶺風土人情的深入摹寫,賈平凹對秦嶺的刻畫和感情亦因之而越來越深入、成熟,越來越清晰、敬畏,并最終寫就了這部細致、厚實、堪稱全面展現秦嶺人物山水、鳥獸蟲魚、神鬼禮俗的“秦嶺百科全書”。《山本》不僅表現出秦嶺人家的自然生態、經濟營生、更表現出一種對人事、對歷史的新認知,為當代文學的版圖開拓了新疆域。具體而言,我們認為,其突破意義至少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用平淡冷靜的筆調表現了身處秦嶺山區地帶的英雄人物的庸常生活,真實表現了出入于平凡日子的英雄的生與死,拓展了英雄人物描寫的新視閾。“英雄”歷來在人們心目中生得偉大、死得壯烈,也多是一種“神”一般的超凡存在。新時期以來,英雄開始由“神”回歸到“人”,“凡夫俗子”式的英雄書寫成為文學的常態:莫言《紅高粱》中的余占鰲、蘇童《米》中的端白、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的許三觀等等,都以各自的人格樣態去生存、去抗爭,不卑不亢,表現出雖有英雄氣概但仍不失為凡人的英雄品格。賈平凹對“英雄”的書寫,也是遵從生活的本相,以回歸歷史現場的姿態書寫英雄的成長足跡。無論是《浮躁》中不畏權勢巧妙斗爭銳意進取的金狗,還是白手起家奮斗立足城市后被名利腐蝕的莊之蝶(《廢都》);無論是生于荒村而立志于出人頭地的夜霸曹(《古爐》),還是以拾破爛為生卻自詡比城里人高貴的劉高興(《高興》)……賈平凹筆下“英雄”的血性和煙火氣越來越接近于普通人、身邊事,越來越體現出英雄的平凡生活和庸常點滴。到了《山本》,賈平凹更注重用基層生活的磨礪來表現“英雄”的長成,在現實生活與七情六欲的日常細節中表現英雄的生存樣貌,將“行動著的人”與“人的行動”表現得凡俗而樸實。作家用平淡的筆調書寫秦嶺深處的渦鎮英雄井宗丞、阮天保和井宗秀,用日常的愛怨情仇、名利爭奪來表現井宗丞、井宗秀等英雄的成長過程、人生選擇和與眾不同的性格氣質,可謂真實自然。你看,為籌集游擊隊的經費,井宗丞讓隊友綁票自己的父親,而自己卻在成為威震一方的游擊隊領導之際被阮天保的護衛邢瞎子一槍斃命;井宗秀在龍脈護佑的心理暗示下步步為營成為渦鎮最大的掌權人,為了鞏固地盤和勢力,他拉攏麻縣長、火燒阮家宅、攻打保安團、建鐘樓改造渦鎮,正直事業穩定之際又被阮天保打死,死得悄沒聲息,甚至有些窩囊;而阮天保事事趨利避害,善于鉆營,被井宗秀打散后投靠井宗丞,借游擊隊的勢力保存壯大自己的實力,利用共產黨的“反右傾主義”,除掉井宗丞,又利用井宗秀疏于防范之際結束了對方的性命,反成為渦鎮滄桑巨變中的最大贏家。阮天保成為最后的勝利者,實在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整個過程作者沒有任何鋪墊和伏筆,讓一切變得自然而又平常。但正是這種“英雄”的平淡結局,才強烈地沖擊了讀者既有的英雄觀念,解構了英雄必然轟轟烈烈的生與死的“歷史必然”。作家讓英雄回歸到歷史現場和生存本相中來,將他們視為與普通人一樣都只是滾滾歷史大潮中的一粒塵埃,與大自然的草木鳥獸一樣,實實在在且又平平常常。這種回歸本真的人生觀、英雄觀,還原了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本來面目,也將生活的本相原原本本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對此,賈平凹坦言,如此處理是因為現實生活也往往是這樣,很少有人死得轟轟烈烈,大多是或偶然或毫無意義就死了。賈平凹自覺地將英雄人物還原到歷史和生活的本然狀態,用新的歷史觀、英雄觀來重新建構歷史生活中的英雄,具體而微地展現現實生活中的人性百態,可以說,作家已經進入到了對人事書寫“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至高境界。掩卷體味,《山本》實為“人本”,小說中的英雄人物的生死和秦嶺的草木鳥獸一樣,普通而又自然,而人生平平淡淡的終結何嘗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樣態呢?
2.用人物大量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構成對歷史的敘述與闡釋,將宏大歷史消解于鮮活生動的民間記憶中,拓展了文學新的審美形態。賈平凹在《山本》中對歷史和人物的敘述,完全不同于傳統小說中宏大歷史視野里的帝王將相,也不同于新時期稗官野史的個人主義,而是關注歷史的空隙與人物庸常瑣碎的小細節,用活躍在歷史小舞臺上的非凡人與普通人的雞零狗碎來表現中國動蕩不安的大歷史,使之成為整個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政治變幻的歷史縮影。歷史的崇高理想也就在這里化為生活的瑣碎與庸常,成為一出出人生常見的正劇、喜劇,甚或悲劇。阮天成的保安隊搶走了預備團的12只騾子,鎮上居民都找陳來祥索要損失,陳來祥卻像賊一樣躲著不見,于是山民們也不在北門口抬石條壘門洞了,反都到皮貨店來,有的拿皮子,有的搬家具,更多的人則說,陳掌柜,我們知道你拿不出錢來賠,我們也不強取硬奪,但我們就靠騾子過活的,現在沒有騾子就只能在你店里。這里,沒有同仇敵愾時的慷慨無私,只有各自為己的生活的法則與現實的訴求。保安隊押著人質喊井宗秀投降,有家人在人質里的居民承受不了,咆哮大鬧,幾個婦女還攔著陸菊人要求她去給井宗秀說情,否則她們也不活了要陸菊人一起死。這里,同樣也沒有大敵當前時的同心同德,有的只是每個家人的私情與訴求。對改變渦鎮世事的陸菊人的愛情、人生的書寫,作家同樣處理的稀松平常:父親因為還不起楊掌柜的棺材錢將她嫁給楊家做童養媳,丈夫少不更事大大咧咧,陸菊人在失望哀嘆中生下兒子剩剩,后來丈夫在誘騙阮天保時大腿中槍流血而死,兒子又從井宗秀的馬上摔下來成了跛子后做了藥店的學徒。她一心認為龍脈能成就井宗秀的人生,處處維護他的威嚴,為了讓花生能配得上井宗秀,陸菊人教花生怎么做女人,怎么做飯,怎么行、走、坐、站,怎么對待男人,服侍男人的衣食起居,苦口婆心,事無巨細,簡直就是秦嶺地區的“女戒”。賈平凹用平實的觀念,表現人物在世態人情、吃喝拉撒中的日常紛爭,將歷史的大事溶解于雞零狗碎的潑煩的小日子中,讓時間在瑣碎的細節中凝滯,而宏大的時空和歷史事件則被具化為渦鎮人們為日常的生活訴求而引發的爭權斗利的計較之氣與生活場景。于是,所有的崇高與偉大、渺小與卑微,都是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與生活本相。《山本》以一種反史詩、反英雄的姿態,借助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民間的認知記憶來表達對通常的歷史觀念和政治意識的灌輸與反叛,表達了別樣的歷史的真實。所以,《山本》沒有讀者一貫所能感受到的那種宏大、震撼的歷史和鮮明的性格與特殊的人物命運,他們只是渦鎮五谷雜糧養育的平凡子民,縱然有強大的時間磨礪和命運之神的觀照,也只能以一種平淡的、自然的本能存立于世,生死如草芥、如螻蟻。作者將記憶中或知識庫里的內容都匯集在了小說中,命運、時機、神諭、地利等等,很難說清是哪種力量主導人物的命運轉折和歷史的發展進程,或許這些都不是(就像龍脈也保護不了井宗秀一樣),一切偶然就是必然,一切必然也就是偶然。從《秦腔》《古爐》《老生》到《山本》,賈平凹用日常細節激活被遮蔽的民間力量,重新喚起那個鄙陋又強大的民間本相,樸素而自然。正是作家對生命的存在與消亡、對政治歷史風云變幻有了一種來自民間的大樸素和大悲憫,塵埃落定后,英雄與凡人的是非成敗都是“轉頭空”,才使我們對歷史有了新的認識,有了新的體味。這才是真實的歷史,也是作家欲意給我們復現的秦嶺的真實的歷史。賈平凹寫出了對歷史的新感悟,當代文學也因之呈現出新的審美形態。
3.對秦嶺山水、鳥獸、花木、神鬼、時令節慶、婚喪嫁娶、絕活土話的詳細書寫,擴大了當代文學表現的文學版圖。中國鄉土文學自20世紀20年代由魯迅開拓以來,在鄉村風情的展現上,自成一脈又各具特色,如沈從文傾心于對邊城人性自然樸素的野趣描畫,趙樹理
側重于對山西民間俗諺俚語的藝術轉化,而汪曾祺鐘情于“最后一個”的民間技藝的鋪陳銘記;葉廣芩、遲子建醉心于鄉土風情與人物的性情交融,等等,都為中國鄉土文學增添了別樣的風景。而賈平凹對鄉土的書寫“立此存照”的意圖十分明確,他用文字記錄鄉土在城鎮化現代化進程中的衰落和消亡,尤其是那些被現代文明和科學漸至遺忘的民間藝術和信仰,在賈平凹的筆下開始復活起來。《山本》小說的構思與命名就是他為秦嶺書志的欲望再現。因此,小說中關于秦嶺的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作者都盡量詳其物態、性狀以及掌故傳說,尤其是秦嶺所獨有的物種,作家更是不厭其詳。作家痛惜癢癢樹瀕臨滅絕,于是讓它長在了陸菊人家的院子里;可以洗衣服的皂莢樹成了“渦鎮之魂”;飽含民間智慧和藝術的彩繪成了渦鎮梟雄井宗秀的拿手絕活;預兆吉兇的蝙蝠和水鳥成為起承轉合人物命運的先知神諭;用鐵水耍火花的民間雜技,biangbiang面、醪糟酒、磚茶、金蟾、放蜂的營生、麻縣長對草藥和動物的習性的整理、寬展師傅做樂器尺八的方法、花生出嫁的規矩禁忌、陳先生開處方的藥性與病人性情結合的原理等等,作家都不惜筆墨地予以展示,甚至不惜以大量的無關于情節發展的風物介紹作為閑筆,備忘錄式地詳細記錄并且反復點染其奇特之處,使其成為斑窺秦嶺博大深邃的文學窗口。可以說,賈平凹對秦嶺的細致書寫不僅記錄了大山的地情地貌,更勾畫了其獨特的山水特色與風土人情。這當然關涉到作家對秦嶺地域特性發自內心的喜愛和銘記,關涉到小說敘述藝術甚至文學創作問題。他已不是純粹為了寫作而寫作,而是想把自己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對人生、命運的感悟塞入小說,所以,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出,這部近50萬字的《山本》似乎就是其對生命認知的一個總結:菩薩一樣的寡婦、畫匠、奮斗者、“閹割”者、智慧的民間星相大師、對未知世界的敬畏、對瀕臨滅絕的樹木習俗的銘記等等,盡現其中。豐瞻的細節盡量照顧到方方面面,即便龐雜而瑣碎也在所不惜。為使秦嶺的風貌顯得更為真切,他甚至用地方性土話語詞、句法結構來體現秦嶺兒女的一種生命情態。秦嶺作為陜西人日常生活的特定性背景,成為賈平凹作品最容易辨識的身份印記,成為當代文學最為鮮明的身份印記。我們也因之可以說,《山本》是最秦嶺、最民間、最中國的小說。
《山本》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風云激蕩的歷史充分具象化、細節化,以廣袤的秦嶺為背景,用瑣碎的日常和普通人構成小說的血脈溫度,以一種專注于細節的修辭姿態,摹寫出秦嶺世界的人間世象,挑戰了既有的敘事思維和表現方法,實現了文學版圖的新拓展,作家對歷史和英雄的反傳統書寫不僅顛覆了人們的慣常認知,而且對歷史的敘述展現出新的途徑和審美性開拓,這無疑是賈平凹對當代文壇的新貢獻。不過,我們也看到,在《山本》中,一些看似豐富的文學細節卻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人物的個性亦淹沒在過于詳細的日常敘述和無關緊要的人物閑筆中,這多少沖淡了主要人物也即是典型人物的描寫。在敘述過程中,敘述者“搶話”甚至代替故事人物說話,語言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干擾痕跡也時常出現,而作品中一些語言過于粗鄙化等,更大大妨礙了讀者審美趣味的進一步生成。我們認為,這些出現在《山本》創作中的創作問題,也當引起賈平凹先生的充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