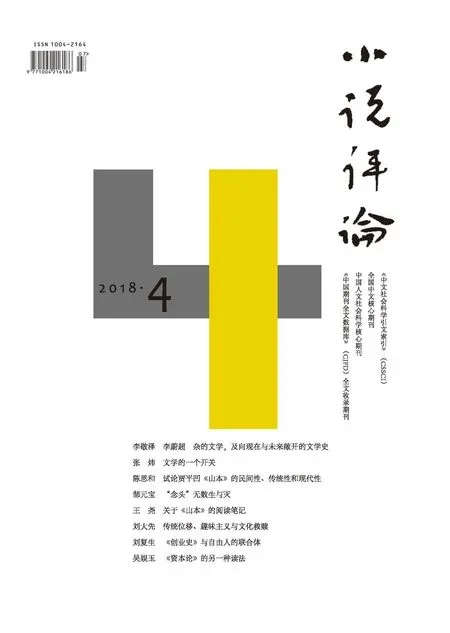關于《山本》的閱讀筆記
王 堯
一
在《山本》未在收獲發表之前,聽朋友說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新作原名為《秦嶺志》,后改為山本。我索來《山本》電子文檔,初讀時也以為“秦嶺志”是更妥帖的書名,細想,賈平凹不以“秦嶺志”作為一本小說的名字,或許因為他迄今為止都在寫一部叫《秦嶺志》的大書。“山本”是“秦嶺”的一座山峰,一座高峰。賈平凹似乎并不想以一本書,即便是最重要的小說之一,消費掉“秦嶺志”。
二
如同我們意識到的那樣,這些年賈平凹每部長篇小說的“后記”作為“副文本”,幾乎都抵達小說家的靈魂深處,穿透小說文本。讀《山本》“后記”,我想起賈平凹寫于1985年的《自傳——在鄉間的十九年》,《自傳》堪稱是賈平凹的“心理傳記”。以此相關聯,我們可以讀到賈平凹的“秉性”如何在在秦嶺、出秦嶺和再回秦嶺的循環中養成。《山本》“后記”,也可視為《自傳——在鄉間的十九年》的“后記”。
1972年4月的最末一天,19賈平凹離開了商山,走出了秦嶺,到西安讀大學。十多年以后,賈平凹回憶說:“看著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車站,淚水婆娑的叮嚀這叮嚀那,我轉過頭去一陣迅跑,眼淚也兩顆三顆的掉了下來。”他不知道走出秦嶺后會不會從此不再孤獨和寂寞,這樣的記憶刻骨銘心:“我不喜歡人多,老是感到孤獨。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條臺階上,看著那遠遠的疙瘩寨子山頂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一只很大的鷹在空中盤旋,這飛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樣沒有一個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藍瑩瑩的長有艷紅尾巴的蜻蜓無聲地站在荷葉上,我對這美麗的生靈充滿了愛欲,喜歡它那種可人的又悄沒聲息的樣子,用手把他捏住了,那藍翅就一陣打閃,可憐地掙扎。立即就放了它,同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茫然。”賈平凹說他的這種“秉性”在上學后更“嚴重”了。
盡管這樣的孤獨和寂寞一直伴隨著賈平凹,但我在這是篇《自傳》和類似的文字中,印象更深的是少年賈平凹萌生的莊子式的“物我”關系。從1985年的《自傳》,到《山本》的“后記”,賈平凹終于悟透了《道德經》和《逍遙游》的不同:“一日遠眺了秦嶺,秦嶺上空是一條長帶似地濃云,想著云都是帶水的,云也該是水,那一長帶的云從秦嶺西往秦嶺東快速而去,豈不是秦嶺上正過一條河?河在千山萬山之下流過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萬山之上流過是我感覺的河,這兩條河是怎樣的意義呢?突然醒開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學,莊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學。這就好了,我面對的是秦嶺二三十年代的一堆歷史,那一堆歷史不也是面對了我嗎,我與歷史神遇而跡化,《山本》該從那一堆歷史中翻出另一個歷史來啊。”
三
賈平凹在古廟里讀完小學,古廟教室的四壁上端畫滿的那些山水、神鬼、人物,不僅是他成長的環境,而且熏染了他的思維方式、精神特質和藝術感悟。
與此相關的神秘氣息,對賈平凹而言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娘生我的時候,上邊是有一個哥哥,但出生不久就死了。陰陽先生說,我想那面炕上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個八個也會要死的。娘卻懷了我在第十月的日子,借居到很遠的一個地方的人家生的,于是我生下來就‘男占女位置’。穿花衣裳,留黃辮撮,如一根三月的蒜苗。家鄉的風俗,孩子難保,要認一個干爹,第二天一早,家人抱著出門,遇張三便張三,遇李四就李四,遇雞遇狗雞狗也便算作干親。沒想我的干爸是一位舊時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寫銘錦。”可以說,這位“干爸”是古廟墻上的人物之一。賈平凹小說中的很多文化人是這位私塾先生的分身。
墻壁上的山水、神鬼和人物,多少年來一直在賈平凹的文本中“神出鬼沒”,現在又更大規模地集結在《山本》中。用賈平凹的話說,《山本》打開了一扇天窗,神鬼要進來,靈魂要出去。
四
《山本》的寫作也是一種困惑中的寫作。2015年構思《山本》時,內心極其糾結:“面對著龐雜混亂的素材,我不知怎樣處理。首先是它的內容,和我在課本里學的,在影視上見的,是那樣不同,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諱。再就是,這些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我想我那時就像一頭獅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鉆進偌大的荊棘藤蔓里,獅子沒了辦法,又不忍離開,就趴在那里,氣喘吁吁,鼻臉上盡落些蒼蠅。”(《山本》后記)
這不是賈平凹一個人的困惑。即便在歷史學界,多年來關于“大寫”的歷史和“小寫”的歷史的合法性之爭從未停止過。在談到歷史敘述時,埃爾頓反對創造科學化的或“大寫”的歷史,他認為任何的定論真相和元敘事(任何的大寫歷史)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那些沒有大力支持小寫歷史的剔出正規歷史/歷史學家的范疇。而在另一些歷史學家看來,埃爾頓的“歷史學原理”其實也是一種“信念”和“偏見”。這種歷史敘述的困境,同樣反映在文學的歷史敘事中,“宏大敘事”解構與建構的紛爭便是例證。就小說寫作而言,當作家重新敘述歷史時,往往是想打破曾經的“信念”甚或“偏見”。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歷史敘事,不是告訴我們歷史“是什么”,而是告知我們歷史“不是什么”。如果還用這樣的句式表達,賈平凹的小說不是告訴我們歷史是什么,而是說歷史不是什么。這其實是賈平凹多年創作的一個軌跡。在《山本》之前的《老生》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我以為要讀懂《山本》,需要先讀懂《老生》。關于現實的敘事也是如此,《秦腔》敘述了已經不是什么的“鄉土中國”。當賈平凹敘述了歷史和現實是什么時,他和被規定的“信念”和諧,如《浮躁》《土門》等,當他說不是什么時,比如《廢都》遭遇的那種劇烈批判,正意味著小說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某種信念或偏見之下的歷史敘事或現實書寫發生了劇烈沖突。
從一堆歷史中翻出另一個歷史來,這是賈平凹的《山本》。在這里,賈平凹將歷史涂上了另一種色彩,或者寫成了另一種隱喻:“過去了的歷史,有的如紙被漿糊死死貼在墻上,無法扒下,扒下就連墻皮一塊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邊爬滿了蟲子和苔蘚,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還是蟲子和苔蘚。”他由此生出的疑惑和忌諱是:“這一切還留給了我們什么,是中國人的強悍還是懦弱,是善良還是兇殘,是智慧還是奸詐?無論那時曾是多么認真和肅然,虔誠和莊嚴,卻都是佛經上所說的,有了置礙,有了恐怖,有了顛倒夢想。”
五
我們不妨說,《山本》是一本寫“山”的小說,而非寫“人”的小說。如果上溯現代文學時期,可以發現《山本》有著非常明顯的譜系,那就是蘆焚的《果園城記》、蕭紅的《呼蘭河傳》——它們同屬于為一個地方作傳的小說。在此類小說的文本結構中,“地點”占有著高于一切的中心地位,所謂的“人物”完全是內屬于“地點”的結構部件。
從文本構成的內部來看,“人物”并不具備高于動植物或山水景物的優先性,這種文本策略本身就曲折地映射出賈平凹本人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與其說是“賈平凹的”世界觀,還不如說是緣起于莊子的“齊物論”。賈平凹在后記中是這樣表述小說中的“人物”的:“一次去了一個寨子,那里久旱,男人們竟然還去龍王廟祈雨,先是祭豬頭,燒高香,再是用刀自傷,后來干脆就把龍王象抬出廟,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們在家里也竟然還能把門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為XX神,XX公,XX君,一一磕過頭了,嘴里念叨著祈雨歌:天爺爺,地大大,不為大人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風調雨順長莊稼。一次去太白山頂看老爺池,池里沒有水族,卻常放五色光,萬字光,珠光,油光,池邊有著一種鳥,如畫眉,比畫眉小,毛色花紋可愛,聲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葉寸荑,它又銜去,人稱之為凈池鳥。這些這些,或許就是《山本》人物的德性。”
可以發現,“人物”在《山本》中已經消隱在“自然造物”之中,本身淡出而成為“混沌”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典現實主義作品的“環境”描寫是為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那么在《山本》中,人物/環境都是平等同一的。天地——人——神——鳥獸萬物齊一,甚至可以達到相互轉化的地步。“院子東邊的墻里有了一朵花,花在行走著,噢,那不是花,是蝴蝶。”由此可見,花和蝴蝶是同一的,繼而“井宗秀癡眼看著,一朵花就飛起來,飛過了墻頭,在街空中忽高忽低,扭頭看時,那不是花,是一只蝴蝶,而遠處站著陸菊人。”花便成了蝴蝶,蝴蝶又牽引著陸菊人。所以花蝶人都是同一的。此處,豈不是可以看出“莊周夢蝶”的印記?
六
這種“造物”之間互相“轉化”的例子本身將會成為構成小說文本審美特征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有這種觀念,所以小說內部的結構元素可以自由地“淡入淡出”、相互轉化生成,從而使得文本具有極強的律動感,獲得一種“水性”。一切文本構件在文本“空間”中取消了高低等級次序,全都莽莽蒼蒼混融一體,甚至達到“作者”消泯的境界,從而獲得一種均質同一的境界,一種天人合一的蒼茫至境。
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曾經梳理出中世紀時期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造物”主義的傾向,“生命”在那一時期的作品中被凸顯出了極強的“生物性”,從而伴隨著“升華”的消失。奧爾巴赫的論述建立在基督教神學的論述系統之上,而在此處我們可以策略性地借此一表述描述賈平凹小說中的“人物”,《山本》中的“人物”也有著非常明顯的“造物化”的傾向。所以《山本》中的人物都像葦草一樣易折,“人物”的死亡并沒有一種“升華”的沖動——與此可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革命現實主義的文本中英雄人物之死的“主題升華”。由此可以看出賈平凹的史觀的“叛逆性”,這種“叛逆性”在后記中顯示出了某種敘事的焦慮。因為“造物”傾向的出現,所以原本的“階級”這一敘事層面被自然而然地取消了,“自然”在《山本》里獲得了戰勝“歷史”的地位,甚至所謂的“階級斗爭史”被納入了“自然史”的論述框架,這之間的駁詰、對話耐人尋味。
有人說:一個認識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頭里,而非十字架上。賈平凹接著這句話說:《山本》里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寫戰爭的書,只是我關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這木頭和石頭中去了。
七
《山本》這個題名是非常具有哲理意味的,相較于《秦嶺志》而言,顯得更加形而上。就像“山”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本身就不是一種純然具象的形而下事物,它充分浸透著“精神”的質素,所謂“山水精神”,正是此意。而“本”更是如此。賈平凹自己在后記中從“發聲學”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他的嬰兒發聲比喻就將《山本》的寫作置于一種非常具有根性的文化史氛圍之中。所以我們讀《山本》,覺得它莽莽蒼蒼,氣象泱泱,皆因它分享著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初音”。這種“初音”從《山海經》《道德經》《莊子》中流溢而出,注滿了《山本》的字里行間。所以《山本》內部有非常豐富的潛藏文本,這些文本各自的“傳統”都在形塑著小說,使小說具有著一種非常復雜的“厚度”。
《山本》的語言,非常類似于《秦腔》和《古爐》。整部小說中,形容詞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小。語言就像隨著物的流動緩緩滲出的,具有非常明顯的流動性。比如在《山本》的開始部分有這樣一句話:“話剛說完,廟梁上掉下來一條蛇。她拿了樹枝子打蛇,蛇身上一坨大疙瘩跑不動,就往出吐,吐出來了一只蛤什螞。蛤什螞還活著,陸菊人就把蛤什螞放生到樹林子去了。”。句子前遞后接,中間都是動詞名詞勾連,自然流暢,宛如流水。
賈平凹“密實的流年式的”語言既用于敘述也用于人物對話,從《秦腔》開始的這種幾乎讓一些讀者覺得喘不過氣的寫法,既是語言的變化,也是賈平凹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變化。他在《秦腔》的“后記”中說,“只因我寫的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種寫法”。在和批評家對話時,賈平凹認為彼此對話時實際上還有很多事情同時發生,因此需要喬伊斯那種寫法,在對話時看到后面的風景:“是對話的時候看見后面的風扇,窗子啊,一邊對話,一邊想到那里去了,不停地游離,全部寫出來。他覺得現實生活實際就是這個樣子。現實的枝蔓特別多,我想把生活的這種啰嗦繁復寫出來。”這是賈平凹所理解的“內容決定形式”。
八
《山本》的風格是非常“老”的。這種所謂的“老”在賈平凹新世紀以來的文本表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是作者一種非常自覺的審美選擇,比如直接就用“老生”一詞為題。這種“老”一方面是因為它賡續了中國文學非常早期的文學傳統(尤以先秦、西漢文學精神為甚);另一方面就是薩義德所謂的“晚期風格”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平行地比較中國文學的相關表述,比如杜甫論庾信的“晚期風格”:“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在中國本身的文學傳統里,作家進入晚期或者說是老年時期,都會相對自覺地形成一種迥異于“青春寫作”的“晚期風格”,這種風格意味著“境界”“氣象”的出現;再者,“陜西”本身的敞開的歷史空間,使得賈平凹非常自覺地體認到一種“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借由“滄海桑田”式的歷史觀不斷生發,成為一種相對穩定的“文本景觀”。這里的“老”不是“廉頗老矣”的“老”。
這種“老”的風格,其實源自于一種復雜的“閹割”操作。這種操作在《秦腔》時期就已經體現了出來。引生就是一個被閹割者。這種文本的“閹割”策略如果放在和《廢都》的比較中來看,則更其明顯。如果說“縱欲”的表述混合著世紀末的末世情結而形成一個生殖力喪失、都城頹敗的“荒原”,那么《秦腔》則先行閹割,使得文本本身構筑在沒有力比多沖動的“荒野”之中。《山本》也是如此。如果和《廢都》中莊之蝶和眾多女性都有著的性關系來對比,那么井宗秀和陸菊人之間的關系則要“單純”得多。二人之間的關系似乎至終都沒有沖決出男女之大防,反而顯得相互尊重,惺惺相惜。所以“性”一開始就沒有在兩人的關系中形成一種“力比多”表述。井宗秀和陸菊人的實際關系其實是被隱喻的,如果物化出來那恐怕就是陸菊人的“三分胭脂地”了。聯想到賈平凹前期的《美穴地》,那么這種關于“地”的隱喻就更其顯豁了。所以《山本》中的男女關系是一種類似于“被閹割”的狀態,一種純屬于精神層面、情感層面的休戚與共的狀態。因為力比多威脅的喪失,所以小說的內部顯得平靜,具有一種內在的收斂氣質。小說中的好多人物為“性”所困擾,然而卻最終以閹割、身滅為結局。這種被淡化的“性”,暗暗地營造出一種晚郁的風格特征。
九
我們可以說賈平凹已經完全形成了一種晚期的風格,文本系統內部呈現著非常濃的“同一性”色彩,一種彌漫全篇,蒼茫混沌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集中地體現在“色彩”的“譜系”: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發現《山本》的“黑色系”特征,“黑色”成為彌散在整部小說中的基礎色調:“所有的街巷全有貨棧商鋪,木板門面刷成黑顏色,和這種黑相配的是街巷里的樹,樹皮也是黑的,在樹枝與屋檐中間多有篩子大的網,網上總爬著蜘蛛。”鎮子里的豬都圈養,雞狗卻隨便走,豬狗是黑的,雞也是烏雞,烏到骨頭里都是黑。
在小說的尾聲,靠在椅背上睡著了陸菊人做了夢,在似醒未醒之間,陸菊人琢磨著,“夢里的情景就模糊了,像一點墨滴在水里漸漸就暈開散了”。在陸菊人的視野中,河水黑了:“是黎明之前的緣故吧,黑來得比剛才更深,鎮子越來越沉重,遠處的河面和河灘卻發生了變化,先是河面發白,河灘是黑的,過一會了,河灘發白,河面竟成了黑的,它在流動,看上去一動不動。”這種黑色籠罩了地面上的一切:“天亮了,能看到了130廟里的大殿和巨石上的亭子,能看到了自殺成焦黑的老皂角樹,能看到縣政府和城隍院。而對面的屋檐下,店鋪在卸下門板、掛上了招牌旗子,旗子是黑色的,三角的,上面寫著白字,像是刀子,所有的旗子都掛上了,整條街上都發出仇恨,而同時有無數的煙囪在冒炊煙,像是魂在跑。”
“黑”的選擇,“黑”色的統治全篇,應當說有著非常深刻的文化內涵,我們不妨粗略勾勒一下“黑”的譜系:“坤其於地也爲黑”(《易經》);“北方色也”(《說文解字注》)。可以說“黑”本身有著鮮明的地理特征(北方),抽象言之,還代表著“大地”屬性,所以也暗合著我們上文論述的“造物”傾向。如果再考慮到賈平凹雅好文物收藏,又深通水墨,那么他“黑色系”的自覺選擇,古拙蒼茫的審美風格的形成也就有了創作主體自身的經驗支持。
十
《山本》延續了賈平凹之前創作的一貫傾向,就是以一隅之地(商州/秦嶺/“西京”)來折射“中國”。就像在《古爐》中那個著名的比喻(“碎成一地的磁器”來預示中國“china”),在《山本》一開始,賈平凹就說“一條龍脈,橫亙在那里,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
“龍脈”的修辭表述,仍然是一種正統的“王朝”修辭,它折射出的是一種“中心”的意識。就像廢“都”仍然是“都”一樣,秦嶺在賈平凹的筆下,也就成為了“核心”的象征。那么推而廣之,與其說《山本》是“秦嶺志”,毋寧說它是“中國志”。那么賈平凹筆下的人物,故事,就獲得一種寓言性質,一種傳奇性質。它本身成為一種國族寓言。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山本》開頭的寓言/傳奇性質,也就不言自明了:“陸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帶來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渦鎮的世事全變了。”
放到賈平凹創作的漫長譜系中來看,這些小說連同《山本》就共同講述著一系列“中心”失效、中心“潰散”的故事。《廢都》里的“莊之蝶”/西京的一同頹敗,疊合了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失語的時代境況;《秦腔》里鄉土的荒原化夾雜著以秦腔為象征、以“仁義禮智”為代表的儒家傳統秩序的消泯;而《山本》更是將歷史的更迭投射到自然造物的大框架中,演繹著滄海桑田的歷史潰敗。在這種大潰敗、大頹喪的文本背后,婉轉曲折地樹立起一個“焦慮的主體”的形象,這個創作主體不斷激活古老的文學資源去重塑“中心”的生機,這種策略在沈從文那種用苗人的蠻力去激活中華文化的生機的嘗試中也已見過,可以說這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尋找文本現代化的一種曲折的嘗試。如果投射到整個的文化語境來看,這也是一種主體焦慮的征象,一種欲確立主體價值的文本實踐。
所以,賈平凹寫作《山本》時,在室內掛了兩條條幅:左邊掛的是“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右邊掛的是“襟懷鄙陋,境界逼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