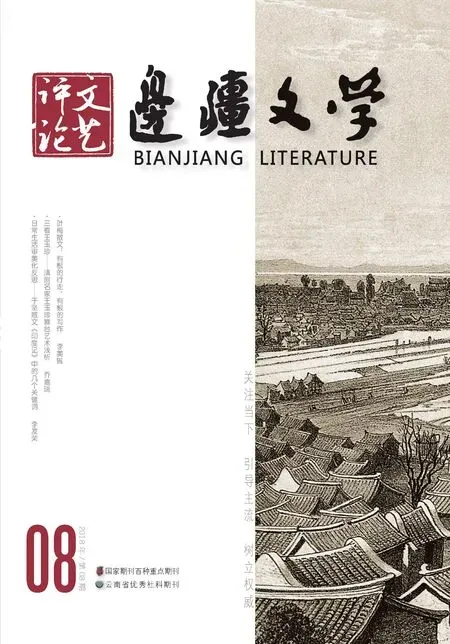日常生活審美化反思
——于堅散文《印度記》中的幾個關鍵詞
李發榮
于堅的散文《印度記》不僅僅是停留在對古老印度游覽時的所見所聞的記錄上,在這篇散文里,于堅融入了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性思考和哲學思辨,并上升到了文化反思的高度。在記錄印度日常生活的同時,從中反思了當下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況,并在文中折射出了他對日常生活以及審美化的個人理解。
在《印度記》里,于堅打開了他記憶的大門,再一次反思了關于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其中包括對舊世界的堅守和對物質世界的抵抗;對故鄉、對童年日常生活的懷戀;對去蔽、去象征化,對還原事物本相,突出人的不懈追求;對生活細節審美的無比熱衷等等。本文從中提取和歸納出了舊世界、故鄉、本相、改革以及細節等五個鍵詞,力圖以這五個關鍵詞作為切入點窺探于堅散文《印度記》中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反思。
一、舊世界
在《印度記》里,舊世界隨處可見,“當汽車駛進公路,我看見了印度。這是之后我一直看見的印度。我們的賓館其實只是印度的一個相當有限的局部。廣大的、普遍的印度是在公路的兩旁。這一眼所見的印度令我難忘,一個舊世界。陳舊、破爛但是安詳的村莊,五顏六色的垃圾、有人在旁邊汲水的古井、古老的田野、一列古老的火車穿過的古老大地,車廂口掛滿了古舊的人們,他們仿佛剛剛從田野上收工回家”。都是舊的,在于堅看來,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由“舊”構成的。但是,這里的舊是一種后退的,是一個生活場,它與落后,貧困無關,那些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們所謂的落后貧困、臟亂差的評價標準完全不適用于印度這個地方,因為這里才是“日常生活的天堂”。于堅寫道,在印度這個地方“生活轟轟烈烈,熱火朝天、生龍活虎,人們忙忙碌碌,只為一件事,生活,更激情或更腐爛的生活。”在舊世界里,生活本身就無所謂好壞、對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生活的氣質不同而已。在印度的舊世界里是可以徹底無政府,莫衷一是的,各種聲音嘈雜,商人,游客、苦力各忙各的,各有各的目標,而唯一的目標就是生活。
“許多大樓停工了,熱火朝天的是舊日子,現代化在此地還沒有高歌猛進。”這是印度的現狀,在印度的舊世界里只“有一種叫做生命的暗流在其間洶涌澎湃”。那是怎樣的“洶涌澎湃”呢?“密密麻麻的人群螞蟻般穿行,談生意、購買、裁布、修鞋、玩游戲、睡覺、乞討、吃食物、漫游……許多人席地而坐,擦皮鞋的大師、詩人(長得像泰戈爾,留著白胡子)、打磨工具的手藝人、胖嘟嘟的黃色的出租車、撿到了玩具的兒童、一群剛剛爬出泥濘的羊逃兵般的跑回……剛剛抵達不久的鄉下人在灰塵和垃圾中睡得死去活來,從睡態看,他們在做美夢。”這就是舊世界的生活,是印度人的日常生活。
在印度,在臟亂差的舊世界里,人們在那里進行著最普通、最平常的日常生活,那里沒有高樓大廈,沒有嶄新的購物中心,那里有的只是舊世界,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天堂,“從郊外向市區去,不是涌向世界大都市通常的珠光寶氣的嶄新的購物中心,而是向著舊世界的心臟而去。”而“舊世界”是怎樣的呢,于堅接著寫道:“鬧市區太舊了,混亂、垃圾破爛堆積蔓延、黑漆漆的、灰乎乎的、無邊無際,擠著各式各樣的老爺車,仿佛是從廢品倉庫開出來的。街道兩邊一家接著一家的都是鋪子,賣百貨的、做衣服的、賣香燈的、賣水果的、賣鎖具的、修三輪車的,只要你想得出來的行當,街上應有盡有,日常生活的天堂。”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于堅取消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他的文字就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場景。舊世界足以讓人震撼,因為它是一層一層積淀下來的,就像巖層一樣,其中的化石才是最平常和珍貴的:“加爾各答老城令我震撼。一切正在被創造出來的和已經死去的都擺在那里,像是某種天堂和地獄的混合物,古老、陳舊、累疊、堆積、阻塞、發霉……就像巖層。”在于堅看來,日常生活必然是舊的,因為它是基本的。如果歷史是某種無休無止的裝修的話,那么日常生活就是裝修下面那些基本的部分,不變的部分。它是舊的,只是相對于時代的變遷,它的舊不是由于變,而是由于以不變應萬變。
對舊世界的固守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于堅對新事物的抵觸。“守住舊事物”不僅僅是守住那些臟亂差的鬧市、街道和房子,最重要的是守住家園、守住文化,守住一種永恒的信仰,這是于堅為了避免我們僅存的日常生活被大眾文化吞噬而做出的最后的努力。在于堅看來,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不在新生事物上,而是在舊世界里,在精神上。“眼花繚亂一般是相對新生事物而言的,這里的豐富確是屬于舊世界的眼花繚亂,舊世界的五彩繽紛、舊家什的雨后春筍。一切都被用舊了,像是二手貨倉庫,但沒有死去,沒有自卑感,繼續活著、用著,用得生龍活虎、熙熙攘攘、層層疊疊、密密麻麻、前呼后擁、此起彼伏。舊是偉大的,生活的目的是做舊。煥然一新在這里非常刺眼,那只意味著出事了,反常了。”這種“舊世界”里的生活,與其說是落后,不如說是一種選擇。在《印度記》里,印度是緩慢的存在的,而不是一路狂奔著向前。印度保持著過去,即使遇到變革,也不迷信未來,否定過去。印度的過去是活著的,它不是在史書里,而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陳舊的世界里。
二、故鄉
如果說舊世界是于堅日常生活審美化反思框定的視野范圍和落腳點,那么對故鄉的懷戀和一幕幕記憶就成了他具體可感、切身實際的范式。和以往的散文一樣,于堅在《印度記》中也不時會回憶起自己的故鄉、少年時代的生活,這些記憶片段交織在游歷印度的過程中,雖然只是電影鏡頭式的切換,一瞬間的閃回,但是這些記憶,這些片段將現實的場景和記憶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在印度—故鄉昆明的場景切換中,于堅進一步反思了日常生活,其中既包含著一種懷念,也蘊含著他對現世生活的不滿,企圖回到過去,回到童年的日常生活的無望追憶。
其實,進一步來看,印度只是提供了一個參照,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一扇窗口,通過這扇窗口,于堅可以回憶過去,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反思自身的存在的同時反思生活的原在。無論是一個陽臺,狂歡的人群,一個露天自由市場還是一條河,都能勾起他的聯想,使他回憶起自己的少年時代:“這個陽臺我似曾相識,昆明如今已經沒有這樣的陽臺了,少年時代我就在一排這樣的欄桿旁邊長大。昆明受法屬印度支那影響,許多建筑物中西合璧,我十一歲以前住的那個四合院,由一個歐式的陽臺在照壁上穿過中式四合院的天井,正對著我家,那兒是我的天堂,我家的夏日餐廳,我曾在晚霞的映照下,在一天的余光中做作業、吃晚飯;也捕捉過麻雀,越過陽臺去摘房頂上的花朵。這是第二次了,印度喚醒了我的記憶。”是印度喚醒了他的記憶,于堅由窗外的“大陽臺”回憶起了昆明少年時代的陽臺,雖然在陽臺上面發生的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瑣事,但是,其中充滿了令每個人都向往的童趣生活。于堅的記憶在返回到故鄉,返回到昆明或是曾經去過的某個地方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歡喜的。在看到清晨涌向恒河的偉大的游行、狂歡的印度人的舞蹈時,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鄉昆明馬街的場景:“回憶再次閃現,在遙遠的少年時代我到過瓦拉納西,那是昆明的馬街,環繞著一個神廟,山地民族的狂歡、對歌、跳舞,無數的新衣裳、無數的裙子和山茶花。”在相似性的聯想與想象中,于堅獲得了某種內心的喜悅和滿足感。
一個露天自由市場、一條河在于堅看來也是非比尋常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某些記憶有關。由古老的恒河,于堅想到了故鄉童年時候玩耍過的盤龍江:“恒河,平庸的令人絕望,就像從我家鄉穿過的盤龍江,那被改造過的水庫式的河。”在這些回憶里面,我們隱約可以感受到于堅內心的失落。他曾經這樣說道:“革命所要摧毀的庸俗生活卻是人生最基本的東西。”(于堅《何謂日常生活——以昆明為例》,7)那些便于人們生活的露天自由市場,供人們游泳取涼的河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變得面目全非,甚至已經被消滅了,這是于堅所無法容忍但也是無可奈何的。
在于堅對故鄉的回憶中,有一個人使他始終無法繞開的,那就是他的外祖母,他曾在其他散文中多次提到他的外祖母,在《印度記》中也不例外。“我第一次聞到桂花香是在昆明連接著越南和云南的滇越鐵路的終點站,1962年的某日。法國人設計的昆明車站里有一個巴黎出廠的大鐘,看起來像一只腿長在自己胸部的昆蟲,當我盯著桌面上那根腿在羅馬字母上爬的時候,風帶來了這氣味。外祖母說,那是緬桂花香,外祖母總是告訴我氣味,上一次她說那是夜來香的氣味。很奇妙,在如此遙遠的天空下,故鄉卻不時閃現,仿佛我正在回到故鄉。”這是導游送給于堅帶著緬桂花氣味的花環時他的心里想到的。獨在異國他鄉,思念之情自然倍增,特別是對已經過世的親人的懷念那便是縷縷涌上心頭,外祖母在他的童年記憶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她充當了啟蒙者的角色,而且她無微不至的關懷令于堅永生難忘。還有,在看到印度服裝店里的土布時于堅也想起了外祖母,想起了他少年時的土布以及用土布做成的褲子:“我對此印象深刻,是因為我外祖母曾經是開布店的,在1949年以前,她在昆明有兩家小布店,賣的大部分是蠟染的土布。但在我少年時期,社會風氣已經以穿土布為落后了,我記得70年代的某日,我父親在專為干部開設的內部商店買到了一塊日本進口的化纖布料,叫作‘塊巴’,全家歡欣鼓舞。我得到一塊來做了一條褲子,成為我最珍惜的褲子,只在節日或約會時才穿。”文字中除了對外祖母的回憶之外,內心多了一份對往日生活的回憶、心痛、不舍和依戀。
三、本相
本相,即事物本來的面貌。由于歷史的不斷發展和演變,社會以及人們賦予事物本身的象征意義越來越多,越來越濃厚。于堅在《印度記》中對本相的追求是孜孜不倦的,他清楚地看到了事物的本相正在被遮蔽起來,工具性的地位正在漸漸散失,而變成某種身份、地位或是更高追求的象征,所以他一再地強調本相,要求“去蔽”“去象征化”,還原物與人的最基本的關系。
要還原日常生活中物的本相,首先要“去蔽”。于堅在文中這樣寫道:“狹義的說,中國是文明的世界,以文明世;印度是神明的世界,以神明世;無論文明、神明,都必須一次次去蔽,非歷史、非理性、洗去雅馴、神話的積累重疊所導致的對生命本源的遮蔽,出去形而上的污垢,回到身體,回到原人。”去蔽就是去除“對生命本源的遮蔽”,回到人類生命本身的存在,去重新審視日常生活中的物,排除歷史的、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對物重新命名。“唯有超驗的本相保持不變,所以唯有這個本相才是真實的。”但是怎樣去蔽,怎樣回到人間,回到日常生活的場,回到身體的狂歡上,于堅給出的答案是:“垃圾化是解構、去蔽最有利的方式。解構就是復活。解構不是革命,而是復活”。這是一種去蔽的方式也是一種待物的態度,把物還原成最初的東西,甚至是垃圾,目的只是為了重新給他們命名,確定它們的意義。
去象征化,也是于堅反復強調的一種回歸本相的形式。而在印度去象征化最明顯的就是建筑物。他這樣寫道:“城市(加爾各答)普遍的矮,可以看見落日和新月。河流兩岸零零星星的有幾棟高樓。極少裝飾,平庸而實用,暴露出了這種西式盒子基于幾何數學的本源性的貧乏、呆板和丑陋。沒有花功夫把它設計裝修出某種意味,比如象征高大壯麗輝煌雄偉、成功、富裕、‘站起來了’等等。”相比于中國的現狀他得出的結論是:“印度的建筑很少象征性,看上去政府的政績大約也不體現在建筑物上。”這就使印度的建筑,它很少“裝修出某種意味”也“很少象征性”。在印度建筑物不是用來象征欣欣向榮、崛起、發達的意思,矮樓就是矮,高樓就是高,平庸正常。其實,于堅去象征化的目的就是為了去除語言賦予物本身的象征和隱喻功能,還原出物的本相;去除物自身的象征和隱喻意味,還原出物的本相,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把人突顯出來。
在印度于堅看到“物與人沒有等級。物不貴,人也不賤。不像別的地方,人越來越賤于物了。物被頂禮膜拜,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于堅看來,汽車、飛機,甚至是書都只是工具,是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物品,在去除了表象賦予的意義和象征之后,它們是平等的,在本質上的、在性質上是平等的。在印度,于堅親眼目睹了那里的人們的待物態度,他似乎領悟到了某種印度人待物的某種真諦,那就是物“壞了就壞了,像古跡一樣,讓它們繼續待在那里”。
四、改革
改革也是于堅在《印度記》中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于堅時常會因為看到眼前的印度而反思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生存狀況。在《印度記》里涉及改革這一關鍵詞的主要是房屋拆遷、城市改造等等。于堅在看到印度的房子時這樣寫道:“有些舊建筑部分倒塌了,并不拆掉,后來的建筑物接著那倒塌之處繼續生長。沒看見拆遷。”其中我們隱約可以看出于堅對現今拆遷問題的態度與立場,他有一部紀錄片講述的就是昆明的城市拆遷問題。接著,他又繼續討論物的歸屬、所有權問題:“物各有主,都是私人的產物,那是怎樣尊貴凜然的物產或者怎樣卑微下賤的物產,與他人無關。怎么住都行。建筑的無政府主義。建筑物幾乎沒有雷同,除了基本的立方形、長方形格局。每一棟棟房子,無論是豪宅還是貧民窟,一旦蓋起來,就矗立著直到死去。因此有了無數老態龍鐘,垂垂將死的建筑物。甚至已經死了,已經是一片廢墟,那也是有主的廢墟,由它廢著,任何人不能擅動。”在印度,文明的速度不是有計劃的人為推進,城市和鄉村的歷史更迭有其自身的規律。“拉瓦納西處于從村落向城市過渡的途中,不是有計劃的城市改造,而是時間、歷史使從前的荒野變成聚落,變成村莊、變成集市、變成是市中心,又使曾經的市中心退回了村落。”遵循的是時間和歷史的秩序,而不是人為的推進速度、加快毀滅的歷程。
改革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但是它的基礎不是廣大人民的意愿,在印度,在貧民窟里“大白天,有人在睡覺、有人在縫補、有人在彈琴、有人在下棋或者聊天。蒼蠅洶涌,孩子們撲在地上做作業,屁股上趴著昆蟲。”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即將離開這里或追求改善和進步,更高、更快、更強在印度的貧民窟是看不見的,他們也不熱衷這些。印度人并不視貧民窟為臟亂差的毒瘤,這是他們的一種選擇,一種活法,印度人尊重這種活法,然后研究它為什么以及是什么,而不像中國,強行動用武力,使之拆除、抹平。中國人最喜歡設定標準,用各種尺標來丈量人的生活,恨不得每個人都是一種生活。于堅對這場波及中國的巨大的遷移運動的反思是尖銳,他深知拋開了歷史、傳統的根基,那個叫作民族、地方、故鄉的地方正在被一個個連根拔起、拋棄,趨向滅亡,所以在印度面對眼前的景象,于堅才會忽然想起,“很久沒有看見大地了,在我的家鄉,大地日異成為碎片,偶爾在郊區的縫隙里一閃而過。”
可以說,“與印度比起來,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歷史,就太像一場大掃除了,一個忙著搬新家的國家。印度沒有煥然一新,印度灰暗而深厚(舊世界),那顯而易見的歷史感沉重得令人窒息。這使得人們的表情呈現出某種尊嚴,某種自我意識,自信、安詳、平靜。不知道為什么別的民族會那樣自卑自殘自我否定自我毀滅,那么熱戀歸零。”在不斷反思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心痛的老者形象,他堅守著最后的家園,反對甚至憎惡暴力的拆遷,他要守護的是屬于他的舊世界,雖然那片土地正在漸漸縮小。“這座城市似乎從來就沒有拆遷過,除了戰火、天災,沒有人進行過人為的大掃除,無數世界的舊物、故居成為灰燼、廢墟、遺址。堆積在原處。廢棄與過剩,舊世界與新景觀,形式消逝了,灰燼留下來,比形式更堅固的原材料留下來,成為苔蘚們的樂園,它們瘋狂地在已經失去了圍困對象的古墻上爬過。新世界在廢墟旁邊生長起來,并且一個個跟著落日淪為舊世界。”在新世界與舊世界之間,拆遷是一座橋梁,而于堅站在上面,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后者。
五、細節
于堅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反思最后必將落到一個點上,那就是細節,細節成為了他日常生活的審美對象,意義的生成空間。于堅的寫作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強調經驗、強調身體、強調存在,只有具備了這些才有可能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美,才有可能生成意義,從而形成審美活動,獲得審美愉悅。例如在《印度記》他中這樣寫道:“大街上時常有男人在洗澡,只穿了短褲,脊背水淋淋地閃著光,嘩嘩的澆著水。街邊每隔一段就有一組水龍頭,供路人飲用沐浴。”在存在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調動身體的感官,去發現、去感受,用細節展示出真實的生活,這就是于堅對體驗日常生活審美的要求。那些一瞬間、一剎那的經歷,有如電影的慢鏡頭一樣,在最短的時間內他捕捉到了每一個細微的細節,在經過收費站時,于堅看到:“收費站是一處監獄般的建筑,鐵柵隔著,污跡斑斑。看不見收費員,一只手從鐵柵欄后面伸出來接過盧比。盧比也是臟兮兮的,失去了硬度,像一塊千萬人用過的手帕。”在看到電車時于堅這樣寫到:“電車幽靈般駛來,大概已經用了兩百年,似乎從來就沒有清洗過,污垢像漆一樣閃光。車廂里面陰暗如山洞,沒有窗玻璃,木制或鐵制的扶手被磨得像不銹鋼般光滑。看不見乘客們臉上的細節,印度人深邃莫測的大眼睛一排排在窗口亮著,像已經出世的寶石。”
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我們忽略的細節,在于堅的眼里它們有了存在的意義。從小巷到電纜電線到街心,沒有一處能逃過他的眼睛,“這些小巷大多數僅可容一輛三輪車,人們溪流般的從里面涌出來匯入大街,蔓延到街道上,提著的、扛著的、抱著的、拉板車的、甩著兩只空手的閑人、黃包車一輛接一輛的跑著,后面坐著神情高貴的人……”“街道上空密布各種直徑不同的電纜電線,粗如麻繩,細如蛛網,糾纏絞結。路線不是一個方向,而是無數方向,東拉西扯,七上八下,似乎每家都從主線上接一根進自己家去,電線密集的就像亞馬遜叢林中的藤子。”“街心也是一樣生動,大街具有人行道,車行道、廚房、公園、浴室、商店、娛樂場、臥室等五花八門的功能。”似乎他的眼睛就是一臺精密的記錄儀器,能捕捉到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不易被人察覺的細微之處。
我們再來看一下,于堅的這一段描寫,這是他站在船板上,游恒河時所見到的:“駛過一座水泥平臺,鶴發童顏的瑜伽大師,赤裸上身,領著一群人盤腿而坐,大聲叫喊,他的聲音那么嘹亮尖利,好像把淤積在身體里的悶音都噴了出來。信徒白花花的一大片,都跟著他盤腿而坐,一起喊,驚天動地。火葬臺在冒煙,光輝的火葬場,堆積著柴堆,死者被火焰舉起來,死亡光明正大。烏鴉銜著一縷青煙朝蒼茫飛去。狗在一尊神向下翻個身,又睡過去了。有頭牛站在河岸,與河岸平行,已經粘了一個世紀。另一個石砌的神龕里坐著一位穿襯衣的男子,他剛剛洗了澡,在里面穿衣服。某人站在神廟臺階上向著恒河嘩啦啦小便,奏出來一段音樂。”這些細節精準、生動,人物栩栩如生,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只有像于堅這樣的雕塑家才能如此細膩。這樣的細節在《印度記》里不勝枚舉。于堅用一處處細節把場景描繪的一清二楚,這種詩意的記錄一直是于堅所慣用的方式,它一方面突出了日常生活的真實感,使場景真實可信;另一方面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審美立場,即從細節現美,發現意義,最后用細節確定自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