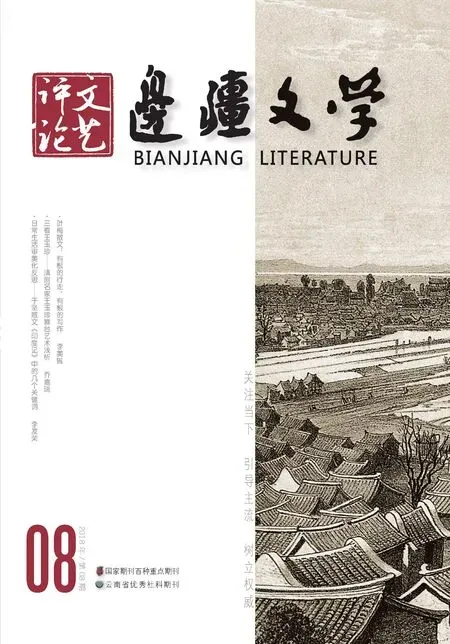談張雁超詩歌語義的聚合與擴展
朱 江
張雁超是近年來云南涌現出來的著名80后詩人,其詩歌散見于《人民文學》《詩刊》《星星》等刊物,出版有詩集《大江在側》。他的詩歌語義上顯示了很好的聚合及擴展關系,本文希望以此為出發點探求其詩歌的某些特征。
一、詩歌語義的聚合
討論詩歌語義的聚合,即討論詩歌語義的向心力,它指的是詩歌語義指向某一點,或者詩歌在行文過程中的一種行文指向。詩歌向心力起源于物象動態的一種方向合力。張雁超的詩歌善于通過主體意識來推動詩歌的行文,在行文中,力求指向主體,從而實現詩歌語義的聚合,這樣就使其詩歌結構十分緊密。
討論張雁超的詩歌語義的聚合關系,可以從其詩歌的主體開始。《噗通》這樣寫“整個下午,我們把/岸邊的石頭撿起來/扔回江里。那些/被江水拋棄的石頭/命運又被我們修改了一次/流水的路途也被修改了一次/我們不必分辨流水和石頭/誰的命運受到了更大影響/反而應該關注那些‘噗通’聲響/我感覺到這些聲響/在我們前后左右良久等候/當石頭與水面相觸/跑得最快那一聲‘噗通’/就獲得了它的一生”,“噗通”是什么,是石頭落水形成的聲音,詩歌先是鋪墊,然后通過“反而應該關注那些‘噗通’聲響”的轉換進入詩歌的真正對象,直到“跑得最快那一聲‘噗通’/就獲得了它的一生”完成寫作,將“噗通”寫活,“噗通”的主體性得以確立。這里的所有語義都指向詩歌的結尾。這無異于一個情節,開始交代一個背景,在交代背景的過程中,詩歌還利用“那些/被江水拋棄的石頭/命運又被我們修改了一次/流水的路途也被修改了一次”對詩歌語義進行了一次擴展,照道理,詩歌要指向的是主體“噗通”,但通過擴展,“命運”“路途”與結尾“一生”構成語義的閉合系統,這在語義上是聚合的。這也說明語義是有指向的。詩歌向前發展,通過語句中轉,之后進入了主體,“我感覺到這些聲響/在我們前后左右良久等候”借助先前語言呈現的慣性,將詩歌語義繼續推進,一方面“等候”借助擬人化,語義上聚合到主體“噗通”,同時在閱讀視覺上有催化作用。自始至終,語義都指向主體“噗通”。以主體的向心力來左右詩歌語言的呈現是張雁超詩歌的一種呈現意識,他的很多詩歌從題目開始就指向主體,這似乎構成了其詩歌的主體情節,這樣的詩歌比較多,如《子彈》以子彈為出發點,一貫而終,零狀態的描寫回歸子彈。諸如此類還有《刑》《山上的現場》《提訊》及《繩》等,這些詩歌幾乎都是從物自身出發,直觀地呈現物或者事,進入無我狀態。
事實上,語義的聚合是一切語言呈現的重點,詩歌尤其突出,因為詩歌語言的密度是比較高的,詩歌要求在極少的文字內體現聚合關系,而且詩歌語言又含有跳躍關系。聚合關系的起源依然是詩人詩意思維,即使是與語義有一定距離的語音在語義聚合上同樣也有表現,這本身就包含詩人對事物的詩意感知與呈現。如《誰動了我的鄉村》中 “讓”字開頭的十二個句子帶有排比、鋪陳的味道,本質上這是借助語義的聚合來呈現物象,只不過這是在語音的極致背景之下來完成的。如果擴展到一般物象的排列,語言方式的聚合同樣存在。因為,在物象呈現的過程中,只要向心力的存在,語義的呈現也帶有慣性,這里以《黃昏》第一節為例來討論,“蝙蝠扇動翅膀,扇開落日的濃煙/蝙蝠飛過西山東山,把一個球場夾在腋下/懶散的慢跑著被蟲鳴塞滿了耳朵/樹林越來越深,天終于黑了下來”,前兩句不必說,因為它都是以“蝙蝠”開頭,聲音上是連續的,而到第三句第四句,整個詩歌句式都是以主謂句的方式來完成的。這樣,整節詩歌在語義上就構成一個敘述整體,蝙蝠——慢跑著——樹林,主體的一貫意味著呈現中內部心理節奏的統一,這或許就是讀起來“順口”的原因。另一方面,對一個物象的描寫,張雁超詩歌同樣表現了很好的語義聚合關系。他有一首詩叫《鴿子》,其中有“鴿子在夕陽下從容散步的時候/翅膀收在身后,細紅的爪/把一片片樓房輕輕放回城市……”,這里對“爪”描寫就是如此,“爪”上承“散步”,下啟“把一片片樓房輕輕放回城市”,而用“把一片片樓房輕輕放回城市”來陳述“爪”,本身就是物象主體性的表現。語言的呈現向心力指向的就是“爪”。按慣例,是“爪”在樓房上走,但作者將句子轉換成把字句,從而實現語言呈現上的一貫,聚合關系顯示的是呈現物象的主體優先地位。主體優先地位就是靠主體來顯示其語言呈現的向心力,就是在語言呈現過程中利用主體的指向性牽引著語言向前。這也是對物象的直接呈現,或者說是讓物象自我呈現。也許就是這種寫法,張雁超的詩歌很多時候表現出了語言的陌生感,《地震后的龍頭山》中有“太陽被堵在云里,雪到了山頂/沒忍心下來,只是風冷,榕樹更薄”,“沒忍心下來”就是承接上句的“雪”的,這利用這種比擬的手法保持了語言呈現的一貫性,使語言變得“陌生”,這種呈現方式飽含著文學性,因為“忍心”的使用,它不單是“雪”的,而且是作者心理的,它的聚合關系與呈現的主體性是相關的。
除了詩歌語句的一些聚合關系外,詩歌結構更講究聚合關系。這是因為,詩歌語義依然是一個大的聚合系統,它需要通過語義的聚合來實現某種主旨,從而使眾多物象在呈現向心力的左右下運行。如果詩歌在語言呈現上沒有向心力,它所有呈現的物象將是一盤散沙。《但字訣》這樣寫,“夕陽比黃昏雖不能持久/但空中閃現了較多的鳥鳴//大壩橫截空谷,抹去家園/但竹林處流水徘徊//草木皆不虛無,但空枝隱于濃綠/老婦人越發蹣跚,但藤蔓覆蓋黃花//春風漸行漸遠,但四月尚無倦意/天空有時素裝而行,但/不是你要它藍它就藍//云朵故鄉易被云朵遮蔽/但云在山后,另起一峰”,詩歌以“但”為題形成一個封閉而又開放的呈現系統,在“但”的左右下,每一節內都構成一個語義的逆向關系,整首詩節與節之間是并列關系,每一節結構幾乎相似。這首詩語義的聚合關系主要借助詩歌節與節之間語義的相似呈現模式來構建,從而促進語義的向前,這里語義的向心力并非來自句內單一的語義,而是一種相似性語義結構。整首詩語句結構的相似達成散點式的開放,它的向心力指向的是題目“但”,這種帶有鋪陳式的寫作意味著所有物象的整體格局相似。同時也意味著整首詩的文字并非指向結尾,它如同類比似的也許還可以呈現一節詩歌,或者再來一節,似乎沒有止境。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探討詩歌將聚合向心力直線地指向收尾的另一種詩歌形式。這種模式同樣出現在張雁超的詩歌之中,比如《林邊悟》,詩歌就是在呈現向心力的推動之下,語言呈直線,直指結尾“自從有了女兒,看萬物都如親生”,結尾一句總結全詩,一峰突起,戛然而止,語言截斷了語義的歸路,聚合找到了皈依。如此情況《問答錄》結尾兩句也一樣,“一定有什么在剝奪我使我匆忙使我疑問。/一定有什么在拯救我使我回憶使我深刻”可以視為是一個語義之下的總結。這些詩歌,在語義聚合的過程中,前面的描寫是造勢的,是為結尾服務的。這與《但字訣》并列關系的聚合是不同的。當然,無論什么形式,詩歌都要在作者詩性思維的控制之下運行,這本身就是一個大的聚合關系。
但當代詩歌最大的特點是詩歌的總體格局是利用物象的空間維度來維系組合關系的,在空間維度之下顯示時間維度,這也是當代詩歌的主流。在空間維度的組合關系上,詩歌同樣意味著詩歌語義的聚合關系,《滾燙之日》這樣寫“臥室門留下兩聲憤怒腳踢/那時,我女兒在澡盆里玩水/驚異的扭頭接上我擠出的鬼臉/露出她新生的小牙齒對我笑/又放心地繼續玩水/一整個晚上她都很乖,趴在我肩頭/小手圈著我脖子,嘴里一直說著/她僅會的發音:爸爸、抱抱、寶寶/就像知道我是一個需要安慰的人/入夏后,氣溫驟升/窗外蟲鳴大面積剝落,空中蒙著一層/淡白色焦躁聲響/這狗日的生活多滾燙啊/她的媽媽在臥室里哭/我的媽媽也在臥室里哭”。這首詩敘述的事情即是婆媳發生的一點不愉快。這種詩歌看起來像是完成時態的詩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詩歌。敘事性的詩歌應該是通過物象的語義詩意組合構成相應的語義流,從而整體呈現事情的過程。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是,即使是敘事的詩歌也必須保持住它的跳躍性,這就是說,詩歌物象語義之間是有間隔的,同時,又要在間隔之間通過某種東西使這些間隔的語義關聯而且貫通。這就意味著要找到一個恰當的要素來承擔如此的任務,這就是聚合的向心力。只有這種力存在,物象的詩性才有邏輯關系。如此一來,如果事情按時間順序來呈現,其跳躍性就不一定能完成,很顯然,對物象的空間重組十分重要。《滾燙之日》所要呈現的事情可以切分為臥室門留下腳踢、女兒玩水、入夏的環境及媽媽的哭泣。詩歌呈現的幾個場面顯然不是按時間的先后順序來呈現的。這就是作者在聚合關系上根據自身的詩性感知對事情做了空間順序的重組。
二、詩歌語義的擴展
語義擴展是詩歌語言延伸的一種手段,是張雁超詩歌寫作中語言的呈現策略。如《垂柳》中“它撩開枝條,云涌枝頭/除了風,只有樹皮中引擎轉動/趁月光初明,它拋出暗鴉/立根一沉/出手奪得了/白墻上的柳樹陰影”,詩歌從一開始就進入主體“垂柳”,“它撩開枝條”,“它”指的就是垂柳。但后面的“云涌枝頭/除了風”、“趁月光初明”似乎游離在主體“垂柳”之外。這是作者故意宕開,使主體的呈現更有厚度。語義的擴展古也有之,簡單的舉個例子如《莊子·逍遙游》開頭就有“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這里“齊諧者,志怪者也”中的“志怪者”就是“齊諧”語義的擴展。當代詩歌語言本質上是圍繞物象進行的一種呈現活動。擴展須整體地體現某語義事件或者情感過程,它自始至終是一個完整的語義流。
鋪陳手法是一種典型的擴展策略。諸如《錄死》《父親》《誰動了我的鄉村》等詩歌中張雁超大量使用鋪陳,這些詩歌借助物象的慣性展示了一個立體的空間畫面。以《錄死》為例,詩歌語義的擴展以題目為起點,通過第一人稱的方式進行全知描寫,排出了二十多種死亡的方式。在語義擴展過程中,語言呈現以物象并列進行,仿佛要將所有死亡方式呈現,照道理,死法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寫一百種一千種也未必寫完。但詩歌盡量呈現,目的就是通過鋪陳將物象語義擴展開來。在呈現物象的過程中,詩歌借助語義的變化顯示物象的多種形態,比如“捆好扔下橋”“小偷用菜刀送我死神”“我將針管里的幻覺,大量注入靜脈”“卡墻縫餓斃”“與鉆孔中的炸藥賽跑”等,這同樣是語義擴展的表現。這些死法是現實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同樣是想象和虛構的,是詩性歸納之后的,每一種死法都蘊含了一個甚至一系列的事件。
重造語境是張雁超詩歌語義一種擴展策略,一般來說,語境是靠物象來支撐的,只有物象存在,才會產生語境。也只有這樣,文學的創造性才會顯示出來。《為什么繞開地上的漿果》中這樣寫“踩爆漿果的悶響/真像山腳的公路上/貨車失控后/碾破了一顆人頭”。如果這首詩不擴展,詩歌所呈現的就是一個事實,即“踩爆漿果的悶響”。正如伊格爾頓所言:“假如沒有上下文語境,就會有不被理解的風險,脫離這個困境的辦法便是在不斷推動的過程中為自己創造語境。”《為什么繞開地上的漿果》中由踩爆漿果擴展到碾破人頭,它的價值在于擴展過程中建立新的語境。詩歌利用“踩”與“碾”關聯,抵達另一個細節,漿果與人頭關聯蘊含了一種人文關懷,蘊含著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及對語言的熟練運用。
而再造語境中產生虛構語境的情況是很重要的,因為那就涉及到了文字虛實關系的處理,如《綏江》《會澤箋注》之類都是這種詩歌。以《綏江》為例,詩歌從一個綏江人的“讓”開始,“一步一步/仿若為滄海讓路//讓出田園,讓出寺廟,/讓出道路與橋,讓出所有小地名”,這些都是實的,身后嶄新的城也是實的,但是作者不是直接寫這座城,是以消失掉的城市來模擬新城,新城實際上是用文字虛構出來的,“身后是一座嶄新的城/這座城是水里那座城/的亡魂,墓碑,祭文/和轉世投胎的肉身/還將以綏江之名/再修寺廟,住舊人”通過虛與實的交匯來完成新城與舊城的關系的,新城是舊城的“亡魂,墓碑,祭文/和轉世投胎的肉身”,以此指向的虛構本身也是一種擴展手段和策略,它在文字呈現的過程中使文字的厚重感得以表現,這就是文字的魅力與價值。這里的厚重感是建立在歷史感之上的。歷史感指向的是時間性,這也意味著空間性的擴展同樣可以展示時間的變化,從這個角度,張雁超詩中時間性與空間性是交匯的。
語義擴展還包含作者對詩歌的背景的設置。《我們一起去看稻子吧》這樣寫:“蓑衣我給你拿好了/秋雨持續了好久,現在/讓雨落進稻田之前/先打濕你的蓑衣,讓雨/打濕蓑衣之前先打濕你臉龐/面對稻田,你也是個有雨的人//谷老稻黃,學你佝僂的樣子/遠處是靜默不老的群山/你的旁邊是忽然要高歌的我/是忽然要痛哭的我”。這里“你”隨著語言呈現的推進,即隨著時間(“谷老稻黃”)的演進,讀者會產生一種閱讀依賴。這種依賴說的是詩歌的閱讀過程即讀者追尋“你”的過程,讀者可以隨著文字的推進追問“‘你’是誰?”這就是在問題的引領下閱讀,應該說,閱讀過程又是讀者的語義再造過程,“你”成為一個懸浮在文本之上籠罩著文本的物象。“你”是作者預設在文本之上導引物象,只要讀者去讀,都會受到影響。以此,可以看出,語義的擴展不單在文本內部擴展,同樣包含作者對文本之外語境的擴展。
注:文中所選詩歌來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