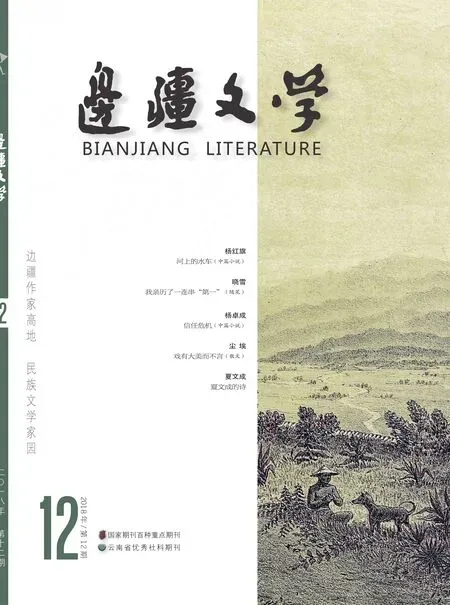琉 璃
鄒世奇
一
出生年月、籍貫、個人簡歷、社會關系……一項一項,紫蘇終于填完了所有的表格,吁一口氣,存在U盤里,拿到校門口王娟的店里打印。王娟正教店里新來的女孩用繪圖軟件呢,看見紫蘇來了,讓女孩給伍老師打印,自己則一邊輪流在另外兩臺電腦上忙活,一邊跟紫蘇寒暄。她腿細腳小,臀部以上卻突然圓潤,把一件小西服撐得炸開來,西服上五顏六色的印花似乎就要尖叫著、四散逃離那艷粉的底色。紫蘇為這聯想覺得對不起王娟,雖然多年沒有交集,但畢竟是小時候的玩伴。
她把目光從王娟身上移開,開始漫無目的地上下左右打量這間文印店。突然,她的注意力被腳下廢紙箱里的一張照片吸引了。這張照片明顯是一張打印表格的一部分,表格在紙箱底部,可是偏偏就從兩摞廢紙的縫隙中露出這張照片來。這種頭發緊貼頭皮全部掠到腦后的免冠照片對女人特別不友好,一般人照出來要么表情僵硬,要么骨相奇突,要么就雙耳招風,可是這張照片上的人卻出奇地漂亮。紫蘇忍不住走近,費力地扒開山一樣的廢紙,從兩山之間的峽谷中抽出那張表格仔細端詳。
那真是一張美人的臉,五官的每一部分都堪稱完美,整體看起來與年輕時的胡茵夢有三分像,但比胡茵夢美得更濃烈、更令人過目難忘。中英文雙語的表格,中文是繁體字,內容好像是申請婚姻移民,名字是“黃琉璃”。紫蘇忍不住贊嘆出聲:“世上居然有這么漂亮的人啊。這個黃琉璃,她是誰呀?”王娟回頭,見紫蘇拿著那張表格,笑到:“哈哈,認不出來了吧?你再仔細看看。”“難道我認識?不可能。”紫蘇再看,這人美得太出挑了,實在無法與自己記憶中任何一張熟悉面孔對上號。但當她看到曾用名一欄里“黃柳麗”三個字時,記憶被瞬間喚起:“小學同學里有個人叫這個名字來著,但是……”“就是她呀。”“啊?”紫蘇太震驚了,怎么也無法把眼前這張照片和記憶中那個黃柳麗聯系起來。王娟有些興奮:“嚇壞了吧?沒想到她后來長成這樣了吧?老實說她第一次走進我的店,我也完全沒把她認出來。”
紫蘇自認為智商一般,唯一值得驕傲的是記性好,她記得學齡前所有玩伴的名字、長相,幼兒園、小學同學就更不在話下。當她大學畢業回到這個廠辦中學教書,第一次在校門口遇見王娟,就準確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要知道她們最后的見面是在近乎十五年前,小學一年級。可是這個黃柳麗——如果真是同一個人,這變化也太大了吧。
紫蘇記憶中的小學同學,準確地說是學齡前玩伴黃柳麗,是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她一頭狗啃過一般的短發,一看就不是出自哪怕最便宜的理發店之手。饒是頭發短得像小男孩,紫蘇仍然記得不止一次,王娟或者別的小伙伴從她頸后摸出雪白、肥胖的虱子,而黃柳麗也只是尷尬地笑笑。
這樣的黃柳麗,小伙伴們之所以還愿意跟她玩,是因為她有幾樣“絕活”,一個是愿意做小伏低,跳大繩愿意甩繩子,打沙包主動扔沙包,拍皮球愿意撿球;別人擠兌她,故意當著大伙兒的面說她身上有味道,她也憨厚地不計較。另一個現在看來是某種天賦:小女孩們喜歡自編自演一些“劇”,內容有時候是媽媽和孩子,有時候是醫生和病人,有時候是老師和學生。無論分給黃柳麗什么樣的角色,她都能演得惟妙惟肖。紫蘇清楚地記得,有段時間大家總讓她演一個生孩子的女人,小姑娘們已經朦朧地有點懂事了,都羞于演這個角色,可是黃柳麗就很大方。她往那巷子深處、不知誰家堆在路邊的水泥預制板上一躺,捂著肚子、分開腿,壓抑地低聲呻吟、慘叫,痛苦地翻身,那表情、那語調,看在小女孩們眼里,真是絕了,電視上生孩子就是這樣的啊;讓她演一個瞎子,她就睜著眼睛一眨不眨,眼珠子不動,眼神也沒有焦點,一只手拄個棍子在前面探路,另一只手在空氣中無助地摸索,腳下步子遲緩而沉滯,活脫脫一個盲人,把大家都看呆了。那時候大家都不說普通話,連老師上課都不怎么說,但是不知為什么,大家演戲玩的時候卻要說普通話,自己也知道說得不好,自嘲為“彩色普通話”;只有黃柳麗,也不知她怎么弄的,說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就像電視里的人一樣。因為這些,大家雖然有些嫌棄,但始終沒有拋棄“丑小鴨”的她。
現在回想起來,黃柳麗即使穿戴如同乞丐,也仍然是不難看的。但那時候,大家認為長得漂亮的是那種穿粉色公主裙、白襪白鞋、五彩皮筋扎小辮的小女孩,誰會把邋里邋遢的黃柳麗和“漂亮”聯系在一起呢?那時候,誰會想到黃柳麗將來會長成一個絕色美人呢?紫蘇盯著那張證件照看,和記憶中黃柳麗的臉反復比對,最后只能承認:“沒錯,就是她,而且是天然的,沒有整過容。天哪,她怎么能長得這么漂亮呢。”“大頭照就算漂亮了?那是因為你沒見過她現在的真人!”王娟突然想起什么,“等著,我好像還有她別的照片。”她站起來走到店里唯一的文件柜前,蹲下來在最下面一層抽屜里一通翻找,找出三張放大的藝術照遞給紫蘇,“她說照得不好,讓我幫她放進碎紙機碎掉。我覺得太好看了,比明星照都好看,沒舍得全碎,偷偷留下幾張。”
一張穿著棉布旗袍、拿著折扇的民國風寫真;兩張結婚照,西服、婚紗的一張,狀元袍、鳳冠霞帔的一張。紫蘇的注意力全在黃柳麗,不,現在應該說黃琉璃身上,只感覺她的先生好像是位中年人。那是一種太過耀眼的美,完全令人移不開眼睛;不是因為藝術照,不是因為化妝。紫蘇是語文老師,隨著目光在照片上一寸寸移動,她腦海里凈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腰若流紈素”、“清輝玉臂寒”這類句子。過了很久,紫蘇才回過神來,又想起小時候的黃柳麗。造物太過神奇,那對總是眼神閃爍、神情討好的眼睛,是怎么變得這樣顧盼生輝、眼波欲流的?那總是仿佛結著一層黑垢的臉色,是怎么長成這白得發光、吹彈得破的皮膚的?最關鍵的是,美人兒全身上下那種自信、舒展,仿佛天生就是萬人寵愛的公主,哪有一點小時候的影子?這點石成金的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
黃琉璃小時候的境遇不是一般的糟糕。她和紫蘇、王娟都是國營大廠的子弟,住在同一個廠區的家屬院。當時家屬院里年齡相當、經常一起玩的女孩子有六七個,其中她們三個同年,一起上了廠里的小學,是同班同學。從紫蘇認識黃柳麗的第一天起,她就形如流浪兒。廠區是一個熟人社會,黃柳麗的故事,這里每一個人都知道:她的母親去世了,后媽十分兇悍,又生了個弟弟;在后媽的挑唆下,親爹看見她就想揍她。黃柳麗睡在家里的狗棚里,與狗為伴,吃飯也有一頓沒一頓的,還好有個出嫁不久的小姑,許她三天兩頭去蹭飯。因為街道辦事處三令五申,廠辦學校又免她學費,才勉強沒有失學。一年級上了一半,紫蘇的爸爸調去另外一個廠區,與這一個隔著大半個城,媽媽本來就是家庭婦女,家里就退了原來的筒子樓房子,到爸爸的新工作地點重新申請房子,全家搬過去,紫蘇也轉學了。所以黃柳麗也好、王娟也好,所有那一群女孩子后來怎么樣,紫蘇就都不知道了。
當紫蘇今年畢業回來進了廠里的中學,當年的小伙伴早已風流云散,在校門口遇見開文印店的王娟已屬意外;至于黃柳麗,如果不是機緣巧合,大家可能根本不會想起她來。
紫蘇的驚艷完全在王娟意料之中:“要不是親眼見過,我也不相信。去年的事了,她回來辦結婚,在我這里打印了好多材料。她認出我這個發小,還送我東西,請我吃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誰知道小時候那樣一個人,后來能長得那么漂亮呢?又誰知道她能嫁得那么好呢?”紫蘇問:“之前你和她也沒有聯系嗎?”“能有什么聯系?她初中上了一年就退學了,然后就去南方打工了。什么地方敢雇用童工,還能掙到錢寄給家里……不敢想象。”紫蘇很不習慣王娟說這話時那種曖昧的、含沙射影的語氣,微微皺了下眉。王娟沒察覺,繼續壓低聲音說:“那個男的我也見到了,比她總要大二十幾歲吧。據說早幾年就住一起了,去年琉璃到了結婚年齡才結婚的。”紫蘇笑笑,一式三份的材料早就打好了,她拿了材料,借口學校有事,付了錢離開了。
二
紫蘇作為新人,工作緊張,日子過得飛快,黃琉璃給她帶來的最初的震動很快便淡化了。直到有一天在教師集體辦公室,有學生家長跟她打招呼,她一抬頭便認出是熟人——黃柳麗的小姑,沒錯,雖然她看上去老了一些。黃柳麗的姑姑說:“伍老師,還記得我們黃柳麗嗎?我是她姑姑。”紫蘇說:“姑姑你好。我當然記得了,我和琉璃是發小嘛。琉璃什么時候回來,你讓她來找我玩啊。”姑姑沒想到她這么熱情,連忙說:“好啊好啊。她一般兩年回來一次。明年回來我讓她來找你。我孩子現在上初一,在葛老師班上……”
黃琉璃的姑姑走了,紫蘇想,她差不多算是黃琉璃唯一的親人了,雖然她年輕時脾氣不好,對柳麗態度很差。紫蘇記得,她嫁給了廠外的小生意人,就住在和廠區一墻之隔的巷子里。那時候女孩子們在巷子里玩,有時候會遇到她,柳麗喊“姑姑”,她一般是不耐煩地瞪柳麗一眼。有時候不知是她心情不好還是怎么的,會朝侄女粗暴地喊:“滾回去!就知道在外面瘋!怪不得你媽天天揍你!”這時候柳麗就飛快地朝家的方向跑,當然不過是跑開躲在暗處看,等她姑姑走遠了再笑嘻嘻地回來。于是女孩子們都有點怕這個姑姑,覺得黃柳麗家的人除了她本人全都好兇。
但是有天下午,紫蘇路過這個姑姑家,看見她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把半支粉筆橫過來,細細地往柳麗的舊運動鞋上抹,地上還有幾根白粉筆頭,柳麗光著腳坐在旁邊樂呵呵地看著。第二天學校開春季運動會,要求所有的學生都穿白色運動鞋;白色帆布鞋一舊就黃,需要刷一種叫“鞋粉”的東西讓鞋子看上去白一些,和大人們往臉上擦粉一個道理。看到這個場景,紫蘇無端想起不知從哪里聽來的小調:“人家的閨女有花戴,爹爹錢少不能買,扯上了二尺紅頭繩,給我喜兒扎起來。”那一刻紫蘇就想,這個姑姑只是看起來兇,其實心里還是疼黃柳麗的嘛。
紫蘇回來當了老師后,父母仍然住半城之外另一個廠區的家屬樓,她平時住在教師宿舍,只周末回家。這個周日下午,紫蘇從家回學校,她習慣走小時候經常玩耍的巷子,從巷子里的廠區側門進。巷子原來的城中村已經拆遷,原址上建起了一片別墅,透過黑色雕花柵欄看過去,里面都是獨門獨院的二層小洋樓,整個小區花木蔥蘢,儼然高檔住宅區。突然聽見有人叫“伍老師”,原來是黃琉璃的姑姑在柵欄那邊,熱情招呼她來家里坐。紫蘇有點意外,沒想到她家經濟條件已經這樣好了。看到對方真誠地迎出來,懷著對黃琉璃的濃厚興趣,紫蘇對自己說:“就進去坐一刻。”
紫蘇跟著黃姑姑走過小區里一段石子路,走進主人家的院子,穿過小花園,進了客廳。黃姑姑殷勤地沏了龍井茶,擺出水果、零食招呼紫蘇。紫蘇心里清楚,人家是因為孩子在自己的學校讀書,出于對教師的尊重,也防備哪天自己成了她孩子的老師,預先做功課的意思。紫蘇配合地問了幾句關于對方的孩子,然后就問琉璃現在怎么樣?什么時候回來?姑姑說:“她在廣東打了很多年工。去年結婚了,丈夫是香港人,開著公司,對她很好。她現在懷著孕,下個月就要生了。下次回來,總要等孩子大一點吧。”紫蘇就問:“家里有她的照片嗎?我們多年沒見了,想看看她。”姑姑想了想說:“照片應該是沒有。去年回來照了很多婚紗照、寫真照,后來都帶走了。但是聊天的時候她傳過一個視頻過來,伍老師要不要看?”
于是就打開電腦看視頻。是一個大公司的年會,滿場節日的狂歡、浮夸氣氛,女人們都打扮得十分賣力,花紅柳綠,有的袒胸露背,現場乍一看像個巨大的盤絲洞。然后,她出場了,挽著比自己略矮的夫君,款款走來。所有的光線瞬間集中到她的身上,世界突然安靜了,男人們肅然,女人們在心中嘆息,她們的姿色,在那一瞬間斑駁、皸裂,掉落在地上摔成碎片。
她頭發全梳在腦后,綰成一個低低的髻,著一襲黑色緞面及地禮服,白玉一般的面孔旁,兩只流蘇狀鉆石耳墜搖曳、明滅不定,有時像兩條明亮的瀑布,有時又像兩團閃爍的星云。此外全身上下再無半點裝飾,已然貴氣逼人、不可方物。她的夫君致辭,用廣東普通話簡短說了兩句,然后就隆重地介紹了自己的夫人——黃琉璃女士。
掌聲響起,黃琉璃女士含笑點頭,目光巡視全場,那氣場,比一位王后巡視自己的王國也毫不遜色。然后她開口了,居然說一口流利的粵語,紫蘇立刻想起她從小就能毫不費力地說一口標準普通話。連猜帶蒙聽了個大概,黃琉璃說的是,感謝大家一年來對公司的貢獻,對她先生、也就是對她的支持和關愛。她先生和她也一直致力于為大家創造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她本人愿意做大家的知心姐姐。新的一年,希望每一個人共同努力,共同創造越來越美好的未來。
造物太不公平,美麗高貴的人,連聲線都美麗高貴。在她發言的時候,她丈夫始終含笑看著她,眼神里全是驕傲。這一刻,誰能想到這個女子曾經住在狗棚里、初中只上過一年呢?
這個視頻帶給紫蘇的震撼持續了那么久。等到出了黃琉璃姑姑的別墅,一直走回宿舍,她才又能思考了:也許,應付任何場合、任何人和事對黃琉璃都是容易的吧,就像她小時候就能在游戲中輕松扮演一名產婦、一個盲人,如今的她當然更知道怎么扮演好一位總裁夫人。也許,人生中更多的重要場合,于她都只是做戲,所以她才能那樣游刃有余。
日子沙沙流逝,紫蘇的工作早已上了正軌,越來越駕輕就熟了。在老爸老媽的安排下,她幾乎每半個月都要相一次親,大多數時候她沒看上對方;少數時候雙方互相沒有感覺;只有一次,對方沒看上紫蘇,這件事除了讓紫蘇有點小小地傷自尊以外,幾乎沒在她的心上留下任何痕跡。無聊的相親生活結束于姚志浩。姚志浩比紫蘇大三歲,本市人,家境小康,本科學歷,銀行小主管。紫蘇父母很喜歡,紫蘇自己不討厭,于是就波瀾不驚地談起了戀愛。
三
一眨眼,紫蘇已經工作一年了。某個傍晚,學生放了學,紫蘇像往常一樣改著作業,想著姚志浩出差了,今晚是否該給他打個電話關心一下,他總是抱怨自己太不黏他了。有人在門口喊“報告”,紫蘇抬起頭,是一位穿著本校校服的女生。小女生說,她是黃琉璃的妹妹,她姐姐昨天回來了,請伍老師去她家玩。紫蘇精神一振,答應一聲,抓起小包就跟著小女生出了門——她對這個黃琉璃實在是太好奇、太有興趣了。
走進別墅區,紫蘇發現琉璃的妹妹領她走的不是上次她來過的路,仔細一想,是了,琉璃回來一定是住父母家,不該住姑姑家呀。到了主人家,空間比琉璃姑姑家越發開闊,院子里居然有一泓藍瑩瑩的泳池。紫蘇心里感嘆:真是富人啊。然后,琉璃迎出來,如同一道光照過來,什么富麗的房子,在她的美面前都不值一提。紫蘇才知道,無論照片還是視頻,都無法完整地傳達琉璃的美。當她的真人站在你面前,那種震動是難以言傳的。紫蘇原本已經做了心理準備,這一刻還是有點發懵。
還是琉璃笑著先說話了:“我本來要去學校找你的,但你看我這身打扮,沒法出門。”她的語氣溫柔而密切,就像她們一直是童年玩伴,只分開過至多一個月。被琉璃這么一說,紫蘇才凝神細打量她的裝扮:她臉上一點妝都沒有,一頭天然長卷發隨意地披瀉兩肩,穿著絲質白襯衫,白色闊腿褲,外罩著一件黑色斜紋軟呢外套;雖然穿著拖鞋,仍然比自己高出小半個頭,身姿難以形容的瀟灑挺秀。紫蘇忍不住喃喃:“這身打扮有毛病嗎?”“沒毛病嗎?哈哈哈,”琉璃笑起來,眼睛彎成兩彎明月,“你仔細看看,我穿的是我姑姑的睡褲啊哈哈。”紫蘇再細看,可不真是睡褲,純棉針織的,還是松緊腰呢,可穿在她身上怎么就那么妥帖高貴呢。
琉璃牽著紫蘇的手往里走,進到客廳里,琉璃的爸爸、后媽都出來打招呼,童年記憶里,這一對都是滿臉橫肉、極其兇悍的人,此刻卻都笑容滿面,特別是那個后媽,看琉璃的眼神簡直散發著慈母的光輝。琉璃姑姑也在,和伍老師打過招呼又坐回角落里,右手拿著一卷透明寬膠帶,低頭忙著什么。見紫蘇看她,歉意地說:“琉璃今天上午出門坐了個出租車,回來裙子就粘上條口香糖。早知道讓她姑父送她去。”紫蘇這才看見她在用膠帶清理膝上鋪著的一條黑裙子。
琉璃揚揚手:“不過是一條裙子,本來就只能穿一次。粘上東西就扔掉,非不聽,非要拿個膠帶粘,都粘了一下午了,看得頭暈。”姑姑嗔怪地看了她一眼:“一身衣服頂人家一臺車了,十幾萬呢,說扔就扔,又不是十幾塊。”琉璃一臉無所謂。后媽滿臉堆笑地接口說:“不然就別粘了,反正琉璃也不差那一半條裙子。說不定你粘半天也還是不能穿呢,白費工夫。”姑姑不應,也不抬頭,繼續一點點地用膠帶清理黑裙子上若有若無的灰白印子。這場景,令紫蘇又想起多年前,她往柳麗運動鞋上涂白粉筆的那一幕。
紫蘇決不是口拙的人,但在琉璃面前就相形見拙了,琉璃一路引領著聊天節奏,聊的都是關于紫蘇,紫蘇的大學生活、工作環境、父母健康狀況,當著琉璃家人的面,不會令紫蘇感到尷尬的話題。直到琉璃姑姑說“裙子好了”,琉璃拿過來看過,完全看不到臟的痕跡,回房間去換裙子,紫蘇才想起,琉璃好像基本沒有說自己;與來這里之前相比,她對琉璃的了解增加,僅限于坐什么航班回來,幾點到家。
琉璃換了和外套成套的裙子出來,越發高貴得不可逼視。紫蘇發現,她好像很喜歡穿黑色——可是她即使穿家庭婦女的睡褲都那么美!琉璃手捧一條米駝色織物:“送給你,紫蘇,指環披肩,回家找個戒指試試,有點好玩。”紫蘇略難為情:“哎呀,這怎么好意思,我都忘了帶禮物給你!”“這有什么,咱們之間不講究這些。”琉璃一眼看見紫蘇放在沙發上的坤包,就把披肩折了折,給她放進去,然后對紫蘇說:“咱們出去走走吧,我每次回來都沒時間看看長大的地方。”紫蘇當然不反對。琉璃爸媽和姑姑、表妹一齊把她倆送出大門,紫蘇覺得,琉璃現在在這個家里,簡直就是貴妃省親的待遇。
琉璃帶著紫蘇,熟門熟路地穿過廠區,從一扇偏僻的小門出來,外面就是護城河。兩人沿著河堤走了一段,到更僻靜處,琉璃就往地上一坐,紫蘇下意識看看她那十幾萬的套裝,只好在她旁邊也坐下來。河對岸是一片新城,間或有幾幢高樓孤獨聳立,天空混沌空濛,看不清天際線。琉璃一改在父母家活潑歡快的樣子,沉默下來,整個人仿佛籠進一團薄薄的、憂郁的霧里。
護城河的水幽幽的,水靜流深的樣子。從她們小時候起,河邊就遍植著柳樹,現在每一棵都有碗口粗了。正是落葉的季節,河面、地上都是半枯的柳樹葉子,像無數人老珠黃的細長眼睛。見琉璃看著河水出神,紫蘇慢慢地說:“你對親人真好,給他們買那樣大的房子,其實我知道,他們當年對你并不好。”琉璃淡淡笑:“你都看在眼里的,我爸和后媽對我,真的很不好;我姑姑……比他們強一些。小時候,我是真的想做些什么讓我爸還有我后媽喜歡我,可是一直沒有能夠。現在我終于可以了,你看,他們現在對我多好、多滿意。”她笑得有一絲傷痛,一絲嘲諷,“他們對我不夠好,可是其他人更不好,人活在世上總要有幾個真心在意的人吧,現在他們就是我最在意的人,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他們過得好。”要過很久,紫蘇才想起來說:“你的丈夫、孩子,那才應該是你在這世界上最在意的人。”琉璃笑得空茫:“丈夫,他那么強大,不需要我照顧;孩子,他有那么強大的父親,照顧他的人那么多,也不需要我特別照顧。”紫蘇又不知該說什么了。
琉璃說:“姑姑家的老房子拆遷了,原址上建別墅賣,安置房非常遠。后媽說,姑姑姑父祖祖輩輩都在這里住習慣了,怎么能讓他們搬到城外鄉下去。還好內地小城市房價不高,就給他們都買了。然后后媽希望我能把全家移民到香港,說主要是為了弟弟。我也正在做,應該說,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等他們都去了香港,我也就不會回來了。如果你去香港玩,記得要找我。”輪到紫蘇不說話了,她總不能說:“也許你不值得。因為他們不配。你后媽像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里那個老太婆。”
沉默了一會兒,紫蘇說:“那么早出去工作,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太苦了,比挨后媽和爸爸的打苦多了,苦得我都麻木了。紫蘇,你永遠想象不到有多苦。”琉璃仍然不看紫蘇,紫蘇卻看見她眼中有水霧升起。紫蘇瞬間知道了什么叫“我見猶憐”,她趕緊說:“好在都過去了。你身上可一點都看不出吃過苦的痕跡。”琉璃蒼涼地笑,不說話。
紫蘇開始找話說:“你的寶寶還不到一歲吧,你走這么遠,不會想寶寶嗎?”琉璃仍然看著那河水,眼神空茫:“還好吧。反正就算我在家里,也不太帶他,都是保姆們帶。”“不帶寶寶,那你每天都忙些什么?”紫蘇半開玩笑地問。“每天起床就超過十二點了,吃了早中飯,由司機開著車,去購物,或者做美容、做spa、做瘦身按摩、做美甲……有時候別的太太約喝下午茶,有時候晚上有party,就這樣啰。”紫蘇又問:“你先生的生意你完全不過問的嗎?這樣不怕有一天他把錢給別人花嗎?”
琉璃嘴角浮起一個極淺的微笑:“你如果認識他你就會知道,他這人只關心兩件事:第一,賺錢;第二,賺的錢給太太花。如果離婚,也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我堅決要離開,另一個是他發現我有了外遇。”紫蘇點點頭:“我小時候就知道,你其實是一個特別聰明、特別清醒的人。”
琉璃仍然不說話,看著水面慢慢移動著的“眼睛”,像要一直目送它們到河水的盡頭。她真是美呀,全身一層淡淡光暈,簡直不像真人;或坐或立,無論何種姿勢、何種角度,都是一首詩、一幅畫。河兩邊偶有人經過,紫蘇留意觀察過,沒有一個不是回頭兩次以上看琉璃的。琉璃一直看著眼前的護城河,紫蘇覺得,連河水都該為她停留,或者打個旋兒。紫蘇本來自詡中上等容貌,但是在琉璃面前,甘愿化為一粒塵埃。所謂“女人間的嫉妒”,在琉璃面前,都是笑話。
紫蘇遲疑地說:“為什么,我覺得,你看上去沒有很快樂?”琉璃忽然展顏一笑,說:“也許我并非不快樂,只不過,我的快樂在別處,不在他們認為應該在的地方。”紫蘇想,天哪,那一笑簡直傾城。琉璃問:“紫蘇,你有喜歡的人嗎?”紫蘇笑了笑:“有男朋友,我想,我們應該是相愛的吧。”琉璃點點頭:“那真好。不像我,結婚以后才遇到喜歡的人,那人不是我的丈夫。”
琉璃會對自己說出這樣的話,紫蘇一點都不吃驚。畢竟,她倆的世界相距那么遠,琉璃告訴自己,跟告訴一個陌生人、告訴樹洞,有多大區別呢?紫蘇輕輕問:“你有多喜歡他?”琉璃凝神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說:“就好比,你一直活在黑白默片里,沒有聲音,沒有顏色;然后,他出現了,世界一下子變成現代電影,五光十色,鳥兒在枝頭唱歌。你說,你要怎么才能退回默片時代?”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眼中光彩流轉,整個人都在發光,像是沉浸在一個無比美妙的夢境中,就像——童話里那個在圣誕夜街頭劃亮了火柴的小女孩。紫蘇嘆息,知道已經無法、也無須給她任何意見了。
起風了,整條河堤的柳樹颯颯作響,柳條在風中狂舞,柳葉兒簌簌落下,拍在臉上像小手指頭。紫蘇看見琉璃抱緊了膝蓋,她打開坤包,取出琉璃送的披肩,展開來蓋在琉璃裸露在短裙外面的光潔修長的小腿上,琉璃立刻裹緊了,嘻嘻笑著說:“回頭再送你一條。”
幾天后,琉璃的表妹來紫蘇辦公室,帶著一條米灰色披肩,說她姐姐已經走了,走前來不及來學校看伍老師,讓她送來這條披肩。紫蘇暗笑:不來也好,她要來了,會影響師生正常教學秩序的。小女生走了,紫蘇撫著一灰一駝兩條披肩,觸手細膩溫潤的開司米,最頂級的牌子,又想起琉璃父母、姑姑的別墅;想起王娟說的,琉璃送她很多東西,紫蘇想,其實琉璃有一點沒有變,就是希望她小時候遇到的人都能喜歡她。琉璃的家人很快就要移民了,那么,很有可能自己和琉璃此生都不會再見了。
四
新的學期,紫蘇當了班主任,工作量一下子大了一倍。姚志浩和雙方父母催著結婚,紫蘇也覺得,自己越來越離不開姚志浩了,于是婚事正式提上議事日程。結婚是個大工程,看房子、買房子、買材料裝修、選家具,加起來少說有一千件事要辦,紫蘇和姚志浩工作之余全都在弄這些事,全城跑,忙得腳不沾地。
有一天,紫蘇走在廠區旁的巷子里,聽到有人喚“伍老師”,一回頭,是琉璃的姑姑。很久沒見,現在紫蘇是她孩子的語文老師、班主任了。琉璃的姑姑還保留著廠區老街坊的習慣,熱情招呼伍老師去她家里坐坐。天知道,紫蘇完全是因為琉璃的緣故,才破例答應去學生家的。
到了琉璃姑姑家,說了幾句關于她女兒,紫蘇就問:“小婭應該很快會轉學吧。上次聽琉璃說,你們的移民已經辦得差不多了。”姑姑露出一個勉強的微笑:“不移了。琉璃離婚了,她現在連自己都顧不了了。”紫蘇一驚。
這時琉璃的后媽來了,來借吸塵器,站在客廳門口說她家的吸塵器壞了,“這個破房子,那么大,自己打掃能累死個人。”琉璃姑姑找出來遞給她,一邊對紫蘇說:“琉璃沒成算,基本上一個凈人被趕出來了,現在漂在香港呢,說要進演藝圈、拍電影,哪那么容易啊。反正現在就是她也顧不了我們,我們也顧不了她了。”一聽到談論琉璃,那個后媽突然激動起來:“賤貨生的小賤貨、小野種!打從她小時候我就說,老黃家根本沒有這條賤根!放著好好的闊太太不當,非要跟個司機亂搞,還讓捉奸在床!自己讓休出門不說,還連累我們,移民手續都辦了一大半了!”那個姑姑也不說話,紫蘇有點坐不住了。門口的女人扭曲著一張臉:“拍電影?說夢話吧,都生過孩子的女人了!我看她還是當回婊子靠得住!她身上流著當婊子的血呢。”紫蘇吃驚地看著她,她從未從一個人的眼里看到那樣多的怨毒。
從那家出來,紫蘇有些難過,為了琉璃跌宕的命運。琉璃的親生母親姓柳,曾是老城區有名的“雜貨西施”。紫蘇記事的時候,她已經去世了,她的故事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這一帶的談資。她跟一個常來她雜貨店買東西的中學老師好了,對,就是紫蘇現在工作的中學,那人還沒退休,教歷史的,扔在人堆里找不見的一老頭。那歷史老師當年也是有婦之夫,婚外情暴露后,兩人一度私奔,被琉璃爸爸帶著人抓回來,“奸夫”很快就悔過自新、與媳婦重修舊好了;淫婦”本來熬過了很多折磨和羞辱,但在確知這個消息后,趁家人看守不嚴,在一個漆黑的夜晚逃出來,跳進了護城河。尸體流進了江里,流到下游幾十里外的地方,抬回來的時候,整具尸身漲得有兩個那么大,婆家、娘家都不肯收葬,在外面擺了很多天,蛆蟲爬進爬出。人們掩鼻而過的時候都說:“看,這就是‘雜貨西施’,這就是破鞋的下場。”那時候,琉璃還不滿三歲,可身上卻從此背負了來自母親的“原罪”。奶奶不情不愿地照顧了她兩年,這中間琉璃的后媽進門,轄制丈夫,辱罵婆婆,霸道潑辣得神鬼都怕,各種加在一起,老太太也很快撒手西去了。然后,琉璃就成了紫蘇小時候認識的黃柳麗。可憐不久前琉璃還把血緣上的親人當做這世上最在乎的人。
本以為琉璃終于否極泰來了呢,誰知前方仍不是坦途。唯一值得替她高興的是,她已經完成了某種蛻變,終于要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了,也許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紫蘇的婚房裝修得差不多了,于是開始籌備婚禮,準備年底結婚。周日中午他倆跟父母一起吃飯,父母突然感嘆他們辦了護照,卻還沒出過國,下午姚志浩就給他們報了一個去俄羅斯的旅行團。周一下午,紫蘇去王娟的店里復印父母的身份證,預備辦手續用。王娟一邊復印,一邊神神秘秘地說:“你知道嗎?黃琉璃離婚了。她出軌司機,被老公抓了現行,凈身出戶。”作為語文老師,紫蘇簡直要表揚王娟的表達能力——用最凝練的語言準確概括了一樁八卦。但她只是說:“為什么我覺得你看起來對這事很興奮呢?”“嘿,你沒看她得意的時候狂得那樣。”“她不是還送你好多東西的嗎?怎么狂了?怎么就得罪你了呢?”
王娟顯得有點猶豫,但終于還是扭捏地說:“她上次回來的時候,我請她吃飯,她開始還挺感動的。然后我就跟她說,能不能,能不能給我介紹個香港男朋友,我也想婚姻移民,結果你知道她怎么說?她說‘這不可能,香港人又不缺老婆,不會接受婚姻介紹的。’你聽聽,說得好像我多差似的,憑什么她一個小學畢業生就能嫁給有錢人,我好歹還是高中畢業吧。”紫蘇聽了這話,簡直震驚得無以復加——原來在她心目中,她的條件比琉璃好,只因為她學歷比琉璃高!一個人的自我評價究竟可以荒謬到何種程度!還有,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在什么地方得罪一個人。
王娟將紫蘇的沉默理解為認同,繼續絮絮叨叨:“從小活得比狗還賤,仗著長得好,就能烏鴉變鳳凰嗎?現在打回原形、重操舊業也是活該!”紫蘇要到這時才說:“你知道嗎,有位美國第一夫人,她的總統丈夫遇刺死了,人人都以為她的人生完結了,結果她中年再婚,嫁給了希臘船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有的女人天生不平凡,她們想要什么,總是能得到。”說完這話,紫蘇放下錢,拿起身份證和復印件就走,一秒鐘也沒有停留。
走在校園里,紫蘇想,琉璃今年才二十二歲,卻已經結過婚、有了兒子,后面的日子全是屬于她自己的了。也許人生如一幅長卷,之前不過是長長的引首,畫心要到此刻才在她面前徐徐展開,此后山山水水都將鮮明生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