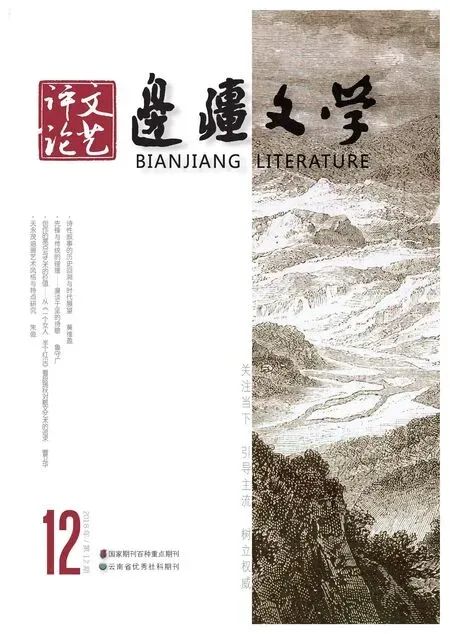用心經營的敘事藝術
——關于小說《斷層》
宋家宏
文學刊物每月都在發表小說,我們卻很難讀到不是重在講故事,而是用心經營小說敘事藝術的作品。當我讀到今年《邊疆文學》第三期上發表的、何貴同的短篇小說《斷層》時,不由得眼前一亮,作家在這篇小說的敘事藝術上顯然是下了功夫的。
小說以礦山為背景,寫了一場礦難發生之前的幾個人。礦難,是可以寫成驚心動魄的故事的,很多小說已經這樣寫了。情節起承轉合,絲絲入扣,出人意外,或凄慘,或悲壯,引發讀者的同情與憐憫,憤怒與批判。這篇小說卻不這樣寫,礦難故事幾乎全然被被虛化了,若有若無。萬余字的短篇,敘事人稱都是第一人稱“我”,“我”卻不是一個人,而是四個人,整篇小說的敘事角度在不斷地轉換。小說的主角是紅星煤礦的總工程師馬志平,其余三人皆與他有關系。一個是他的徒弟,一個是他的妻子,另一個是他的情人。作品就從這四個人的角度共同完成了小說的敘事藝術。
紅星煤礦的又一起透水事故是否與總工程師馬志平的設計有關?讀者不知道,事故的原因也被作家虛化了。小說只告訴我們,馬志平是一個技術高超、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在紅星煤礦人人敬仰。小說開篇他的徒弟就目睹了馬志平與煤監局檢查組的工程師“干起來了”的事。為了節省幾十萬人民幣,對不符合“規程”的操作,煤監局作為監管部門已經睜只眼閉只眼,網開一面了,馬志平作為礦山的自己人卻不干。他據理力爭,最后摔門而去。他的這種德行,師娘拿他沒辦法,礦長拿他也沒辦法。“可每回上面的大領導一來,都緊巴巴地把我師傅拉了坐在旁邊”。師傅的同學,一個個都是處長局長了,他還是個礦山的小工程師。紅星煤礦幾年前曾經發生過另一起透水事故,死了幾個人。馬志平因此成了夜夜做噩夢的可憐人,連一個完整的覺都沒睡過。他總是夢見那幾個死去的人,戴著瓜皮小帽,臉色鐵青,慢慢站起來,在井口晃悠。每次他都被嚇得魂飛魄散,大聲喊叫,卻叫不出聲來……。
小說的重要情節是馬志平“失蹤”。礦長在找他,馬志平的妻子牛春花在找他,找到他就可以讓他拿出那張比黃金還值錢的設計圖紙。馬志平似乎在與礦長討價還價。牛春花見到礦長才知道,“原來我們家老馬清醒著呢,他看到的是大錢。”這讓一向對丈夫充滿怨氣的牛春花欣喜異常。礦長威脅牛春花:“如果礦上找到這塊煤,黃金做的圖紙也就成了張廢紙了。”馬志平遍尋不見,所有人都聯系不上他。最終牛春花與馬志平的徒弟敲響了一家賓館客房的門,馬志平與他的情人梅小麗陷于人生中的最不能忍受的難堪。馬志平安慰他的情人:“等著我,我回去處理完所有的事情,我們結婚。”半年后,梅小麗等來的是法庭上被審的馬志平。紅星煤礦又一次透水事故發生。這次事故與馬志平的設計有關嗎?也許有,那就是命運。人算不如天算,那張比黃金還貴重的圖紙出了漏洞。也許沒有,過去礦上也不完全按他的設計施工。在沒有找到馬志平之前,施工已經開始,礦上已經在找“那塊煤”了。馬志平的圖紙有沒有漏洞,作為總工程師,出了問題,沒人會替他承擔這個責任。
我們常見的書寫礦難的作品,作家的道德審判,對事故原因的分析引向的法律制裁,是必然的。往往是上層的冷漠,底層的悲慘,引導讀者作出鮮明的價值判斷。這篇小說卻沒有太鮮明太直接的價值判斷,作品對總工程師馬志平的同情卻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對他與其情人這種見不得人的關系,作家也寫出了他家庭生活的不幸,妻子牛春花的驕橫、粗俗,使讀者對他與情人的關系有所理解。小說是否完全放棄了對礦難這樣的悲劇性事件的道德評價了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作家就會呈現出對生命的冷漠,尤其對底層礦工生命的冷漠,這是有良知的讀者絕對不能容忍的。小說并沒有放棄對一場礦難的價值判斷。
小說以變換敘述角度的方式,直接進入了人的內心世界。讀者會發現,小說中的人物內心都充滿了對金錢的渴望,而他們對金錢的渴望也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礦長要盡可能地節約成本,要找出最好的那塊煤;檢查組的專家們也在為礦山節約成本服務;牛春花粗俗,驕橫,對更多的金錢追求是她天然的本性,就連正直的馬志平,因為想擺脫家庭婚姻的不幸,與自己情人結合,也需要更多的錢。正是對金錢的渴望,礦難再次發生。小說的價值批判指向了魔獸一般的怪物——金錢,在它的籠罩下,小說中的人物都沒能逃離最后的悲劇。我以為,這樣來認識生活,理解礦山上不絕的礦難,也許是更真實的一個角度。
作家何貴同有豐富的礦山生活基礎,他完全可以寫出很好看的礦山故事來。這篇小說不僅沒有營造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甚至對礦難的原因也沒有追根溯源,而是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才是文學藝術的方式。事故原因的分析,悲劇場景的描寫,道德與法律的審判,這些應該交給新聞,交給報告文學去完成。小說應該從新聞無法抵達的地方開始,這就是人的心靈與隱秘的情感世界。在一個短篇小說中,變換了四個敘事角度,似乎給人太奢侈,太刻意,作家似乎有玩技巧的嫌疑。但讀完小說,你會發現,這一奢侈的多角度敘事,與作品要表達的意圖天然吻合。它與那些刻意營造敘事的迷宮,讓讀者去猜謎,走出迷宮卻感到內心空空如也的作品根本不同,正是這直接進入人物各自心靈的方式,使這篇小說有了別樣的藝術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