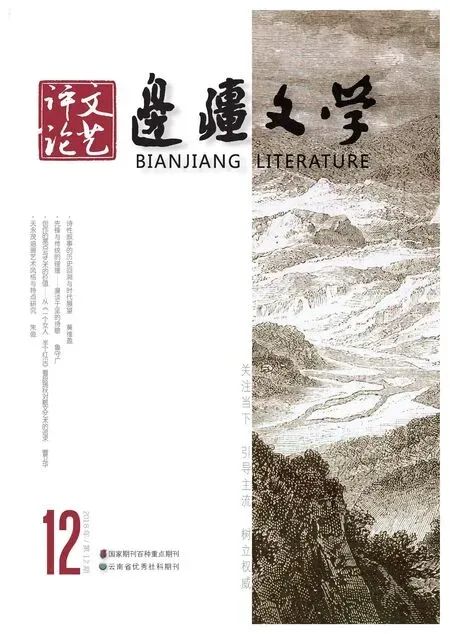“向下的”歷史
——于堅對昆明歷史的呈現
王宇歌
于堅對于城市的歷史,有著自己的進入方式和敘述手法,他用“向下的”目光觀察著昆明,用“向下的”筆觸記錄著昆明。在他的眼中,昆明一直在中原文明的陰影下成長,盡管一直被中心地帶所忽略,但是于堅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座城市的獨特氣質,在整座城市都在追逐主流文化的時候,他的雙眼和身體都發現了被隱藏的屬于昆明的,也屬于自己的歷史。于堅用個人視角進入歷史的敘述方式,呈現不同于主流話語下的“小歷史”——城市的歷史,不光是教科書里充滿政治化的體現,也是城市里每一個人的記憶、想象和感受。那些百姓的平凡生活,在他看來,才是真正的城市歷史。
在離中原文明的中心地帶十分遙遠的昆明,并沒有發生過什么驚心動魄的事件,在恢弘的中華歷史中,昆明引起人們注意的時刻并不多,無非是辛亥革命時期蔡鍔領導的革命起義,護國運動,以及后來南遷的西南聯大。“它奉獻給世界的不是濟世英雄、開國功臣、鐵血宰相和無道昏君,而是單純樸素的陽光、藍天、白云、鮮花……”“千百年來,昆明每一代的城市統治者從未產生過要把這塊大地建成一個羅馬的念頭,因為這大地激發的不是征服世界的野心,而是回家、歸宿和享受生活的渴望。”昆明的平凡并沒有讓于堅覺得乏味,相反,這種平凡生活里的故事和百姓,卻讓于堅異常著迷。他認為普通人經歷的平淡事件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真正乏味的不是那些日常,而是類似于“文革”時期的口號宣傳式的教育,是看似偉大實則虛假的“大歷史”。因為那些恢弘的背后沒有收集著人們的感情,沒有具體的發生過程,而是某種政治的導向,這對于非常注重“向下的”的于堅,注重回歸大地的于堅來說,是蒼白無力的。“我發現,人們僅僅記住了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分析和判斷,而那時間中的細節被全然忘記了。”于堅并沒有陷入這種集體的遺忘中,而是另辟蹊徑來展示歷史。“我雖然長著詩人的翅膀,卻比通常的詩歌更接近地面。”于堅所理解的昆明史,也應該是“向下的”,回歸本真的,而不是漂浮在半空的教科書里的宏大敘事。這種“向下的”歷史觀源自于他特殊的時間觀,這種時間觀提出了對“進化”的質疑,在《大地記》中,于堅表達了一種永恒的時間。“在這片高原上,時間的方向與我手表上的不同,萬物通過一次次返回它的開始獲得永生。”這種“永恒”的代表是烏鴉的漫游,于堅對烏鴉所體現出的古樸的哲學有著深深的迷戀:“烏鴉總是在這一帶,它的漫游不是要改變,而是要保守著原在。”在大部分人看來,時間是前進的,我們并沒有質疑過這種狀態;在于堅看來,時間“只是世界的無數個可以停下來、稍事逗留的點”,他從“前進”的狀態里抽身出來,仔細觀察著周圍的“點”——一個個零碎的生活片段。于堅并不迷信“進化”的時間觀,也就不會被“進化”的歷史表象所束縛,可以說,教科書里的歷史就是一種進化的歷史,人類和社會總是朝向一定的方向發展,歷史是進步的,時間是線性的,在于堅眼里,歷史也許是一只烏鴉的漫游,一個圓,它日復一日地在同一個地方堅守,城市里的居民每天重復著同樣的事情,他們的一日是一個輪回,生死是一個輪回,城市里上演著同樣的故事,時間流逝,總有一些人像烏鴉一樣堅守,那些充滿生命力的“點”,是時間,也是歷史。
“向下的”于堅絲毫不掩飾對小說的輕視,這種態度來自于他對虛構和情節化的排斥:“小說的虛構性和情節性令我厭惡,這種虛構既缺少詩歌的真正的空靈,也缺少記錄式文體的真實和第一性。”虛構讓他感到漂浮不定,仿佛離開了土壤的大樹,失去了根。他的歷史當然不是教科書里對社會全貌的概括敘述,也不是情節跌宕起伏的歷史事件,更不是虛構出來的傳奇世界,那么他所認為的歷史真相是什么呢?是關于普通人的忠實記錄,關于小人物平實的經歷和小故事,才是于堅心中的歷史。他用外祖父荒誕哀傷而又稍顯屈辱的故事和外祖母的日常生活解構了常規的歷史觀,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布匹商人,在一次運輸途中不幸被挑夫殺害,然而死時手里緊緊握住布匹不讓它被搶走,就是這樣一個沒有精彩情節,沒有殊死搏斗的平淡事件,構成于堅心中的歷史:“這歷史的一章如此寫道,曾經存在過一個為自己的布匹、妻子、兒女和家庭而死去的老板,他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獲得了世界,他活得體面、愉快。”他看到的歷史不是驚心動魄的場面,而是一個個樸素無華卻讓人心動的生活場景,是外祖母借著陽光修剪她的小腳,是某個節日里全家人外出賞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也都會忘記的事情,這些普通的場景和事件,卻造就出了時代。
在于堅筆下,“向下的”歷史也是個人歷史與城市歷史的重疊。光鮮亮麗的大事件是好比城市歷史的外衣,外衣的里面,才是真正的“里子”,這些里子是個體生活的寫照,是精神層面的個體總和。城市的歷史由個人的歷史組成,個人的歷史離不開城市這個載體。城市的物質結構,裝著個人的精神世界,個人的私密體驗和感受,也豐富著城市的內涵。
“我們熱愛一個城市,是因為你的生命和它的某條街道、某個門牌號碼、某個房間有關,它們塑造了你的生命。”城市建筑提供了可看可觸摸的歷史,這些建筑不僅僅是一座城市的外殼,它里面的精神內核就是個人的記憶、感情。城市不僅存在于客觀世界,也存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些時間積淀下來的實體空間里,存放著人們的經歷和精神世界,這些個人化的細節相互交疊著構成了城市歷史,人們的某種感情,某種生活都是從城市里的某一個房間開始的,在具體的時空里,城市塑造了個人,個人也塑造著城市,“老昆明”這個名詞正是解釋了城市和個人的密切關系:“‘老昆明’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對于居民來說,是一個空間的物質的傳統生活資料,是導致一個人的基本氣質、修養和靈感的各種氣味、光線、色彩、故事、傷疤,是記憶的種種細節和來源。”“老昆明”是什么呢?是西南聯大時期的汪曾祺在茶館里度過的一個個下午,是青春年少的學生在翠湖公園的漫步,是尚義街六號宿舍里的老吳晾在二樓的褲子,是昆明人鮮活的昨天,是生命最先開始的地方。“老昆明”是飽滿的、生動的,連接起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被澆灌上人們的私密經歷。這些正是于堅“向下的”歷史,也就是個人的歷史,私人的歷史在時光的流逝中漸漸成了城市史,關于昆明的一個個普通尋常的記憶沉淀出了“老昆明”。
一個特殊的地點,包含著無數的城市過往,也包含個人私密的記憶,這種記憶既是自己的,也是城市的。南屏街、翠湖、花鳥市場、尚義街六號、金馬碧雞,這些字眼,存活在個人鮮活的記憶里。說起翠湖,于堅想到的不是贊美,也不像汪曾祺那樣描繪詩意的湖水,翠湖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世俗的大教堂”,“欄桿下面,到處是賣小吃的,煮花生啦、五香雞蛋啦、越南春卷啦、腌蘿卜、烤紅薯、蒸蕎糕啦,還有擺象棋子賭博的……”。在于堅的視野中,翠湖是充滿著文化意蘊的,這里曾經是云南貢院,也是各種文化活動的中心,真正讓翠湖“活”起來的,是自1985年開始飛來的海鷗:“人鳥同歡同樂,一起把那一年翠湖的冬天鬧得熱氣騰騰,春意盎然。”翠湖在不同的人眼中有著不同的景觀和含義,翠湖的歷史意義在這種多元化的解讀中得到了豐富。于堅對這座城市的歷史似乎有著比別人更加敏銳的觸覺,他將個人記憶最大化地融入進了歷史中:“武成路、文廟和長春路,土雜店、館子、茶館、評書、花燈、棺材鋪、小吃攤、廟會、朱門大院、蜘蛛網一樣四通八達的小巷是明清風味的,像年老祖母自由散漫……;云南大學,哥特式的建筑,希臘式的圓柱,高貴、尊嚴;在大觀河一帶,魚腥味的碼頭,順著沿岸、赤著腳、光著膀子、用竹竿撐船前進的船夫;黃昏,沿河停滿了木船,漁民在船頭生火做飯,孩子們在船尾光著屁股跳水,悶下去,不久,就舉著蚌鉆出來。”這些具體的地點,已經升華成精神坐標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說起某個地名,浮現在眼前的就是那些往事,那些遐想。精神上的認知不僅是個人的思想史、成長史,更是這個城市鮮活的生命史和發展史。這種感性化、個人化的城市歷史,就像初春的和風一樣溫暖自然,從地點到地名,是從物質到精神的演變,個人的記憶和歷史不僅構成了一個城市的歷史,也延續和傳承著歷史,歷史在現實層面發生,在意識層面延續。城市的歷史不是孤立冰冷的,而是混合著個人情感和記憶的。可以說,城市的各個角落隱藏著個人的歷史,個人的歷史重構了城市史。
于堅心中的昆明史,是充滿一部充滿人情味的生活史,是從地下生長起來的個人記憶,瑣碎平淡而充滿感情。在其中,有我們熟悉的親人,以及那些透過日常所表現出來的看似輕描淡寫卻又深沉厚重的愛,對親人的愛,對一朵花的愛,對一間房的愛,是他以“向下”的姿態觀察和搜集的“空靈”與詩意,如果你忽略了那些人和事,你也忽略了自己。
【注釋】
[1]出自于堅的自我描述:“我的寫作方向一直是向下的,是回到大地上的。”于堅:《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2]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3]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4]李劼、于堅:《回到常識,走向事物本身》,《南方文壇》,1998年第5期,第33頁。
[5]于堅:《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6]于堅:《大地記》,《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7]于堅:《大地記》,《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8]于堅:《大地記》,《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9]于堅:《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10]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
[11]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頁。
[12]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頁。
[13]于堅:《翠湖記》,《人間筆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
[14]楊楊:《昆明往事》,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頁。
[15]于堅:《老昆明:金馬碧雞》,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