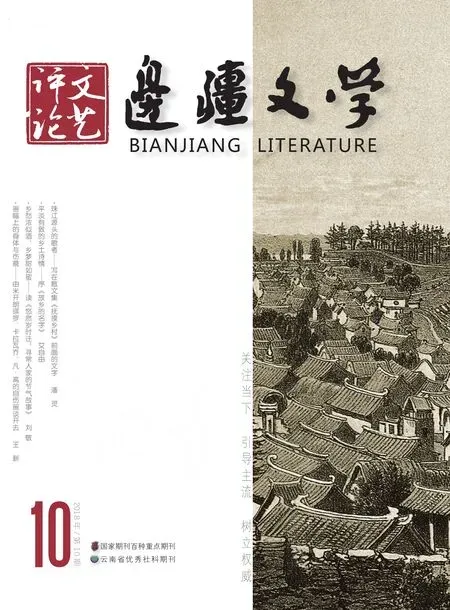沉重而綿長的民族史
——評一葦長篇小說《洱海祭》
高思遠
大理擁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以及鐘靈毓秀的蒼洱風光,在西南邊陲這片高地上,涌現了一個又一個讓大理人驕傲與自豪的民族作家,如“走出寓言”的納張元; “故鄉即他鄉”“他鄉是故鄉”,永遠走不出“心靈深處”那個兒時故鄉的趙敏……在這些譽滿大理文壇的作家里,有一位出生于洱源縣煉鐵鄉的白族農家,用心創作、用情言說民族歷史的作家一葦(楊義龍)。
讀一葦融歷史、戰爭、武俠、愛情、自然風光于一體的《洱海祭》,心中總有一絲抹不去的沉重感,這是一場發生在公元737年部落群雄間的博弈。唐王朝運籌帷幄,蒙舍詔主皮邏閣劍鋒所指,石和城、石橋城、太和城、大厘城,洱海周圍的城堡悉數攻克,鄧賧、浪穹、施浪等各部落節節敗退,終至消散在高天流云間。拿起這本書時,原本想用一種輕松的心態去閱讀這部歷史武俠小說,可讀至文末卻沉重感倍增。作品中的多數情節會讓我不時地想起曾經看過的一部震撼人心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影片講述了馬關條約簽訂后,清政府將臺灣島割讓給日本,在摧毀尊嚴和壓制信仰的民族欺辱下,臺灣高山族的族人奮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實故事。整個過程,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和部落抵御外敵的決心和堅定信仰。人性的善與惡、烈與柔,英雄的揮桿而起與部落的星墜云落,以及在戰火中綿延不絕的民族文化,無一不深深震撼著我的心。
一、烈與柔的兩極審美雜糅
《洱海祭》采用了章節體的敘述形式,這樣書寫更有利于讀者對整個故事情節的把握。在清晰的脈絡之下,使讀者去思考、去想象,作者沒有生硬地強加給讀者一些個人化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一葦和余華有著相似的表達方式。在描寫戰爭場景時,他直白的寫到皮邏閣計劃對其余五詔發動戰爭,并欲稱霸云南的野心;寫到慈善夫人與皮邏鄧相濡以沫的愛情,以及皮邏閣處心積慮想要占有慈善夫人的丑惡嘴臉;開篇淡如水的田園風景描寫,乃至后文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戰爭描寫……都為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與審美空間。一烈一柔、一剛一弱的兩極審美雜糅,使讀者在激烈的情節碰撞中進入情景,讀至文末便會悄然感嘆,惋惜良辰美景的消逝,以及民不聊生的愁苦。這種語言的雕琢與審美的碰撞讓人們讀起來,時而溫柔細膩,時而膾炙人口。
小說大量運用對比、渲染等手法,極力展現烈與柔交織的矛盾沖突。作品通過對戰前蒼洱秀麗風光的描寫以及戰后橫尸遍野、血染洱海的場景進行對比,使讀者產生矛盾,在想象視覺和心理上都受到了一定沖擊。殘酷的戰爭與人性的光輝同樣也構成一對矛盾。烈焰燃燒的天空、布滿血跡的刀鋒、凄慘煎熬的呻吟聲……無一不為我們構建了一個殺聲震天、殘酷冷血的戰爭場景。在此之下,作者沒有停筆頓足,事情到了極度壞的程度也會向好的方向發展,此可謂“物極必反”。人性的光輝充分體現了“柔”這一審美特征,慈善夫人深明大義、高風亮節;德隆、邏莎雖高居將領之位,卻保有一顆赤子之心、行善之心;百姓們在鄧賧民族被圍剿時的鼎力相助,都為我們展現出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兩組矛盾交相呼應,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凸顯烈與柔的兩極審美視角。
二、民族的形象,形象的民族
小說能不能打動讀者,跟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的精神、情感投入有直接關系。在《洱海祭》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許多性格鮮明突出、心理變化復雜多樣的個性人物。與《遙遠的部落》相比,此書以德隆這個虛設人物作為第一人稱來敘述,情節性更為嚴密,人物性格更為精細復雜。如老來糊涂、茍且偷生的咩邏皮;善良仁和卻慘遭焚身的皮邏鄧;聰慧美麗、深明大義的慈善夫人;殘忍血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皮邏閣;以及作者虛設的人物“我”,德隆這一千夫長形象。其間糅合了歷史文化小說、武俠小說、奇俠小說等眾多小說的特點,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呈現出一個形象的民族。
其中以“我”為文章的中心點,貫穿于整部作品的脈絡中。“我”是慈善夫人的愛將,是她的一柄“無比鋒利的長劍”。我們通過德隆的眼睛和心理,看到了慈善夫人的烈性、高潔、細致、靈敏,還看到了她奮力掙扎的靈魂、深明大義的性情。文始“我在心里已為她立了一座廟”“我的一生彌漫著愛情的憂傷”。“這么多年來,我已看老了蒼山,看皺了洱海,看淡了世間一切的一切。”與文末“在沉下去的那一瞬間,我似乎又看到了她含笑的臉”,“用我的一生,用我所有的力氣去思念她。很快,我也將死去。可我的精魂,仍會在蒼山洱海上空飄蕩,日日夜夜思念著她。”相呼應,在這里文字已不再停留于表述故事內容這一功能,而是從人物內心世界挖掘潛藏的歷史文化內涵。在作者筆下,將簡潔樸素的語言和豐富奇幻的想象結合,將敘事與抒情結合,倒敘、插敘、補敘、內心獨白等藝術手法的運用,使小說的深層意蘊直指讀者心靈深處,感染力可謂之巨大。
書中的母親河——洱海,在整部作品中的象征意蘊也十分濃厚。水之柔、水之剛、水之善、水之凈,能容戰爭之污濁、惠及西南高原上的百姓。這無不體現著我們中華民族寬廣的胸懷。作品中形象的鄧賧民族,實則象征了堅強不息、正義凜然的整個中華民族。中華魂、民族魂在這里重現,一個堅韌、正義、頑強的民族巋然屹立于東方這片凈土之上。
在深明大義、懲惡揚善的民族的形象背后,潛藏著深層意蘊中的形象的民族,有力地向我們呈現出人性的真善美和世俗的假惡丑。
三、戰火燒不斷的民族文化
激烈的敘事情節背后,作者為我們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此之前,我們所了解的傳統小說中的故事是統一的,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經典模式,往往由一個簡單的“由頭”開始,經過一場復雜的變化歸于一個簡單的結尾。這構成了傳統故事中穩定的平衡結構: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尾。按照德國學者古斯塔夫·弗萊塔格的描述,“一個標準的故事”有些類似于一個倒放的“V”(∧)字。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小說的故事組成往往依賴于戲劇性的沖突與巧合,而一部分現代小說組織故事所依據的是生活或存在自身的邏輯和規律。
一葦的《洱海祭》突破了傳統敘事的宏觀性和崇高性,以純文學之筆敘寫了主流歷史之外的民族文化和民俗傳說。作品中出現的“百抖茶”“餌塊、苦蕎餅粑粑”“摜斗”“榆石”等眾多滇西地區的飲食、農耕、山石特色。讓讀者從傳統的敘事情節中走出來,好似中場休息、旅途觀賞一般欣賞這些主線情節之外的民族文化。作者大膽的構思與描寫,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呈現了紛繁復雜的歷史圖景,展現了一部歷史長河中綿延不絕的民族文化史。
其中不乏對中原地區與民族地區文化差異的對比。中原地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遠,人們大多崇尚中庸之道,語言表達較為含蓄、委婉;與民族地區粗獷的風格、豪邁的情懷,以及崇尚自由、語言直白相對比。使讀者從一個新的層面了解到,中原地區重“禮義”,而民族地區則更重“自由”。
《洱海祭》構筑了一個以個人、社會、民族、文化、靈魂為一體的極力表現個體心靈體驗與審美體驗的一部長篇敘事小說。充盈的畫面感和歷史的厚重感鮮明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對民族英雄形象的繪制、人物心理細致的刻畫,無一不深深地留在讀者的腦海中。作品打破傳統敘事模式,大膽勾勒、想象,格調高雅沉寂、意味深長,詩性的語言和深邃的思想帶給讀者巨大的感染力。讀完整部作品,我們看到了作者扎實的寫作功底和獨具特色的構思藝術。一部好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