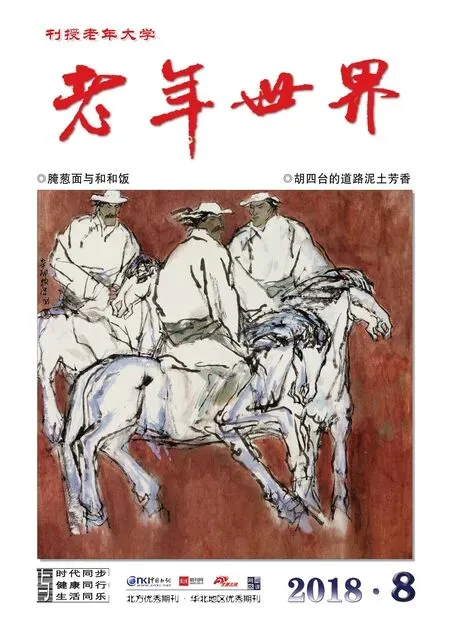當(dāng)年的內(nèi)蒙古文化局農(nóng)場(chǎng)
明 亮
上世紀(jì)60年代初,我從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xué)校畢業(yè),被分配到內(nèi)蒙古電影制片廠。是時(shí),國(guó)家連續(xù)遭受?chē)?yán)重自然災(zāi)害,吃飯成為國(guó)人頭等大事。內(nèi)蒙古文化局(現(xiàn)內(nèi)蒙古文化廳)為緩解饑荒,按著當(dāng)時(shí)的政策,在畢克齊鎮(zhèn)南的溝子板村辦了一家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場(chǎng)辦公的地點(diǎn),我們統(tǒng)稱“場(chǎng)部”。場(chǎng)部不知從哪里弄來(lái)20來(lái)只羊,借村里的飼養(yǎng)院,白天放,晚上圈。文化系統(tǒng)各單位抽調(diào)人員輪流前來(lái)農(nóng)場(chǎng)勞動(dòng)。我來(lái)的時(shí)候,農(nóng)場(chǎng)已初具一定規(guī)模,有房住、有地種,頓頓能吃到一些城里人見(jiàn)不到的新鮮蔬菜。
見(jiàn)我到來(lái),場(chǎng)部領(lǐng)導(dǎo)喜出望外。原因是現(xiàn)有的人員,除了幾位年紀(jì)較大的干部,其余全是女性,各年齡段不等。我從學(xué)校出來(lái)時(shí)間不長(zhǎng),剛19歲,給農(nóng)場(chǎng)添了一個(gè)小伙子。“你來(lái)得正好,”場(chǎng)部領(lǐng)導(dǎo)說(shuō):“你就住飼養(yǎng)院里,那一群羊歸你了。”
飼養(yǎng)院一進(jìn)院門(mén),左手便是羊倌住的小屋,院里挺大,20來(lái)只羊都抬起頭來(lái)望我,它們或許猜出來(lái)了,我是它們新上任的“司令”。院落北面,有幾口菜窖。
從沒(méi)有放過(guò)羊的我,1962年3月9日,當(dāng)上了羊倌。北方的早春,乍暖還寒。我把幾只產(chǎn)下不久的羔羊托付給一位年長(zhǎng)者就出發(fā)了。野地滿目一片干枯褐黃景象。這個(gè)季節(jié),羊群盡管低頭親吻大地,經(jīng)過(guò)一冬,大地上可以吃到的剩草很少,它們的肚子里和我的一樣,總是欠缺的。所以,每天晚上,我還得給它們煮黑豆喂。順便,煮黑豆者也可嘗幾口黑豆。現(xiàn)在想起來(lái),那些天,我還沾了羊的光。只是當(dāng)年肚里沒(méi)油水,每次出外放羊都要忍饑挨餓。
那天,我照例起得很早,把羊圈大門(mén)打開(kāi),趕著羊群走向村東。冥冥之中,開(kāi)闊的野地里傳來(lái)一個(gè)嫩弱的不知是什么聲音。記得有一天晚上,我曾經(jīng)從村里遠(yuǎn)遠(yuǎn)地望見(jiàn)東邊這片草灘上有過(guò)一群野雁露宿。難道是雛雁的聲音?我循聲走去,不遠(yuǎn)處的地面上有一個(gè)黑東西。靠近細(xì)看,只見(jiàn)一個(gè)被棉褥裹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只露出紫色小臉的初生嬰兒在無(wú)力地哭喊。棄嬰!我立馬感覺(jué)到緊迫。在這樣一個(gè)饑餓的非常年代,這樣的事情難免出現(xiàn),養(yǎng)活一張嘴,不易呀!面對(duì)眼前一個(gè)奄奄一息的脆弱小生命,我豈能繞過(guò)去不管。刻不容緩,沒(méi)有時(shí)間考慮許多,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嬰兒,羊群顧不上了,火急火燎地往場(chǎng)部跑。早晨的場(chǎng)部里,領(lǐng)導(dǎo)們剛剛到。快!我推開(kāi)門(mén)喊他們,“給這娃喂點(diǎn)什么!”聽(tīng)我揀來(lái)一個(gè)娃子,外面人都來(lái)看,你一句我一句獻(xiàn)策。還是年長(zhǎng)的人,不但有經(jīng)驗(yàn),辦事也牢靠。很快,他們拌好一碗不稠不稀、不冷不熱的奶粉,找來(lái)一具奶瓶,還不知從哪家請(qǐng)來(lái)一位有奶的農(nóng)婦。屬于我的大任,我已經(jīng)大功告成,我還得看好我的羊群,把棄嬰交給場(chǎng)部里的領(lǐng)導(dǎo),輕輕的我走了,帶著幾絲牽掛。

中午回來(lái)后聽(tīng)說(shuō),那是一個(gè)女?huà)耄钸^(guò)來(lái)了,讓一位在農(nóng)場(chǎng)勞動(dòng)的某單位一位同志抱回了城里的家。這事,算起來(lái)距今已有56年了,那個(gè)女?huà)耄F(xiàn)在也已奔花甲了,不知在哪里,日子過(guò)得一定很幸福。
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場(chǎng)部的領(lǐng)導(dǎo)來(lái)找我,說(shuō):“小烏,羊群暫先讓別人放吧,給我們農(nóng)場(chǎng)放馬的云二旦病了,馬要夜牧,馬不吃夜草不肥嘛!你先替他放馬,行不?”我這才知道農(nóng)場(chǎng)里原來(lái)還有6匹馬,從村里雇了一個(gè)小伙子放著。“行啊!”我說(shuō)。
夜幕四合,我從村東頭的羊圈走向村西頭的馬廄,從云二旦的手里接過(guò)6匹高頭大馬,向野外走出。初夏的夜晚,沒(méi)有月亮,深空群星閃閃爍爍。病中的云二旦曾說(shuō),夜里天黑,你得蹲下身子,靠地面向遠(yuǎn)處望。此刻,我想起云二旦的話,臉貼近地面望去,嗬,果不其然,能望到很遠(yuǎn)。站起身來(lái),我尾隨6匹馬不停地走。突然,馬群呼啦地跑起來(lái)了。怎么回事?貼地面向東向西望,沒(méi)有什么呀。再轉(zhuǎn)過(guò)身往北望時(shí),遠(yuǎn)處有一個(gè)黑東西影影綽綽向這方竄動(dòng)。不好,可能是近來(lái)村里人常提起的那個(gè)叫狼的可怕家伙。我一激靈,撒開(kāi)腿,朝馬群奔跑的方向拼命跑起來(lái)。那速度絕對(duì)是今生所沒(méi)有的,地面凹凸不平,幾次險(xiǎn)些磕倒。一口氣跑一大截,見(jiàn)馬群停息了,我喘著粗氣再向北邊望時(shí),什么也沒(méi)有了,四周靜悄悄的。一直挨到天麻麻亮,我趕著6匹馬往回返。到村里,把馬群圈好后,我到場(chǎng)部,把夜里發(fā)生的事,向大伙兒說(shuō)了一遍,大伙兒聽(tīng)得十分認(rèn)真。領(lǐng)導(dǎo)對(duì)我說(shuō):“好了,你回去休息吧,今晚別放馬啦。”
7月9日,我被調(diào)回制片廠。人有時(shí)候很奇怪,越是餓的、累的、苦的日子,越是讓人懷念。我懷念當(dāng)年的畢克齊溝子板村文化局農(nóng)場(chǎng),它給我的一生留下了東邊放羊,西邊牧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