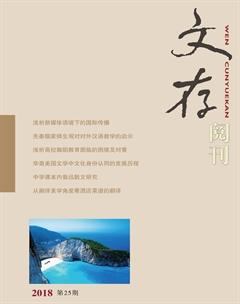新時期以來文學中的“上海懷舊”現象探析
黃瀚
摘要:新時期以來,文學中的“上海懷舊”大致可以1990年代中期為界分成前期和后期。前期的“懷舊”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全球化趨勢中尚未充分現代化的上海尋找“鏡像”,透露出上海及其中產階級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尋求身份認同的迫切需要。后期的“懷舊”開始關注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試圖建立昔日上海生活與當下生存狀態的“對話”,但受到消費文化裹挾,多重上海形象亦受到遮蔽。如何處理“懷舊”對象的“上海性”與“世界性”,是“上海懷舊”書寫必須應對的問題。
關鍵詞:“上海懷舊”;文化認同;“對話”
新時期以來,文學中的上海想象可謂洋洋大觀,“張愛玲熱”方興未艾,又出現“上海懷舊”熱潮。單就文學創作而言,起初是程乃珊的《藍屋》《女兒經》吹起微瀾,而后王安憶、王曉玉、趙長天、沈善增、陳丹燕、孫颙、王周生、殷惠芬等作家紛紛加入創作隊伍,掀起“上海懷舊”風潮。[1]繼王安憶《長恨歌》轟動文壇之后,金宇澄的《繁花》再次引發熱議,并于2015年獲得茅盾文學獎。面對文學中的“上海懷舊”現象,我們不禁要問:作家們“懷”的什么“舊”?為何要“懷舊”?這種“懷舊”有何價值或存在哪些問題?
一、城市歷史的追尋:記憶與遺忘
1990年代中期之前,文學中的“上海懷舊”風潮看似鋪天蓋地,“風暴眼”實則相對穩定。首先,從作家們追懷的歷史時期來看,“上海懷舊”作品的故事時間相對集中。王曉明在論及王安憶的小說《富萍》時指出,之前“上海懷舊”作品的“視線始終流連在20和30年代,仿佛那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不曾發生”。[2]且不說上海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單是1843年開埠通商以來,上海的歷史也足夠豐厚。可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普遍把“懷舊”的目光聚焦于二三十年代,顯然那個時期的上海是作為“東方巴黎”的國際性大都會登峰造極的上海。其次,就作品中的空間展示來說,新世紀之前的“上海懷舊”作品普遍“既不懷蘇州河兩岸工廠、倉庫和棚戶區的舊,也很少懷市南、市北那些彎彎曲曲的平房里弄中的貧民生活的舊,甚至也不大懷石庫門里‘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擁擠生活的舊,它的目光只是對準了外灘、霞菲路(今淮海路)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對準了舞廳、咖啡館和花園洋房。”[3]再次,就作品中的人物來看,如程乃珊《上海探戈》里的阿飛、老克勒、ARROW先生,《上海女人》中的上海Baby、少奶奶、彈性女孩兒、上海名媛,以及陳丹燕《上海的金枝玉葉》中的戴西、《上海的風花雪月》中的皮克夫人等,無不屬于當時上海中上階層時髦者中的一員,他們常常流連于豪華、奢侈的場所,成為物質消費層面上的上海傳奇。
一般來說,對一座城市的追懷是多層面、多維度的,而“上海懷舊”卻傾向于追懷二三十年代最為繁華的上海、呈示現代化和全球化意義的上海、富有中上階層生活想象的上海。多數作家為何對苦難的上海、落后的上海、市井的上海進行了選擇性遺忘?其實,在這種懷舊中,作家們賦予昔日上海全球化、現代化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再次成為國際性大都會而又尚未充分現代化的上海尋找“鏡像”。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雙重文化認同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國各地經濟取得飛速發展,而上海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卻節節下降;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跌入了它自開埠以來命運的最低谷”[4]。在這個階段的“改革文學”敘述中,上海成為保守、落后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象征。而此時,“人民公社”“上山下鄉”等政治話語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市場經濟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背離國家元敘事的中產階級生活敘事悄然興起。1993年,伴隨著上海的全方位開放,尤其是浦東新區的開發,上海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迅速崛起,再次走上時代前沿,成為星光璀璨的“東方明珠”。一方面,經濟的發展極大豐富了國人對未來國家現代性的想象,上海作為昔日的“飛地”、今日的“魔都”,在全球化進程中再次被賦予國家現代性的意義,這時的上海再次面對全球化趨勢,迫切需要進行自我身份建構;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以風卷殘云之勢驅散1980年代浪漫主義精神殘留之際,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底層市民需要精神寬慰,更廣泛意義上的民眾精神危機愈益凸顯。因而,“倘說今日的‘市場經濟改革正需要一處地方來酵發人們對于‘現代化的崇拜,釀制能安撫人心的意識形態,那上海無疑是最恰當的地方了。”[5]上海的獨特性在于,它仍舊部分地保留著租界時代的生活方式、日常趣味和審美心理,這恰恰符合中產階級在新的全球化想象中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需要。因此,在多種因素的促使下,“上海懷舊”成為一種社會集體行為:不僅有“整舊如舊”的大規模的街區改造;也有商業資本注入后興建的帶有1930年代歐陸風格的娛樂消費場所;還有大量相關文化產品的廣泛傳播,如程乃珊《上海探戈》、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素素《前世今生》等上海懷舊文學作品的出版,以及王家衛、侯孝賢、謝晉、陳凱歌、張藝謀等執導的舊上海題材電影的公映。
文化認同的需要常常來源于身份不確定時的焦慮,在新的歷史機遇面前,如此大規模的懷舊其實暴露出國人對全球化經驗的普遍匱乏。一方面,在這股懷舊風潮下,“新上海”被嫁接到1930年代舊上海的“全球化邏輯之中”,“新舊上海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瞬間構成了一種奇妙的互文性關系,它們相互印證,交相輝映。舊上海借助于新上海的身體而獲得重生,新上海借助于舊上海的靈魂而獲得歷史。”[6]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作為最缺乏安全感的社會階層,有著“迫切要讓自己從屬于什么的欲望”,“小資”“時尚”“消費”等可供身份確立的表述對其“總是具有強大的誘惑力”。[7]“經歷了大的國家動蕩后”,中產階級要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找尋那“雖然困頓但不失精致且有些許榮光的中等階級的生活方式”,通過個體經驗或想象的書寫接續張愛玲等開創的上海文學敘事傳統,以完成“中產階級層面上的上海身份認同”。[8]
三、在懷舊中尋求“對話”
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懷舊”呈現出別樣風貌:王安憶《長恨歌》的故事時間起始于1940年代,也就是昔日摩登的上海開始走向下坡路的時期;《富萍》則把故事安放到了混雜著殖民遺風和社會主義風尚的1950年代;金宇澄的《繁花》則以1960年代為故事的起點,1960年代恰恰是之前上海懷舊故事終結的時間。不僅如此,《長恨歌》里的里弄、《富萍》里的梅家橋、《上種紅菱下種藕》里的華舍鎮、《繁花》里的石庫門,這些更加切近市民日常生活的上海民間空間取代了外灘、百樂門、霞飛路等全球化、現代化意義上的空間指稱。在《長恨歌》中,王安憶開篇對上海弄堂、閨閣、流言、鴿子等細致入微的把握已經觸摸到一個有溫度、有性格的上海。及至《富萍》等作品,作家又將懷舊的對象由資產者國際化的摩登生活轉向普通市民平淡、堅忍的市井生活。“懷舊”的時空轉移后,作家們所要追懷的對象、作品所傳達的精神意蘊顯然會發生巨大轉變。
然而,這幅貼近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上海面孔真的可靠嗎?在《長恨歌》中,敘述者雖對追新逐異的年輕一代不無批判,可當昔日“滬上淑媛”王琦瑤在80年代再度成為時尚主角而引人注目時,她卻戲劇性地因此而丟掉性命。這層意義背后似乎隱藏著王安憶對“上海懷舊”的態度:那個逝去的上海已經追不回來了。既然昔日的上海已經無法再現,那么任何對上海的基于經驗或想象的書寫,實質上都是作家對城市的再解讀。
馬林內斯庫認為,“懷舊”是后現代主義的重要表征,“后現代派對于現代主義烏托邦式僵化的回應,是提倡一種有記憶的(現代)城市”,在懷舊中“過去開始不斷被修正”,“它不僅是可以在理性主義情境中重加利用的僵死或過時形式的一個倉庫,而且是理解和自我理解的一個‘對話空間”。[9]我們注意到,“上海懷舊”的作品常將故事安插在舊上海與當下之間,舊上海的人物行為和生活方式常常與當下形成“對話”,從而實現對歷史和當下的理解或批判。金宇澄的《繁花》奇數章寫60年代阿寶、滬生們在上海的少年生活,偶數章寫90年代他們在上海的成年生活。豐富有趣的成長故事經由“文革”、進入九90年代后變得越來越扁平,由于生活意義的空洞,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無非是由一場飯局到另一場飯局,由一場偷情到另一場偷情。任由欲望肆虐、縱情狂歡之后,阿寶、滬生們落個支離破碎、猙獰可怖的結局。一場繁華夢幻滅之后,題在扉頁的那句“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圣諭般照亮整個故事:成年世界的秩序失范直指“文革”時期的價值顛倒與人性扭曲,而阿寶們的欲望泛濫、生活盲目折射出當代人的精神空洞與信仰危機。在此,上海“已不僅是文學、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點綴,而深入小說肌理,再造了小說的敘事技術,因此能夠解放文體,以小說的方式傳達作者的情趣理念,從而真正使上海這一具體的地方,成為一種小說方法。”[10]
市場經濟興起后,社會矛盾迅速激化,人們精神空虛、道德淪喪、物質崇拜等問題亦亟待應對。在此情勢下,返回歷史尋求歷史資源,就成為作家重返當代生存現實,重建對社會巨變的深入理解的必然選擇。這樣,有著一百多年的現代歷史、長期以來具有獨特國族寓言意味的上海,就自然而然地進入作家們的視野。對于作家們來說,“上海無疑就是研究中國現代轉型中的人性和社會過程的實驗場所”,“這也是今天,在文化、經濟和政治建設各方面有所迷惘的我們,依然覺得上海經驗與上海敘事是如此重要的原因”。[11]因而,“上海懷舊”成為作家們洞察當代中國人基本生存狀態的審美門戶和處理當下生存困境的一種思考方式。
綜上所述,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上海懷舊”作品,上海形象基本上依附于中國全球化的想象圖景,上海只是作家們展開對歐美的想象性敘事的地域基礎,上海本地的文化身份并不具備獨立意義。也就是說,那股“上海懷舊”風潮的盛行,在某種程度上是以“上海性”的喪失為代價的。大約從王安憶《長恨歌》開始,一部分作家逐漸將目光轉移到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上海懷舊”敘述呈現出離棄國家宏大敘事,而從個人經驗或想象出發進行個體化書寫的特征。但“這種‘反宏大敘事修辭早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流行且最不容忍異議的宏大敘事”。[12]如研究者指出,這些“上海懷舊”作品“從對于上海話乃至于上海風俗文化的無限熱愛出發,吊詭地把上海文學變成了地方文學”。[13]如此“懷舊”風潮下,革命的上海、沉重的上海基本上已被遮蔽,文學中邊緣的、個體的上海事實上成為一種文化產品而被消費、被觀賞,那個本應充滿內在裂隙和多重經驗沉淀的上海愈發難得一見了。如何在“上海性”與“世界性”之間尋求某種平衡,抑或如何跳脫出“上海性”與“世界性”的思維模式,尋求另一種可能,是“上海懷舊”書寫面臨的一大難題。
參考文獻:
[1][4][8]張鴻聲.文學中的上海想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9,80-81,259-260.
[2][3][5]王曉明.從“淮海路”到“梅家橋”——從王安憶小說創作的轉變談起[J].文學評論,2002(3).
[6]鄺新年.另一種“上海摩登”[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1).
[7][美]保羅·福塞爾.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48.
[9][美]馬泰·馬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302-303.
[10]叢治辰.上海作為一種方法——論《繁花》[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2).
[11]張屏瑾.日常生活的生理研究——《繁花》中的上海經驗[J].上海文化,2012(6).
[12]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346.
[13]黃平.從“故事”到“傳奇”——《繁花》與上海敘述[J].當代作家評論,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