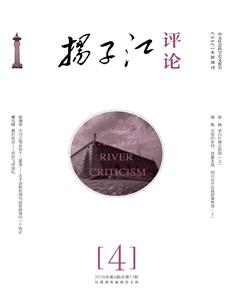新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動向
余凡
一、“十九世紀創作方法”與文學經典化的主導標準
新世紀以來,文學經典化問題的討論是一個持續性的文學景觀。顧彬的“垃圾說”是引發這一討論的導火線之一。顧彬在《語言的重要性》中對其所持觀點作了學理性闡釋,主要涉及當代文學的語言和創作方法兩個方面問題。顧彬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語言問題的判斷是準確的;而對后者的判斷則偏失較大,與文學現實狀況不符。
顧彬認為導致中國當代文學“衰微”的原因不在于文學外在發展環境等影響因素,而在于作家未做到對語言的錘煉與經營,語言應當是作家首先關注的問題。“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基本難題,是語言沒有成為作家最重要的關懷,而只是用來編造書面娛樂的工具。”a對于當代作家作品語言現狀的不滿,在中國學者這里達成了共識。王彬彬較為認同顧彬對當代作家語言表達能力的判斷,二人在強調文學修辭審美、詩性追求方面以及對當代詩歌的肯定方面是相契合的。并且,注重語言上的返璞歸真、準確練達是王彬彬在文學批評中一直強調的標準。王彬彬認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成為好作家的條件之一即“對語言的高度敏感和一字不茍的寫作態度”b。且在語言美的背后則是作家和學者對筆下創造物的精神追求,文學思想觀念必須通過好的語言才能得以傳遞。語言既是陳述的媒介,而其表達所營造的多重意境和意象又使語言超越了工具功能,達到了新的層次。“在文學創作中,語言是第一位的,語言是最根本的,語言甚至就是文學的全部。孫犁也好,汪曾祺也好,王家新也好,都是在強調一個老得像木乃伊的道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c具體到當代作家創作,語言是其軟肋,拉低著當代文學的成就。當代作家作品的語言寡淡,好似“從水龍頭里流出來的語言”d,缺乏文學意味,缺失對語言的細致打磨、細致修改,這是當代作家的通病。顧彬、王彬彬對語言突出強調的背后是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對語言的長期忽視。自新時期以來,西方多種文學創作方法和批評方法引入中國,不同方法對文學創作和批評發揮著不同的功效。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作為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之一的語義學批評方法,是文學創作、批評和研究的基本標準和基本出發點。文學語言的敘述姿態在于表現“顯性文學自身,亦即作為美的終極性本身”e。當作家和學者忽視了語言這一基本規范,而追求一些“高深渺遠”的理論方法標準時,文學偏離了自身的基本軌道,最終會造成思想因語言低劣而無法展現。莫言語言的“泥沙俱下”是“質疑其小說藝術水準的最有力證據”f。因而,恢復語義學批評在文學研究中的基礎地位,才能夠促進文學的進一步發展。
在創作方法上,顧彬立足于文學現代性的追求,反對“十九世紀創作方法”,認為今日標準下好文學應當具有先鋒精神,注重對心靈世界的開發,排斥小說文本的故事龐雜、篇幅巨大、人物眾多。然而,顧彬對創作方法高下優劣的判斷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其“對現代性的理解和文學價值觀的持守都非常狹隘、偏執,缺少必要的多元化眼光和容納性”g。顧彬對文學經典所持的標準、對文學傳統的態度和中國文學基本形態的把握是錯誤的。顧彬所推崇的現代主義創作方法,與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追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就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現狀來看,顧彬所反對的“十九世紀創作方法”非但未過時,反而占據著當代文學創作方法的主導地位。“十九世紀創作方法”是中西傳統的文學創作方法,這種“方法”一直以來被中國包括作家、批評家在內的讀者所普遍接受與認可,其指導下的創作作品比20世紀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方法下的創作具有更多的讀者群。更為重要的是,“十九世紀創作方法”背后的文學立場標準恰恰也是文學經典化甚至當代文學地位評價的主要評判依據。新時期以來的四十年間,中國文壇將西方百年來新的創作方法都“操演”了一遍。然而,創作方法狂歡的同時則是對方法有效性的反思:從讀者接受角度而言,最接近文學傳統的創作方法才是讀者最能接受的文學樣態,其背后的價值標準和文學立場也最具恒定性。中國讀者對傳統文學經典有著良好的接受基礎和閱讀慣性,使得中國讀者對小說的故事、人物、情節等方面的傳統構成模式天然地認可。在《問答錄》這部創作談中,李洱將自己所處在的“60后”作家稱之為“懸浮的一代”h,講述了“60后”作家與“50后”作家在價值觀念、創作理念上的明顯差異。程光煒根據對《問答錄》的觀察,認為中國“60后”作家未成為文壇的主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堅持以二十世紀創作原則“制作”他們的作品,而“廣大讀者和文學批評家對小說的認知仍停留在19世紀文學那里”i。這是為何“60后”作家雖曾崛起但依舊不溫不火,而“50后”作家依然是中流砥柱、無法被取代的原因。程光煒的觀點反映出中國讀者群的基本現狀:關注文學敘事容器內盛物的“十九世紀創作方法”契合了中國的文學傳統,和讀者的知識結構、閱讀習慣;注重文學敘事容器自身的二十世紀創作原則在讀者群接受上卻無法占據太多的優勢。陳忠實曾警醒地認識到:“現代派文學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j李銳的“拒絕詩意化”k創作理念則也是對現代和后現代主義創作理念的警惕。這說明,“十九世紀創作方法”背后所涵涉的文學價值觀念、創作形式和審美趣味,并未因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流行而被文壇所舍棄,而是依然被廣泛認同。同時,新世紀文學創作模式的主流是回歸文學出發之地——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創作風格與“十九世紀創作方法”之間具有內在統一性。因此,所謂“50后”作家“精神主體的自覺”l,其實質依然是作家對“十九世紀創作方法”所具有的直面現實、對話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進行繼承的體現。
中國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不滿和在世界文學視域下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焦慮是文學經典化討論得以擴大化的關鍵,而顧彬這位漢學家的“垃圾說”僅僅是引發文學經典化討論的一個由頭。爭論雙方能夠各持一詞并都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于,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創作模式和評價方法具有多樣性,致使經典與非經典之間界限模糊,以往的經典可能被去經典化,而非經典作品則可能被請上經典之高臺。從文學理念的新變和研究方法的轉型角度上看,導致文學經典評判標準的變遷和多樣原因有三:第一,破除舊研究方法、舊話語邏輯的束縛后,新的研究方法啟發了人們對問題的深化認知。人們一旦解除原有思維觀念的束縛,對文學問題的思考就可以站在更高層面,發現原有思維標準和研究方法的偏執和缺陷。盧新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對《傷痕》所涉及到的那段歷史的思考,“政治悲劇”已無闡釋效力,應當回到傳統文化,“從文化悲劇的角度尋求根源”m。這說明從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積弊與缺陷角度來審視特定階段的歷史事件,則看的更加深遠、更具科學性。有學者以《子夜》的“主體性缺失”和《家》的“非審美性激情膨脹”n等缺陷為由,認為二者在藝術性和思想追求上不符合經典的標準。相比較而言,《駱駝祥子》因其凸顯了主體意識、呈現出人性的多面而可以被歸于經典。這是文學研究方法由社會政治標準轉變為人本主義標準后對文學經典進行再解讀的典型。第二,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秩序影響下的讀者觀念和審美趣味左右著文學的發展走向。社會生活的秩序與原則影響著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知,時代新變導致了人們認知方式、創作理念和審美標準的變遷,影響到作家和學者對歷史和文學的表達方式。且時代文學主潮、品格形成由“當下興趣”o主導著:左右文學觀念、文學書寫的最大因素是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念、社會生活和讀者趣味,而非通常認為的文學“制作者”——作家和批評家。這就是說,從某種程度上講,對理想文學的指認并非由作家和批評家所決定。第三,文學的代際差異和作家的先鋒精神導致了文學創作風格的新變。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與“文革”記憶》考察了從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文革書寫呈現出情緒情感、敘述風格、主題思想上的顯著差異。即由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情感上由悲痛敘事基調下的傷痕、懺悔和反思到90年代的怪誕和游戲狂歡,很明顯地體現出對歷史事件書寫由統一化、整體性的“大歷史”走向零碎化、個人化的“小歷史”轉變p。這里的懺悔書寫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式懺悔,更多地體現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體現出“同情人道主義”q的精神實質。而90年代的文革書寫怪誕化在體現作家主體性的同時,書寫對象本身也作為一種景觀而存在。“當歷史處于主體化想象時,人成了歷史的闡釋者,這必然意味著對某種規范化歷史真實的懷疑和重構,人對歷史不是無窮地認同事實和探究真相,而是以消解客觀性歷史真實來解構主體性歷史神話。”r且對歷史的個人化書寫,使“被遺忘或被壓抑了的歷史真相浮出水面,在對歷史進行去蔽的同時,實現了對歷史的祛魅”s。文革的不同書寫風格暗藏著不同作家對待歷史的態度:懺悔體現出作家作為當事人或者作為悲劇的共謀者的態度,每一位當事人和共謀者都是他人的地獄;怪誕作為闡釋歷史的方法,其背后是敘述者對怪誕歷史的質疑、對歷史真相本身的嘲弄和戲謔。
二、文學世俗化的兩副面孔與人文精神重塑
文學世俗化是上世紀90年代文學市場化以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面向。世俗化是現代性啟蒙的重要議題,本是社會啟蒙題中應有之義,是上世紀50-70年代被遮蔽的新思想文化內部“新新矛盾”t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孕育和生成的結果。“世俗化是啟蒙理想的基礎和前提”,“世俗化以及‘世俗化啟蒙是啟蒙的起點,不是終點;是部分,不是全部。啟蒙可以從‘世俗化啟蒙開始,但絕不能從‘世俗化啟蒙終結。”u經過世俗化思潮的洗禮,中國文學最大的變化是“自覺地回到了文學的人性立場,凸顯了文學的民間意味”v。強調擺脫宗教和政治束縛,關注個體生命狀態,凸顯人的欲望和世俗生活,復歸長期被遮蔽的人性,個人主義話語生存空間極大拓展,個人本位主義思想得以充分展現;解構了宏大敘事和虛假崇高,對過去的虛假、虛偽文學觀念與文學標準的祛魅,引發文學價值觀念的新變。這是文學世俗化的初衷,也是其正面價值。以往一些因宗教或政治的目的而被拔高或者賦魅的作家作品,在世俗化思潮下得以祛魅,還原了其本來面目。如“魯迅”在世俗化思潮下被重構,“回到人間”,“從‘大魯迅向‘小魯迅”轉變w,不再充當意識形態的工具。
世俗化思潮在實際社會運行和文學實踐中呈現出兩幅面孔:神圣化和物化。這兩副面孔共同左右著上個世紀90年代文學的基本形態,也影響著新世紀文學發展、轉型的基本走向。其中,物化傾向是導致人文精神滑坡的重要原因。因此,認清世俗化思潮的兩副面孔對剖析和把握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基本形態有著重要價值。所謂世俗化的神圣化傾向,就是對物質與精神這對概念中的精神一方進行過度強調,一味地宣揚某種可貴精神的崇高性和人的道德完美性,忽視物質的短缺與不足對人所造成的傷害;企圖以精神的富有遮蔽物質的匱乏,“貧窮,成為驕傲和光榮的標志;富有,則是邪惡和墮落的象征。窮人,成為品德高尚的化身;富人,則是道德敗壞的別名”x。這些皆體現出虛無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傾向。實際上,人們所面臨的物質生存困境無法通過精神撫慰得以解決,物質的空乏應當以物質的滿足作為唯一解決途徑。一旦將精神與物質混淆、以精神替代物質,就使世俗化啟蒙走向其對立面,形成反啟蒙。所謂世俗化的物化傾向,就是對人的欲望的過度放縱,媚俗與鄙俗成為日常美學,私人化寫作、下半身寫作泛濫,道德滑坡嚴重。這就偏離了倡導文學世俗化的初始目的:恢復被遮蔽的人性、指引個人人格健康發展。“抹去了現實生活的豐富性、詩意性,以感官刺激、娛樂快感取代了文學的審美性、崇高性,表現出宣揚虛無、頹廢的人生享樂思想的動機。”y物化傾向說明文學在走向世俗的同時,未能做到對其進行理性的審美觀照,對生活本身缺乏審美過濾和典型化處理,物欲展露有余而節制不足。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許多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皆可從神圣化和物化上找到關聯性,抵制和擺脫文學的兩種不良傾向是推動新世紀文學創作、批評和研究新變的起點。
以“肯定人的合理欲望,高揚人的主體精神”z為目的世俗化思潮,一旦滑向了神圣化和物化,也就造成對“人”的控制,轄制“人”的自由,導致“人”的主體精神偏離本真、真情,造成人文精神缺失。世俗化啟蒙背離其初始目的,純文學受到冷落,文學的人本主義方法標準被廣泛擱置和質疑,普世價值標準遭到調侃與解構。受世俗化影響,文學批評對作家作品或戲謔貶損、或吹捧棒殺,過分重視西方的命題邏輯,批評的不及物性使批評自身的有效性降低。以上問題的產生與批評者自身存在的問題密切相關,“迎合世俗趣味和功利主義的文化價值觀”@7等現象值得深思。面對文學世俗化的兩種極端面孔,呼喚人文精神的重塑,“重振五四時代的‘人的文學的精神”@8,則是新世紀文學批評所關注的重要方面。具體而言,重塑文學的人文精神、捍衛普世價值和人類立場體現有三:其一,注重人性挖掘的深度和尺度。文學創作和批評應“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政治,從人性的視角,用人性的目光,去觀察、發現、捕捉那些潛藏在人性深處的、不易為一般人察覺的、帶有普遍性的東西”@9。同時,應對人性惡保持警醒,防止“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濁再次泛起”#0。其二,呼吁人的道德完善。保持著“智識階層”職責與擔當的作家如張煒,面對物化泛濫、道德觀念的轉型所帶來的傳統道德的墮落、對人的德性的戕害,張煒在創作中堅守德性與知性,“抗拒德性的蒙難”#1。其文化保守主義在物化時代成為“制約商業社會物欲主義”#2的一種彌足珍貴的守望,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進行歌頌,堅守人文精神,一次次走向精神的高地#3。其三,廓清歷史小說書寫的價值立場。學者們對《大秦帝國》等作品的批判則是捍衛人文精神、廓清歷史小說書寫標準的典型學案。董健認為《大秦帝國》在思想內容上體現出“崇拜暴力和強權,否認人道主義,否認自由、民主、法制、人權以及科學精神這些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化價值觀”#4。吳功正認為《大秦帝國》“不是以自由、民主、人的尊嚴,而是以專制、殘暴、人被否定,作為價值評判的尺度”#5。而一些學者對《大秦帝國》的一味歌頌和對批評的辯護則違背了啟蒙立場,顛覆史實、消解歷史、漂白罪惡、混淆歷史真實與小說之間界限、為專制思想唱贊歌,這些混亂的價值立場預示著“文學批評的沉淪”#6。在價值觀念多元共生、異質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為了堅守價值觀的一元立場——人類立場、處理好普世價值與世俗趣味之間的關系,則需要對大眾進行新啟蒙。這也表明捍衛人文精神是一項需要長期堅守的未竟事業。
三、從“主義”到“關系主義”:文學史研究的去蔽與擴容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三種誤區:其一,在概念命名上,一些文學現象、問題和流派的命名具有隨意性、隨機性,并無科學的根據與來源。而文學史的編撰又建立在對已設定好的概念命名進行再闡釋的基礎上。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概念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概括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學創作的本質屬性是值得懷疑的。這種將復雜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的歸類方法并不具有可靠性,也得不到作家們的認可。以這種臨時性的概念命名、簡單化歸納方法來審視文學,造成了審視者視野的固化,遮蔽了文學闡釋的多樣性和意義豐富性。其二,在指導思想上,往往文學史撰寫的指導思想是某一種或幾種“主義”,而這些“主義”的內涵在發展演化過程中逐漸走向泛化:后續研究者在對“主義”進行運用和再闡釋的過程中,刻意或者無意識地對其內涵進行伸縮、偏義和誤讀,造成“主義”的無限擴張,而其原點和初意卻遭到忽視。這就造成了“主義”作為研究方法既萬能又空洞、所指與能指都具有不確定性的現狀。另外,“主義”也會對非該“主義”理念下的文學現象和問題造成遮蔽。于是,以“主義”為指導思想所編撰的文學史其本身的科學性與穩固性就值得懷疑,終極的“主義”既指導著編撰的思路與方法,也束縛著編撰者的闡釋視野、認知深廣度。其三,在具體操作層面,局部研究法有意地將研究對象進行切割,缺乏對文學的整體性認知,在認知上的碎片化導致了無法抵近文學的真實面向。如何以一種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學的真實、解決文學史研究中的誤區?這就需要拋開舊的、隨機產生的概念命名,摒棄單一性的“主義”指導,杜絕對文學對象的切割,研究者才能抵近文學的真實狀態,觸摸其原本的溫度。南帆在《文學研究:本質主義,抑或關系主義》中提出的“關系主義”,“文學必須置于多重文化關系網絡之中加以研究,特定歷史時期呈現的關系表明了文學研究的歷史維度”#7。這為審視文學提供了新視角,彌補了“主義”觀念主導下文學研究存在的不足。“關系主義”理念強調在相互關聯的“他者”視域中審視中心議題,“一種‘主義的意義不是單獨完成的,不是來自所謂的‘內在本質。相反,一種‘主義的問世由于‘他者的存在而意義倍增。”#8“關系主義”作為研究方法,有利于避免文學研究誤區,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長點。“關系主義”強調中心議題與“他者”間的互攝互入、相互生成。從“關系主義”視角下,可以發現文學被遮蔽的部分、可以對文學作品進行更為深刻全面的再解讀。
尋求審視研究對象的新視角,將被遮蔽的文學意義進行呈現,是文學史研究去蔽和擴容的有效途徑,也是文學研究適應整體性文學發展潮流新變的結果。新世紀以來,一些注重“他者”視角的文學研究實踐暗合了“關系主義”的基本要旨。王彬彬的《中國現代大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相互哺育》#9從現代大學與現代文學良性互動、相互哺育的角度重新審視影響文學發展演變的因素,在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大學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文化意蘊濃厚的場域,大學學統也左右著文學的品格。朱首獻的《論文學史的“個體意識”與“類意識”》指出理想的文學史編撰方法是將文學史家的類意識與個體意識放置于共融狀態。文學史編撰的深層對話不是史料與史料的對話,而是“文學史家與文學史料、文學文本乃至文學史家與文學家”的對話$0。從這一角度而言,文學史家的角色不僅僅是文學史料的考古,而且是“審美立法者”。審美立法工作則需要個人意識的積極參與其中。唯如此,才能再現文學史的內在靈魂脈絡。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以西方話語作為中國文學創作方法和文學研究理論資源會造成對文學本土性的遮蔽。于是,新世紀文學研究立足于中國經驗、中國故事和中國問題,重新解讀文學發展的動因問題,破除西方話語的絕對權威地位,探尋文學發展的本土影響因子,注重“文學與其產生的本土現實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性”$1,是新世紀文學研究的顯著趨勢,體現著新世紀文學本土話語再造的自覺。對于中國魔幻現實主義創作的研究,以往較多地強調這種創作模式的拉美屬性,而忽視其本土屬性。新世紀以來,研究者認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作家創作上影響更多的是技巧方法上的啟迪,而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內核依然是本土傳統文化。本土神秘意象參與了“魔幻”的建構,這就凸顯了中國同類創作在來源上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質。魔幻現實主義被充分中國化,按照中國的思維和審美習慣對“魔幻”進行改造,注重本土神秘意象、傳統文化觀念的運用,傳遞著中國本土獨特而濃厚的文化意蘊,體現出小說“向民族性回歸的價值取向有著內在的一致性”$2。樊星指出:當代文學主題中的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追尋魂靈,“昭示了當代神秘文化思潮的發展態勢:一面追問民族精神的坎坷命運,一面猜想民間信仰的玄秘幽深”$3。這強調了神秘意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繼承性。對于莫言創作的資源取徑問題,新世紀的研究將目光轉向本土傳統資源,王洪岳的《夷齊文化的鳥崇拜和莫言小說鳥意象的元現代闡釋》認為:夷齊文化中的巫幻意象在莫言創作中得以充分發揮和創造性轉化,使其創作形成“巫幻現實主義”$4的特征。將“魔幻”置換為“巫幻”是將莫言創作的影響因素由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轉向內——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體現。這種轉向代表著新世紀文學研究的整體性范式由重視“他者”經驗書寫向本土話語再造轉化。
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無形中契合了以“關系主義”透視文學史的精神宗旨。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研究將文學的整體發展進程放置于制度層面進行考察,注重文學史與制度史二者的相互闡釋,將被遮蔽的文學外部隱形因素進行挖掘。丁帆認為: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是“構成文學現象的根本動因”$5。在筆者看來,這一觀點的背后支撐是制度為文學發展、停滯甚至倒退提供了最大的場域與慣習,模塑著文學的基本形態。著眼點于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制度既可作為文學研究的方法視角又是文學研究的內容,探索“‘有形的文學制度和‘無形的文學制度”$6對文學形態、文學生態的制約和規范作用,目的是以此來重新解讀文學、展現文學的整體性風貌。其中,文學管理制度、出版規范、文學思潮、社團組織、教育制度等是進入顯性和隱性文學制度生成的具體切入口。這些具體文學制度規范影響和制約著文學發展方向,甚至成為文學一體化的指揮棒。王愛松的《出版制度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7梳理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出版制度、出版法規對文學生產過程的制約、阻礙作用。楊有楠的《“文革”主流文藝創作的生產機制考察》指出作為文藝主流規范樣本的革命樣板戲對其他文藝形式的示范作用,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傳聲筒”$8。趙普光的《文學機構的恢復與重塑——80年代文學制度研究之一》從上世紀80年代文學機構的重組角度考察文學組織體系,使作家“處于文學制度的整合當中”$9,作家歸文聯、作協的層級化組織建設是文學制度運作正常化的關鍵。韓松剛指出:“90年代出版領域所出現的各種新策略、新現象、新問題”%0是文學出版轉型和期刊改版的出發點。這種獻媚于市場的轉型和改版,最終依然要返回到文學應有運作模式中來,純文學期刊即使向一般讀者靠攏,也無法長久吸引其關注。因此,保持純文學應有的風格與品格,才是堅守陣地的正確選擇。
在呼吁現實主義精神回歸、注重本土話語再造的新世紀,文學研究在考查經典化、世俗化甚至文學史編撰等議題時,依然需要亮明的原則是:文學研究方法可以多元,但價值觀必須一元,即普世價值和人類立場。以某一種“主義”為視域的文學研究因其對非“主義”的遮蔽而無法還原真相,文學史撰寫也只能是一種“再想象”。因此,應當呼吁以“關系主義”勾連文學事件、現象,注重研究對象與“他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在關系中揭示研究對象的多面模態。
【注釋】
a[德]顧彬:《語言的重要性——本土語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四卷第1期。
b王彬彬:《成為好作家的條件》,《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
c王彬彬:《一個批評家應該從語言中得到快樂》,《南方文壇》2011年第3期。
d王彬彬:《我所理解的顧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e邵振國:《敘述的表現性及其訴諸的形式》,《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十一卷第1期。
f陳黎明:《精英與民間的話語碰撞——試論莫言小說的語言風格之爭》,《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年第十二卷第2期。
g張志忠:《故事·現代性·長篇小說·價值尺度——與顧彬論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文學批評》2017年第3期。
h李洱:《“傾聽到世界的心跳”——與魏天真的對話之一》,《問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頁。
i程光煒:《“60后”的小說觀——以李洱的〈問答錄〉為話題》,《文藝研究》2015年第8期。
j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頁。
k劉皓:《“拒絕詩意化”的努力——李銳〈厚土〉 〈銀城故事〉 〈舊址〉的精神取向》,《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1期。
l黃燈:《“50后”作家何以仍是中流砥柱》,《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2期。
m盧新華、王冬梅:《積蓄力量“再出發”——盧新華訪談》,《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5年第十卷第1期。
n黃書泉:《論“啟蒙經典”的文學經典性——以〈子夜〉、〈家〉和〈駱駝祥子〉為例》,《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三卷第2期。
o王毅:《“人民”的迷思:處于想象中的新詩讀者》,《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四卷第1期。
p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與“文革”記憶》,《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8年第三卷第1期。
q王達敏:《同情人道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1年第六卷第2期。
r宋世明:《形式革命中的意識形態法則——當代先鋒小說解讀》,《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三卷第2期。
s夏楚群:《在歷史敘述與現實書寫的罅隙之間——莫言小說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5年第2期。
t王勇:《新思想文化的內在張力及其沖突——中國百年新思想文化運行規律初探之一》,《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十一卷第2期。
u海馬:《“世俗化”啟蒙語境與90年代中國大陸戲劇(下)》,《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2年第七卷第1期。
v@9曉蘇:《文學世俗化的功與過》,《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2期。
w禹權恒:《“世俗化魯迅”的得與失》,《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2期。
x海馬:《“世俗化”啟蒙語境與90年代中國大陸戲劇(上)》,《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1年第六卷第2期。
y戴海光:《祛魅與返魅:新時期以來小說的世俗化向度》,《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2期。
z陳國恩:《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學及文學批評》,《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2期。
@7任毅:《當下文學批評的世俗化傾向》,《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4年第九卷第2期。
@8林治賢:《中國文學呼喚精神還鄉》,《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8年第三卷第1期。
#0劉心武:《談邊緣寫作》,《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0年第五卷第2期。
#1黃軼:《“現代反思”下的價值困惑與德性堅守》,《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四卷第1期。
#2趙東祥:《張煒文學創作之理性精神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2年第七卷第1期。
#3趙東祥:《論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下的張煒及其作品》,《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0年第五卷第2期。
#4董健:《論〈大秦帝國〉的反動性》,《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1年第六卷第1期。
#5吳功正:《歷史理性·人文關懷·審美本體——當前長篇歷史小說的現狀分析之一》,《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三卷第2期。
#6董健:《再論〈大秦帝國〉的反動性》,《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1年第六卷第1期。
#7南帆:《文學研究:本質主義,抑或關系主義》,《文藝研究》2007年第8期。
#8南帆:《現實主義、結構的轉換和歷史寓言》,《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09年第四卷第1期。
#9王彬彬:《中國現代大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相互哺育》,《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0年第五卷第1期。
$0朱首獻:《論文學史的“個體意識”與“類意識”——百年中國文學史學科發展論析》,《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2年第七卷第2期。
$1賀仲明:《本土化: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另一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2期。
$2陳黎明:《論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小說魔幻意象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0年第四卷第2期。
$3樊星:《追尋魂靈——一則讀書筆記》,《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3年第八卷第1期。
$4王洪岳:《夷齊文化的鳥崇拜和莫言小說鳥意象的元現代闡釋》,《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十三卷第1期。
$5丁帆:《文學和文學史的制度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項目研究小議》,《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3期。
$6丁帆:《文學制度與百年文學史》,《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
$7王愛松:《出版制度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十一卷第1期。
$8楊有楠:《“文革”主流文藝創作的生產機制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6年第十一卷第1期。
$9趙普光:《文學機構的恢復與重塑——80年代文學制度研究之一》,《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年第十二卷第1期。
%0韓松剛:《1990年代的文學出版轉型與期刊改制》,《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年第十二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