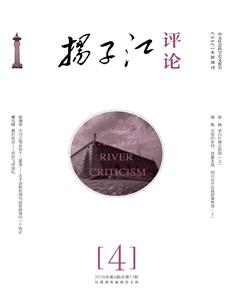皆自混沌莫分明
韓春燕
人類無疑是一種局限性的存在,但人活在世上卻總需要對事物進行明晰的判斷:黑與白、是與非、好事與壞事、好人與壞人、美麗與丑陋、進步與落后……既然,人類的整個認知系統都是建立在這種局限性上的,那么這種判斷就難免帶有著先天的缺陷。正如《莊子·逍遙游》所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我們人類與那不知晦朔的朝菌和不知春秋的蟪蛄有什么兩樣?
但是判斷分明,卻讓人類擁有了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是人類存在的必需。政治需要判斷分明、法律需要判斷分明,而文學卻應該將人類放在那個局限的位置上,盡可能去還原世界的豐富與復雜,包括人自身的豐富與復雜。判斷分明就意味著簡單化,而世界和人卻恰恰是無法簡單化的。對有局限的人類認知來說,只能不斷去探究,卻最終也無法探其究竟。
萬事萬物皆自混沌,是因為我們人類的渺小和認知的無力,對其,我們也許只能心懷敬畏。《列子·天瑞篇》中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不壞,吾所不能知也……”
對這個世界,我們一直在勤勉地認知,卻不斷重復判斷的謬誤,這也許就是人類的宿命。
趙本夫的長篇小說《天漏邑》也許正力圖在文化思考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接近和呈現這個世界的混沌狀態。
惡地?美地?
《天漏邑》作者匠心獨運地建構出一個“罪惡的淵藪”天漏村,這個神秘的古代小城邑在作者筆下成為一個被“神設”的天地間的大破綻。天之漏對應人之漏,“……天意,補而存隙,是為天漏,懲罪也……”女媧補天時在天漏村上空留下縫隙,為泄風雨雷電,警示懲戒世人,讓天漏村的人世世代代頭頂天漏,世世代代在風雨雷電中掙扎存活。
雷劈電擊必是大惡之人,而天漏之地也無疑是一處大惡之地,兇險如地獄的天漏村聚集著一群罪惡之徒,他們隨時都有遭天譴的可能,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不僅沒有毀滅,沒有搬遷消失,倒是歷朝歷代不斷有人來天漏村定居,有的甚至來自幾千里外。好像這是一塊風水寶地。其中包括達官貴人、文人隱士、商賈掮客、奸夫淫婦、匪盜囚徒、巫婆神覡。還有一些根本不知來路、不明身份的人……歷史上各個朝代,都有人像尋找桃花源一樣尋找天漏邑……”
天漏村除了吸引國內的人跋山涉水前來投奔,竟然還有許多外邦人不遠萬里遷徙而來,正如書中所寫:“這是個古老的村莊,對大多數人來說,它是隱秘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但對世上那些懷有同道之心的人,自會有一種神奇的信息和通道,把他們引領到這里。”物以類聚,同氣相求,那么天漏邑的魅力到底何在呢?在作者的敘述中,我們發現天漏村是個難得的逍遙自在的地方。因深知死生無常,天漏村人活得灑脫超然,他們淡泊名利、得過且過,不經營家園,不積累財富,崇尚馬馬虎虎的生活態度,追求隨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天漏之下,他們活得本真舒展,把地獄活成了天堂。
在天漏村,世上的倫理道德不能約束他們,他們生死都已看輕,有的只是野性和天性,他們暢快地野合、偷情、嫖妓,且無比坦然。
小說中的專家禰五常困惑于天漏村這樣的村莊為什么能存活那么長?它長過了一個個朝代,它憑借的是什么?
也許,人類對生命自在狀態的追求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僅僅憑借人自身的欲求是無法維持一個村莊的歷史的,這里面還另有玄機。
天漏村確實是玄機重重的,它三千多年的歷史里隱藏著一個個巨大的秘密,這些秘密也吸引來一撥又一撥試圖破解它們的人。
沒有一種混亂是絕對的,在每一種混亂的背后都有一個看不見的秩序。在天漏村散漫隨意的生活后面,悄然運轉著一套古老的管理制度,這套幾千年來都在自行運轉著的制度,是村莊秩序的保證,也是天漏村和天漏村文化綿延不絕下去的保證。
“自古以來,天漏村村長實行禪讓制,村長必得是賢者、有德之人。村長如果任職期間被發現有徇私不公,或有違反公德民俗之事,村民可以彈劾,這里叫糾彈。” “天漏村的村長從來不擺臭架子,老百姓有啥意見,隨時都能講,只要對,村長準聽……”
而村長從上任伊始就要培養發現繼任者,每到禪讓時,繼任村長由老村長提名后,還要經過村民投紅黑豆來決定,在天漏村,村民擁有神圣的權利,他們給權力以足夠的監督。那只放選票的黑陶館已傳承幾千年,成為神圣之物,說明這套制度幾千年里都有效地發揮著作用,說明一代代的天漏村人都自覺地擁護和執行著這套規則。選舉在天漏村是神圣的,村長選舉出來后,他們還要鳴21禮炮慶祝歡呼。這等古禮古風,分明是一禮儀之邦,清明之土。
大惡之地卻是最為民主之地,推崇賢者和德行,沒有權貴,沒有惡霸,平等自由,這分明是一處樂土。更為神奇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歷次運動都沒有影響到天漏邑,他們仍然在做古代人,仍然這樣生活和選舉,完全自轉,成為真正的化外之地。
天漏村人遵從著從古而來的神秘訓誡,那些秘密制度幾千年來都在被嚴格執行著,除了村長的禪讓制,還有啞巴修史的制度,一代代的啞巴作為天漏村歷史的見證者和書寫者,成就了九龍洞一洞竹簡“乍冊”。
天漏村是天譴之地,也是人類的自我完善之地、自我救贖之地,作為天地之間的大破綻,它既是罪惡之人聚集之地,也是自然、文化和人性的美地。
天漏村是開放包容的。這個深山里的村莊對投奔它來的任何人都是敞開的,來者不拒,要來就來,可以永久定居,也可以要走就走,把這里當作驛站,隨時離開。他們對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種職業都懷著平等心,沒有歧視,沒有排擠,對各種離經叛道的行為也都坦然接受。
天漏村的人是勇敢的,他們能夠直面自己的罪過,直面生死,他們敢于賭命地活著。
天漏村的人是最真的, 他們看破生死,不虛偽不矯飾,不為世間名利所動, 不羈隨性地活在天地之間。
天漏村的人從四面八方懷罪而來,在隨時準備接受上天懲罰的同時,將生命活成一種哲學。
小說中,天漏村除了宋源和千張子外,其他都是古代人。這兩個人活得驚天動地,而其他人則追求活得無聲無息。兩種生命態度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
作者在小說中不斷將這惡與丑的化外之地天漏邑同善與美的桃花源相提并論,桃花源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對唯美化外之地的想象和追尋,而與美地桃花源對應的惡地天漏村則顯現著另一種巨大的魔力。
惡人?善人?
一個優秀的作家寫人物是要把筆探進人性深處,寫出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來。《天漏邑》在人物塑造上最大的特點是寫出了人物身上善惡糾纏的狀態。
主人公宋源無疑是個快意恩仇充滿血性的真男人、大英雄,他英勇善戰足智多謀,當游擊隊長時,領導游擊隊與日本侵略者作戰,親手射殺過七十多個鬼子,手刃過一百多個漢奸、偽軍和叛徒,令敵人聞風喪膽,立下戰功赫赫;他當公安局長時,清理監獄、清剿殘匪特務,兢兢業業,盡心盡力,成績斐然。他還癡情,暗戀著女縣長檀黛云,檀黛云之死讓他痛徹心扉,而他為檀黛云復仇也不遺余力……
然而,這只是宋源的一面,如同他的陰陽臉,他還有著另一面,他性格怪異生性殘暴,用小說的話來說是手黑、人鬼,像一個黑煞。 也就是說,宋源作為一位大英雄,他同時也具有著某種黑暗人格。
悖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英雄的塑造,宋源的出生不是紅霞漫天的祥瑞,而是在天雷滾滾中,被霹靂閃電從母親腹中崩出來的,一出生他的半邊臉就帶著被雷擊出的黑痣,這塊雷擊的黑痣無疑是一種原罪的標志。
宋源自我、強悍、獨來獨往、孤僻倨傲、冷硬無情,他不喜歡弱者,他的內心也缺乏柔軟和溫情,無論七女還是千張子對他都情深似海,但他回報給他們的終究還是漠然。
他心狠手黑、膽大妄為,在小說里無疑是個戰神的形象。他瞧不起下賤的生命,他殺憎惡的人能用刀劈絕不用槍打,因為他覺得刀劈才過癮。殺戮使他快意,血腥使他興奮,即使對方已經舉旗投降,他也絕不罷手;他性欲旺盛,不愛七女,卻和七女長期保持著肉體關系,即使對他的女神檀縣長,他也不能克制自己下流的想象。
用檀黛云的話來說,宋源“你一面是邪惡,一面是正義,就像你的一張陰陽臉,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還有侯本太,按照我們慣常的思維,侯本太就是一個投敵叛國的漢奸,但作者并沒有把侯本太臉譜化、簡單化。一方面,侯本太是個沒心沒肺沒有國家民族概念的糊涂人,他為了日本人給他的一點小甜頭,甘愿帶領他的土匪隊伍投靠日本人,去做日本人封他的警備司令;而一方面,他良心未泯,在耳聞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種種惡行后,他的國家民族意識和良知都開始覺醒,他幫助宋源和他的游擊隊營救檀縣長,在日本人準備屠殺十個孩子的緊要關頭勇敢地站出來阻止,愿意替孩子們去死,因為百姓祭奠檀縣長不斷被槍殺,他冒著生命危險,取走城門上檀縣長的人頭,并用銀匣子裝殮入土……他是漢奸,但他也是英雄。
小說中,最為復雜的人物要數千張子,這個人物是作者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
千張子生而為男,卻在男人的身體里盛著一個女兒的靈魂,他美麗俊秀,他嫵媚多情,他喜歡大男人宋源,卻終其一生讓宋源厭惡。年輕的千張子是柔弱的,他慈悲、心軟、粘人、愛哭,但戰爭改變了他,血與火讓他成為一個戰士,一個英雄,一個讓敵人聞風喪膽的人,也成為了一個勇敢的男人。千張子注定是被命運捉弄的人,他因為救人被捕,受盡酷刑,卻最后因為忍受不了疼痛出賣了檀縣長,成為了可恥的叛徒,而他的叛變是為了更好地殺敵報仇,他一個人也確實化身復仇之神殺了更多的鬼子,讓整個彭城的敵人為之恐懼,被百姓譽為大英雄。千張子清楚自己的罪行,他要坦然接受組織對叛徒的懲罰,他不怕死,他只是怕疼而已。
如果說《天漏邑》力圖呈現人物的復雜性,那么千張子這個形象確實做到了。
宋源是個可敬的大英雄,但他身上陰森森的東西,讓他并不可愛;侯本太是個漢奸,可他的草根化的憨和糊涂以及關鍵時刻的善良和勇敢,卻讓他有一種呆萌的可愛;而千張子這個人物卻只能讓人扼腕嘆息,嘆息命運的吊詭,嘆息他的一生可悲可憐。
背叛?忠誠?
叛徒是可恥的,人們憎惡叛徒甚于仇視敵人。曾經,王連舉、甫志高這些名字成為被全國人民唾棄的對象,我們從來不允許為叛徒做一絲辯解,不允許對叛徒懷有一絲同情,叛變就是叛變,叛變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與忠誠相對并沖突。
然而,《天漏邑》卻寫出了背叛的無奈與叛徒的復雜性來。
天是有漏的,人也是有漏的,有漏的人中千張子怕疼,宋源怕癢。在抗擊日寇的戰斗中,千張子一直是個英勇的戰士,他本是一個膽小羞怯的年輕人,是敵人的屠殺激發了他的血性,是長期的對敵斗爭將他淬煉成了一個真正的男人,一個英雄。
千張子不怕死,然而,他怕疼,因為怕疼,英雄千張子出賣了檀縣長成了叛徒,被釘在恥辱柱上。
在千張子與宋源的對話中,千張子承認自己出賣了檀縣長罪不可恕,他也一直準備承擔叛變的后果,接受對他的懲罰,但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信仰,背叛了祖國和人民,他強調自己比叛變之前更恨日本侵略者,只是因為怕疼,承受不了疼痛而成為了叛徒,這與信仰無關,他仍是忠誠的,忠誠于自己的信仰,忠誠于祖國和人民。而宋源明顯懷疑他的這種說辭,宋源認為千張子這種說法很荒謬,叛徒就是叛徒,叛變就是全部的背叛,就是死心塌地為敵人服務,根本沒有資格談忠誠的問題。
這是強大的信仰與脆弱的肉身的沖突。小說中千張子提出的質疑,相信也是作者的質疑,那就是把大多數人放在千張子那個位置,承受他所承受的酷刑,能撐下來的到底有幾個。也正因為千張子的質疑,宋源一直想檢閱一下自己對酷刑的承受能力,在文革中,他想方設法想激怒審問者,以檢驗自己能否在酷刑下挺過來而不成為千張子那樣的叛徒。
按照邏輯,沒有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愿意成為叛徒,很多人不怕死但怕自己承受不了被捕后的非人折磨,嚴刑拷打下,你的肉身能否配得上你的靈魂是個問題,所以,酷刑下的叛變雖然可恥可憎,但如果說這樣的叛徒馬上就會死心塌地地為敵人服務也不合邏輯,有誰會愛上一個對自己施以非人折磨的敵人?在這個意義上,千張子的自述應該是可信的,他肯定更恨敵人,更想復仇。
千張子認為自己只是背叛了檀縣長并沒有背叛信仰,沒有背叛祖國和人民,雖然這種說法存在問題,但也確實反映了他真實的心態。千張子之所以選擇出賣檀縣長而沒有出賣宋源,他的理由是檀縣長發動群眾在行,但打敵人不行,留著他和宋源都能消滅更多鬼子。其實,千張子在選擇出賣檀縣長時,應該有更復雜和隱秘的心理動機,他喜歡宋源,而知道宋源喜歡檀縣長,在權衡之后,他決定出賣檀縣長……
按照我們對叛徒慣常的思維,是不是千張子成了叛徒后還可以出賣宋源,出賣聯絡站,甚至出賣整個游擊隊?事實是,他只出賣了檀縣長,也確如他所說,他更瘋狂地打擊了敵人,他在為自己和檀縣長和所有死難同胞復仇。
當然,檀縣長是真正的英雄,雖然作為女同志她被捕前也曾擔心害怕,囑咐宋源他們要打死自己,不能讓自己落在敵人手里,但她被捕后面對凌辱和折磨卻顯現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這不僅讓叛徒千張子無地自容,也讓她的敵人無比欽佩。
有人做過統計,在被捕后的酷刑面前,高級干部叛變的比基層干部多,男人叛變的比女人叛變的多,是女人的信仰比男人更堅定,還是女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比男人更強?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捫心自問,我們如果遭遇酷刑,能否一直堅強?是不是就一定不會成為叛徒?很多人是不能給自己打保票的。
在《紅巖》中大名鼎鼎的叛徒甫志高是幾個真實的叛徒合在一起的形象,劉國定、任達哉、冉益智、李文祥、涂孝文、蒲華輔……
蒲華輔叛變后,首先出賣的就是他的妻子郭德賢,造成郭德賢和她的兩個孩子不幸被捕。這不能不讓人驚詫,一個丈夫和父親,他叛變后竟然首先出賣自己的妻兒?而據資料記載,“蒲華輔在獄里‘痛定思過后,又表現出剛強不屈來”。他與家人一同被關在白公館十個多月中,一直表現很堅強,再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與陳然(成崗原型)、王樸等一同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睹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犧牲沒有什么不同。”a
而另一個叛徒原型涂孝文被敵人叫去與萬縣女縣委書記對質也沒有指認對方,且在對方受酷刑仍堅強不屈的感召下開始痛悔自己的叛變,并不配合特務審訊,最后唱著《國際歌》、高喊“共產黨萬歲”走向刑場。
正如另一個叛徒駱安靖回憶材料上所言:“我被捕后既不愿出賣組織,也不想淪為可恥叛徒,但又缺乏堅貞不屈和自我犧牲勇氣——”b
這些叛徒肯定再也無法用忠誠來定義,無論什么原因的叛變都是可恥的,叛變不僅是叛變者人生的污點,也是革命事業的巨大危害。
背叛與忠誠,在政治意義上兩者的界限是明晰的,不允許絲毫含糊,然而,文學卻要始終面對人,面對現實和歷史,要盡力還原其雖然復雜卻逼近真實的面目來,在這個意義上,趙本夫的《天漏邑》做出了努力。
【注釋】
a《她的丈夫是叛徒甫志高的原型》,百家號微信公眾號2017年5月30日。
b紀文伶:《〈紅巖〉叛徒原型里唯一活到80年代的人是誰》,《重慶商報》20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