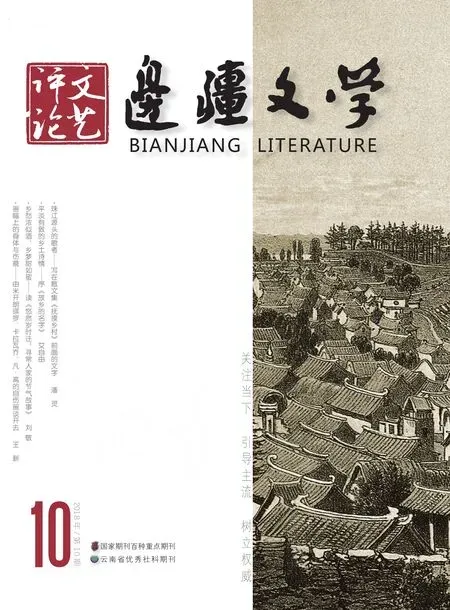呂翼長篇小說《寒門》的新鄉土小說書寫意義
朱海燕
迎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發展的旭日陽光,在中國的西南邊陲,或者常被稱作烏蒙山腹地的昭通,出現了一股文學創作的力量,它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端,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興盛,以致蔚為壯觀。進入2000年以來,昭通作家群與昭通文學現象更加凸顯,尤其以長輩作家夏天敏中篇小說《好大一對羊》獲得2005年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將昭通文學創作推向了第一個高峰,一是凸顯了昭通作家創作的實力,二是帶動了外界對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學現象的關注,三是帶動了昭通文學整體創作的動力。時至今天,昭通文學創作一直在持續發展,一些中青年作家顯示出了創作的強勢勁頭,呂翼就是其中的一員。這位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昭通作家,主要以中長篇小說創作為主,兼及散文書寫,已出版的小說集有《靈魂游蕩的村莊》《割不斷的枯藤》《別驚飛了鳥》,長篇小說有《土脈》《村莊的喊叫》《疼痛的龍頭山》《寒門》等。呂翼對小說創作持著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眼光時刻關注鄉村社會的轉型與發展,關注著底層民眾生存的意義,探索著人性的復雜與閃光點。
呂翼現為云南省作協新農村建設文學創作簽約作家,中國作協重點題材作品簽約作家。他對于故土的關注,對于鄉村敘事的執著,對于“三農”問題的深刻思考,使得其作品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2017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寒門》,書名雖然為《寒門》,乍一看上去,容易讓人聯想起近幾年新聞報道之“寒門學子放棄高考無奈之舉”,或者每逢高考之時,當今社會的熱點話題討論“高考真是寒門難出貴子?”“學歷真的能改變寒門學子的命運嗎?”“高考對寒門學子意味著什么?”等等。的確,呂翼長篇小說《寒門》確實是從敏感的高考制度入手,以一個中國西南偏遠山區的村莊——碓房村作為鄉村縮影,并以碓房村馮家、趙家、萬家三家孩子在高考影響下各自不同的命運及發展為敘事重點,但是縱觀全書,作家的創作主旨并不是借小說反思高考制度,文中并沒有流露出明顯的對高考制度的批判或者贊揚態度。作者是把高考這一敏感話題,這一自“文革”結束所恢復,影響眾多社會階層命運的人才選拔制度,切入到中國的鄉土社會,以碓房村為中國鄉土社會的縮影,把高考作為一個獨特的敘事視角,以此展示了20世紀后20年到21世紀初十幾年這個歷史階段,農民心態行為的變異以及思想觀念的嬗變。沒有史詩般的宏大視角,沒有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沒有風起云涌斗爭發展,但《寒門》這部長篇小說在今天的新鄉土小說書寫中,卻具有獨特的意義與價值。
《寒門》這部27萬字的長篇小說,打破長期大部分作家對新鄉土小說城/鄉二元對立模式的書寫。而是在恢復高考40年的今天,把高考這一中國選拔人才的制度方式作為切入點,就像照相機的長焦距,深入到中國西南邊區封閉的村莊,透過長焦距的鏡頭,看高考支配的村莊眾生相。中國的鄉土小說起源于20世紀初,魯迅從文化視角對鄉土中國封建性、人性、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和揭露;沈從文則從“真善美”方面展示著鄉土中國的溫情,反襯當時的戰亂與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以魯迅、沈從文為代表的現代鄉土小說,承擔著進入20世紀之后,中國現代性的啟蒙重任,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在他們身上也體現得非常充分。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刷新著人們的價值觀,全球化與市場化以不同的速度影響著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現代化轉型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把國人概念中的“鄉村”擠進了一個狹窄的生存空間,模糊了城鄉之間的界限,所以鄉土小說創作面對的已經不是相對自足的“鄉土經驗”,那么表現在文本創作中,更多的卻是“鄉下人進城”“打工文學”“城市價值觀對農村人的侵蝕”或者“工業文明對鄉村文明的擠壓”等等。拋卻全國范圍內的其他新鄉土作家的作品不論,但就昭通作家群中的作家也就有很多這一方面的表現,比如夏天敏在《接吻長安街》中寫道:“在長安街看著望不到頭的車陣,看滾滾人流,你覺得自己就是一粒砂子,一粒隨時可以被風吹走,吹走了不會起任何反響的砂子”;劉平勇中篇小說集《天堂邂逅》第一篇小說《天堂邂逅》寫進城謀生的小攤販張大鵬,殺死城管隊長何勝利后畏罪自殺;《找啊找》中進城尋找丈夫的農村婦女趙嵐失手殺了丈夫的情人梅子,身陷囹圄;《茶花的月亮》中清純善良的茶花被城里的簫劍吸引后,春心蕩漾,進城找簫劍無果后淪為失足女,最終遭兇殺身首分離等。在這些文學創作中,城鄉差距的懸殊,農村人因為鄉村匱乏的物質環境而到城市“討生活”,城市是農村人幻想的“富裕天堂”,這種從鄉到城的過渡中,鄉不再是田園的鄉,城也并不是理想實現的天堂,異化墮落、身體致疾、精神失落、心靈失去皈依,是大多數新鄉土小說表現的對象。 “鄉土小說作為20世紀以降中國文學最繁盛豐茂的敘事文學之一,從誕生之日起就在城市與鄉村兩大文化系統與人生樣態相互碰撞的歷史漩流中激蕩流變,‘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思維是其基本內核。90年代以后,新鄉土小說跨越40年代至80年代的‘農村題材小說’重續此前城/鄉二重奏的現代化旋律,煥發出新的生機。”
的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鄉土小說,在城與鄉的敘事模式,及城市形象與鄉村形象的塑造中,使得中國的鄉土小說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迷狀態中走了出來,豐富著中國的當代文學,并占據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模式化是特點也是禁錮,從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這十幾年,新鄉土小說城/鄉二元對立的模式化書寫方式,無疑是“問題小說”的一種變相呈現,本質上仍然持著只問病源、不開藥方的創作態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鄉土文學作為社會發展的表征,向我們揭示社會轉型期,鄉村到城市,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帶給我們的文本感受大多是鄉村苦難,農民焦慮,被金錢異化,小農意識,價值觀畸形……雖然大部分作家對農村、農民持著同情和悲憫的情懷,但不可否認,他們帶給我們更多的是絕望,或者苦難無邊的感性沖擊,而很少理性的思索,思索現代化轉型中鄉土中國的出路問題。
昭通作為烏蒙山腹地的一塊土地,一直屬于中國欠發達的地區,拿當下的城市發展等級劃分,就昭通作為市級單位,在國內也只屬于五線城市行列,那么昭通市轄區的其他區域,城鎮化進程也就相對比較緩慢。呂翼作為昭通的一個彝族作家,生于昭通農村,工作于昭通城,從來沒有離開過昭通這塊土地,所以其作品中“鄉土”書寫相對來說具有一定的“封閉性”,這是因為沒有“離開”就沒有“歸來”,就沒有對自己熟悉的這塊鄉土“間離”化審美,他看待自己生活的鄉土,就像母親看待懷中的孩子一樣,具有天然的血脈情感。所以呂翼一直以一種博愛溫和的情感書寫著這塊土地,沒有強烈的批判與人性揭露,沒有讓筆下的村長有“衣不遮體”之感,鄉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反映在其作品中,就表現為城/鄉二元對立模式的消解。之前出版的長篇小說《土脈》講述了彝族龍家三代人為核心的紅泥村人的坎坷命運和對土地情感,作者蘊含在文本中的情感訴求像書名一樣,具有深厚的“土地情結”;“楊樹村系列”農村題材的小說,對鄉風民俗,神秘傳奇,性情人性等的書寫,則重在展示鄉村日常生活樣態。
在《寒門》這部小說中,作者同樣持著相同的鄉土書寫方式,所不同的是,《寒門》對于鄉土的書寫,介入視角比較開闊,與國家層面的教育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以當今教育改革的熱點“高考制度”作為切入點,并以此來書寫西南邊區一個封閉的村莊“碓房村”的故事。因為介入視角開闊的原因,所以作者筆下的“碓房村”就具有了典型的特征,這個碓房村不僅是屬于昭通的碓房村,也是屬于中國的碓房村,它以農村出身的孩子求學為主線敘述故事,這樣的故事,是任何一個中國的鄉村社會家庭都避免不了的,從古代的“學而優則仕”之說,到后來的“知識改變命運”之說,通過制度性的選拔考試,是底層人改變命運的一個重要的途徑,有時候甚至被認為是唯一途徑。中國自1977年恢復高考,它就一直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國人觀念,尤其是前些年,拿“一考定終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高考,讓高考成為多少寒門學子心目中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高考影響著千千萬萬的寒門學子,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農村家庭,那么以此視角書寫中國的鄉土社會,既有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注,又有對鄉土社會時代變遷,所帶來的人的價值觀、倫理道德、思想情感、審美趣味等方面的思考。高考是城的高考,也是鄉的高考,在《寒門》中,雖然有馮嬸帶馮維聰到省城看精神病被醫藥騙子所忽悠,以及離家出走的馮天香到東南沿海都市打工從事不正經職業的書寫,但那不是整部小說的重點,“城”在小說中不是“鄉”裂變的導火索,也不是作為“他者”視角,構建鄉土形象的參照物。
對應作者獨特的敘事切入視角,小說采用的是完整的鄉土經驗敘事模式,把碓房村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的敘述對象,重點以馮敬谷一家為敘事線索,兼及趙成貴、萬禮智兩家。馮敬谷家的三個孩子馮天香、馮維聰、馮天俊和馮春雨,趙家的趙得位與萬家的萬勇,六個孩子與高考緊密掛鉤,從他們讀小學到上大學到參加工作,這幾個孩子的發展歷程,是鄉土中國一代農村娃成長的縮影;同時他們的父輩也是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無論是“望子成龍”的心態,還是“砸鍋賣鐵也要供兒讀書”的決心,在這一點上,碓房村的父輩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村的父母的真實寫照。縱觀小說構建的整體鄉土面貌:貧窮的碓房村,苦苦掙扎的村民,以萬家為權力代表的鄉村勢力對鄉村政治倫理秩序的管控,生活重壓下被高考逼瘋的馮維聰,為獲得高考獎反復高考的馮春雨,腦子靈活文學才華突出開廣告公司掙錢的趙得位,還有為孩子付出所有一輩子心血、認定高考是唯一出路的馮敬谷、趙成貴以及萬禮智等父輩農民,這樣鄉土的人與事,是當代中國農村最熟悉的場景。
但是作者筆下的碓房村又是個性的。從自然生態環境上講“碓房村是茫茫無邊的烏蒙山區里一個小小的村落,雖然隔酒州縣城有五十多里,略顯偏僻,周圍是山,交通曲折,但懷抱著上千畝的良田沃土。那土層至少是上萬年的堆積,黑得發亮,黑得發臭”;從農業生產狀況上講,“因為谷多,谷要脫殼,這里的石碓窩就多,幾乎家家都有一個一抱大的碓窩。而生產隊里,專門備下幾大間房擺碓窩,數十個大碓窩,青石琢成,結實敦實,一字擺開,大半截塞在土里。”;從鄉風民俗上講,碓房村人對老人過世極其重視,“請道士先生,扎紙火,買煙酒鞭炮,辦豬羊祭”,同時,信鬼弄神“趙嬸是村里的巫師,常和神呀、鬼呀打交道……村里村外,好多人家關于求神打卦的事、生老病死的事、家里丟東西的事,一般都要問她”;從精神生活上講,趙嬸用巫術為馮維聰治病。碓房村還流行以一種說法,就是剛死去的人的腦髓可以治病,效果非常好,為此馮嬸沖進刑場去收剛被行刑犯人的腦髓,這無疑讓我們想起了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而墳地更有講究,相信到了陰間的長者,會給后輩以看不見摸不著但卻又實實在在的庇佑。如果長者的棺木埋在龍脈上,后輩就會通達順暢,遲早是要出達官貴人。”為此馮敬谷、萬禮智都請陰陽先生看過風水,在遷墳時候還鬧過笑話。所以,碓房村是個性的中國西南偏遠山區的碓房村,是封閉保守的碓房村,是物質匱乏,精神也略帶愚昧的碓房村。
但是碓房村落后愚昧歸落后愚昧,碓房村人有堅忍不拔的生存毅力,碓房村人貧窮,但窮得有骨氣有正氣。在馮天香出走后,馮家收到一大筆匯款,被外界猜測為來歷不正經的錢,馮敬谷與馮嬸為孩子的學費“跑了好些家,紙煙抽掉一包,好話說盡兩筐,時間磨掉半夜,嘴上起了涼漿大泡,卻一分錢也沒有借到時”都沒有動用那筆錢。馮嬸到郵局去問,整不清匯款人是誰,退錢找不到退處,她還要弄清楚,如果錢是馮天香寄的,還要看錢的來路,如果是臟的就不用,如果有人寄錯了還是要還的。馮天香換著地址與姓名寄給馮家很多錢,在極其艱難的時候,他們從來沒動過那筆錢,家里的孩子也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剛正有骨氣,上學及其需要錢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人提出動用那筆錢,馮維聰看著父親為借錢傷腦筋,覺得自己是累贅,服下農藥想要了結生命;馮家受趙四之托,在自己養三個孩子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對趙四撿來的孩子馮春雨視如己出,把她培養成了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社會急劇地轉型,經濟領域的變革也沖擊了人的價值觀,人被物欲所奴役,社會誠信嚴重缺失,但在碓房村,作為偏僻鄉村的農民,木訥老實,誠實守信,快被生活逼瘋的時候,他們仍保持著錚錚鐵骨,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沒骨氣。在碓房村,最高的精神追求就是對知識的尊重,對教育的重視,他們建孔廟,祭孔子,幾乎成了一種宗教式的虔誠,“碓房村有三件寶,前兩件和土地有關,與肚皮有關:碓窩、稻谷,這不用多說。第三個寶,說的是村莊精神世界里的東西,讀書人說的上層建筑——孔廟。”孔圣人生日那天,村里人隆重祭孔,曾經趙四在“破四舊”運動中,為了維護孔廟,為了保護孔圣人的泥像,被打殘廢,并導致了一生連家都沒建立的悲劇,最后趙四死在了為修教室而倒塌的泥墻中。沒趕上祭祀儀式,馮維聰虔誠地自雕孔圣人塑像,擺在堂屋正中,馮家孩子經常跪拜,就在馮天俊到城市漂泊之時,仍然懷揣孔圣人像,這是一種精神信仰的虔誠,代表著碓房村人對知識的景仰與尊重。哪怕是馮天香在外靠出賣肉體掙錢之后,回到碓房村仍然想著重修孔廟,捐資助學。可以說,碓房村是偏僻落后的,但碓房村人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當改革開放的大潮沖擊著中國大地的時候,當一切以金錢作為衡量標準的時候,當大眾文化以感官享受建構著國人淺薄的審美觀時,當娛樂精神至上的時候,碓房村,作為一個相對保守、鄉土經驗自足的村莊,由自己獨特的精神信仰引領著,走向了新生活。在小說的結尾,碓房村得到了省教育廳的支持,教育條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高考瘋子”馮維聰也得到了清華大學研究所的關注,碓房村也引來了外商,那是學有所成的馮春雨個人發展后對家鄉的反哺。曾經執著于高考的碓房村的年輕人對學歷的觀念發生了改變,但是對知識依然尊重。碓房村人,迎著新生活的陽光,奔向了發展的康莊大道。
曾經有學者對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特征這樣判斷“一是村莊社會多元化, 異質性增加;二是地方性共識銳減,村莊傳統規范的力量漸弱;三是村民對村莊的主體感喪失,更多的依賴村莊外部力量。”的確,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也使封閉的鄉村社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敞開,新的思想和思潮改變著農村人的觀念,農村固有的社會秩序也在被瓦解著,作為土地主人的農民,也與土地產生了疏離感。面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除卻國家政治層面對農村農業農民的關照,今天的農村,今天的農民,該何去何從,是迷茫,是守舊,是完全地失去自我,還是依靠自身固有的特質,改變不適宜的一些觀念,迎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謀得自身的發展?無疑,《寒門》這部小說,給了我們最好的解答。作為關注農村農民發展,并常寫三農題材的作家呂翼,面對改革開放后的鄉土中國,用作品表達著自己的思考,他沒有把新鄉土小說的書寫僅僅停留在“問題”的揭露上,而是針對中國的鄉土現實,從內部審視中國農村發展的出路問題。
今天的農村,外部國家政策扶持是一方面,作為鄉村自身,也應該審視自身,是否有像碓房村那樣的文化積淀,是否有堅定的精神信仰,是否有恒定的價值觀與道德準則定位。“無論政治文化怎樣變化 , 鄉土中國積淀的超穩定文化結構并不因此改變,它依然頑強地緩慢流淌,政治文化沒有取代鄉土文化。”碓房村的“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就體現在它的精神心態文化層的穩定性上,碓房村人追求“寒門貴子”的理想,碓房村人對待知識像信奉宗教一樣虔誠,碓房村人守信義,碓房村人貧窮但對金錢“取之有道”,碓房村人發家發達后不忘本……這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無比可貴的鄉村品質,是它指領著碓房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觀念,沒有迷茫,沒有墮落,價值觀沒有被現代化進程沖擊得七零八落。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于一個國家如此,那么于中國農村的發展也如此,于中國廣大農村中的一個鄉村發展更是如此,作家呂翼借《寒門》思考的可貴之處也就在于此。
所以,縱觀整部小說,雖然在情節構思與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馮天香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離家出走,到東南沿海謀生路,這樣一個農家姑娘,渴望上學,渴望知識,返回家鄉后對教育事業不遺余力,但是作家對其情節的設置就落入了俗套,馮天香在外謀生的手段好像與人物秉性出現了錯位,當然也存著作家對現代都市異化人的想象。但這些并不影響《寒門》在當今文學語境中新鄉土小說書寫的意義與價值。

肖文虎 國畫 箐中柿子紅
【注釋】
[1] 程麗蓉.新鄉土小說的敘事模式及其文化內涵[J].北方論叢,2010(4):3.
[2] 楊柳.劉小峰.鄉村社會巨變與農村研究進路——以《鄉土中國》與《新鄉土中國》為范例的比較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9):155.
[3] 孟繁華.百年中國的主流文學——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新鄉土文學的歷史演變[J].天津社會科學,200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