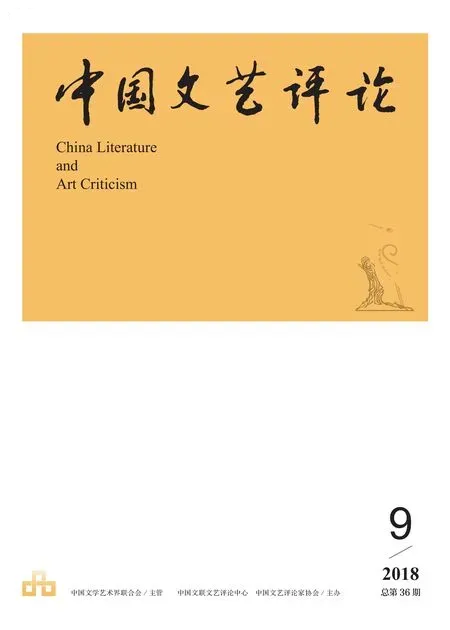新詩之難如是說
2018-10-08 05:26:40孫仁歌
中國文藝評論
2018年9期
孫仁歌
詩歌作為人類文學史上起源最早的一種文體,較之后來的散文、小說、戲劇等,可以說最接近人類的靈魂。更干脆一點說,詩歌是距離詩人靈魂最近的一種文學話語形態,當然,優秀的詩歌也能及時融入讀者的心靈,讀者與詩的互動,其實就是靈魂與靈魂之間的交匯與融合。讀者能在優秀的詩歌里找到屬于自己的靈魂乃至哀愁,恰證明詩歌具有穿透讀者靈魂的強大藝術“殺傷力”。
在西方,縱然發生過柏拉圖驅趕詩人的誤會,但詩人享有的地位一直至高無上,詩人一度被譽為是神的代言人,是為哲學命名的人等,但丁、歌德等就是鐵證。在中國,詩人的地位也同樣倍受推崇。屈原、陶潛、李白、杜甫等等,在讀者心中不啻于遠古圣人,可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正因為詩歌擁有這樣一種神圣的地位及其深遠的影響力,所以后世的詩歌創作一直長盛不衰,尤其新詩的崛起與繁華,更是花團錦簇,萬紫千紅。但浩如繁星的新詩創作及其傳世的作品,也并非都是經典之作,在不計其數的現當代詩人中,許多詩人僅因為一兩首詩的出名,便讓汗牛充棟的大量平庸之詩也跟著大行其道甚或傳世了,因名而文,也算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惡性循環,此當別論。
也就是說,新詩并不容易寫。筆者十分認可一種說法,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新詩的寫作難度最大。朱光潛先生在《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的書信體隨筆中,真誠地奉勸青年朋友不妨多練習散文、小說,認為把才華浪費在新詩上實在可惜。……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