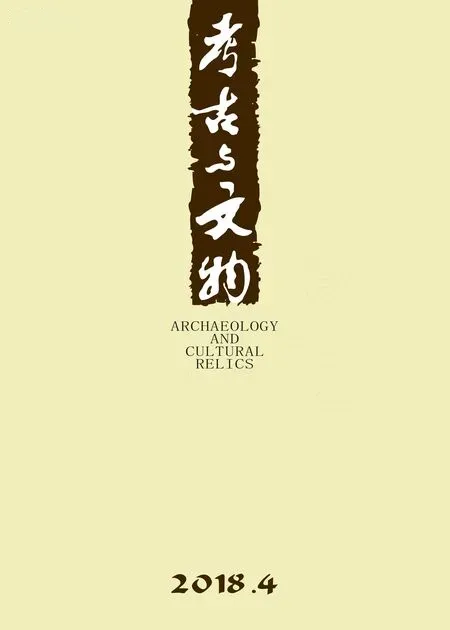試論楊官寨遺址墓地的年代*
楊利平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楊官寨遺址自2004年首次發(fā)現(xiàn)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開展了持續(xù)的考古工作,確認(rèn)了一處總面積達(dá)100多萬平方米的仰韶中晚期特大型中心聚落遺址[1]。并發(fā)現(xiàn)了廟底溝文化時(shí)期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環(huán)壕、半坡四期文化制陶作坊區(qū)等重要考古材料[2],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獲。
2015至2017年,在遺址東段環(huán)壕外發(fā)現(xiàn)一處大型公共墓地,并探明墓地西端與東環(huán)壕毗鄰,面積9萬余平方米。目前已揭露面積3800平方米,共發(fā)現(xiàn)343座史前墓葬,是研究楊官寨遺址乃至廟底溝文化時(shí)期史前社會(huì)的重要材料,但是關(guān)于墓地的年代存在諸多爭議[3]。本文將根據(jù)出土陶器的類別及其特征,結(jié)合人骨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對墓地的年代進(jìn)行初步研究,揭示其在學(xué)術(shù)史上的重要意義與價(jià)值。
一、相對年代學(xué)研究
本次發(fā)掘的墓葬開口層位一致,均開口于⑤層下(局部發(fā)掘區(qū)上部被擾動(dòng)或破壞,但是該層在發(fā)掘區(qū)內(nèi)都有分布),且分布如此密集的墓葬之間無任何打破關(guān)系,不僅體現(xiàn)了史前社會(huì)對于墓地的集中管理,也體現(xiàn)了該批墓葬應(yīng)屬于一定時(shí)間內(nèi)被史前先民普遍認(rèn)同的大型墓地。同時(shí),⑤層中還出土有少量的殘?zhí)掌鳌執(zhí)掌绯鐾恋募獾灼俊A砂罐等,均為廟底溝文化時(shí)期典型陶器,為判定墓地的年代下限提供了幫助。

圖一 尖底瓶
目前已發(fā)掘的213座墓葬中僅16座墓葬隨葬有完整的陶器,隨葬陶器的比例非常低,且鮮有陶器組合情況,僅在M64發(fā)現(xiàn)彩陶壺、單耳杯、陶盤的器物組合,M68發(fā)現(xiàn)兩件夾砂小罐。除此之外,還有18座墓葬出土了部分殘?zhí)掌鳌F渲心乖醿?nèi)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彩陶盆、泥質(zhì)筒形罐、淺腹陶盤、夾砂陶罐等器物,都具有明顯的時(shí)代特征,均屬廟底溝文化的典型陶器,為我們斷定其相對年代提供了依據(jù)。
重唇口尖底瓶M323∶1(圖一,1),重唇口,內(nèi)外唇較明顯,截面略呈臺階狀,形體瘦長,細(xì)頸,溜肩,略帶束腰,銳尖底。整體特征、造型與楊官寨遺址W18∶1[4](圖一,2)、山西夏縣西陰村西陰文化G1∶28[5](圖一,3)、華陰興樂坊第一期文化遺存H34②∶2[6](圖一,4)等別無二致。口部內(nèi)斂、唇面雙重階梯式的特征與華縣泉護(hù)村廟底溝文化第一期遺存II式尖底瓶H4②∶83[7](圖一,5)、華縣泉護(hù)村遺址一期I段尖底瓶T205③∶01[8](圖一,6)、寶雞福林堡第一期尖底瓶H41∶2[9](圖一,7)、三門峽南交口遺址尖底瓶H22∶18[10](圖一,8)等相同。底部夾角為銳角、內(nèi)部有多圈泥條盤筑痕跡的特征與三門峽南交口遺址H62∶7[11](圖一,9)如出一轍。
卷沿曲腹彩陶盆M58∶1(圖二,1),泥質(zhì)紅陶,圓唇,斂口,弧折沿,上腹外鼓,下腹微內(nèi)曲,小底內(nèi)凹。該類器物在廟底溝文化諸遺址中十分常見,如楊官寨遺址環(huán)壕內(nèi)出土的彩陶盆H776②∶7[12](圖二,9)、華縣泉護(hù)村一期文化Ⅱ段彩陶盆H14∶01(圖二,8)、H224∶501[13](圖二,11)、華縣泉護(hù)村廟底溝文化遺存B型Ⅱ式陶盆H107②b∶65[14](圖二,12)、山西河津固鎮(zhèn)遺址第一期Aa型Ⅰ式陶盆H15∶10[15](圖二,10)、三門峽南交口遺址仰韶文化二期乙類Ba型Ⅳ式陶盆H2∶1[16](圖二,13)、廟底溝遺址深腹盆H59∶29[17](圖二,7)等,其整體器形相似,均為深腹,且腹部的弧度較大呈上鼓狀態(tài),下腹略內(nèi)收,平底。M58∶1彩陶盆雖殘損嚴(yán)重,但器表裝飾彩繪圖案仍可清晰辨識,其沿面施一周條帶狀黑彩,上腹部飾有月牙形豎向弧線圖案,該類彩繪圖案在以往的廟底溝文化遺存中較為少見,僅在華縣泉護(hù)村遺址廟底溝文化第II期遺存B型II式彩陶盆H61①∶13(圖二,3)發(fā)現(xiàn)了完全相同的彩陶圖案[18],另在楊官寨遺址環(huán)壕內(nèi)出土的彩陶盆H776⑥∶51(圖二,2)、華縣泉護(hù)村一期文化Ⅲ段H1127∶871[19](圖二,5)、秦安大地灣第三期C型Ⅱ式曲腹盆H302∶5[20](圖二,4)、岐山王家嘴遺址出土彩陶缽[21](圖二,6)等器物上有相似的發(fā)現(xiàn),表面裝飾豎向月牙狀彩陶紋樣。

圖二 彩陶盆
夾砂罐M68∶1(圖三,1)、M68∶2(圖三,5),均為夾砂紅陶,圓唇,口微敞,束頸,腹部略鼓,平底,通體飾斜向繩紋。該類夾砂罐的整體器形較小,《華縣泉護(hù)村1997年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中將其定為G型罐單獨(dú)介紹,如H105③∶70(圖三,3)、H105③∶75(圖三、7)、H107①∶50(圖三,4)、H107①∶5(圖三,12)、H46⑤∶77(圖三,10)、H46⑥∶65(圖三,11)等[22]。該類小罐在楊官寨遺址中也有大量發(fā)現(xiàn),如G8-2③∶190(圖三,2)、G8-2②∶187(圖三,6)、H776③∶78(圖三,9)等。夾砂小罐在以往發(fā)掘的廟底溝文化遺址中也十分常見,如河津固鎮(zhèn)遺址第一期D型夾砂罐T106④b∶2[23](圖三,8)等。
泥質(zhì)筒形罐M193∶1(圖四,1)方唇,敞口,斜直腹內(nèi)收,平底,素面。該類器物在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時(shí)期各類遺跡中十分普遍,如筒形罐G8-2②∶21(圖四,2)、H776∶28[24](圖四,3)等。華縣泉護(hù)村遺址廟底溝文化二期D型素面直腹罐H86∶36(圖四,4)、H46③∶41(圖四,8)、H107②b∶71[25](圖四,6)、華陰興樂坊第二期筒形罐H13④∶6[26](圖四,10)、寶雞福臨堡一期B型缸H41∶9[27](圖四,7)、彬縣水北遺址深腹盆H58∶12[28](圖四,9)、山西河津固鎮(zhèn)遺址第一期筒形罐H10∶13[29](圖四,5)等器物與其形態(tài)形似,均為外翻或略內(nèi)折的沿面形成疊唇,斜直腹、小平底,器物整體呈筒狀。

圖三 夾砂罐
陶缽根據(jù)口部形態(tài)可分為直口缽和斂口缽二型,其中直口缽M183∶1(圖五,1),泥質(zhì)紅陶,圓唇,弧腹,小底微凹。與楊官寨遺址素面陶缽G8-2①∶29[30](圖五,2)、華陰興樂坊第二期文化遺存中的直口缽H27∶1[31](圖五,5)、寶雞福臨堡一期A型Ⅰ式陶缽H124∶3[32](圖五,4)等形制相似,均圓唇,直口微敞,淺腹,小底微凹。斂口缽M215∶1(圖五,3),泥質(zhì)紅陶,圓唇,斂口,上腹稍鼓,下腹斜收,小底微凹。與秦安大地灣第三期A型Ⅰ式陶缽T302③∶23[33](圖五,7)、扶風(fēng)案板遺址第一期斂口缽H24∶3[34](圖五,8)、三門峽南交口遺址仰韶文化二期A型Ⅲ式陶缽H8∶2[35](圖五,9)、山西河津固鎮(zhèn)遺址第一期A型Ⅱ式陶缽H16∶14[36](圖五,6)等形制接近。
單耳杯是墓葬內(nèi)出土數(shù)量最多的陶器,共6件。其中M139∶1(圖六,7)圓唇,敞口,束頸,溜肩,鼓腹,口、腹部接有一較寬的橋形器耳,小平底。墓葬內(nèi)出土的同類器還有M64∶2(圖六,4)、M196∶1(圖六,1)、M173∶1(圖六,6)等。該類單耳陶器在以往的廟底溝文化考古發(fā)現(xiàn)中非常罕見,但在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環(huán)壕中出土了數(shù)件,如H776④∶41(圖六,2)、G8-2⑤∶17(圖六,3),均為長頸,在口沿與上腹部接制一橋形耳作為把手,鼓腹,小平底,造型與墓葬內(nèi)出土單耳杯完全一致,共存的其他器物均為廟底溝文化典型陶器。在泉護(hù)村遺址二次發(fā)掘中也出土1件單耳帶流杯H160∶5[37](圖六,5),敞口,束腰,平底,單耳上端接于口部,下端連于腹部,整體造型極為相近,頸腹比例略有差異。
單耳罐M222∶1(圖七,1),泥質(zhì)灰陶,方唇,敞口,束頸,斜肩,鼓腹明顯,近似折腹,下腹斜收,橋形耳接于口、肩部,平底較小,素面。該類器物形態(tài)與單耳陶杯相近,但器物整體略大,在華縣泉護(hù)村一期文化Ⅱ段遺存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細(xì)泥紅陶的單耳陶罐H24∶332[38](圖七,2),二者在整體形態(tài)別無二致,均為敞口、束頸、鼓腹、平底,且二者尺寸亦相當(dāng),均在12厘米左右。楊官寨遺址環(huán)壕內(nèi)出土一件單耳罐(壺)H776③∶45(圖七,3),器物略顯瘦高,高度可達(dá)15厘米,但是其敞口、單耳、鼓腹、小底的整體造型與單耳罐相近。

圖四 筒形罐

圖五 陶缽
彩陶壺 M64∶1(圖八,1)和素面陶壺M187∶1(圖八,2),在以往的廟底溝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極少,楊官寨遺址環(huán)壕內(nèi)發(fā)現(xiàn)一件陶壺H776∶198(圖八,3),泥質(zhì)紅陶,敞口,長束頸,鼓腹,小底微凹,與墓葬內(nèi)發(fā)現(xiàn)陶壺的形制如出一轍。另在華縣泉護(hù)村一期文化中發(fā)現(xiàn)一件泥質(zhì)紅陶罐H224∶50[39](圖八,4),與墓地發(fā)現(xiàn)的陶壺M64∶1形態(tài)相近,均為長頸,鼓腹,頸部飾數(shù)周凹弦紋,但其腹部裝飾一突鈕耳,略有差異。M64∶1陶壺腹部施有一圈由弧邊三角形、圓點(diǎn)等組成的黑彩紋飾,構(gòu)成留白部分呈四瓣式花紋圖案,該類彩陶紋樣在廟底溝文化中較為常見,且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一類彩陶題材,如泉護(hù)村遺址廟底溝文化一期彩陶缽H28∶39(圖八,5)雖然已殘,但是器表裝飾圓點(diǎn)、弧線三角紋彩陶圖案,留白的應(yīng)為四瓣式花瓣紋[40]。華縣泉護(hù)村廟底溝文化二期彩陶缽H105④∶5(圖八,6)器身裝飾一圈黑彩,組成圓點(diǎn)、弧線三角的黑彩圖案,留白部分為四瓣式花瓣紋[41]。廟底溝文化還流行大量雙瓣、三瓣、多瓣的花瓣紋[42]。
盤M64∶3(圖九,1),泥質(zhì)紅陶,圓唇,斂口,斜沿,淺腹,平底,素面。該器物與陶壺M64∶1、單耳杯M64∶2共存,也不是廟底溝文化常見器物。楊官寨遺址曾發(fā)現(xiàn)一件彩陶盤H43∶1(圖九,2),為泥質(zhì)黃褐陶、斂口、寬弧沿、淺腹、平底,已殘,器物表面殘存八組弧線三角與半圓組成的圖案[43],與M64∶3形態(tài)相近。而且該類器物還在其他遺址中有零星發(fā)現(xiàn),如華縣泉護(hù)村廟底溝文化二期遺存中陶盤H74②∶10(圖九,3)、H105②∶21(圖九,4)[44]、扶風(fēng)案板遺址第一期陶盤GNZH67∶24[45](圖九,6)、秦安大地灣第三期陶托盤T219③∶4[46](圖九,5)等,與M64∶3造型一致,均為斂口、較窄的沿,淺腹、平底。

圖六 單耳杯

圖七 單耳罐

圖八 “花瓣紋”彩陶壺

圖九 陶盤
二、絕對年代學(xué)研究
從已發(fā)掘的情況看,絕大部分墓葬都沒有隨葬品。零星發(fā)現(xiàn)的殘?zhí)掌瑹o法作為判定其年代的直接證據(jù),一般被認(rèn)為是早于墓葬的遺存[47]。因此,需要對墓葬所出人骨進(jìn)行碳十四測年,以為墓葬斷代提供依據(jù)。其中出土隨葬品的墓葬測年結(jié)果為判斷墓地的年代提供了基本的范圍,再綜合其他不出隨葬品的墓葬進(jìn)行全面測年得出墓地的整體年代。
出土陶壺、陶杯、陶盤的M64出土人骨直接測年結(jié)果經(jīng)兩個(gè)SIGMA校準(zhǔn),其 年 代 為Cal 3485~Cal 3475.BC(Cal 5435 to Cal 5425.BP)、Cal 3370~Cal 3330.BC (Cal 5320~Cal 5280.BP)、Cal 3215~Cal 3185.BC(Cal 5165~Cal 5135.BP)、Cal 3155~Cal 3130.BC (Cal 5105~Cal 5080.BP)。出土夾砂罐的M68出土人骨直接測年結(jié)果經(jīng)兩個(gè)SIGMA校準(zhǔn),其年代為Cal 3490~Cal 3470.BC(Cal 5440~Cal 5420.BP)、Cal 3370~Cal 3335.BC(Cal 5320~Cal 5285.BP)、Cal 3210~Cal 3190.BC(Cal 5160~Cal 5140.BP)、Cal 3150~Cal 3140.BC(Cal 5100~Cal 5090.BP)。 可 見,M64、M68兩座墓葬的測年結(jié)果十分接近,約Cal 3490~Cal 3130.BC(Cal 5440~Cal 5090.BP)。 另 M218、M398等墓葬測年結(jié)果基本與此相同。還有兩座不出隨葬器物的墓葬M243、M145測年結(jié)果更早,年代上限為3637.BC。
出土陶缽的M183出土人骨直接測年結(jié)果經(jīng)兩個(gè)SIGMA校準(zhǔn),其年代為Cal 3365~Cal 3264.BC(Cal 5314~Cal 5213.BP)、Cal 3241~Cal 3104.BC (Cal 5190~Cal 5053.BP)。還有 M388、M233、M108、M203、M302、M292等不出隨葬品的墓葬測年結(jié)果基本與此年代相同。
出土重唇口尖底瓶的M323的測年結(jié)果經(jīng)兩個(gè)SIGMA校準(zhǔn),其測年結(jié)果為Cal 3341~Cal 3087.BC(Cal 5290~Cal 5036.BP)、Cal 3059~Cal 3030.BC(Cal 5008~Cal 4979.BP)。 還 有 M410、M198、M204等墓葬測年結(jié)果基本與此相同。
出土單耳罐的M222測年結(jié)果為Cal 3092~Cal 2918.BC(Cal 5041~Cal 4867.BP),是年代最晚的墓葬,另M175年代上限較M222略早,但下限基本與此年代吻合。
綜合目前已知部分墓葬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來看,楊官寨墓地的年代約Cal 3637~Cal 2920.BC(表一)。這一結(jié)果與早期發(fā)掘的環(huán)壕聚落西門址的測年結(jié)果基本相同,其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約Cal 3490~Cal 2930.BC(表二),二者年代下限完全吻合。墓地的年代上限略早,似乎說明墓地的形成年代略早于環(huán)壕的使用年代,具體情況有待進(jìn)一步發(fā)掘研究。
三、結(jié)語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rèn)為楊官寨遺址墓地的相對年代當(dāng)屬廟底溝文化,從墓葬出土的尖底瓶、夾砂罐、陶盆、彩陶壺等器物來看,其年代應(yīng)為廟底溝文化中期[48]。而出土的陶杯、陶壺等器物在以往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雖不常見,但仍有發(fā)現(xiàn),且組合關(guān)系明確。唯單耳罐可供對比的同類器物較少,與其共存人骨絕對年代也較晚,似乎說明墓地仍然存在分期的可能性,具體有待進(jìn)一步發(fā)掘研究。根據(jù)碳十四測年結(jié)果可知,該墓地的年代約Cal3637~2918.BC之間,近年來發(fā)掘的楊官寨遺址聚落環(huán)壕內(nèi)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也多在這個(gè)時(shí)間段內(nèi),為我們進(jìn)一步認(rèn)識廟底溝文化的絕對年代提供了新的資料。

表一 楊官寨墓地測年數(shù)據(jù)

表二 楊官寨環(huán)壕測年數(shù)據(jù)
總之,楊官寨遺址墓地是國內(nèi)首次確認(rèn)的廟底溝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填補(bǔ)了該時(shí)期有關(guān)考古發(fā)現(xiàn)。該墓地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為我們從空間上進(jìn)一步認(rèn)識楊官寨遺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據(jù),初步厘清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時(shí)期聚落由大型環(huán)壕及其西門址、環(huán)壕中心水池遺跡、環(huán)壕外大型墓地等部分組成,這是關(guān)中地區(qū)首次從空間上清晰構(gòu)建的廟底溝文化聚落形態(tài),對于廟底溝文化聚落形態(tài)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寫作蒙王煒林研究員指導(dǎo),特此致謝!
[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fā)掘簡報(bào)[J].考古與文物,2011(6).
[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縣楊官寨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J]考古,2009(7).
[3]由于墓地內(nèi)流行偏洞室墓,而且還出土了部分帶雙耳的陶罐、陶杯,因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該墓地的年代可能為仰韶晚期。
[4]同[1].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陰村史前遺存第二次發(fā)掘[C]//三晉考古(第二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護(hù)考古研究所.陜西華陰興樂坊遺址發(fā)掘簡報(bào)[J].考古與文物,2011(6).
[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華縣文物旅游局華縣泉護(hù)村——1997年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8]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華縣泉護(hù)村[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3.
[9]寶雞市考古工作隊(duì),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工作站.寶雞福臨堡——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南交口[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9.
[11]同[10].
[12]同[1].
[13]同[8].
[14]同[7].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河津固鎮(zhèn)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C]//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學(xué)會(huì)《三晉考古(第二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同[10].
[17]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9.
[18]同[7].
[19]同[8].
[2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1]王仁湘.史前中國的藝術(shù)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22]同[7].
[23]同[15].
[24]同[1].
[25]同[7].
[26]同[6].
[27]同[9].
[2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彬縣水北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J].考古學(xué)報(bào),2009(3).
[29]同[15].
[30]同[1].
[31]同[6].
[32]同[9].
[33]同[20].
[34]西北大學(xué)文博學(xué)院考古專業(yè).扶風(fēng)案板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0.
[35]同[10].
[36]同[15].
[37]同[8].
[38]同[8].
[39]同[8].
[40]同[7].
[41]同[7].
[42]同[21].
[43]王煒林.廟底溝文化與璧的起源[J].考古與文物,2015(6).
[44]同[7].
[45]同[34].
[46]同[20].
[47]夏鼐.齊家期墓葬的新發(fā)現(xiàn)及其年代的改訂[C]//考古學(xué)論文集.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61.
[48]余西云.西陰文化——中國文明的濫觴[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