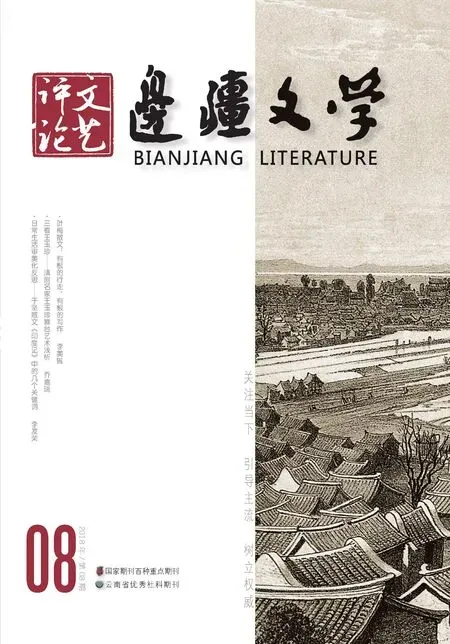“兩爨”書法與魏晉南北朝銘石書源流探微
王曦云

爨寶子碑 王建之墓志
提到《爨寶子碑》《爨龍顏碑》一般認為是云南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造成的書法現象。此觀點最早可以追溯到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里敘述的“南碑今所見者,二爨出于滇蠻,造像發于川蜀。若高麗古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啟自遠夷,來自外國,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蠻夷筆跡,猶尚如是……”雖康氏對“兩爨”書法大加贊賞,但始終認為出自不毛之地的蠻夷土著民族之手。而筆者認為此實為認識上的偏差造成的誤會,“兩爨”碑書法同南北朝時期漢地書法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
20世紀60年代,由郭沫若《由王謝墓志的出土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引發了“蘭亭論辯”。據郭文記載,早在清代李文田就提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近而后可。”而郭沫若更從新出土的王興之墓志、謝鯤墓志、興之婦墓志來進一步論證李文田觀點。爭論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爭論焦點其實是銘石書(用于書寫碑文字體)與行狎書(日常書寫、手札等)的不同,另外蘭亭真偽也不是本文討論范圍,而這里重點的是李文和郭文無意中把兩爨碑和新出土的幾塊墓志放到了一起,就是不習書法的人也能看出他們之間的聯系,這幾塊王氏家族的墓志從用筆到結字與《爨寶子碑》如出一轍。
回過頭來再梳理一下爨氏家族的起源,出現在史料中的第一個姓爨的人為爨襄,戰國時期魏國的將軍,因戰功賞十萬畝采邑,封地就在魏故都安邑(今山西南部夏縣禹王城)附近。爨是稀姓,爨襄應該就是后來南中爨習一支的祖先。這支爨氏如何進入云南不得而知,從其為“方土大姓”,可斷定其為兩漢時期從內地遷入的漢族地主豪強或落籍官吏。最早見于正史記載的爨氏人物為爨習和爨肅,兩人同時代。《三國志·蜀書》載:“爨習為建伶令”,是為漢末益州郡人,《諸葛亮集》記其在蜀漢政權為“行參軍偏將軍”,《華陽國志·南中志》云其后來“官至領軍(將軍)”,是為蜀臣。三國時期吳國謝承《后漢書·蜀志》有“爨氏望出晉昌(今山西定襄),后漢河南尹爨肅”之載,《爨龍顏碑》云其曹魏代為“魏尚書仆射、河南尹”,是為魏臣。因此,兩人分居南北而各事一主,互不相屬,僅是同姓而非同宗,但均為南中爨氏之先人。故爨氏來源實為兩支。《爨龍顏碑》記錄其祖先為南方楚國王族,開始姓羋,后來姓班,遷到山西后改姓爨。也有說可能為附會,但至少說明其先人為爨姓漢人,爨字太難寫,后來又改成姓寸。山西是爨姓的發源地,兩支爨氏都是從那里南下進入云南的。可以看出爨氏家族根本就是進入云南的中原門閥世族。在與南中幾個大姓豪族的博弈過程中最后勝出,統治云南400多年,并與當地滇人包括古老族群的人們融合為爨人,創造了影響深遠的爨文化。
爨文化的代表“兩爨碑”承襲了漢文化,并創造了書法藝術史上的一個獨特的高峰。首先,從的形制來看,碑額的飾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顯的漢文化特征。再從碑文來看,我們可以看出其文辭優美古雅、音韻和諧,整體寫作水平和文化修養同內地碑文相比毫不遜色。“冰潔蘭靜”“鴻漸羽儀,龍騰鳳翔”“濯纓滄浪”“至人無想,江湖相忘”大量用典涉及《論語》《楚辭》《孟子《莊子》《周易》等典籍,并且信手拈來,恰如其分,說明寫作之人受到過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書寫者也必然受過專門的書法訓練,有說法認為其幼稚的筆法、結構造成了現在呈現出來的拙趣,還有人認為其帶有游牧民族粗獷奔放的蠻夷之氣。以筆者研習書藝數十載摹寫爨碑數年的經驗來說,其結構用筆哪里是幼稚,完全是筆法熟練掌握后,結體受魏晉銘石書影響后的自然流露,直接秉承了華夏文化的正脈,何來蠻夷之氣。其形態和魏晉南北朝許多碑刻墓志極為相似,而其結構用筆更為巧妙、老練,其藝術價值超越了同期具有隸楷形態的銘石書。
“二爨”為世所重,因其獨特的面貌,而隨著新出土墓志的發現,一批與其結構用筆相似的碑刻讓我們發現了其內在的聯系。“兩爨碑”為人們所樂道的橫畫的獨特造型——形似建筑上的飛檐,兩頭翹起。正是書法發展到隸書到楷書的過渡造型,便捷向下斜切筆起筆到結束時仍保留了隸書的向上的波挑,書丹者保留了這一重要的隸書元素。而這一特征在比《爨寶子碑》(立于405年)早幾十年的《王興之夫婦墓志》(刻于東晉永和四年公元348年)《謝鯤墓志》刻于太寧元年(323年)上也能找到。而比《爨寶子碑》晚三十多年的《嵩高靈妙碑》也出現了同樣的用筆和結字特征。我們再找的話還會發現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這樣造型的書法。這批“銘石書”(包括北方的刻于公元456年的《嵩高靈廟碑》,1998年在南京出土的東晉瑯琊王氏《王建之墓志》其妻《劉媚子墓志》書風和《爨寶子碑》更為接近,此二碑比《爨寶子碑》早三十多年,選字對比見圖例)的出現有著內在的聯系,當時用于書碑的字體,必然選擇“合于古法”的隸書,而由于時代的關系,隸書已經呈現楷化,末筆波挑是承襲漢代隸書的慣性使然,而時代又進步到起筆便捷的楷化時代,兩者的雜糅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這種過渡的形態。到了比《爨寶子碑》又晚五十三年的《爨龍顏碑》(立于458年)則已完全是典型的魏碑體書法,同大量出土的魏碑、墓志相比雖各具特色,但共性也一目了然,正如阮元在《爨龍顏碑》左側跋語:“此碑文體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而當時文化的交流也許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封閉,云南爨氏家族在儒家文化的傳習上同漢地基本保持同步,而其“夷化”后產生的新的文化類型則是后話了。
“兩爨碑”一經發現就受到了康有為、沈曾植等一批學者的褒揚,以他們的學養和眼光對爨碑書法的價值認識是具有前瞻性和權威性的。綜上所述,兩爨碑的出現有其偶然的因素,南朝禁碑,而爨氏家族所在云南山高皇帝遠,才可以實施如此巨制墓碑,而爨氏把漢文化帶到云南又和當地文化相融合,為我們留下了書法演變過程中這一難得的實物資料,而其藝術價值和魏晉南北朝書法一脈相承,甚至在這批隸楷過渡的銘石書中獨占鰲頭,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并且對云南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呂他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