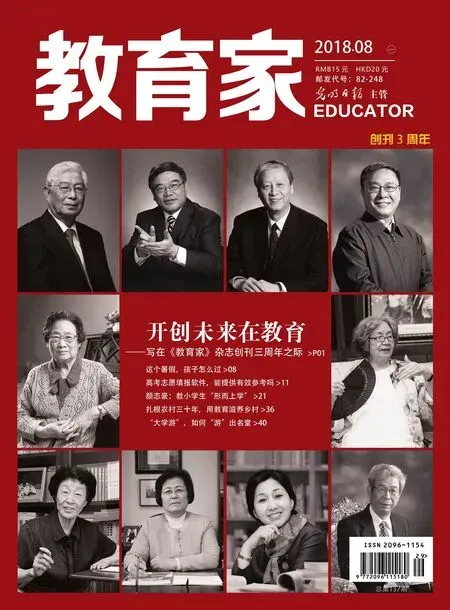自覺而快樂的閱讀時光
文 |
我從1963年7歲入小學算起,到1998年取得博士學位止,跨度達35年,這個“學生時代”真不知從何說起。我愿跟大家說一說學生時代閱讀的故事!
我于1963年在長沙新湖南報子弟小學入學,后轉入衡陽中南路小學。到1966年三年級快結束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的教學秩序亂了套。我本來對學習是很上心的,老師也經常表揚。“文革”期間無課可上,我不愿意在學校浪費時間,開始逃學,常和一幫小孩搗蛋,如把黃蜂窩裝進墨水盒放到局長案頭。后來,母親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你這小孩不教育將來不得了呀!”不久,我又在暗處用彈弓擊中一個司機——他在批斗會上正摁著一位我所愛戴的長輩的腦袋。父親在地委上班,朝不保夕,這事讓母親心驚肉跳,便把我送到長沙祖母處,這正中我下懷。
我從小生活在祖母身邊,大家都批評祖母溺愛我,祖母很不服氣:“他們哪里懂得教育!”后來我才知道,祖母清末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師范第一班讀過書,以第一名考入,1912年元月以第一名畢業,她的畢業證書由校長朱劍凡親手書寫,是第一號。而管她這個班的,是徐特立。后來,她又當上了徐特立辦的幼兒師范學校附屬幼稚園的主事,當時也就20來歲。
她卻并未“教育”我。吃完早飯,我就到附近的小人書鋪租書回家,天天如此。這時,我家所在的學宮街已改名“學工街”,緊鄰的蔡鍔路也成了“大寨路”。干部們自顧不暇,許多小人書攤便冒了出來。
要說迷上看書,早可追溯到我1964年在新湖南報子弟小學時,有次看見教室隔壁一間房里好幾個架子上全是彩色大幅連環畫,字不多,還有拼音,情節生動活潑,后來便常去那。可惜1965年轉學衡陽,就沒這條件了。
后來字認得多了,看連環畫不成問題。和祖母各拿一本讀,真是其樂融融。除了租的,也有家藏的,如民國出版的《米老鼠開報館》,有趣極了。還有許多書講的是歷史故事,如《夏完淳》《李定國》《楊家將》《岳飛傳》《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有講外國故事的,如《福爾摩斯探案集》《神秘島》《海底兩萬里》《雪萊的故事》《托爾斯泰的故事》。一兩年時間,大約讀了幾千冊小人書。我最基本的中外文學歷史知識,就是從小人書得來的。
漸漸地,小人書被當成“封資修”一掃而光,學校早已“停課鬧革命”,每天除了讀書取樂,還能干什么呢?沒老師教,錯別字自然不少。幸虧我讀了便愛說,把“得寵”講成“得龍”,把“捧出”講成“棒出”,雖然總是笑聲一片,卻因之得以及時糾正。這時候來看沒圖畫的“字書”,火候自然到了。
那時讀書是要擔風險的。老保姆總是說:“你莫凈看些鬼舞尸起的書,危險咧!”鬼舞尸起,是長沙話亂七八糟的意思。當時我看的,卻是一本紅色兒童讀物《微山湖上》。至于《莫里哀戲劇集》,只能關在屋里讀。不能不說,我家躲過了抄家,是一大幸事。(見拙文《丹書鐵券》)
就這樣,當我把所能得到的白話文中外名著讀完后,開始了文言作品的閱讀。一開始,是讀表哥表姐的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文章。這種課本原文注釋都在一面,無需翻頁,十分方便。將中學六年的文言讀完,再去讀《鏡花緣》《聊齋志異》什么的,就沒啥障礙了。我現在的一點文言底子,就是那時候打下的。
我也愛讀詩。一天,祖母拿了本七伯楊德豫譯的《朗費羅詩選》給我,讀到《人生頌》時,真是熱血沸騰。外國人的詩,我只能背幾首和一些零散的句子;唐詩宋詩清詩等,卻能背下幾百首。其實除了《長恨歌》《琵琶行》,我確實沒“背”過唐詩,都是因為讀書多,經常見面記住的。
這時候已經開始看學術論著了。由于到手的書有限,便反復讀。如周有光的《字母的故事》,有趣極了,但印數僅300冊。
有一天,我發現了祖父所著布面精裝《積微居小學述林》,一問,才知道是專門給蘇聯人印的。這是一部文言寫作的訓詁學專著,我試著閱讀,發現也能讀懂,而且趣味盎然。我至今沒弄明白怎么會對這本書感興趣。而這,大約就是我研究古漢語的開端。
我還養成了廁所讀書和邊走邊讀的習慣。記得有次在大寨路上買了個蔥油粑粑,店家竟然用線裝書頁來包它。我邊吃邊讀,邊上的娭毑(對老年婦女的尊稱)說:“咯只伢子硬是只書憨子咧!”
中小學因為改為春季招生,延長了半年,1970年春,我小學畢業了。幾年沒到學校,中南路小學管事的說不能直接畢業,還要讀個六年級。見到同班同學辦離校手續,而自己“留級”,真是羞愧難當。
幾年沒學算術,上課有些跟不上。受祖母長期熏陶,如果功課不名列前茅,就無地自容。于是課后看教材再做習題,一周之內就趕了上來。再過一周,就考了九十多分。這使我認識到閱讀對于學好數理化的好處。今后若干年,這一招屢試不爽。
1971年春,在我14歲半的時候,分到了郊外湘江邊風景優美、藏書豐富的衡陽市第九中學。由于交通不便,這里成了“走資派”和“黑五類”子女比較集中的學校,老師也多是“政治上不過關”的。但這未必是壞事,在這兒我學到了不少東西。
在這中學總共四年(初中高中各兩年)。這時候,武斗已經結束,上課也逐漸走向正軌(雖然經常學工學農學軍,還挖防空洞)。那時升大學靠推薦,跟成績好不好沒什么關系。有熟人被推薦,考官問他:X=2,2X等于幾?他瞠目結舌,答不上來卻依然被錄取。所以前兩年,我還經常往長沙跑。幾乎每學期都去,有的期中考試都被耽誤了,但期末考試從沒耽誤過。每當這時,我便故技重施,看書,做習題,總能全班第一。開始,班主任彭老師還說兩句,后來甚至讓我給他姐姐捎東西。

1988年在武漢大學,楊逢彬(左)與同學合影
長沙的長輩為了我遇到問題時能有所請益,相繼給我介紹了幾位祖父的學生,他們要么住得不遠,如易祖洛、易仁荄(他們是遠房兄弟)、何申甫;要么常來,如廖海廷。跟他們,我又學到了不少東西(見拙文《我的四位家庭教師》)。
能找到的書有限,就開始買書了。七十年代初,上面發了一個極薄的16開解禁書小冊子,有我祖父的《詞詮》;近處的長沙古舊書店也恢復營業了。我買了竺可楨的《物候學》,讀得爛熟。有次姑媽拿錢讓我買肉,我花四塊多“巨款”買了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釋林》。
班主任讓交班費用來訂報紙,組織大家讀報。這樣,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在此之前,在家中床底下找出幾十斤《參考消息》,仔細讀了一遍。這份報紙是內部讀物,每日精選世界各地的文章。這對一個十三歲的少年,該有多震撼啊!九中圖書館新到了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書中講杜甫家有“三重茅”,因而是“地主”。中華書局版的《史記》也到了,管圖書館的老師見我讀得起勁,就一冊冊借給我。
也看數理化的書,還迷上了裝礦石收音機,居然能收聽十幾個臺。還用鐵絲做捕鼠籠和能夠連發的彈弓槍,劈竹子做弓箭,都很成功。
后兩年,和同學感情日深,去長沙的次數減少了;參加了校田徑隊,短跑在全市取得了名次。這時,正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各種競賽如火如荼。我得了作文比賽、俄文比賽第一名,繪畫比賽也得了名次。只是后來作文比賽第一名作廢,因為我的作文中引了柳宗元的《江雪》。老師同學都安慰我,不快也就煙消云散了。這兩年,除了和同學互相交換小說外,內部出版的國外小說也讀過不少。一次,同學借來《白居易詩選》,轉借給我,沒想到它后來不翼而飛,為這事我差點挨了書主人的揍。這時候,我長沙的大姑去了街道圖書館做事,還辦了市圖書館借書證,借書方便了不少,我也因此讀了《太平廣記》《山海經》等書。
我把我的學生時代,寫成了一部自覺而快樂的閱讀史。貪玩是孩子的天性,我希望當今的父母們要給孩子玩的時間,不要帶著他們在各種課外班中間穿梭。若想讓孩子成才,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動手的興趣是首要的。一旦這種興趣養成,無論學文史哲,還是數理化,都不成問題。腹中空空,縱然會彈鋼琴,能“高雅”得起來嗎?胸無點墨,字寫得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從前課業負擔重,孩子想閱讀沒時間;如今下午3點就放學了,而家長還在上班。建議各校建閱讀室,由一兩位老師輔導學生讀各種新奇有趣的課外讀物。最初可講故事(如《神秘島》),緊要處戛然而止,同學們自然會到書中尋找答案。還可建手工室,培養孩子做各種東西,如裝礦石收音機、望遠鏡、潛望鏡,等等。在玩中學的東西,是記得最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