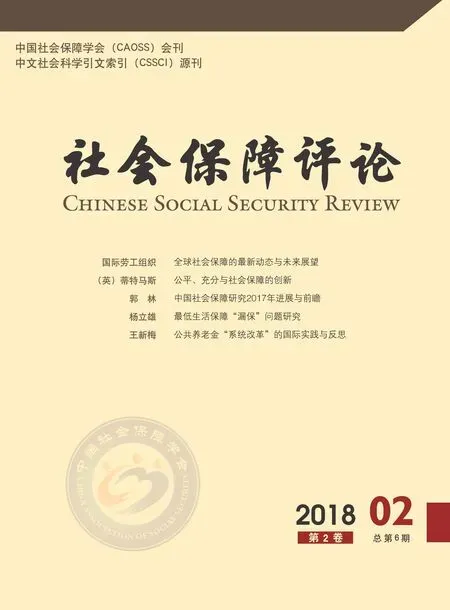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對貧困緩解的作用
——基于收入和熱量貧困線的比較分析
吳本健
一、引言
因病致貧是我國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了提高農民健康保障水平、減輕醫療負擔,解決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問題,2003年7月國務院開始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工作,建立了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截至2014年年底,新農合已經覆蓋了7.36億人,參合率高達98.9%。理論上而言,新農合不僅能幫助農民減輕高額醫療費用帶來的負擔,而且可以削弱因疾病帶來的后期負面影響,包括勞動力生產能力下降、家庭成員照顧病人所付出的時間和成本,從而降低因病致貧率。①Xiaoyun Sun,Sukhan Jackson,Gordon A. Carmichael,Adrian C. Sleigh,"Catastrophic Medical Payment and Financial Protection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Shandong Province," Health Economics,2009,18(1);Wuxiang Shi,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Alan Geater,et al.,"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Health Security Schemes on Health Utilization and Household Impoverishment in Rural China: Data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of Western and Cent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10,9(1).然而,過去20年我國因病致貧率卻不降反升。1998年因病致貧率為21.61%,2003年為33.4%②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中國衛生服務調查研究——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27頁。,2015年全國700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率為42%。截止到2017年2月,我國仍然有2000多萬因病致貧的貧困戶。③定軍:《中央正制定脫貧攻堅地區考核辦法 對貧困縣考核將取消或減少GDP權重》,《21世紀經濟報道》2015年12月16日,第5版。這不禁讓我們產生疑問:新農合能有效緩解貧困嗎?
目前,關于醫療保險計劃緩貧效果的研究已有很多。Sepehri等的研究發現,越南的醫療保險使得居民的衛生支出減少了28%—35%,且低收入者的費用支出減少的更為明顯。④Ardeshir Sepehri,Sisira Sarma,Wayne Simpson,"Does Non-profit Health Insurance Reduce Financial Burden? Evidence from the Vietnam Living Standards Survey Panel," Health Economics,2006,15(6).Wagstaff的研究也表明,越南的窮人健康保障基金(HCFP)大幅減少了窮人在健康方面的現金支出。⑤Adam Wagsta ff,"Estimating Health Insurance Impacts Unde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e Case of Vietnam's Health Care Fund for The Poor," Health Economics,2010,19(2).Hamid等研究發現,孟加拉國微型醫療保險計劃顯著地提高了家庭收入及其穩定性、降低了陷入貧困的概率等。⑥Syed Abdul Hamid,Jennifer Roberts,Paul Mosley,"Can Micro Health Insurance Reduce Poverty?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Risk &Insurance,2011,78(1).Kaestner等則討論了美國的醫療保險支持計劃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發現政府補貼醫療保險大大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提高了窮人的福利。⑦Robert Kaestner,Darren Lubotsky,"Health Insur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6,30(2).新農合作為我國新型的農村醫療保險計劃,其緩貧效果也備受關注。但是,目前關于新農合緩貧效果的研究結論存在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新農合提高了居民的疾病應對能力、減少了居民就醫經濟負擔,從而緩解了“因病致貧”現象;⑧Syed Abdul Hamid,Jennifer Roberts,Paul Mosley,"Can Micro Health Insurance Reduce Poverty?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Risk &Insurance,2011,78(1);齊良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減貧、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年第8期;任靜、趙東輝、宋大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保障狀況分析》,《中國衛生經濟》2012年第12期;盧洪友、劉丹:《貧困地區農民真的從“新農合”中受益了嗎》,《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2期。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新農合效果不明顯,甚至還引發了“過度醫療”,從長期來看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和陷入貧困的可能。⑨Adam Wagsta ff,"Estimating Health Insurance Impacts unde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e Case of Vietnam's Health Care Fund for The Poor," Health Economics,2010,19(2);Wagsta ff Adam,Lindelow Magnus,Jun Gun,et al.,"Extending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9,28(1);朱玲:《農村醫療救助項目的效果》,《經濟學動態》2006年第8期。
上述研究在測量貧困時大多采用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但由于收入在年際間的波動較大,且農戶收入和消費之間可以通過儲蓄和借貸平滑,這可能導致測量的偏誤。有研究用消費作為貧困線標準,但有些消費支出(如大額醫療費用支出)并不代表福利,這也可能導致貧困測量的偏誤。此外,新農合除了能夠在疾病風險發生時降低農戶的醫療費用支出,還能夠在疾病風險未發生時釋放預防性儲蓄、增加當期消費與生產性投資、提高勞動力健康水平,而上述研究并未將這些因素完全納入醫療保險支持計劃的分析范疇。本文將在考慮上述問題的基礎之上,厘清新農合緩解
貧困的機理,并采用收入和熱量兩個貧困線標準來評估新農合的緩貧效果。
二、新農合的緩貧機理:理論框架
新農合的緩貧機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農合能減少支出、提高勞動力質量和風險應對能力。“因病致貧”的主要路徑有:巨大的醫療開支消耗了家庭的收入導致消費減少,勞動力喪失或者減弱導致收入和消費能力下降,借債和變賣資產導致收入能力下降等。①劉遠立、饒克勤、胡善聯:《因病致貧與農村健康保障》,《中國衛生經濟》2002年第5期。理論上,新農合可以降低農戶個體面臨疾病風險時醫療費用的自付比例,平滑農戶的消費;新農合中政府補貼可以分擔農戶的醫療負擔,增強貧困農戶的就醫意愿,提高勞動力的健康水平,從而減少勞動力因看不起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此外,新農合可以阻止農戶通過借貸、變賣資產來應對疾病風險,從而減少疾病對農戶長期收入的影響。
其次,新農合能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家庭的基本消費。在未發生疾病風險時,為了防止未來的大額醫療支出,抵御風險能力差、處于貧困線邊緣、脆弱性明顯的農戶會進行預防性儲蓄,導致當期消費可能低于貧困線。新農合能大大提高這類農戶的風險應對能力,減少其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可能,釋放出的預防性儲蓄可增加當期消費和投資,從而提高了勞動力質量和收入水平。有研究表明,新農合使得參保農戶的家庭非醫療類消費增加了5.5%,且對沒有醫療支出的家庭的影響大于有醫療支出的家庭,②白重恩、李宏彬等:《醫療保險與消費: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經濟研究》2012年第2期。參保家庭比未參保家庭的人均熱量攝入多144.26大卡。③馬雙、臧文斌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分析》,《經濟學(季刊)》2011年第1期。

圖1 新農合緩貧機理圖
最后,從長期來看,新農合可以增加農戶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生產效率。就農戶角度而言,新農合可降低農戶的就醫成本,提高農戶的健康意識和就醫意愿,從而增加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有研究發現,新農合實施后農民的患病就診率提高了32%。①顏媛媛、張林秀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實施效果分析——來自中國5省101個村的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06年第5期。Wagstaff等發現,參加醫療保險增加了人們高額醫療費用的開支,參保人會傾向于到更高級別的醫院去看病。②Adam Wagstaff,Magnus Lindelow,Jun Gao,et al.,"Extending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9,28(1).Morduch的研究表明,消費平滑化有利于改善農民的教育條件。③Jonathan Morduch,"Income Smoothing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3).可見,農村合作醫療可以降低農村家庭未來醫療花費的不確定性,減少預防性儲蓄,除了增加當期消費以外,還會增加生產性投資和改善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這些投資會增加未來的收入,但在短期內很難體現出來。
三、數據、方法及變量
(一)數據來源及整理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CHNS(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該調查覆蓋9個省或自治區(遼寧、黑龍江、山東、江蘇、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的城鎮和農村,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樣本對全國總體具有一定代表性,包含了人口統計學特征、社會經濟狀況、職業狀況等方面的信息,目前有9輪數據(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由于本文旨在評估新農合的緩貧效果,而新農合自2003年試點推廣,2006年覆蓋率為80.75%,2008年覆蓋率為91.5%,之后一直保持在90%以上,且變化不大。評估新農合的緩貧效應需要了解新農合實施前后農戶收入、消費等方面的變化情況。因此,本文選擇新農合制度開始實施到覆蓋率超過90%這幾年(2004、2006和2009年)CHNS的數據,并且僅使用農村樣本,以準確評估新農合的緩貧效應。
關于個人問卷中合作醫療保險的問題,2004年和2006年的調查題目為“是否有合作醫療保險”,并未對新農合和舊農合做出區分。④2009年問卷中的問題為:是否參與新農合。新農合實施以前,農村即存在合作醫療,該制度最早開始于1955年,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其逐步衰落。截止到20世紀80—90年代僅有大約5%—10%的農村居民在該制度覆蓋之下。參見顧昕、方黎明:《自愿性與強制性之間——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嵌入性與可持續性發展分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鑒于該數據為跟蹤調查數據,利用上一輪(即2000年)的問卷找出有合作醫療的社區(29個社區),即為可能存在舊農合的社區。在2004年和2006年的問卷中扣除掉這些社區(2004年去除179個家庭,2006年去除206個家庭),剩下的社區如果擁有合作醫療,則為新農合。
為了更好地考察新農合與貧困之間的關系,本文刪除了一些異常觀測值,如中途退出新農合的家庭、購買了商業保險或者不明確是否擁有商業保險的家庭以及沒有參加新農合卻享受了政府公費醫療的家庭。另外,還去除掉了關鍵變量有缺失值的樣本。本文用Hadi法去掉1%的奇異值。為了得到對照組和實驗組,本文去掉了連續兩輪均參加新農合的家庭,最終剩下的面板數據有2016個家庭樣本。表1展示了對照組和實驗組的樣本量。

表1 對照組和實驗組樣本量(單位:戶)
(二)實證方法
本文利用農戶參與新農合狀態的變化來估計其對農戶陷入貧困概率的影響。本文使用倍差法(DID)來估計新農合的影響,即通過比較參合農戶與未參合農戶在新農合開展前后陷入貧困概率變化上的差異來估計。本文的方法為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陷入貧困概率的不同。DID的統計量為:

DID統計量可以在一個回歸方程中被估計出來,本文把2004—2006年與2006—2009年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數據合并一起,估計以下方程:

其中,Yit是一個啞變量,代表農村家庭i在時間t是否陷入貧困的狀態,如果貧困則為1,否則為0;Tt是一個代表時間的啞變量,第一組中,2004年取值為0,2006年則取值為1,第二組中,2006年取值為0,2009年取值為1;Xi是用來區分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啞變量,實驗組取值為1,對照組取值為0;Tt*Xi是時間和保險政策的交叉項,其系數就是DID估計的新農合對農村居民陷入貧困概率的影響;Zit為戶主和家庭的特征變量;Wi為地區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在這個式子中,DID統計量可表示為:

Tt的系數β1表示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共同時間變化趨勢;Xi的系數β2測量了對照組和實驗組隨時間不變的差別;交叉項的系數β3是本文主要關注的預測值,代表了新農合緩解貧困的效果。
(三)變量及其測量
被解釋變量為農戶的貧困狀態。為了更好地反映農戶的貧困狀態,本文采用了收入和熱量兩條貧困線。收入貧困線采用國務院2011年確立的農村貧困線2300元(2010年不變價格)作為標準,熱量貧困線以維持一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日均2100千卡作為標準。CHNS的人均熱量攝入數據獲取方式為調查農戶正常飲食情況下三天的食物攝入量,則:

其中,食物消費量指的是攝入的一切能提供能量的食物,包括油、調味品及正餐以外的小吃和飲料。參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測定的《中國食物成分表》中每種食物百克的熱量值,計算出攝入各種食物的熱量值加總。
解釋變量為是否參與新農合,具體指區分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變量Xi。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實驗組指的是“至少有一人參與新農合的家庭”。實際上,家庭中參合人數的比例會影響到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但本文暫不考慮家庭中參合人數比例的影響,原因有二:一是對于家庭而言,參與新農合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即把家庭作為一個決策單位,家庭中第一個參與新農合的個體是風險最大的,這說明家庭中第一份保險對于削弱家庭致貧的效果是最顯著的;二是根據白重恩等利用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樣本縣中有97%都要求以家庭為參合單位。①白重恩、李宏彬等:《醫療保險與消費: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經濟研究》2012年第2期。
控制變量包括戶主特征、家庭規模、勞動力占比、是否為少數民族家庭、人均耕地面積、人均固定資產價值、地區特征等。
(四)內生性問題的討論
影響內生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遺漏變量、模型誤設、測量偏誤、樣本選擇偏誤和互為因果等。②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2nd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2007,pp. 186-218.本文在控制變量的選取上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將那些既與新農合相關又與貧困相關的變量全部納入控制變量的分析中,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遺漏變量問題。為了解決模型誤設問題,本文采用了政策評估常用的DID模型,并設計了兩組實驗組和對照組。為了解決測量偏誤問題,本文采用了收入和熱量兩條貧困線作為貧困標準。關于樣本選擇偏誤問題,CHNS的調查覆蓋9個省或自治區(遼寧、黑龍江、山東、江蘇、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的城鎮和農村,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本文采用的面板數據和工具變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互為因果問題。
四、描述性統計及回歸結果
(一)參保趨勢和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我國2004—2014年中部分年份的新農合參與率。從表中可見,新農合自2003年試點實施以后,2004年4月參合率就達到54.7%,2006年達80.7%,2008年超過90%(為91.5%),之后基本保持穩定。在中國健康營養調查數據(CHNS)的農村樣本中,2004年的參合率僅為9.12%,但到2009年增至71.83%。

表2 我國新農合參與率情況
圖2為中國健康營養調查數據(CHNS)中對照組和實驗組2004年、2006年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的貧困發生率對比圖。①由于2006—2009年這一組對照實驗中,對照組只有32個樣本,實驗組有506個樣本,所以本文選取2004—2006年這一組的對照實驗來展示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該組的對照組為884個樣本,實驗組為594個樣本。可以看出,對照組和實驗組的貧困發生率均未有大的變化,維持在30%左右。②此處的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正常水平,因為本文在數據處理的時候去掉了以前擁有舊農合的家庭,以及未有舊農合的村莊卻參加了商業保險或擁有公費醫療的家庭,這些家庭通常收入水平較高。圖3為對照組和實驗組2004年、2006年以熱量作為貧困線標準的貧困發生率對比圖。對照組的貧困發生率從2004年的43.67%提高到55.43%,增加11.76%,而實驗組的貧困發生率基本穩定在36%左右。可見,如果以收入作為貧困線的度量標準,新農合沒有顯著緩解貧困;如果以熱量攝入作為貧困線的度量標準,新農合則可以緩解貧困。本文在之后的計量分析中,將進一步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以得到新農合對貧困緩解的凈效果。

圖2 收入標準的貧困發生率

圖3 熱量標準的貧困發生率
(二)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的回歸結果
農戶是否參加新農合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有些居民參加新農合可能是由一些不可觀測的因素所決定。參合決策中出現的自選擇效應問題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即當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時候,農戶的參合決策與自身收入相關,而農戶的收入又會影響其脫貧的能力。為此,本文通過計算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來判定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很強的相關性。經檢驗,農戶的收入與是否參合的相關系數為0.1311,統計上并未顯示出很強的相關性。為了進一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本文以村莊參合率作為工具變量替代個人是否參合做回歸。

表3 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的DID回歸結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0.0346 -0.0291 -0.0139 0.0259 -0.0131 -0.0108(-0.86) (-0.712) (-0.33) (0.60) (-0.31) (-0.26)戶主性別(女性=0,男性=1)時間*實驗組0.1495***(5.12)戶主年齡-0.0088(-1.18)戶主年齡平方(/100)0.0091(1.32)戶主教育年限-0.0149***(-4.46)戶主健康水平0.0266*(1.94)0.0347 0.0024 0.0325 0.0230(0.94) (0.06) (0.88) (0.81)勞動力平均年齡 0.0042 0.0016 0.0029 0.0051(0.60) (0.23) (0.41) (0.71)勞動力平均年齡的平方(/100)勞動力男性占比-0.0024 0.0014 -0.0011 -0.0029(-0.32) (0.20) (-0.15) (-0.39)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0.0159*** -0.0061 -0.0160***-0.0143***(-4.09) (-1.55) (-4.08) (-3.57)勞動力平均健康水平0.0221 0.0115 0.0230 0.0303*(1.36) (0.70) (1.41) (1.82)人均耕種面積-0.0140 -0.0244*** -0.0164 -0.0259***(-1.59) (-2.589) (-1.80) (-2.71)人均固定資產對數-0.0403***-0.0294***-0.0408***-0.0431***(-5.88) (-4.26) (-5.90) (-6.16)-0.1937 ***-0.2079***-0.1834***-0.1849***(-3.63) (-3.85) (-3.42) (-3.41)是否少數民族(否=0,是=1)勞動力占比-0.0671** -0.0523* -0.0462 -0.0313(-2.59) (-1.99) (-1.516) (-0.935)家庭規模0.0469*** 0.0311*** 0.0468*** 0.0447***(5.80) (3.77) (5.66) (5.38)

注:表中上欄為回歸系數,下欄括號內為t統計量,***、**、*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下表同。

表4 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的使用工具變量(IV)的DID回歸結果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勞動力平均年齡的平方(/100)-0.0677** -0.0511* -0.466 -0.0311(-2.61) (-1.94) (-1.57) (-0.94)家庭規模 0.0473*** 0.3122*** 0.0472*** 0.453***(5.85) (3.79) (5.73) (5.46)村莊人均收入對數 -0.2478***(-11.37)是否控制三大經濟地帶(東中西)-0.0021 0.0013 -0.0010 -0.0029(-0.29) (0.17) (-0.13) (-0.39)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 -0.0159*** -0.064* -0.0161***-0.0145***(-4.10) (-1.59) (-4.10) (-3.63)勞動力平均健康水平 0.0223 0.0116 0.0231 0.0303*(1.37) (0.71) (1.41) (1.82)人均耕種面積 -0.0135 -0.0247*** -0.016* -0.0258***(-1.54) (-2.61) (-1.76) (-2.69)人均固定資產對數 -0.0398***-0.0293***-0.0403***-0.0425***(-5.82) (-4.25) (-5.856) (-6.10)勞動力占比 -0.1941***-0.2073***-0.1836***-0.1847***(-3.64) (-3.84) (-3.42) (-3.40)是否少數民族(否=0,是=1)是是否控制省份是常數項 -0.461*** -0.270 -0.194 5.808*** -0.0262 -0.832調整的R2 (-10.97)0.0014(-1.43)0.0987樣本量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0.46)0.0215(-0.36)0.0807(7.54)0.1398(-0.05)0.0827
表3列出了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的回歸結果。表3顯示,六個模型交叉項的系數有正有負,影響方向不穩定,且在10%的水平上不顯著。利用村莊參合率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在加入地區效應的控制變量之后,交叉項系數亦有正有負,且不顯著,結果見表4。這說明,短期內新農合對農戶的收入未產生顯著影響。
從表4還可以得出,戶主的教育年限、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健康自評水平、戶主性別、人均耕地面積、人均固定資產、勞動力占比、家庭規模等對農戶陷入貧困的概率都有顯著影響。如果家庭為少數民族,陷入貧困的概率顯著降低6.77%(5%水平上顯著)。分別加入村莊人均收入對數、三大經濟地帶虛擬變量、省份虛擬變量作為地區效應(見模型10、模型11和模型12的回歸結果),民族變量的系數逐步變得不顯著,且隨著地區控制變量的增加,t統計量逐次遞減,說明地區效應沖淡了民族效應。
(三)以熱量作為貧困線標準的回歸結果

表5 以熱量作為貧困線標準的DID回歸結果

0.0923*** 0.0932*** 0.0474 0.0177(3.07) (3.10) (1.40) (0.47)家庭規模 0.0128 0.0115 0.0257*** 0.0336***(1.42) (1.25) (2.77) (3.51)村人均收入對數 -0.0174(-0.95)是否控制三大經濟地帶(東中西)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人均固定資產對數 -0.0186** -0.0178** -0.0168** -0.0153*(-2.42) (-2.30) (-2.17) (-1.91)勞動力占比 -0.0918 -0.0923 -0.0840 -0.1196**(-1.60) (-1.61) (-1.44) (-2.00)是否少數民族(否=0,是=1)是是否控制省份是常數項 -0.170*** 2.721*** 2.503*** 2.861*** 2.454*** 1.493***調整的R2 (-2.90)0.0080(2.72)0.1049樣本量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4.68)0.0255(4.86)0.0357(4.48)0.0360(4.66)0.0612
表5列出了以熱量作為貧困線標準的回歸結果。模型13到模型18的交叉項均顯著(顯著水平為1%和5%)且系數為負,對農戶減少陷入貧困的概率貢獻值在10.3%—12.3%之間,結果穩健;如果家庭為少數民族,陷入貧困的概率顯著提高9.23%(1%水平上顯著),且加入村莊人均收入對數作為地區效應,系數和顯著水平均未發生變化。表6展示了以人均熱量攝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OLS回歸結果,參合家庭的人均熱量攝入增加214.7—262.7千卡之間,①根據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2006),18—44歲中等勞動強度的人的推薦營養素攝入量(RNI)男性為2800千卡,女性為2300千卡。可見熱量攝入不是越多越好,多到一定程度會導致肥胖等一系列富貴病。因此,同等200多千卡的熱量增加值對人均熱量攝入低于2100千卡的貧困家庭效用更大。顯著水平均為1%。另外,本文以收入貧困線作為標準將樣本農戶分成貧困家庭和非貧困家庭,并分別對人均熱量攝入做OLS回歸。表7的結果顯示,參加新農合對兩類家庭的營養攝入均起到顯著改善效果,但對于貧困家庭效果更強,貧困家庭平均比非貧困家庭多增加20—30千卡的熱量攝入。

表6 以人均熱量攝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OLS回歸結果

注:戶主特征變量、家庭特征變量以及地區控制變量均與表5相同,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模型14中戶主年齡及其平方的系數顯示,戶主在50.94歲以前,其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但是到了50.94歲以后,其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將隨著年齡逐年增加。前一階段可能是由于戶主的子女開始工作,為家庭提供收入;后一階段可能是由于家里照顧老人的開銷增多,且戶主的子女開始生兒育女,撫養和教育的開銷增加。模型16中家庭勞動力平均年齡及其平方的系數顯示,平均年齡在48.81歲以前,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但到48.81歲以后,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將隨著年齡逐年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勞動力開始隨著年齡增加,工作經驗和管理經驗不斷豐富,人力資本不斷提升;但到了48.81歲以后,人力資本的提升速度低于健康和精力的折損速度,生產力開始下降。

表7 不同收入分組家庭、以人均熱量攝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OLS回歸結果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新農合不僅改善了家庭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減少了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增加了家庭食物消費;而且減少了預防性儲蓄,增加了家庭的食物消費和熱量攝入。這都使得家庭的飲食條件得以改善,并且貧困家庭的熱量攝入增加值更大一些。然而,新農合的這兩項影響不必然導致家庭收入的提高,因此通過收入作為貧困線的回歸結果顯示新農合沒有顯著緩解貧困。此外,新農合雖然可以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但人力資本投資(如教育)改善帶來的緩解貧困效果需要一定的時間方能體現。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結合已有文獻,本文對新農合的緩貧機理做了分析,分別討論了新農合對農戶收入和熱量攝入的影響。研究發現:(1)以人均熱量攝入2100千卡的貧困標準來測定,參合使得農戶陷入貧困的概率顯著降低10.3%—12.3%,日人均熱量攝入增加214.7—262.7千卡;但以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格)作為貧困線標準,參與新農合并沒有顯著緩解貧困。短期來看,參與新農合不能增加農戶當期的收入,只會減少農戶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新農合可以增加貧困線邊緣及以下農戶的當期消費,尤其是食物消費;長期來看,新農合還可以增加農戶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生產效率。因此,如果僅以收入作為貧困標準來評估新農合的緩貧效果,可能會掩蓋新農合政策的真實緩貧效果而影響下一步的政策制定。(2)當戶主和家庭主要勞動力步入中老年以后,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將隨著他們的年齡增加而增加,而新農合能顯著改善家庭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減少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增加其食物消費。(3)以收入作為貧困線標準,少數民族陷入貧困的概率要低于非少數民族;而以熱量攝入作為貧困線標準,少數民族地區陷入貧困的概率則要顯著高于非少數民族。同時,本文也得出戶主特征、勞動力特征和家庭特征對農戶收入和熱量攝入兩方面福利存在影響。
2017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時提出:健康扶貧是屬于精準扶貧的一個方面,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現在是扶貧硬骨頭的主攻方向。截至2017年,我國尚有2000多萬因病致貧人口,如何針對這些人群采取“靶向治療”的精準脫貧方案是當前精準健康扶貧的重要內容。在推進精準健康扶貧的工作中,本文的研究有如下啟示:(1)對于醫療保險計劃的評估,不能僅采用收入的標準,應該綜合考慮消費支出、營養、健康意識等因素。(2)從扶貧的角度,應對當前的新農合制度實施進一步的差異化改革。目前,在新農合的籌資方案中,中央財政對東中西不同省份采取差異化的補貼方案,對西部省份的補貼比例要高于中部省份,而對中部省份的補貼要高于東部省份。可以參照這一差異化方案,對不同年齡段的人采取差異化的補助方案。根據本文研究,若對49歲以上的參合人員采取較高補貼,則會使健康扶貧取得更好的效果。(3)新農合能顯著改善貧困地區少數民族的熱量攝入和營養狀況。因此,除了可對不同年齡段的人采取差異化的補貼方案,還可以利用少數民族扶助資金對少數民族的新農合費用采取差異化的補貼,這將大大改善少數民族營養和人力資本狀況,提升其健康意識,從而推進各民族人口素質的全面提升。(4)在制定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時,應增加對貧困農戶的預防性醫療服務供給,進一步降低農戶在疾病上的不確定性,釋放出更多預防性儲蓄,改善生活狀況。在制定扶貧政策時,應關注收入超過貧困線標準但熱量攝入不足的貧困人口的營養健康狀況。因為這一部分人群在面臨風險時一般會選擇犧牲其食物消費來應對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其熱量攝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