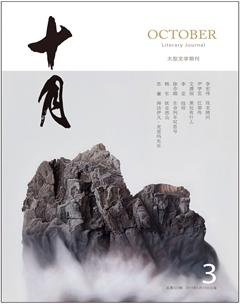候車室
2018-05-19 10:31:50袁凌
十月
2018年3期
袁凌
一
黑壓壓的人群,一進屋就變臉,拿出嚴酷的想象來。這個與我沒有任何共同點的龐大之物,如果離得太近,會在哪里忽然伸出一只腳,不動聲色地踏滅我。我遠遠地望著,找不到連成一體的黑色背部上任何一條縫隙。窗口又是那樣小,從一開始就斷絕了任何希望。
那些擠到窗口近旁的大人,機會也如此渺茫,說不定根本沒有票。肩背有力的他們,面孔在窗口面前卻是完全被動的,幾個人只能同時擠下半張臉,隨著里面的聲音應和。他們臉上現出的神情,如同孩子在父親面前一樣。窗口穿過厚厚的墻壁,是一個通道,從通道的那頭,一種不可知的命運操縱著這邊,除了那些走關系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穿過墻洞,觸到那邊毋庸置疑的權威。售票室里的世界似乎和這邊永無關聯。
在這里,我第一次領會到人生的絕望。
屋子外面停著不少車,但哪一輛也與我無關。一切只能看父親的,他帶著我們在縣旅社大樓住了兩天,參加完了中考,現在正在屋里的人群中,我已經無法在一片黑色肩背里找出他,只能老實地等待。只要走開幾步,我會就此和父親相失,失掉和世界聯系的線索,我出生后的一切都變為未曾發生。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性命攸關的時刻。
父親不知怎么弄到了票,院子里來了一輛卡車,大家拼命擠著爬上去,就像根本沒有票。因為是拉人的車,兩邊的車板加高了,大人們可以爬上去,對我卻高不可及,以往坐車是站在車門踏板上,第二步踏上水箱的臺階,攀到車斗里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