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土地”之二十四】通衢廣陌天地寬
文|景志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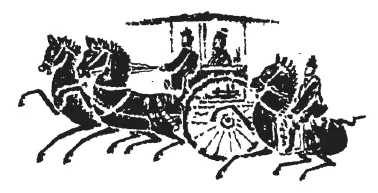
俯瞰中華大地,繁華的都市、喧鬧的城鎮、靜謐的鄉村……如同一顆顆散落的珍珠,而縱橫交織的道路就像那精美的珠鏈,連接城市與農村,溝通夢想與現實,貫穿昨天與未來。
從孤懸絕壁的秦蜀云棧,到通達四海的大秦馳道;從駝鈴悠悠的絲綢之路,到馬蹄陣陣的皇家驛道,陸地交通改變著人們的生存空間,深刻影響著五千年華夏文明的歷史進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自遠古大地上踩下人類第一個腳印,道路即伴隨著文明向遠方延伸。華夏先民們取水、采摘、打漁、狩獵的每一個來回,便是一次“踐地為徑”的造路過程——踏平荊棘,踩實土面,把腳下的足跡永遠印在歷史的起點。史傳軒轅黃帝“命豎亥通道路”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大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開辟道路成為部族首領乃至天下共主的重要使命,筑路史遂變為文明史。
周代分封建制,天子王城與各諸侯封國之間以路相連、往來頻繁,筑路技術和規模大幅度提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當時道路的質量標準已經很高,路面如磨石一樣平坦,線路像箭桿一樣筆直。秦始皇一統天下,頒布“車同軌”詔令,以咸陽為中心修建馳道,“東窮齊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條條大道通咸陽,為后人立下萬世基業。
漢承秦制,除了在原有馳道的基礎上改造、擴建驛道,還新開辟了關中地區通往西北、西南的陸路通道,各地運往長安的貨物“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張騫兩次出使西域,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被打通,東起長安,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橫穿中亞直達地中海,沿途各國通商貿易絡繹不絕,亞歐文明開始近距離接觸,其深遠影響一直延綿至今。
隋唐大運河的通航,開啟了水陸交通的新時代,將江南富庶之地與北方京畿重地緊緊聯系在一起。大唐盛世“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涂,畢出于邦畿之內”;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開通,成為漢藏一家親的紐帶。清代修建“官馬大路”,由北京直達各省城和邊疆重鎮,再通過“大路”和“小路”連接各州府縣城,構成輻射全國的交通網絡。
經緯有序,各行其道
修路離不開占用土地,而占地面積的大小主要取決于道路的寬度,路寬又往往與道路的類型、等級和功能相關。
國中經緯——城市道路。“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軌,車輪的間距,西周時寬8尺,每尺約合0.231米。按《周禮》的說法,天子王城內的南北大道稱經涂,東西大道稱緯涂,均可容九輛馬車并排行駛(寬約16.6米);城垣內的環城路稱環涂,可容七車并行(寬約12.9米);通往城外的道路稱野涂,可容五車并行(寬約9.2米)。諸侯城、采邑城依照相應的等級,路寬依次遞減。



鄙野徑畛——鄉村道路。西周實行井田制,鄉間道路與勞作的井田、灌溉的溝渠統一布局。“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徑是狹窄的小道,僅供人畜通行;畛是田間的道路,可容牛馬通過;涂是村落間的道路,可供一輛馬車行駛(寬約1.8米);道是村鎮間的通道,可供兩車并行(寬約3.7米);路是通往城邑的大道,可供三車并行(寬約5.5米)。
蕩蕩王道——城際道路。西周時期,自王城通往各諸侯封國的道路稱為“周行”或“周道”,相當于今天的國道。“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寬闊平坦的路面已可供四匹馬拉的大車來往通行。秦代修建的馳道更是大手筆,據后人記述“道廣五十步”。秦時6尺為步,50步約合69.3米,遠遠超過今天雙向八車道的高速公路。即使以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也足以稱得上“大路朝天”了。
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古代的工程技術、施工設備和交通工具都不發達,高山峽谷、江河湖泊、大漠戈壁、森林草原……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構成陸路交通的天然屏障。因地制宜、因形就勢,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歷來是道路布局、選址和修筑優先考慮的問題。
華夏之始,傍水而居。遠古時代的因河成道、循河覓路,成為道路選址的最早依據。大禹治水踏遍九州,均是沿河而行。西周時的鄉村道路——徑、畛、涂、道、路,也多建在水系旁邊,分別與遂、溝、洫、澮、川相對應。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沿河修建運河御道,詔令“水陸通,貢賦等”。隨著橋梁技術的發展,江河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塹。伐木作梁、拱石為橋,造型各異的古橋不僅便利了交通,也成為中華傳統建筑和文明的標志。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崇山峻嶺對陸路交通的阻斷,尤以秦巴山地為最。自秦漢開始,人們便沿著山脊、谷地、河槽、溝壑等地形,穿山越嶺,披荊斬棘,北跨秦嶺打通褒斜道、陳倉道、儻駱道、子午道,南越大巴山辟出金牛道、米倉道、洋巴道。尤其在懸崖絕壁之上,鑿石成孔,插木作梁,鋪板為路;又以火焚水激之法,在褒斜道南端谷口開鑿石門,建成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棧道千里,通於蜀漢”,劉邦和韓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歷史大劇,便在這里上演。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對于行旅者來說,茫茫沙海遠不如詩人筆下描畫的這般浪漫。《大唐西域記》載:“東行入大流沙,聚散隨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自絲綢之路開始,人們便利用所掌握的地形和氣候情況,避開變幻莫測的流沙,將商旅線路選擇在內陸河沿線、內陸湖邊緣、綠洲、戈壁以及固定的沙地等區域。這里地勢平坦、地形穩定、植被豐茂、水源集中,形成沙漠中的綠色長廊,成為陸路通行的必經之地。
羈途苦旅,驛路花香
自殷商夯土筑路以來,歷朝歷代的道路修筑技術一直未能有質的改變,到清末時依然以泥土路、沙石路為主。秦修馳道,“厚筑其外,隱以金椎” ,就是用鐵椎反復夯錘泥土,壓實路基、墊高路面。夯土路取材方便、施工周期短,但極易松散、變形和流失,風起塵土飛揚,雨后泥濘難行。地磚雖始見于戰國,也僅限于鋪設王宮或城內路面。而山區則“靠山吃山”,多以石板鋪路。直到進入20世紀,水泥路、柏油路才開始在國內出現。
“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路邊種植行道樹的傳統,始于西周,延續后世。秦馳道“三丈而樹……樹以青松”,東漢“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北宋“路平如砥直如弦,官柳千株拂翠煙”。晚清名臣左宗棠平定新疆時,統領湘軍沿途筑路植柳,僅甘陜驛路兩側就多達26萬株,被稱為“左公柳”。時人曾賦詩感懷:“大將西征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五里一堠,十里雙堠。”古人很早就在路邊設置專門的里程標志——堠。“堠,封土為臺,以記里也”,就是用來記錄道路里程的土堆或土墩,據說源于大禹治水時沿途所作的標記。羈途苦旅,長路漫漫,堠常常成為異鄉游子抒情感懷的象征物——“岸旁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墻上浮圖路旁堠,送人南北管離愁。”唐代韓愈更以《路旁堠》為題賦詩:“堆堆路旁堠,一雙復一只。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名侯館,侯館有積。”自西周開始,歷代就十分重視完善道路服務設施。秦漢設郵、亭、驛、傳,宋代又設館、鋪、站、亭,供往來商旅歇宿飲食。“商路雪開旗旆展,楚堤梅發驛亭春” “旗亭沽酒家家好,驛舍開花處處明”“柳蔭濃遮官道上,蟬聲多傍驛樓前”……歷代詩詞中,旖旎秀麗的驛路風光也屢見筆端。
“道塞山河舊,路通天地新。”神州莽莽,古道滄桑,留下歲月流逝的軌跡、文明進步的車轍、民族奮起的足印。征程漫漫,前路萬里,見證今日的中華大地,時代車輪,滾滾向前,開啟通往未來的康莊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