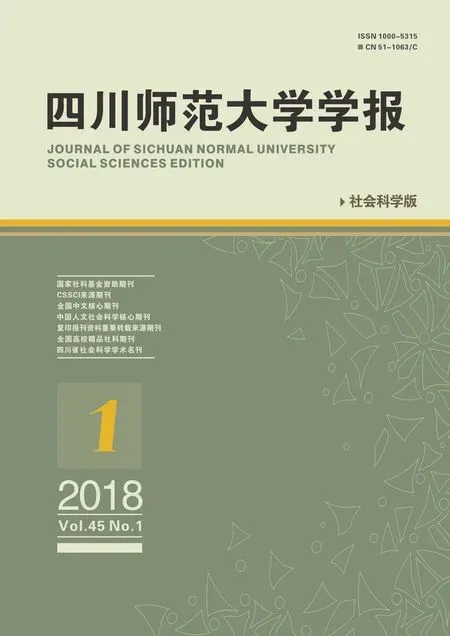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讀《清代今文經學新論》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 610064)
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經學一直占據著核心地位,對經學的研究著作也汗牛充棟,指不勝屈。特別是近年來出現的“國學熱”,將經學研究推向學術前沿。對清代經學的研究,發表的論文、出版的專著已經不少,但是,真正能夠超越前賢、提出新見的著作其實并不多見。清代經學,除乾嘉樸學之外,今文經學則為大宗,占據清代學術的半壁江山。尤其是晚清今文經學,由于其與古今中西之爭、變法維新之政、尊孔反孔之教相糾葛,更突顯出其學術思想史意義。最近出版的著名經學史研究專家黃開國教授主編的《清代今文經學新論》(以下簡稱《新論》)一書,努力揭示清代今文經學的文化學術意義、時代特質及具體表現,是一部研究清代今文經學的最新成果,該書在很多重要問題上力破成說,通過深入細致的梳理,提出對清代今文經學的新解釋,代表了清代今文經學研究的新高度。
一
清代今文經學是整個清學的組成部分。對于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解釋,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提出對清代學術史研究影響頗大的“清學三階段論”——“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章太炎撰有《清儒》一篇,對清代學術的發展變遷作了提要鉤玄式的概括。劉師培著《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對清代學術作了富有價值的總結。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認為:“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不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后來他著《清代學術概論》,對清學的評價有所變化,在自序中,把清代考據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并稱為我國五大學術思潮。梁氏還提出,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一大反動。他的這一論斷,影響深遠,響應者眾。隨后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序言中明確地提出:“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他針對梁啟超的“宋學反動”說,強調宋明學術在清代的延續性和繼承性。后來錢穆的學生余英時教授又加以發展,提出“內在理路”說來解釋宋、清學術的聯系。梁、錢等人重點討論清代學術的緣起,尤其是清代考據學為什么會興盛。他們把清學作為一個整體,著眼于清學與宋明學術之間的關系。這樣的討論,在面對歷史的細節時,其有效性無疑將大打折扣。如關于清代今文學的興起如何解釋,僅僅著眼于漢學、宋學,就會捉襟見肘。
《新論》一書,將清代今文經學放在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重視中國經學發展的內在理路。作者認為,作為經學結束的清代今文經學,絕不是漢代今文經學的簡單回復,而是蘊含了漢代以來整個經學發展的內涵。所以,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討論,絕不僅僅只是清代今文經學的研究,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到整個中國經學發展史的宏大課題。只有站在把握整個中國經學史發展的歷史高度,才能高屋建瓴地對清代今文經學作出公正的評說。清代經學與以往經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從宋明經學的重視“四書”之學變為以《爾雅》、《說文》為中心的樸學。作者指出,這是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經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作者尤其重視研究的方法論,強調對清代經學的準確認識,必須從整個經學發展史來把握,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清代經學本身來討論;如果僅僅從清代經學來說明晚清今文經學的興起,難以對晚清的今文經學作出合理的全面說明。
斷代經學史研究,離不開對整個中國經學史的宏觀把握,否則難免盲人摸象,難免片面。《新論》一書討論聚焦于清代今文經學,但作者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經學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論性問題做了獨特的闡發。如關于經學史的分期與分派問題,涉及到整個中國經學史的定位。這個問題不解決,對清代今文經學就難以做出準確的把握。因此,針對學界關于經學史分期、分派的爭論,作者提出具有理論價值的思考,認為經學的分期、分派不應該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就經學發展而論,一個時期的經學必有相應的特征,這個特征既是經學分期的依據,也是經學分派成立的根據,所以分期與分派應該是統一的。作者將中國經學分為三個時期,同樣也應分為三派。從漢到唐為第一期,是以訓釋五經為主的學派(外王);宋元明為第二期,是以訓釋四書為主的學派(內圣);清代為第三期,是以《爾雅》、《說文》為據的學派(文字訓詁)。作者認為這三期或三派的變化,也就是經學發展過程的演變。正因為作者能夠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來評說清代今文經學,故整個研究給人耳目一新、新義迭出之感。此說的提出,對經學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
二
如何從文獻、歷史與邏輯出發,精準把握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理路、階段與特點,是《新論》著墨較多的重點所在。這也是本書最大的創新之處。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在《新理學》“緒論”開篇提出來“接著講”和“照著講”兩種治學方法:“我們現在所講之系統,大體上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我們說‘大體上’,因為在許多點,我們亦有與宋明以來底理學,大不相同之處。我們說‘承接’,因為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因此我們自號我們的系統為新理學。”簡單理解,“照著講”著眼于繼承,“接著講”立足于創新。《新論》對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階段提出全新的、具有創造性的見解,糾正了前人似是而非之說。作者把清代今文經學發展分為兩大階段,指出其最大的不同在于“照著說”與“接著說”的差別,也就是作、述之別,“照著說”是述,“接著說”是作。在此認識的基礎上,作者對清代今文經學各個時期的理論特征做了科學的定位,認為“照著講”階段是對西漢今文經學的理論復興,所講的今文經學在理論上基本上是漢代今文經學的的再現,還沒有與時代相結合的新理論。當然,“照著講”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還可以分為三個小階段:即開創期、復歸期、擴展期。盡管有三個小階段的變化,但其中有共同不變的東西。如在治學方法上,所采用的主要是清代樸學惠氏吳派重家法的治經方法;在經學內容上,他們講的今文經學,都是按照漢代的今文經學的師法原則,力圖去恢復其原貌;就精神實質而言,還只是一種與現實政治沒有直接聯系的理論,只是從書本來發明西漢的今文經學,缺乏西漢今文經學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真精神,只可以稱之為一種學問,屬于從書本到書本的純學術研究。而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介于“照著講”與“接著講”之間,具有承先啟后的獨特意義。“接著講”的階段以廖平、康有為為代表,他們的今文經學與龔、魏以前的清代今文經學相比較,已經不是梁啟超說的復西漢今文經學之古的“照著講”,而是“接著講”,即利用公羊學的孔子改制說的理論形式,來發揮其與時代相結合的新理論,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時代特點,以近代的現實社會為關照,實際上已經是具有近代文化特色的歷史轉型意義。
任何學術的發展演變都不是孤立的,因此史學大師蒙文通先生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的治史原則。清代今文經學錯綜復雜,著作紛繁,學者眾多,他們的學術思想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繼承又有揚棄。如何從中總結出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規律,對其學術異同做出合理的闡釋,不僅體現了一個研究者的歷史敏感度和研究水平,也關系到研究工作是否成功,研究成果是否有價值。《新論》作者提出的以“照著講”和“接著講”來劃分清代今文經學的階段和派別,是一個獨創。用這樣的眼光來觀照清代今文經學發展,再經過作者的細致分疏,清代今文經學演變的內在理路、邏輯線索、歷史進程,就昭然若揭了。這對重新認識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理論價值。
三
學術研究如果只從宏觀上著眼,難免流于空疏;如果過于微觀,則會有瑣碎之病。優秀的學術著作,會很好地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宏觀論述與微觀分析有機結合,是《新論》的一大鮮明特色。
作者縱論晚清今文經學“接著說”出現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對清學的反動,而且是整個君主專制制度行將滅亡,新的社會階層要求改變舊的社會制度,并朦朧地呼喚新的社會制度的雙重體現,它是社會的歷史發展趨勢在文化上的反映。這樣的判斷,無疑比單純強調所謂“復古求解放”,無疑更有說服力。作者通過對清代今文經學的深入研究,對相關經學家的今文經學思想做了比較準確的把握、詳細的論說和公允的評價,并對一些重要問題提出新的看法。如前人都認為莊存與重視微言大義,而《新論》在區分微言、大義的基礎上,以堅實的證據,指出莊存與只重視大義,并不重視微言,并以“全至尊、立人紀”來概括莊存與重大義的主要內容,同時肯定莊存與重春秋公羊學的開風氣的歷史意義。又如傳統觀點認為龔自珍、魏源以今文經學議政,但該成果通過對龔自珍全部論著的認真研究,認定龔自珍的經學雖然有今文經學的成分,但大多不屬于今文經學;龔自珍、魏源的經學著作沒有以經議政的內容,他們以經議政的著作都不是今文經學的著作。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的來源,一直是學界比較關注和爭論較大的問題。近年有學者提出,康有為在光緒十二年(1886)所著的《教學通義》中,就已經有了今文經學的觀念。這個觀點在學界流傳很廣,影響甚大。《新論》通過翔實的證據,條分縷析,指出《教學通義》的性質是借助所謂周公教學之法的論說來表述自己的基本思想,是一部講治術的政治學著作,與今文經學觀念相去甚遠。其中康有為對經學一些問題的看法,與今文經學存在明確的不同,甚至是相反對的說法;而其中關于今文經學的觀念,不過是康有為后來的增竄。而就《教學通義》的基本思想來說,并沒有所謂今文經學觀念。《新論》這些觀點是通過認真考證得出的真知灼見,不僅具有正謬糾偏的作用,而且具有理論價值。類似的創新觀點在本成果之中還有很多。
四
《新論》作者黃開國教授從事經學史研究30余年,治學嚴謹,學風樸實,成果極其豐碩,許多論著都是開創性的,卓然成一家之言,有廣泛的學術影響力。該成果言必有據,不發空論,立足于整個中國學術文化史的宏大視野,在全面準確把握中國經學史發展演變脈絡的基礎上,重視經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對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進行深入思考,認真研究,既有理論創新,又有歷史考證,義理與考據相得益彰,既解決了不少經學史上的重大問題,又糾正了前人和時下流傳的一些認識誤區,從而將清代今文經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當然,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研究的終結,而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一部好的著作可以創新某種研究范式,開拓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但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問題,必然會為后續研究打開更加廣闊的空間。《新論》無疑是一份優秀的學術專著,但同樣也留下一些尚待繼續拓展的話題。該書以清代著名今文經學家的研究為主,對一些次要經學家的論述略顯不夠,如對戴望、皮錫瑞的經學成就基本上沒有涉及,這是一個遺憾。另外,在行文上略顯重沓,若假以時日細致錘煉,可以更加簡潔。有的章節為課題組成果,故各部分之間文風也有些差異,可以再整齊統一,則為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