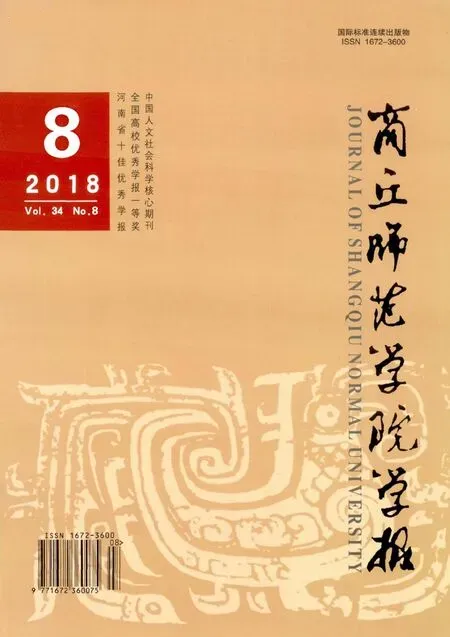異質性探緣:先秦儒道生態經濟思想的比較分析
趙 麥 茹
(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710127)
先秦儒道兩家經濟思想的生態理性十足且很一致,在生產領域都主張因順自然、以時生產,在消費方面都倡導知止知足、節儉消費。但是,在這種表面一致性的面紗之下,兩者的異質性又是非常鮮明的:一者側重人的積極主動性制度安排,一者側重自然本身的內在秩序;一者追求現實的世俗性物質需求,一者追求理想的精神層面的絕對逍遙;一者注重人類社會的等級秩序,一者注重自然世界的萬物平等。
一、異質性:指向一致基礎上的顯著差異
以時生產、節儉消費是先秦儒道在生產思想和消費思想方面的共識,兩者的指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在側重點、目的及核心特質等方面,兩者的差異是非常顯著的。
1.側重點不同:人還是自然?
在生產觀方面,儒家也看到了自然的內在運行規律:孔子的“天何言哉” (《陽貨》)“不舍晝夜”(《子罕》)、荀子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所指的均是自然的客觀性,先秦儒家顯然已經意識到自然有自己的內在屬性,有著人力所無法改變的某種強大力量。但是,儒家側重通過人的主動性適應這種客觀性,強調通過合理的生產活動安排和制度規劃以與自然的運動規律合拍,“不違農時”即是如此,誰“不違農時”?該如何“不違農時”?這樣,其潛臺詞就非常明顯了,儒家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注重“人”在整個社會活動中的中心地位,“人”是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和生產制度的供給者,自然規律成了客體,是人的生產活動的某種不可或缺的因素。可見,儒家的側重點集中在“人”及相關的人事制度。
道家顯然不同。從《老子》25章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難看出,道家不再局限于較封閉的現實社會,不再只側重人事活動,而將關注的視野拓展到更開放的體系中,關注整個自然宇宙。在道家的宇宙體系中,人處于宇宙秩序的初級始端,人是蒙昧的小學生,人成了受教育者。人的積極性、主動性、肯定性、要求性、擴張性等強勢特征不復存在,自然之道成為萬法所宗。為什么要反技巧?為什么明知“桔槔”可大大提高勞動效率卻棄而不用?為什么強調“天行有常”?道家給出的答案只有一個:自然之道。道家在一個更開放的體系中將側重點放在了“人”之外的客觀規律,不是自律而是他律,“人”成為自然體系中的一極,必須配合自然的脈動而采取相應的活動,人成為服從者。
2.目的大相徑庭:現實的世俗性功利需求還是形而上的精神訴求?
在消費層面,儒道兩家都主張節儉消費、知止知足。但是,為什么在明明可以提高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主張節儉消費呢?兩家給出的答案各異。
儒家很現實,在主張實行等級消費制度的前提下,儒家學者認為,各階層的人皆應盡量節用尚儉,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可供消費的產品“不可勝食”“不可勝用”,才能在原來的消費水平上不斷“繼之”,保證較長遠的消費。可見,儒家考慮的是現實層面的長遠生存問題,是很急迫又很務實的與“此岸”而非“彼岸”有強烈關聯性的問題,是出自物質層面而非精神層面的考慮。這種思路源自很典型的世俗性功利需求。
道家主張在消費水平上知止知足,但在解釋原因時卻是從心性修養方面出發的:奢侈消費實為“生之害”,會導致“性命之情病”。道家追求的是與自然之道相契合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51章)的“玄德”之境,道家學者也深刻意識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15章),任何過分的追求和索取都與自然之道相悖,都妨礙了對精神之逍遙無待境界的追求,都應該果斷棄之。
3.核心特質迥異:等級制還是無差別的平等?
等級制是滲透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的一個核心特質,這一特質在強調節儉消費的消費思想領域尤為明顯。
《八佾》篇,孔子對季孫氏使用八佾之禮的行為非常氣憤。他認為,季孫氏僅僅是大夫的身份,但是竟然敢私自享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待遇。這是典型的僭越,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才憤然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主張按照身份享用符合其身份之物質消費水平的觀點也在這種指責中顯露無遺了。
孟子也非常認可消費等級制。他的“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下》)一語道破其立場,顯然,孟子也倡導節儉,但他認為消費的必要前提是符合禮制,這和孔子的“儉不違禮”是一致的。孟子的消費實踐也印證了這一點。他根據父母去世時自己的身份,采取了不同的安葬父親、母親的葬禮標準,前者以士禮(三鼎),后者以大夫之禮(五鼎)。孟子對此很坦然,絲毫不覺得這與傳統的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倫理相悖,他只是根據自己的境遇靈活調整了雙親的身后之事的辦理規格而已,是權變,是根據情況變化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孟子的消費實踐實為對消費等級制的完美腳注。
儒家的另一典型代表人物荀子則直接把這種消費等級制上升到理論層面,給予其道德合理性。《富國》篇的“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和《禮制》篇的“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皆是對這種合理性的說明和闡釋。荀子將這種合理性貫穿到社會各階層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各階段中,并認為這種類似消費等級制的“不齊”是維持社會“齊”的充要條件,他將之稱為“維齊非齊”。荀子的這種做法直接賦予了等級制消費不可撼動的理論依據,將消費等級制合理化、合法化、體制化,其影響是深遠的。
道家在這一方面與儒家截然相反。道家代表人物莊子所主張的“齊物”注定了道家的非等級制消費。莊子認為,所謂的差異都是相對的,在絕對長的時間、絕對大的空間中,所謂的生死、壽夭、長短、高矮、有無等都是一樣的,沒有必然的差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只消轉換一下視角,或者拓展一下想象思維的空間,用巨人的眼睛俯視萬物、用與宇宙并存的絕對存在衡量萬物的內在價值,那么,一切皆是如此。所以,莊子才有了“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的結論,才有了“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天下》)的主張。明白了道家的這種生態主義立場,其針對人類社會的非等級消費觀念也就很好理解了。既然連人在宇宙中都和其他的萬物別無二致,沒有絲毫的優勢而言,在人類社會內部,其等級制的存在也就相當可笑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級制不存在,又談何消費的等級?在道家學者視野里,儒家那種給一切都貼上等級標簽的做法可笑至極,儒家學者太過關照現實的秩序和等級,而忽視了生命的本質。道家認為,從本質上來說,萬物皆是平等無差別的。
二、分歧背后的原因:異質性緣何產生?
儒道生態經濟思想的這種分歧緣何產生?換句話說,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先秦儒道學者在生態經濟思想方面的異質性?兩者在人性假定、邏輯思維方式及終極價值取向的不同應是這種分歧背后的原因。
1.人性假定的迥異
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社會是由無數原子化的個體、無數個人組成的。那么,在社會組織及活動中,為什么在物質屬性及生理構造上相似的個人會在現實社會中產生差異性非常大的行為實踐及選擇?在某些領域,又是什么因素導致原子化的個人的選擇呈現出某種趨同?從無數原子化的個體中能否剝離出某種同質性的因素?如果有,這種同質性因素又將如何影響人的行為模式?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實際上涉及人性假定,不同的人性假定會導致不同的結論。先秦儒道學者在人性假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1)“人皆可以為堯舜”還是“見素抱樸”
先秦儒家的孔子和孟子的人性假定較為樂觀,他們對道德境界的肯定性預期皆建構在這一樂觀的人性假定之上。
孔子認為,原子化的個體也有普適性的同質性,此即人性:“性相近也。”(《陽貨》)孔子的這一觀點,實際上是給從天子至庶人的所有個體提供了一種溝通的理論依據,亦給所有個體實現道德境界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依據。侯外廬對孔子的這一貢獻非常肯定,認為這一命題是“可貴的”,因為孔子“探求出的人類的性能,已經在原則上承認人類的近似性”[1]145。那么,這種“近似性”是什么呢?孔子實際上已明確指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里仁》)孔子已意識到人皆有逐利惡害的基本欲望,但他認為引導欲望并不難,只要取之以“道”即可,此即他的“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而且孔子認為做到這一點似乎并不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這樣一來,孔子的主張就很清晰了:他認為,人性是相近的、共通的,大家的欲望相差無幾,但可以通過“道”的引導使個人實現“仁”的境界,且這種境界的實現并不很難。所以,個體如若克服不符合道義的欲望訴求,達到理想境界是大有可能的。
孟子將孔子的“性相近”學說進一步推進,把人性中相近的特質概括為“不忍人之心”。他認為,這是人性中皆有的普遍因素。此外,孟子還進一步從人對孺子入井的普遍反應推衍出人的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心分別為仁、義、禮、智之“端”,且這四端是人來到這個世界所必備的先驗的要件:“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可見,孟子不僅將人性的內容具體化、豐富化、立體化,還賦予了人性內置于本我的屬性,這樣,“人皆可堯舜”無疑是可能的。那么,為什么有賢有不賢呢?孟子認為,這與個體在追求理想境界時的取舍有關:“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既然四心是大家共有的內在屬性,不存在獲得的不可能性,能否激發“四端”,達到道德境界,就完全取決于個體的主觀選擇了,選擇不同,得失自然不同。
先秦道家對于人性的理解同其對自然的理解是一致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3章),自然對萬物都是一視同仁的,無所謂好壞偏私。而人性也是如此,人性的本真狀態應該是無私無欲的:“圣人之心……常使民無知無欲。” (3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以其無私邪?”“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37章)從老子反復的強調中,不難看出,他對人性的假定是:人性的本質是無私無欲的。不過,老子也看到,在急劇轉型的社會大背景下,各種逐利現象比比皆是,大小國之間的廝殺和蠶食已將這種逐利行為放大到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所以,他意識到要達到真正的無私無欲幾乎是不可能的。他也采取了妥協和讓步,倡導盡可能地將物欲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9章)莊子也是如此,他認為無欲才是人性本真狀態:“至德之世……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但他同樣也作出了讓步,無欲的“至德”境界很難實現,那么,“少私而寡欲”的“建德”狀態也不錯:“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木》)
先秦儒道對于人性的不同假定決定了其在生態經濟思想方面的不同。儒家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發現本心即可,這就需要發揮人的積極主動性,人的能動性越強,越能日臻佳境。而道家認為,人性如同自然般無私無欲,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人為措施,人越努力越使勁,離理想的目標就越遠。最好的做法是效法自然,無為即可。
(2)“存心養性”還是“心齋坐忘”
儒道兩家對人性的不同假定注定了其發明本心的不同路徑。儒家主張內省外禮、存心養性,而道家主張絕學棄智、心齋坐忘。
孔子雖然認為實現“仁”的境界并不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但如何把想法變成現實呢?亦即在“我欲仁”和“仁至矣”之間溝通的橋梁何在呢?孔子給出的方法是內省外禮。一方面,孔子認為,不斷自律是必要的。“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省焉。”(《里仁》)“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衛靈公》)“見其過而內自訟。”(《公孫長》)內省實際上是一個“內圣”的過程,是儒家修齊治平中的“修身”。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外王”,才能談及齊家治國平天下。另一方面,孔子又認為,外在的約束是必要的,而最適合的約束,非“禮”莫屬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顏淵》)與內省的自律相比,這里的“禮”相當于他律。兩者的結合構成了孔子所認為的連接“我欲仁”和“仁至矣”之間的橋梁。
孟子更注重內省。他雖然認為人皆有與世俱來的良善,皆有不忍人之心,且內置于本體,但該如何激活這種善端并達到理想境界呢?孟子認為,對這種善端的發現、培育和擴充是非常關鍵的:“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擴充的過程,實際就是發現自我、認識自我、挖掘不忍人之心并將之不斷釋放和實踐的過程。
道家則反對任何人為的努力,不管這種努力是內省還是借助外力。老子對人類所標榜的智慧不屑一顧,甚至認為這是開歷史倒車:“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18章)要重返至臻之人性,只有將貼有這些人類智慧標簽的一切東西徹底拋棄方可:“絕圣棄智……絕仁棄義。”(19章)如此,一切可復歸原始,回到原來的本我。莊子更追求精神的逍遙無待,但他所求的這種境界實為人與自然萬物的合而為一:“精神四達并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刻意》)徹底的本我只有在這種境界才得以體現。莊子的本我實為“無我”,所以他認為唯有心齋和坐忘才是通達此境界的途徑。何謂心齋呢?莊子借孔子之口這樣陳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何又謂坐忘呢?莊子認為,坐忘即更徹底的忘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道。”(《大宗師》)莊子讓人們忘掉束縛思想的形體,把思想從物質的肉體中解放出來,與整個天際交融溝通。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自然包容萬物,空間無限廣大,束縛思想的肉體是萬物中有形世界的一個組成,但一旦精神從肉體中跳出來,便會與自然融為一體,無所不至。
(3)“圣王之制”還是“無為而治”
梳理出先秦儒道兩家的人性假定和實現路徑,先秦兩家生態經濟思想的差異性就有了較強的解釋。
正因為儒家對人性的假定較為樂觀,且對實現理想人格的可能性堅信不疑,所以在相應的社會實踐中,他們才會在經濟活動中主張采用積極主動的方式引導人們,才會注重發揮人的能動性。也是因為這個,儒家才會注重通過“圣王之制”“使民以時”等政策法令引導百姓因順時令、參贊化育,才會通過禮制限制各階層人士的消費水平,引導大家適度控制自己的欲望、節儉消費。
道家就不同了,因為堅信人性無欲無求,實現理想人格、達到理想境界必須完全忘我、回歸自然本真。所以道家注重順道無為,倡導人們不為物質所累,少私寡欲,追求精神的逍遙自在和真我本我的實現,而實現這一點,只要拋棄人為的智慧和技巧,因順自然的規律活動,無為即可無不為。
2.邏輯思維方式:由內而外還是由外而內
先秦儒道邏輯思維方式的不同是造就兩者差異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儒家習慣由內而外進行思想和推理,而道家則恰恰相反,較為注重由外而內進行思考。
儒家的由內而外體現在他們習慣從自己身邊最熟悉的東西由近及遠地進行觀察和體悟,在內圣之后,該如何把對于君親的關愛擴充到百姓進而到整個自然界呢?儒家主張先推己及人,再推人及物。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荀子的“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非相》)等論述,所談的皆是如何站在個體的立場以“類”的方式進行同情之了解,對別人進行關愛。而孟子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則進一步將這種關愛輻射到自然界。換言之,儒家是從通過剖析最熟悉的個體——自己——來實現內圣,然后通過換位思考了解別人,再進一步拓展思維的觸角,推衍至自然界。這樣的思維方式注定了儒家比較關心個體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性物質需求,從而有了向世俗功利性需求聚焦的傾向。
道家習慣由外而內思考,基于排斥人類智慧和技巧的立場,他們對任何人為的制度文化和文明不感興趣,反而非常注重向外在的遠離人類社會的自然外物學習。比如:“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78章)、“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76章)等自然現象給予老子的啟發是以柔克剛、柔弱勝剛強;“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66章)則讓老子領悟了謙虛不爭的力量。莊子則從故人之鵝“以不材死”、而大木因“不材得終其天年”的反差和對比中,領悟到人也應該處于“材與不材之間”、并能夠“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山木》)的道理。可見,老莊都擅于從自然秩序中體悟生存智慧和人生哲理,這種思路是由外而內的。這樣的邏輯思路導致道家對自然更感興趣、對人類社會秩序之外的自然秩序更感興趣、對物質功利之外的精神境界更感興趣。
梳理儒道邏輯思路及其所導致的側重點差異之后,再重新審視儒道在生態經濟思想方面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就很好理解了。儒家倡導節儉消費更多考慮現實的后續消費需求,是為了“長慮顧后”(《榮辱》),而道家則更多考慮的是奢侈消費會給人精神修養、心性培育方面帶來嚴重的損害,會導致人“性命之情病”。這兩者的差異正是由儒道兩家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所導致的。
3.終極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的相對性還是絕對性
人類衍生至今,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始終如一。真正的自由是剔除各種不平等后的完美形態,但一般來說,絕對的自由很難實現。長期關注社會形態歷史演進的社會學者福山就一方面承認“所有真正的自由社會原則上都會傾力排除習俗衍生的不平等”[2]329,一方面又認為“一個文明耽溺于不能遏止的‘對等愿望’,狂熱地企圖完全消除不平等,馬上就會碰到自然本身所設的極限”[2]334。這種認識是有道理的。福山把自由民主視為“歷史的終結”,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這倒是值得商榷的。誰也沒有足夠的權力宣告哪一種意識形態是歷史演化的終點和最后形態,歷史本身還在演化,還存在無數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終結”一詞很有特點,假設真的有某種完美的終點,那么起點在哪里呢?
實際上,從人類孕育、誕生開始,人類的救贖之道就已啟動,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進步和演進都是同不平等、不自由抗爭的過程。人類的“意志自由”、人類利用屬于自己的意志、“在不相容的目的之間作選擇”[3]83的能力使得人類一步步接近自由。阿瑪蒂亞·森更是從自由的視角來定義發展:“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4]1先秦時期的華夏大地,已處于人類的相對自由時期。鐵器的發明和廣泛使用使得人類為獲得食物而投入的成本(時間、精力)大為減少,脫離集體耕作的個體勞動形式成為可能,社會組織方式和意識形態因而也加以改變。
不過,先秦時期畢竟處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時期,是人類文明的初始階段,人對于自身及社會的理性認知也剛剛起步,因此,那一時期的學者對世界的認知無疑是有局限的。
(1)儒家:自由平等觀的相對性及其等級制消費
關注現實社會的先秦儒家更注重“禮制”外衣裹挾下的人的社會性標簽:出身、地位、血緣、輩分、社會關系中的排名地位等,這些就是福山所說的包括社會分割成封閉的階層、種族差別制度等在內的“阻礙平等的法律圍墻”[2]328。孔子雖然也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初看,此語似乎是講求平等的,但不可忽視孔子對維護等級制度的禮制的尊崇:“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顏淵》)離開“禮制”,人似乎已經無法行動了,但這個禮制的特質卻是為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服務的,這就導致孔子所說的平等和自由只是相對的,只能做符合禮制的事情,這個社會才會承認你行動的合理合法性,才能獲得所謂的平等和自由。孔子終其一生適應這種規則,到七十歲左右的時候才感慨自己做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政》),這也許是孔子的自由王國,但這一王國仍在以等級制為內核的禮制束縛之中。胡寄窗就很明確地指出,孔子的“經濟言論基本上都貫串著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社會倫理觀念。經濟活動大都須從屬于倫理規范”[5]99。
孟子要比孔子進步一些,他對平等的理解多了雙向義務的強調,不再是單向的要求和命令,而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在上級與下級、君與臣、強者與弱者等關系中,雙方權利義務均等,單向的索取和強勢的命令失去了合理性。所以他才會在“好色”“好貨”等方面反復要求君主應該“與民同之”“與百姓同之”(《梁惠王下》)。但是,一旦涉及核心內容,孟子又立刻反戈,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說以及他嚴格按身份等級為父母辦喪禮的舉動都在挑戰他的相對義務說。這樣看來,孟子的平等也是沒有逃離以等級森嚴為特色的禮制。
認為人性惡、主張以禮制約束人之欲望的荀子又退回去了一些。他認為,貴賤上下乾坤天地陰陽強弱等安排是公平的,無所謂不平等。荀子甚至專門從理論上論證了其合理性:“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王制》)“不齊”成了維持“齊”的必要存在,不齊是就整個社會的垂直階層構成而言的,齊是就各階層內部成員之間和整個社會的統治穩定性而言的,外儒內法的荀子為等級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可見,在先秦儒家根深蒂固的等級制觀念中,原子化的個體如若脫離已經按照身份、血緣等條件分割好的階層定位,個體將無所適從。在儒家封閉的社會體系中,個體依附于整體,個人從屬于社會和某個特定的階層,這直接導致了人格的奴性、依附性和封閉性。在這樣的體系中,人的自由、平等只能是相對的。聯系這一點,先秦儒家在消費思想上和道家的不同也就很好理解了,儒家對等級制的重視使其即使在強調節儉消費時仍非常注重區分等級,要求各等級按照身份自動歸位、不可僭越、不可挑戰禮制下的等級排位、不可享受超越身份的一切待遇。
(2)道家:自由平等的絕對性及其妥協與逃避
道家主張回歸自然的立場使其對于類似等級制等人類社會標簽的一切東西都毫無興趣。不同于先秦儒家學者,老莊把視野擴展到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宇宙,在一個更開放的體系中探究自然之道。
老子從人類社會秩序中跳出來,把關注的目光投射到宇宙自然萬物。他所觀察到的宇宙自然萬物是這樣的:“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16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7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32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自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34章)自然在無聲無息中養育萬物,但不居功自傲,自然中的萬物各自以自然之道生長繁衍,天長地久,并行不悖,且不斷地反復循環,永不間斷。老子對這種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頂禮膜拜,他關注到這種法則在歷史時空中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并將其不爭、無為、平均、無私等大平均特征提煉出來。侯外廬對其大平均特質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因為自然秩序是超時代的,所以是無善惡的,無公私的,無主觀客觀的,無上下先后的,無大小的;不私能成其私,不自大能成其大,不主而自主,不勝而自勝,不有而自有,不盈而自盈,無為而無不為,所以是大平均,自平均。”[1]299從老子對有無、陰陽、柔弱剛強、巧拙、智愚等概念的界定來看,老子從自然秩序中提煉出這種大平均特質是必然的,因為萬物不停地進行循環往復的運動,所有看似對立的事物皆是對立統一的。此時大,彼時小;大到極致轉為小,小到極致再轉為大;從這個角度看大,換個視角再看又小了;在小的封閉范圍看著大,在大的開放體系中則小了。其他的類似強弱、盈虛、有無等概念皆是如此。
當老子以這樣的自然觀審視人類社會時,當然會覺得一切的蠅營狗茍、趨之若鶩的爭名奪利、公然的戰爭掠奪與蠶食、人為的等級制度安排等都顯得非常可笑了。人類是自然宇宙中的塵埃,所謂的人的能動性和智慧在老子看來是倒退的:“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38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48章)以這樣的智慧所作出的包括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等級制社會制度安排當然也是愚不可及的,人類的人為等級分化與自然中萬物的大平等是相悖的,所以老子才會主張回到自然之赤子狀態,找回嬰兒般的淳樸之心:“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我愚人之心。”(20章)摒棄人類的智慧:“絕圣棄智。”(19章)在政治制度及一切人為的社會組織管理中,剔除掉任何“有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58章)這樣,才能使人類的行為與自然之道相契合:“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81章)
莊子以其更豐富的想象力、以上帝的視角俯視蕓蕓眾生,所以他才能更徹底地“齊物”:“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齊物論》)這種想象力太神奇了,以現在的天文學知識,地球只是太陽系的一顆行星,太陽只是銀河系上千億顆的恒星之一,而銀河系又只是宇宙數以千億計的星系之一,這樣看來,地球在浩瀚宇宙中的確只相當于一個微不足道的塵埃,類似太平洋中的一滴水。地球的形成歷經46億年,地球形成后8億年才出現簡單的生命,人類的出現只不過是250萬年前的事情,不管是從時間還是空間來看,我們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都太渺小了,而我們人類就生活在類似宇宙塵埃的地球上,況且,地球并非是人類專屬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共存于這顆藍色的星球上,地球屬于所有進化成功順延至今的生物。如果以生態中心主義的視角來看,考慮到自然本身的內在倫理尊嚴,地球還屬于它自己。
莊子雖然沒有這樣的天文學知識,但他憑借人類文明軸心時代智者的敏銳性已感受到這一點,所以,他才能有如此超凡的判斷力和定論:“大山為小”“彭祖為夭”。顯然,他已跳離人類慣常的思維模式,不以人類的視角,而以宇宙之神的視角看待生死、大小、壽夭、物我、高矮、長短等,以這種視角來看,萬物當然一致,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萬物皆平等,皆是自然之道的幻化、是道的載體、是形,而萬物又在時空中隨生隨滅、滄海桑田、往復不止。也因此,莊子才會反復強調萬物在內在價值上的平等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
莊子選擇了徹底的齊生死、齊萬物的立場,因此他才通過對“至德之世”萬物平等的肯定性描述來表達他對人類將人劃為不同等級之做法的反對態度:“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馬蹄》)將人類劃為不同等級已夠可笑了,更不要說建構在等級制度上的消費等級劃分了。莊子認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應該是:“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山木》)莊子認為,應該直接從浸透著所謂智慧、技巧、管理等人為痕跡的人類社會逃離開去,過著與鳥獸為伍、渾然天成、互不影響的生活,當然,消費也無所謂奢侈節儉之分了,只是最簡單的果腹保暖之需。在等級制方面,人與動物都無差別,更別說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了。與儒家相對的自由和平等相比,莊子的自由和平等是絕對的。莊子將齊物平等落實到了極致。
因此,在老莊的思想體系中,貼有等級制標簽的人類社會制度與自然之道相悖,是落后退步的代名詞。老莊在更大更開放的時空中討論自然之道,在這樣的開放體系中,原子化的個人和動物、植物、石頭、河流等萬物一樣,都有相同的內在價值,其本質是相同的,萬物皆平等。以這樣的邏輯推理,個人在社會組織中也不應該被任何制度人為歸屬,個人擁有自由人格、獨立人格和開放人格,個人不依附于任何組織,不存在奴性、依附性和封閉性,這和儒家剛好是相反的。也因此,在論述節儉消費思想時,道家才不會像儒家那樣在意消費的等級制。
但是,道家的這種絕對自由平等追求只局限在精神領域,對于現實社會,他們無可奈何,因此采取了妥協和逃避的態度,莊子在這一方面顯得尤為明顯。當面對現實社會中的種種人為安排和不公時,莊子認為只能“安時而處順”(《養生主》)。他多次表達了類似的想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人間世》)“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德充符》)追求精神的絕對逍遙無待、自由平等與對現實的逃避妥協形成了先秦道家思想的鮮明特點。聯系老莊沒落貴族的出身,這種特點也就很好理解了。他們失去了舊有的家園,對轉型中新興的制度和社會又無力改變,只好一方面從精神上遁世逃避,一方面對現實社會進行妥協讓步。
三、先秦儒道生態經濟思想異質性的現實功能:互補性及其現實關照
互補性成為先秦儒道生態經濟思想的顯著特征:一者入世,一者出世;一者強調人類的社會秩序,一者注重自然的內在秩序;一者側重維持人類等級的禮制,一者側重追求自然萬物平等無礙的境界;一者追求世俗性的物質需求,一者追求超然的精神訴求;一者由內而外思考社會,一者由外而內體悟自然;一者強調“圣王之制”,一者推崇“無為而治”;一者在相對封閉的體系中強調個體的隸屬性,一者在相對開放的體系中探尋個體與廣闊宇宙的對話與通融。
當前,中國正處于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態問題也愈來愈嚴重。面對這種局面,從個體到國家都應意識到“我們的世界是有限的”[6]495,都應慎重思慮并采取行動。所幸,我們已經開始警覺并逐步踐行可持續發展模式。學者們呼吁構建新的發展觀,葉坦研究員用新發展觀的視野審視我國民族經濟學的發展及學理價值時就指出,“我們不能只看經濟數字而不顧社會及自然和諧,只講發展而不談代價”[7]16。國家領導層也不斷強化新發展理念,“堅持和貫徹新發展理念,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8]395,“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8]393。亡羊補牢,并不算晚,這是非常可喜的變化。
先秦儒道學者的思考和感悟可穿越歷史的長河,在現有的時空中為我們提供啟迪: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一方面需要道家基于對自然深層敬畏而自覺遵循自然規律的“無為而治”,需要效仿道家對自然萬物的平等主體地位加以認可;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的“人治”,需要供給完善的糾錯體制以遏制生態的進一步惡化。這兩方面的合力也許可以保障生態與經濟的雙贏,可以使我們在這個空前的轉型時期實現小我與大我的真正完美交融。
注釋:
①下文凡出現(××章)皆指《老子》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