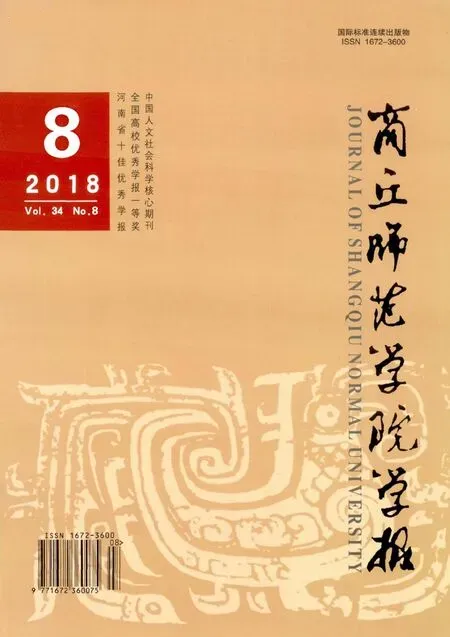清代開封書院刻書探究
劉 耀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明末清初,長期的社會動亂對書院發展損害嚴重,大批書院毀于戰火,院產或為土豪所占,或并于寺僧,以致“講習虛久”[1]卷十四。清朝建立伊始,新貴統治者們認為,書院是“群聚徒黨”之所,有礙地方社會秩序,不利于統治穩定,對書院發展采取抑制政策。順治九年(1652)曾敕令:“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因而起奔競之門,開請托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都察院處分,提學道聽巡按劾奏,游士人等問擬解發。”[2]7994直至康熙年間,社會秩序漸趨穩定,清政府對嚴禁書院諭旨的執行有所放松,各地書院教育才逐漸恢復起來,而書院作為授業育才之所,政府一度鼓勵興辦并提供經費。省會書院,皆籍于禮部;府、州、縣書院,皆申報其管官查覆,各級書院均受學政考查。學子入院所習,多為“四書”八股文之類,因此,書院也就像府、州、縣學那樣成為科舉的預備場所,為國家培養人才。
一、書院發展概況
同全國書院發展形勢相一致,清代開封書院也分為恢復—發展—昌盛—衰落幾個階段。“自宋以降,歷代都很重視對前一代書院加以接管和重建,清初也是如此。”[3]140清順治十二年(1655),提學使張天值、知府朱之瑤將游梁書院改建于開封府儒學明倫堂之后。康熙二十年(1673),河南省城開封重建,巡撫佟鳳彩在新城西北隅恢復重建了大梁書院,占田約2000畝。時任河南提督學政的蔣伊也十分關心大梁書院的教育,不僅親臨書院講授經史,開一省學政主講省級書院的先例,還注重聘請著名學者前來授學,諸如張沐、耿介都有在此授業經歷。康熙二十五年(1686),提學蔣伊又在提學署之南重建書院,并在講堂祀孟子、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巡撫顧汧、布政使李國亮、提學陳義暉等捐造齋舍30余楹,又設雜役2名以備灑掃,并在正殿懸康熙帝御書“昌明仁義”匾額。康熙三十五年(1696),河南巡撫李國亮又把開封城州橋以西古汴水經行處(今開封市政協大院附近)劃歸大梁書院,規制宏備,雅成大觀。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皇帝親賜“兩河文教”匾額,懸掛講堂。乾隆三年(1738),巡撫尹會一懸“王道為昭”匾額于講堂。
隨著社會日趨穩定,統治經驗不斷豐富的清廷統治者為進一步拉攏、限制漢族士大夫,滿足朝野上下對恢復書院的要求,對地方書院發展采取積極鼓動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曾諭令各督撫在省會設立書院,并撥專款資助[4]285。
為響應清世宗諭旨,雍正十一年(1733),河南督撫決定大力整頓、擴建原開封大梁書院,并延請名者講學,招錄中原各地優秀生員肄業其中。此時的大梁書院正式成為河南省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5]61。建成后的書院擁有齋舍數百間,院內建有藏書樓、講堂、先賢祠等,院長由督撫聘任,任期6年。乾隆年間的大梁書院,教學仍堅持以“六經”為本,以理學為宗,教育院生崇尚程朱,沿用孫奇逢、張伯行、冉覲祖教法,以治“四書”“五經”為主[5]61,從而開啟了書院官學化的進程。“這一時期,官府通過直接撥充經費和聘任山長以控制書院的教育方向,為清代書院官學化奠定了基礎。”[3]144此時期,河南所建書院達72所[6]174之多,其中開封建有5所①。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全盛時期,至嘉慶—咸豐年間,清王朝專制統治開始衰落。受此影響,清代書院呈現出一個全新的局面:一方面,學術思想活躍,漢學思潮復興,“通經致用”思想泛起,傳統理學思想受到沖擊;另一方面,書院不可避免地分化成三種類型,即講授漢學、博習經史詞章為主的書院,講授程朱理學的書院和提倡“通經致用”的經文學派主辦的書院[6]202。以大梁書院為主要代表的清代開封書院深受阮元思想影響,逐漸由“推崇理學向講授漢學、博習經史詞章的考據訓詁學方向發展”[3]145。
從嘉慶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河南共創建書院24所[3]146,其中開封4所②。
步入清末的同、光時期,社會矛盾尖銳,內憂外患,政局動蕩不安,清代書院進入最后衰落階段。“在最高統治者的提倡下,各地書院雖然一度復興,但是隨著封建統治的沒落,經過千年之久的發展之后,中國古代書院走完了它的最后歷程。”[6]235
從全國范圍來看,同、光時期的中國書院發展狀況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在書院治學風氣方面,漢宋漸趨合流;二是在書院教學目的方面,仍然為封建王朝科舉考試的附庸。與此同時,八旗子弟書院的數量有所增加,西方傳教士借助書院傳播西學亦開始興起。具體到清代開封書院,清末的開封書院教育隨著世道日益沒落,書院教育內容陳舊、管理方法落后,書院內部腐敗不堪。官員把控書院經營,力圖使書院官學化是導致清末書院急劇沒落的關鍵因素。官員直接插手書院先生的遴選,甚至操縱院長的聘請,嚴重破壞了書院的規章制度,影響了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早在乾隆時期,書院院長聘任就已經出現“徇情延請,有名無實”[7]卷395禮部的情況,后世更為嚴重。清代開封大梁書院,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錢儀吉辭職后,聲望也日漸衰落下來。“清末的50余年間,歷任院長多為督撫直系,很少有真才實學者。院生中有所建樹的也僅周星譽一人而已。”[5]71從同治元年(1862)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開封地區修復和新建的書院有6所③。
二、書院刻書成果
據史料記載,清代開封書院刻書數量相當豐富,但受后世種種原因影響,書單保存下來的很少,現據現存史料記載和學者研究成果將清代開封書院主要刻書成果匯總如下(見表1):

表1 清代開封書院主要刻書成果匯總表

續表
中國古代書院是以藏書為基礎,教書育才兼顧學術研究為目的,以為統治階級服務為根本的活動場所。在自由講學、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書院,主教者多以其研究所得傳授生徒。早在宋代,伴隨雕版印刷業的盛行,書院刻書事業以滿足教學和研究為要務。“書院刻書既可以反映書院的教學水平與研究成果,同時又能豐富教學內容,傳遞新的學術信息,活躍學術氛圍,促進整個書院治學水平的提高。”[8]361
由其性質決定,書院刻書與政府官刻和私家刻書相比,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其專門特色:“有刻書內容的廣泛性,包括有經、史、子、集、叢諸部,又有較強的針對性,即很少刊刻御纂制書,也幾乎沒有面向民間的農桑卜算、陰陽雜家、啟蒙讀物以及戲曲、小說類的文藝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學術性著作,尤其是看重師承學派,講求自成一家之言。”[9]明末清初著名史學家顧炎武認為,書院刻書優良且特色鮮明,在刻書方面具有其獨特優勢:“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所事,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不貯官而易刊行,三也。”[10]798
為更好地開展書院教學、科研工作,清代開封書院收藏并刊刻了眾多書籍,所刊書籍種類繁多,特色鮮明。就其內容和形式而言,可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書院學規、章程
教書育才是書院創辦的首要任務。為方便教學管理,眾多書院在建立之初借鑒前代書院章程,展開自己的書院學規制定。如大梁書院,不僅制定有嚴格細致的學約、院規,還“刊刻宋朱子熹《白鹿洞規條》及元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于講齋”[11],遵照所刻章程進行相應院生教學管理工作。乾隆年間,桑調元制定的《大梁書院學規》中明確強調院生注重“文行合一”,提出“顧千言萬語,只使收已放之心,約之人身,以為向上之尋,斯下學上達之功見。倘文與行二之,則全無一是。幸而軌轍求合,抑猶虞其涂澤為之,則根已全虛,雖自詭文之淹通、行之魁特,終其身無分毫之實獲,為尤可哀也”[12]158。
彝山書院是道光年間建于開封的知名書院。因開封府大梁書院兼收生員、童生,弊病甚多,堅持“念培養英才之道自成童使”[13]164的原則,特建此院專課童生,并設單獨專用考棚,以除試課抄襲頂替的弊端。“彝山書院歸開封府管轄,到此肄業的必須是童生,經過甄別考試,合格者方可入院學習。”[14]199書院院長史致昌在書院任職前后共7年之久,嚴格制定書院章程,刻印書院課藝。
明道書院是清代開封書院中地位僅次于大梁書院的省屬書院,于光緒年間恢復重建后,歸河南學政長期直接管理,制定有嚴格規范的書院章程,是為清代開封乃至清代河南全省書院管理典范。書院堅持“志正學、養正性、明正理、修正行、充正道、綿正傳”,要求院生“敬身、敬事”[15]學規、仁民和愛物。書院規定,“每月發給正課生膏火銀4兩,附課生減半;學子均需住齋學習,黎明即擊板起床,直至二更擊板方可就寢;讀書須是《孝經》《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及一些先儒名臣集,還有史鑒、掌故之書;要求學子保持做日記的習慣,內容包含自己言行,所學書籍及其體會,半月總結一次;每月朔、望日上午會講,由山長登講,下午率諸生習禮等”[16]。
(二)書院教輔性用書
與同時期相關地方書院一樣,清代開封書院的授課方式也采取院生自修為主,教員教授為輔,同院生相互討論、集眾講解相結合的傳統教學模式,要求院生讀書堅持“以經書為根底,以史鑒為作用”[17]。
鑒于清代開封主講書院的先生多為博學之士,為便于教學工作的展開,書院經常為院生指定刊刻教材和相關教輔材料。如大梁書院“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勵諸生學輯賦選評注,刊劉念臺《人譜》。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注》,頒發書院諸生”[11]。此外,教輔閱讀書籍的刊刻也是提升書院教育質量的關鍵。為滿足師生求知需求,大梁書院建立獨有的藏書樓,刊刻了諸如《經苑》《十一經音訓》等眾多著名的叢書和名著。
明道書院在其制定的《章程十條》中規定院生在院學習期間,除必學典籍外,還專門指定院生閱讀諸如《近思錄》《先正學規》《呻吟語》《國朝中州明賢集》等書籍,以擴充知識儲備。在黃曙軒主持明道書院期間,不僅將清朝著名理學家張伯行的著作列入書院平時課考范疇,還“刻印出版《張清恪公讀書日程》,發給院生人手一冊,作為平時功課和月考的重要指南”[18]21。
(三)書院內部師生研究成果和讀書札記
不同于官學機構,書院因其特殊的邊緣化屬性而具有較自由的學術氛圍,成為眾多名儒大賢隱退自由講學的理想場所。此外,書院匯集和招錄了眾多優秀學者和生員,自出現以來一直是地區講學中心,更是區域內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基地,清代的開封書院也不例外。
清代開封書院的歷任院長、主講者均經歷過嚴格選拔聘任,無論是大梁書院的張沐、錢儀吉、顧璜,還是彝山書院的史致昌或是明道書院的黃曙軒等,均為譽滿全國的碩儒。尤其錢儀吉,因深受阮元漢學思想的影響,在主持大梁書院期間銳意書院教學管理改革,主張解放院生思維。這些碩儒在主持書院期間,往往十分關注書院院生的學術研究,鼓勵院生日常札記寫作,并選擇書院考試中試題佳作匯集刊印,傳閱諸生。諸如彝山書院,“余不敏,從恭勤,后來守是邦,深恐無學為諸生表率,幸主教者為宛平史孝廉叔平,勤于訓迪。就其質之淺深,為課之異同,必各盡其所能而后止,士亦靡然從風。未一年,而文章詞賦皆秩然有軌范,乃擇其優,刊而行之,使才之既優者有所鼓舞,以純其業;且使才之未逮者有所激勵,以底于成焉”[11]。
道光二十五年(1845),大梁書院開雕院長錢儀吉帶領書院生徒主編《大梁書院經解》(原名《經苑》)。適時,錢儀吉主講大梁書院,把學習經書作為生徒每天的必修課。書院藏書因一次水災而多丟失,錢儀吉很是擔憂,乃思集刊書,以“廣六藝之教”[19]序,輯得清代以前說經著作41種,親為校刊[20]299。同治年間,大梁書院也曾集中刊印耿介的《大梁書院講學稿存》和孫奇逢的《夏峰先生集(附補遺)》16卷。
三、書院刻書條件
作為培養知識分子的教育機構,清代開封書院在進行書院教育的同時又兼刻眾多書籍,成為清代開封重要的刻書場所。清代開封書院所刻圖書內容豐富,校勘精良,在開本、裝幀上也相當考究。那么,什么原因支撐了清代開封書院刻書多且優良呢?究其緣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充足的書院經費
書院經費是書院辦學所需財力物力,是維持書院教學活動正常運轉的必要支柱,同時也是書院進行刻書的資金保障。“縱觀清代河南的書院發展,盡管省、道、府、州、縣各級都辦有書院,且各具規模,但真正能從事刻書活動的并非很多。”[11]清代開封書院規模有大有小,能力參差不齊,具備刻書能力的主要有大梁書院、明道書院和彝山書院等幾所。清代開封書院的經費來源不盡相同,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
第一,政府專項撥款支持。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頒布諭旨鼓勵地方督撫興建省會書院,并“賜帑金一千兩”[4]285用以支持省會大梁書院建設;光緒《清會典》載:自乾隆六十年(1796)起,省督撫每年撥給“河南大梁書院二千九佰七十三兩”[11],如若不夠使用,還可從省存銀糧中補給;道光十年(1830)《彝山書院經費章程(二)》載:“開封府十五屬捐款每年共銀五百一十八兩,由各屬徑解府庫”[13]168;道光二十年(1840),河南學使邵松年奏請朝廷允許“官員捐款,及由大梁書院每年撥銀600兩,再由各州縣派解銀1447兩作為明道書院的辦院經費”[11]。必要的政府撥款保證了清代開封書院的資金來源,有利于書院的長足發展。
第二,學田收入和個人捐贈。固定的學田田租是清代開封書院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政府財政撥給和富戶捐贈亦補充了清代開封書院經費。“清初的大梁書院即擁有學田十七頃,游梁書院也擁有五頃。”[11]光緒二十二年(1842),祥符縣為明道書院“捐置香火地十二畝”[21]344;乾隆四年(1739),知縣張叔載“又撥河灘地5頃以供公費”[22]35,其中十分之七供游梁書院奉祠生焚香供祭之用,十分之三貯存備修繕;道光年間,蘇源生編成《國朝中州文征》,開封知府鄒鐘泉“聞之甚為嘉予,遂捐俸倡始開雕,嗣后諸先生及同人輩亦各以資來助刊刻”[23]卷首。
個人對書院的額外捐贈也是清代開封書院經費的重要來源。康熙三十三年(1694),巡撫顧汧、布政使李國亮等“捐造齋舍30余楹。乾隆四年(1739),糧驛道黃叔敬捐修正殿5楹,東西廡各5楹及房舍、門宇、坊表、墻垣”[22]35;同治十一年(1872年),巡撫李鶴年等“捐銀數千金修繕彝山書院山長居宅,齋房11間,另增建考棚9間,置備各種器具,書院逐漸恢復舊觀。”[14]199
值得提及的是,清朝末年開封《明道書院學規章程》中明確規定,院生有回報支持書院建設的義務,并詳細規定書院肄業從仕院生從督撫到教授、學正不同職務的具體認捐數額。如示:
凡由書院肄業諸生出仕者,通知續捐,以備擴充添修及后來之用。
大學士、尚書,每任捐銀一千兩;總憲、侍郎,每任捐銀五百兩;寺卿、御史、給事中,每任捐銀二百兩;翰林、郎中、員外主事,每任捐銀一百兩。
督撫每任捐銀一千兩;學政每任捐銀五百兩;藩司捐銀八百兩;臬道每任捐銀四百兩;知府、直隸州,每任捐銀三百兩;知州、知縣每任捐銀二百兩;教職每任捐銀四十兩。
以上各款,到任限六個月內送院,如遲由提調專差走取。[5]106
在明道書院帶動下,清代河南省各級官員逐漸形成在任內定額捐款資助開封書院諸如大梁書院、明道書院等的制度,這也為清代開封書院正常運轉提供了重要支撐。
(二)豐富的書院藏書
藏書與刻書是書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歷代書院的優良傳統,較有成就的書院總脫離不了這兩項事業。書院是古代學者進行學問研究、人才培養和知識傳授的場所,故而對圖書有著特殊需求。鑒于此,中國歷代書院,特別是實力雄厚的知名書院,大都建有獨立的藏書樓,以收藏豐富典籍。清代的開封書院亦不例外,規模或大或小,均重視書院的藏書,其中以大梁書院和明道書院最為代表。
清代的大梁書院很早就重建了藏書樓。康熙二十年(1681),河南巡撫佟鳳彩重建時就在堂后建有書樓和書舍。在最為鼎盛時期,大梁書院修建“有4座藏書樓。均高3層,建筑面積達6000平方米”[24]87。書院藏書“據傳統的經、史、子、集分編,但惟近刻叢書多有單行本,不見經之本,而品類雜糅,不得不于四部外另別一部”[25]。清代大梁書院的藏書,至今已不多見,透過《大梁書院藏書總目》[26]可略窺一二。《大梁書院藏書總目》共1卷,分為書序、購書·編目略例、藏書·借閱規則、經費來源和書目5部分,其中書目部分所占篇幅最大。書中記錄圖書當為清朝末年大梁書院的藏書情況。書院藏書總計2304種,其中經書為665種,史書為152種,子書為164種,集書為262種,叢書為1071種。至清宣統元年(1909)二月河南圖書館成立時,藏書僅1600多種、4300卷、40000余冊,所藏圖書大多來源于清代開封大梁書院和明道書院[27]10。
晚清時期,伴隨 “西學東漸”思潮的迅速擴散,大梁書院順應時勢逐步引入“西學”課程,書院藏書內容發生巨大變化。相對于之前拒收醫卜、星象及一切技藝之書,清末的“大梁書院廣泛收藏包括數學、地理、外國軍政、商務、鐵路、工程、化學、物理、煤礦、天文、植物、英語等方面的書籍”[28]。這些圖書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方面。為滿足書院師生讀書需求,大梁書院還購置了部分書籍。購書堅持不求其全,只求實用原則,“先擇其最有用者購之”[29],“所購各書,大半官局新印,紙質堅韌,可以經久”[29]。
明道書院也以藏書、刻書而聞名,《明道書院志》[15]是我們了解開封明道書院藏書情況的現存志書。該志成書于清光緒年間,共分兩冊10卷,“卷一為沿革,卷二為祠祀,卷三為碑記,卷四為奏牘,卷五為學規、學程,卷六為章程,卷七為修脯,卷八為官師,卷九為選舉,卷十為藝文和藏書目錄”[30]。據《明道書院章程》記載,明道書院的經費較為闊綽,時有節余,“每歲如有盈余,由首府核明,或存儲,或購買書籍,隨時酌辦”[31]。在呂永輝的努力下,清末書院藏書數量相當可觀,不僅“有汲古閣版本《十三經注疏》三百八十六卷、《正義堂叢書》四百二十七卷、《欽定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五十九卷,另有不少珍本、稀本和刻板”[31]。
在書院藏書管理方面,大梁書院和明道書院也有其獨到之處,二者不僅制定有完善的圖書管理、借閱規則,還配備專業圖書管理人員進行經管。大梁書院規定,圖書須集中存放于“西偏精舍”,“設司書吏一人,專管借閱,隨時檢查書的完整情況,及時呈報;設司閽役一名,典守鎖匙”[29],院生每次取書限制為一種且必須在五卷以內,如有損壞還須賠償等。在館藏書籍管理上,明道書院由兩齋長共同負責,如有書院肄業生借閱圖書,則須單獨記錄在冊。同大梁書院規定每名院生借書只限一種相比,明道書院允許每次不超過兩本,需調換時可隨時聯系齋長進行更換。
(三)以山長為首的書院優秀校勘團隊
除充足經費和豐富藏書之外,知識淵博的書院山長的參與也是清代開封書院持有大量優秀刻書的重要因素。清代開封書院山長均為社會名儒,平時著書立說者不在少數,諸如大梁書院的張沐、錢儀吉、吳泰來,彝山書院的史致昌和明道書院黃曙軒等都是譽滿全國的學者,他們希望借助于書院進行學術傳播。為豐富書庫,他們繼承前輩遺風,鼓勵師生著述并擇優刊印。加之沒有刻書經費的擔憂和時間限制,他們可以不計成本地從容刻書。書院刻書一方面十分在意底本選擇且勤于校勘,另一方面又注重書籍紙張、款式和包裝,為后世遺留不少精良本。
清代書院嚴格的山長遴選條件,保證了清代開封大梁書院、明道書院、游梁書院的學術權威性。省城書院以其充足經費和政府的特殊照顧而獲得優先發展權,并在社會中產生巨大影響力,不僅成為各下轄地區書院的效仿對象,還吸引了眾多高水平學者。“高水平學者主掌書院是省城書院維持其高踞本省教學和學術研究中心地位的可靠保證。”[32]同時,院生須經嚴格篩選方可入學,省城書院因此集全省優質生源于一身。
四、清代開封書院刻書的影響及歷史貢獻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王朝,統治者為維護政權、鞏固地位,在大搞文字獄的同時,也主張文治,大興修典整籍,以揚太平。宣揚正統論思想的儒家典籍被大肆推崇,成為官方支持的刻印對象。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清代開封書院多以儒家經典學說為藍本,刻印帝王學說,因其相對特殊的獨立性,亦具備鮮明的時代、地域特色。
(一)傳承儒學文化,推動中原教育發展
儒學文化,是中國優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清代開封書院,不僅在教學中宣揚傳統儒學思想,還刊刻出眾多優秀儒家典籍。諸如道光年間,大梁書院刊刻楊國楨的《易經音訓》;同治七年(1868),大梁書院刊刻李如圭的《儀禮集解》《禮儀釋宮》、王安石的《周官新義》、司馬光的《溫公易說》、黃澤的《易學濫觴》、呂維祺的《孝經本義》《孝經或問》、錢儀吉的《新鐫經苑》;光緒七年(1881),大梁書局刊刻冉覲祖的《五經詳說》《四書玩注詳說》等。其中,尤以《周官新義》《溫公易說》《易學濫觴》最為代表。
《周官新義》原名《周禮義》,又稱《新經周禮義》《周禮新義》《周禮新經義》,為宋代王安石所著,是反映宋代政治經濟的重要著作。與《詩義》《書義》合稱《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新學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們的頒行標志著新學取得了官方統治地位。而王安石對儒家經典的新解釋及其相關著作,也被后世稱為“新學”“荊公新學”。
《溫公易說》又名《易說》,為北宋司馬光所著,全書共6卷,書成于洛陽。該書是從史學角度詮釋《易經》的優秀著作。
《易學濫觴》共1卷,元代黃澤著,為研究《周易》的名作。以《易學濫觴》為代表的黃澤易學,重視象學,精研經傳與前人注疏,于有疑義處深入思考,力求返本探源,講求《易》之古義,其經學于今仍有重要啟迪意義。漢唐易學屬于玄學,重象數之學,至宋代大儒開始以儒家義理代替玄學,注重圖書與占筮,以恢復古《易》面貌。雖然在辭、變、占方面力圖恢復,實際上卻也使“象”變成了《河圖》《洛書》之“象”,棄傳統象說于不顧。黃澤易學則結合宋代《河圖》《洛書》之學對傳統象數易學進行了發明,“盡破傳注之穿鑿”,使傳統象數易學得到長足發展,對明代后學“覺宋易不合,去而為漢易”產生重要影響。
光緒十一年(1885),明道書院補刊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該書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線貫通學術思想的專著,它總結和記述明代漢族學術思想傳統發展及演變過程。此書以王守仁心學發端、發展為主線,依據明代學者文集語錄劃分諸家學術思想宗旨與流派,共立19個學案,記述208名學者的主要學術觀點,開創了我國史學史上學案史書新題材。
此外,作為省會城市的教育機構,開封書院成為河南地方官府傳播漢學的媒介。嘉慶年間,以阮元為代表的漢學派崛起,推崇漢儒樸實學風,反對盲目崇拜程、朱“空談理性”。以開封大梁書院為中心的中原學者受到漢學派影響,改革陳舊教學方法,逐步形成崇尚漢學的特色,并培養出諸如朱士階、周之琦、常茂徠等多名本地學者。道光五年(1825),河南巡撫程祖洛將大梁書院遷往行宮東路北,學院規模進一步擴大。道光十六年(1836),錢儀吉受聘主講大梁書院。作為阮元高足,錢儀吉“治學不課八股文,而以經史之學為主,并及小學、天文、地理、算學等學科,為書院開創了一種新的學風。對河南各級書院的教學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培養出大批學有專長的人才”[5]63。其主要措施有:
第一,改革授課內容。面對書院固守八股文格式的現狀,錢儀吉主張推行漢儒樸實之學風,課試文章做到“理明詞達”即可,不必墨守成規。
第二,提倡經世致用思想。蘇源生在《記過齋文稿·錢星湖先生遺事》載:“錢先生每半月舉行一次課試,命題以經史之學為主,并及小學、天文、地理、算學、歷律、水利、農林諸學。他在批閱完院生試卷后,還親自主持講會,集體討論書卷,并鼓勵院生向他問難,而后,再逐一評定院生的成績,分為甲、乙兩等。”[33]對傳統命題方法和判卷思路的改革可有效解放院生思想,打破傳統思維模式,培養院生經世致用的理念。
第三,擴大招生名額。錢儀吉在正額生外,加收備錄生和附額院生[33]。正額外院生需兩位名士介紹擔保方可參加書院面試,通過后即入院學習。僅道光二十五年(1845),錢儀吉就一次性收錄備額、附額院生17名[3]161。
政府借助錢儀吉在大梁書院進行的改革,不僅直接實現了對大梁書院的優化,開創書院教育新學風,吸引眾多飽讀詩書之士齊聚開封,更是推廣了漢學,為清代開封文人著述及書院和私家刻書注入一股新鮮活力,對清代河南全省的書院教育產生深遠影響。中原學術由傳統單一的宋明理學主宰天下的局面逐漸被打破,漢學、考據學、金石之學開始受到人們關注。改革期間,大梁書院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部分日后于各地府、州、縣擔任院長、教諭、訓導等職務。他們紛紛效法大梁書院進行革新,在將大梁書院改革影響擴大至全省范圍的同時,也推動了整個河南教育的全面發展。
(二)帶動學術交流,促進理學傳播
清順治至康熙年間,是清代開封書院迅速發展時期,也是洛學復興運動發展的恢宏階段。這一階段的河南書院“以開封府的游梁書院和大梁書院為中心,北有百泉書院、南有南陽書院、東有朱陽書院、西有嵩陽書院”[34]相為照應,構成河南洛學文化圈。先有夏峰講學于百泉書院,后有張沐受聘于大梁書院,耿介主持嵩陽書院,而張沐、耿介、湯斌等都曾求學于百泉書院。“皇朝云雷之初,孫鐘元自燕來,徙講席于邵、姚之故址,一時負笈來學者甚眾……兩河文教聿興,如吾里湯潛庵司空、吾師徐我庵處土、上蔡張仲誠、登封耿介石……無不實其歸而樹之風,自是程氏所傳之道復大明于天中。”[34]他們依托書院進行互動講學,來往甚密。清代的大梁書院取代嵩陽書院,成為河南文教中心。書院注重刊刻院生研究成果,注重增強學生自身閱讀學習能力,為書院優良學術氛圍的形成打下堅實基礎。書院山長在教授生徒的同時,也不停地進行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形成 “講學內容——研究成果——講學內容”[11]的良性循環模式,以更新學術思想,傳道窮經。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于開封刊刻的《理學宗傳》是較早且極具影響力的一部中原理學著作。作者孫奇逢是明清之際河南著名理學家,為明清理學在中原地區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他推崇程朱陸王,貶低佛教。主張“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認為王守仁的“無善無惡心之體”與禪宗不同,且不與孟子的性善“相悖”。該書建構了一個自周子以下平列程、朱、陸、王十一子為“正宗”的儒學道統體系,并對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歷史線索作了論述。他認為,整個歷史過程是一個“元、亨、利、貞”的大圓圈,其間又有上古、中古、近古三個小圓圈。此書編成后,不僅受到其時學術界的廣泛贊譽,也為后人所稱頌,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宋明學術的重要參考資料。
道光年間,江永所撰《近思錄集注》為大梁書院刊刻的另一重要理學著作。該書由宋朱熹、呂祖謙合撰,主要依據二人理學思想體系進行結構編排,在我國理學史上占據突出地位,也為儒家道統思想傳承發揮重要作用。
諸多優秀著作的刊刻,不僅出色地傳承了中原學術,也無形中推動清代河南書院士人群體教育理念、教學方式的轉變。如大梁書院,“清初學者張沐講學其中,于是程朱理學風行。到晚清時期,漢學影響不斷擴大,錢儀吉游學于阮元,后講學于大梁書院,教授義理考據之學,并在大梁書院刊刻《經苑》二百五十四卷,由此開啟了大梁書院由對程朱理學的崇尚到經史考證之學的轉變”[35]。河南理學之風更為興盛。
(三)記述地方文化,保存中原記憶
清代開封書院刻書,刊刻了大量富有中原文學特色的著作,在整理地方文獻、保存中原記憶方面作用顯著,是研究清代開封書院教育理念的最好佐證。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彝山書院刊清史致昌編《彝山書院志》1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大梁書院刊《夏峰先生集》14卷及《補遺》2卷;同治五年(1866),正誼書院刊清張伯行撰《伊洛淵源續錄》20卷;光緒十九年(1893),明道書院刊清黃舒昺選輯《中州明賢集》10卷;光緒二十年(1894),明道書院刊清呂永輝編《明道書院志》10卷;光緒二十四年(1898),大梁書院刊清顧璜編《大梁書院藏書目錄》等。
在書院文化影響下,眾多文人借助開封書院進行著述刻書。作為河南地區文化名人學者,他們積極參編地方志,使得大量文獻通過刊刻得以保存和流傳。道光二十五年(1845),錢儀吉重刊《夏峰先生集》于大梁書院。《夏峰先生集》共16卷,是孫奇逢的詩文匯集,也是后世研究孫奇逢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明道書院刊刻《明道書院志》以及大梁書院刊刻耿介所著《大梁書院講學稿存》和賀儒翰所著《大梁書院崇祀考》,書中詳細記載有書院發展演變歷程和教學內容及講學活動,較全面地保存了諸多書院資料。
道光年間,大梁書院刊刻晚明劉宗周的《人譜》。這部優秀著作內容匯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編輯,每篇前有總記,后列條目,間附論斷,是教育時人安身立命的一本普及讀物,對教化民風意義重大。作為晚明心學代表人物,劉宗周的思想宗旨是在心學舊基上重新架設一個“剛刻嚴毅”的人學價值體系,借此矯正陽明后學過于強調“良知現成”而輕忽理性限制和實修工夫之理論偏頗。《人譜》通篇都在講做人的道理和工夫,認為人的道德性理呈現于人的經驗意識和日用常行中,人們可以調節自身活動,實現人的本性德體有意識地向自覺德體轉化。
同治七年(1868),大梁書院刊刻《瑟譜》,為宋末元初文人熊朋來編訂的《詩經》樂譜,全書共6卷。內容包括介紹瑟的形制及演奏方法,歌唱《詩經》的舊譜12首和原創新譜20首以及孔廟祭祀音樂的樂譜等,大梁書院本意用《瑟譜》做該院音樂讀本。其在實現本院院生全面發展目標的同時,也為后世研究清代開封書院教育模式提供了珍貴材料。
五、結語
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和學術研究機構,書院先后存世一千余年,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存在彌補了中國古代官學的不足,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既對中國教育發展和學術繁榮作出重要貢獻,又可以增加一個地區的文化積累,積淀城市內涵,是地區文化發展的重要表征。清代開封書院在政府支持鼓勵下迅速復興,廣拓藏書來源,建立完善書院管理體制,謀求積極發展,不僅為政府培養出眾多優秀人才,而且廣納優秀文人學者刊刻眾多古代典籍和地方志著作,進一步成為中原理學交流中心。雖然清代開封書院伴隨著清末中原地區的衰落而漸趨消亡,其刻書在全國范圍內成就亦并不突出,但其作為清代開封重要文化支撐,對推動中原文化教育、普及地方文化和保留中原文脈也作出了不朽貢獻。
注釋:
①5所書院分別為蘭陽縣“豹陵書院”、杞縣“志學書院”“東安書院”、開封縣“志伊書院”、通許縣“育英書院”。
②4所書院依次為尉氏縣“蓮池書院”、開封府城“彝山書院”、開封縣“萃野書院”、蘭封縣“蔚文書院”。
③6所書院依次為考城縣“生花書院”、開封府城“游梁書院”“信陵書院”“瓣香書院”“明道書院”“培文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