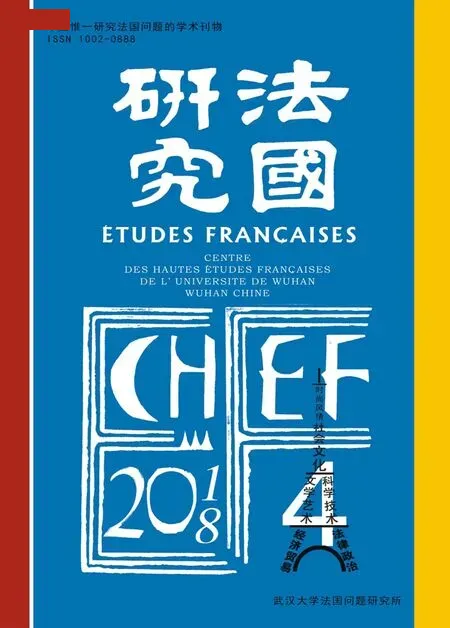莫迪亞諾小說中的永恒輪回
周婷 楊蕊
?
莫迪亞諾小說中的永恒輪回
周婷 楊蕊
武漢大學外國語學院
從作品之間高度相似與重復到多次提及的尼采永恒輪回哲學、從圓形的循環結構到獨特的記憶藝術,永恒輪回一直是莫迪亞諾筆下不可忽略的重要主題。本文將以永恒輪回為重要切入點,梳理莫迪亞諾小說中的永恒輪回意象,探索莫式永恒輪回的內涵與獨特性,解讀“生活就是永無休止的輪回”這句悲嘆。
莫迪亞諾 永恒輪回 圓形結構 尋根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小說作品作品風格獨特,從早期的《星形廣場》到中后期的《青春咖啡館》等代表作,其筆下的人物塑造、故事情節、敘述手法等都體現出強烈的“相似性”。其中,“輪回”作為參與構建文本意象的元素之一與小說中所貫穿的“似曾相識”性(déjà-vu)相契相和。“二十年前我就是穿著那種服裝死掉的。”①在其后期作品中,“輪回”的痕跡愈加明顯。在《地平線》一書中,作者甚至直接使用“永恒輪回”一詞,并同時提及尼采的永恒輪回說。“生活即是永無休止的輪回”出現在莫迪亞諾的多部小說作品中。然而目前國內外卻鮮有研究來深入探討“輪回”在莫迪亞諾小說中出現的意義。鑒于作家對人類整體命運的困境和悲劇性的深切關注、其作品中虛實結合和回憶敘事的寫作手法、非線性的自然空間都與“輪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本文將以“輪回”為主題,嘗試對莫迪亞諾的小說進行解讀,是對莫迪亞諾作品現有研究的一次補充。我們從莫式“永恒輪回”的定義出發,逐一分析“永恒輪回”在其文本中的具體表現,探索獨特的作品互文性和“圓形循環”敘事結構,試圖從作品內容上和結構上完整地展示作品中“永恒輪回”的各個方面和清晰面貌,進而結合作者的個人經歷和時代背景,深入剖析永恒輪回主題下文本的社會意義和時代特性,挖掘莫式永恒輪回的真正意涵,提供給讀者們一個對莫迪亞諾作品的全新詮釋角度。
一、莫式“永恒輪回”的定義
莫迪亞諾曾多次在他的作品中提及尼采的“永恒輪回”說,“我問他有沒有一本關于‘永恒輪回’的書……最后,他終于找到了一本黑白封面的書:《尼采:永恒輪回哲學》。②”然而,莫式的永恒輪回并不與尼采的永恒輪回說相一致,因為后者包括萬事萬物,毫無例外,強調當下選擇的重量與意義,而文學的創作給予作者極大的自由,他并不需要謹遵某一種哲學學說。在作品中,“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像從前一樣。一樣的白晝,一樣的夜晚,一樣的地點,一樣的邂逅。永恒輪回。”(青春咖啡館:93)。莫式永恒輪回談及的是一種內心的期待,一聲腦海中響起的呼喚。作者對永恒輪回這種描述人類生存狀態的學說非常感興趣,確切的說是對相似性的重復和圓形結構十分著迷,從而借用了尼采學說的循環框架,但并未取其本意。
要理解莫式的“永恒輪回”,首先必須從詞源上追溯其含義。“永恒”()指一種永遠持續的、不變的狀態,“輪回”(retour)則是“回歸、回到出發點”、“重現、再次發生”、“重復、恢復”、“周期性的回歸”等含義,從詞根上來看,前綴多表示一種“回歸到原始狀態”、“回到出發點”或是“某種行為的重復”。總的來說,永恒輪回可以定義為“一種周期性地不斷回歸自身的循環,可以是回到原本的狀態,也可以是某些行為的不斷重復”。以上定義脫離了尼采學說的哲學意義,僅僅通過詞語本身來考察“永恒輪回”的含義,但本質上卻更接近莫迪亞諾作品中的永恒輪回。從敘述內容上看,人物不斷從現實回到過去,或是過去穿越時空隧道浮現于此在的世界,過去和現在的界限模糊,人物經常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后期作品中,人物的行為則朝著未來“輪回”,不斷地逃離過去以獲得一種“新生”。其次敘述手法上看,重復相同的主題,相似的情節,相同的時代背景,每一本書都可以看做是作者的自我虛構作品;作品的開頭與結尾經常形成一個怪圈,人物困在尋根失敗的怪圈中形成圓形敘事結構。綜合看來,莫式永恒輪回不僅是人物生存狀態的展現,同樣也是回憶與現實關系的反映,在作者回憶敘事手法構建的時空下,永恒輪回還帶有一種悲觀主義宿命論的意味。
二、永恒輪回的文本體現
第一,過去的重現與未來的回憶。事物或事件在不同時空以相同或者相似的面貌和方式再次出現、再次發生,是永恒輪回在文學作品中主要表現之一。莫迪亞諾的作品中有兩種的重現方式:過去的重現以及未來的“回憶”。第一種重現的方式通常表現為人物在此在的時空再一次真實地經歷了過去。作品中多重時空經常交織在一起,呈現非線性狀態。人物看似在線性的時空中行走,但是生活卻經常發生某些斷裂,過去突然就與現實相接了。“在三十多年里,人們竭盡全力使自己的生活比早期更平穩、更和諧,卻枉費心機,某個小事故就可能突然把你帶回過去。③”通常這種機制的啟動是由于某個可以連接過去的“小事故”。在《夜半撞車》中,“我”再一次進入警局:“一切都會在囚車和警察局里解決。這早就是命中注定的。再說,在我十七歲那一年,因為我的父親想要擺脫我,人們把我送上警車。……這是我十七歲那年,父親把我交到他手中的同一位局長……生活就是永無休止的輪回。”(夜半撞車:56, 57)警察局再一次出現在“我”的生命中,過去的重現如此明顯以至于“我”直接稱這件事情為“生活永無休止的輪回”的確鑿證據,“命中注定”的宿命感撲面而來。人物總在某些境遇中突然掉入時空的黑洞,過去以真實的面貌募地重現在眼前,與現在相接,形成一個圓形的時空結構。這些境遇通常與作者本人的經歷相關,例如警察局、乙醚、黑狗,當每一次相似事件再一次確實發生,都會觸發過去的回憶,人物再一次體味過去,永恒輪回不止。
未來的“重現”則在后期作品中多有體現,人物仍舊不斷回憶著過去,但表現出對未來更大的期待:它并不是一種與過去的割裂和嶄新的開始,而是對某一段溫情過去的再一次回憶。過去的重現對主人公來說是一種輪回,但明顯人物渴望這種輪回,就像羅蘭在露姬死后的獨白:“那邊,也許就是永恒的輪回。跟以前在賓館前臺拿你的房門鑰匙一樣的手勢。同樣陡峭的樓梯。同樣白色的標著11號的房門。同樣的期待。過后,是同樣的朱唇,同樣的芳香和同樣的如瀑布般傾瀉的秀發。”(青春咖啡館:122)事實上這一切的期許都是虛妄,露姬的存在是羅蘭青年生活中唯一的溫暖。羅蘭只有將過去投射到未來,期待露姬的“復活”,渴望永恒輪回,再次體味過去與露姬在一起漫步街頭的時光。永恒輪回的渴望非常強烈,甚至可以說是人物想要進入一個輪回的世界,試圖逃脫心愛的人死亡這一殘酷現實。
這兩種重現雖然都是過去的重現,但前者是由于現在的真實境遇啟動了記憶機制而使人物回到過去,仿佛一次輪回,是時間線往后的一次循環。而對未來的“回憶”則是對過去在未來再一次發生的期待,是時間線往前的一次循環。
第二,尋找過去與否定過去。作品中人物基本處于以下兩種狀態:對自我身份的認知處于空白狀態因此尋找過去來自我定位,或者渴望追尋新的身份來掩蓋過去。總之,此在時空下他們是“無國籍者”、“大都市的無名者”,不論哪種獲得身份的方式,對人物來說都是一種重生。兩種方式都有重復性,人物并不是一次性完成了身份的獲得,而是在不同的身份中不斷尋找和放棄,每一次尋找或逃離都是一次新的輪回,但每一次都沒有找到最終的確認無疑的身份,人物在永恒輪回中持續尋找。
縈繞在莫迪亞諾心中的永恒問題,就是追尋人失去的身份,在《暗店街》中,他讓居伊循著蛛絲馬跡,穿越時間,像拼碎片一樣拼湊自己的一生,卻又始終無法抵達“我”之所在。為什么要追憶過去的時光?因為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未來,而是過去”。如果過去不被記住,那存在又該如何被證明呢?我們最終不就成了“海灘人”,腳印只能保留幾秒鐘,離開之后再也不會有人記起。身份空白的無所適從和遺忘造成的記憶黑洞使人物不斷回到過去,每一次在過去的記憶中游蕩,“我”似乎都確信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獲得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完成了一次重生。然而記憶中的過去都帶著朦朧的迷霧,遺忘和時間帶來的記憶黑洞讓新生的“我”充滿不安,“我”試圖通過篡改記憶安慰自己,像是居伊卻在現實生活不斷被否定,身份又一次被懸置。
另一方面,對于作者來說,過去總是充滿著傷痛與迷惑,父母的無故缺席,猶太身份的尷尬處境,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巴黎,那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在后期作品中,人物轉變了對過去的態度,不再是失憶的人尋找自己的身份,而是主人公有意識地將過去籠罩在遺忘的迷霧當中,希望從過去身份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嶄新的“另一個人”。《地平線》中的瑪格麗特“在生活中是以不規律的跳躍和停止的方式前進,每次都是重新從零開始。于是……她感到自己已活了好幾輩子。④”《青春咖啡館》中露姬是別人給她取的新名字,“可以說,是賦予她第二次生命。”法語,不僅有取名之意,同時有洗禮的含義,即洗去罪惡,潔凈自身從而獲得新生。以忘記過去的方式奔向未來,重生的露姬成為一個沒有過去沒有根的人,生活的意義還是無處可尋。她渴望與過去斷裂,但現在的每一秒都在下一秒成為了過去,而當現在再次成為過去,想要忘記的過去永遠懸置在頭頂,無聲無息地從生活的縫隙中飄散而出,最終將現在吞噬。于是,露姬開始期待又一次的重生,“用劇烈的方式隔斷與日常生活的聯系,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青春咖啡館:104)她被永遠地困在重生的輪回之中。
三、永恒輪回的結構體現
第一,莫式“永恒輪回”體現在結構上的互文性。互文性也被譯為文本間性,由法國后結構主義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用來表示文本的意義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由其他文本所構成,與其他文本相互參照、交互指涉。眾多研究學者中,希利斯?米勒在《小說與重復》中提出了“重復”理論,主要有三大類:一是文本細微處的重復。如:詞語、修辭格等;二是文本中事件或場景的重復;三是文本與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題、動機、人物、事件、場景上的重復⑤。第三種重復已超出單個文本的界限,進入到互文本的廣闊領域中。
縱觀莫迪亞諾的二十余部小說,不僅主題和背景幾乎都是一致的,而且人物、情節和意象都高度重復。《星形廣場》尋找“祖國”,《環城大道》尋找“父親”,《暗店街》尋找“自己”;在同一部作品甚至不同作品中,情節和意象也會重復出現,例如乙醚氣味、警察局、含義不明的正午十二點。此外,當故事永遠發生在巴黎,不同作品之間會交替出現相同的固定點來增加讀者的熟悉感和作品的神秘氣息:報紙、照片、電話薄、街道、建筑。例如在《地平線》中,“她去星形廣場買報,然后返回,一直走到拉佩魯茲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館。”(地平線:83)這樣的描寫讓讀者想到《星形廣場》和《青春咖啡館》,而《青春咖啡館》中也提及“環城大道”等等。好似讀者同人物一起穿梭在不同書本中,走過同一個街道,進入同一家咖啡館。
莫迪亞諾在一次采訪中也曾經說過:“的確,在我的作品中,出現的總是同樣類型的人物,表達的也是同樣類型的主題,但是這類人物和主題的表現不是僅僅通過一個故事或一本容量較大的小說來一次完成的。”正如作家本人所言,不僅是主題上的宏觀重復還是意象上的微觀重復都豐富了單個文本的含義,超越了單個文本的界限……這些重復勢必不斷持續下去,高度的重復讓我們可以將所有的作品看做一次次輪回,作品之間相互補充,相互闡釋,相互構成完整的小說世界,形成一種“文學意義上的輪回⑥”。
其次,互文性也表現為作者與筆下人物之間的關系。莫迪亞諾的寫作藝術特色之一便是自我虛構,結合真實與虛幻。在分析作品中高度重復的人物性格和重要情節時,我們不能忽略作者本人與人物的關系——人物、主題和情節的設置都與作者的真實經歷和記憶緊密相關。莫迪亞諾每一本小說的主角都是年輕時代的巴黎男青年,父親總是缺席,而他總是追尋著一個神秘女子,最后女子突然消失,不留蹤跡。他們與莫迪亞諾的年輕時代極其相似,貧窮又孤獨,游蕩在巴黎街道和一個個咖啡廳、酒吧中。每一本小說的創作,作者都不可避免地將自我經歷糅合在虛構的世界當中,人物在相似的情景中再次啟程,沒有父親,依戀母親,作者迷茫的青年時代又一次再現。莫迪亞諾曾說:“像所有沒有故土亦沒有根的人們一樣,我不停地思索我的史前。”作者如何尋找他的史前?作為作家,他通過不斷書寫與之相似的人物,通過小說不斷找回歷史。被重復書寫的每一個主角都是作者青年記憶的折射,是他的“分身”。每一次書寫,都是作者回到過去的再一次輪回,每一次創作,也是作者再次改寫“史前”的嘗試。
第二,圓形敘事結構也是永恒輪回的另一點體現。若以形象化的方式來表現,那永恒輪回自然具現成一個無限生成的圓,所有的圓都是從一點出發,逐漸遠離,但又試圖不斷接近出發點。每一次的遠離和回歸都是一次新的輪回。原點存在的,被追尋著,但永不能被“完全復位”。每一次企圖復歸原點,每一次都將與最初的原點有所差別,而這一差別也將推動下一次的回歸,輪回永不停止。圓必然是理解莫迪亞諾作品中非常關鍵的要素,他的作品大多在敘事結構上表現出一種回歸和循環,《環城大道》中找尋到的父親最終“得而復失”,《星形廣場》中“我”從巴黎出走最終回到巴黎等等。
作品中的圓形結構首先表現在人物幾乎全部陷入尋根失敗的怪圈——法國籍猶太貴族青年,無論何種身份都難以讓他真正平靜地接受命運,身為法國人,卻希望尋找猶太人生存的意義,作為猶太人,卻難以擁有法國的歷史和血統。他一路都在迷失,從法國追尋到以色列,最終他被處死在星形廣場。主人公在多重身份中幾度來回,希望追尋最真實可靠的身份,得到內心的安寧,卻因為痛苦的歷史失去了人生的基點,故事在巴黎開始也在巴黎結束,持續的尋根也構成了人物輪回的命運。過去從未完整真實地浮現,記憶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現,時間的黑洞卻將主要信息吞沒,遺忘使記憶這一唯一支撐變得不可靠。人物必須不斷往返于過去和現在,在回憶與現實交錯中,找尋確切的印證,但是最終的答案茫茫然不可得。莫迪亞諾筆下人物的生命主題便是尋根,他們或期待找到父親、祖國,獲得認同的身份,確認自己的生命坐標,或希望通過“逃逸線”來逃離當下的處境,打破生活固定的模式,在別處尋找新的扎根之地。他們永遠奮不顧身地開始下一次的尋根旅程,而人生像是困在了尋根——失敗——再次尋根的怪圈當中,永恒輪回。
除了尋根失敗的怪圈,我們必須著重闡釋圓形的原點在作品中的代表意義。這個原點不僅是出發的起點,更是最終的歸宿,即使它遙不可及。在《青春咖啡館》中,一天晚上羅蘭正和露姬穿過童年曾經生活過的廣場,她感到仿佛“一切又從頭開始了,(她)回到了人生的起點,這就是一次輪回。”(青春咖啡館:57)家,即原點、母體、回歸之處。莫迪亞諾對家的感情非常復雜,筆下的人物也同樣如此。他們沒有固定住所或長久的感情聯系,沒有家人和朋友,像幽靈一樣來來去去、了無牽掛。但不論是渴望逃離的露姬,還是行無蹤影的瑪格麗特,都暗自渴望這樣一個溫暖的歸宿,每當她們到達一個新的地方,孤獨和悲傷就悄然浮現了,“到火車站沒人來接她,在一座城市里,卻不知道所有街道的名稱。她從未回到過起點。另外,也從未有過起點。她從未返回她生活過的每一個地方。”(地平線:78)正因為他們未曾有過完整的溫暖的家庭,他們也隱秘地期待著能有這樣一個終點,一個能夠安心歇腳的地方。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和《圖騰與禁忌》中頻繁談及亂倫現象和俄狄浦斯情結,童年經驗中未被滿足的力比多在之后得到釋放,而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移情現象。這種被壓制的本能或無意識最終會尋找到別的出口,即移情:“性本能在青春期開始全力尋求滿足,那種已有的、熟悉的亂倫對象會被重新撿起,并得到新的性力補充”⑦。具有俄狄浦斯情結情結的孩童也渴望回到母親體內,重現早期安全的狀態。不同于負面的男性角色,女性形象在作者筆下被理想化了。她們是美好的代名詞,她們沒有具形,“我”不知道她們的模樣,她們只是一種感覺,只一陣風,一縷頭發,一個微笑,是生活中唯一的亮光。“我”對她們的記憶是模糊的,但包含著淡淡的甜蜜和溫馨。當她們離開,“我”便開始了追尋,但從一開始就預示著失敗——這些女性是童年中缺失的母親形象的再現,他們的追尋也正是回歸母體的一種途徑,但母親同樣也是給作家帶來傷痛的存在,她的缺失是莫迪亞諾筆下人物沒有最終歸宿的原因。這些女性的離開如同母親的缺席,是童年傷痛的再一次震蕩,每一次的短暫幸福都暗含悲傷,回到原點的期待將持續落空,支撐“我”走下去的只有永恒輪回,有朝一日,“我”內心妄想著,“我們”將再次回到這一刻。
四、莫式永恒輪回的特點
首先,生死界限模糊。永恒輪回的敘事主題下,莫迪亞諾并未對“死亡”主題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但在行文當中,人物的故事都像是“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一旦失去記憶的保護,那這些“歷史”就隨風逝去,與男主人公的生命發生短暫交錯的人們,就消逝不見了,仿佛沒有存在過似的。不同于肉體的殞滅,存在標記的消失就相當于被宣告“死亡”。生與死并不是輕與重的兩極,相反,兩者的界限難以界定,例如《夜半撞車》中:“惟有乙醚的氣味有時使我想起了它,這種令人介于陰陽兩界的氣味把你一直帶到生與死之間一個脆弱的平衡點。”(夜半撞車:75, 76)在生死界限模糊的輪回中,人物的存在也變得幽靈化。《暗店街》中的居伊?羅朗從疑似曾經住過的地方出來,堅信在樓房的入口處,仍然回響著曾經毎日走過、然后又失去蹤跡的那些人的腳步聲。“其實我或許根本不是這位佩德羅?麥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聲波穿過我的全身,時而遙遠,時而強烈,所有這堅在空氣中飄蕩的分散的固聲凝結以后,便成了我。⑧”
既然“我”什么都不是,那“我”與幽靈的區別又是什么呢?我的存在又將如何證明?而那些被人遺忘的人們,他們曾經居住的房屋還在,或許還殘留他們生活的足跡,但已被人遺忘。處于城市邊緣的“我”,同這些人一樣,都只是游蕩于世上的幽靈。正是由于“我們”本質相通,所以“他們才凝結成了我”。這些幽靈或生或死并不清晰,莫迪亞諾將他們幻化為“幽靈”,一些“無根的”、沒有過去和未來,被旁人遺忘的缺失身份的幽靈。即使存于世上,但在無根地漂泊。這不就是戰爭年代法國在德占時期的形象投射嗎,人民失去家園、猶太人失去身份、國家失去尊嚴。深受戰爭創傷的人們,無一不想重構身份,逃離過去。但沒有歷史的我們還依舊存在嗎?
中國尋根文學中生死界限模糊也同樣存在,但不同于莫迪亞諾的處理方式,在輪回轉世情節中,人物常常死后依舊以鬼魂的形式切實存在著,例如莫言的《我們的七叔》中“我”看著已死的七叔頂著滿頭的血污在院子里修車,他向“我”炫耀淮海戰役的功勞,埋怨七嬸不把軍大衣作為他的壽衣……即使莫言筆下的人物死而“復生”,突破了生死界限,但在輪回的敘事結構中,肉體的死亡并未影響靈魂依舊并保有完整的前世記憶,同活著的人一樣,他們依舊體味著人間的苦痛,我們能很明顯感受到這種生死界限的消除是受民間和古代的鬼怪故事影響,因此更具魔幻色彩和東方特色。莫迪亞諾的幽靈對話雖然模糊了生死的界限,但是死亡已經超越了肉體殞滅的含義,而是一種存在的消失,生與死更在于被世界遺忘與否。若沒有過去,沒有歷史,那“我們”就已“死去”,與幽靈并無區別,是被人遺忘在時間里的孤獨靈魂和那些無根的游者。
其次,時空構建上的獨特性——時間與空間抗衡的張力。《敘事美學》探討了輪回時間與線性時間的區別:在線性時間下,人們顯得有序、冷靜,完全清楚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在這種時間觀念下,未來可以預見,過去只是現在的對照面。但“圓形時間”下,時間似乎“空間化”了,“它使過去、現在和未來處在同一層面上,使其具有‘同時的’或‘共時的’意義。⑨”莫迪亞諾筆下的時間線是混亂的,敘事在時間層面上是完全自由的,具有靈活性。作者甚至在小說中直接描寫了這樣一種并存:“這種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所有的一切都通過一種疊印現象,在你腦海里交錯疊加在一起⑩”,時間平面的并存、疊印,讓人眩暈、迷失。其次,這些看似毫無章法的不同時空相互交織,形成了時間線上的“輪回”,作品中展現給讀者一種“圓形時間”。主人公們為了印證自己的身份,因此在記憶和現實不斷來往,“永恒輪回”由此形成。與其說作者在書寫尋根的旅途,不如說莫迪亞諾在書寫記憶,非線性的時間為描寫一個支離破碎的朦朧的記憶而存在,因此各個時空相互重疊交錯,看似相互補充卻又暗含對立。在他的筆下,所有的回憶甚至現在,都是碎片化地存在著,碎片之間通過回憶的邏輯相連,記憶不斷閃回。
與流動的、碎片化的時間相對的是固定的空間基準點。在《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中約瑟夫?弗蘭克提到現代小說家們構建空間形式的創新之處:“(現代小說家們)來回切斷了同時發生的若干不同的行動和情節,取消了事件順序,中止了敘述的時間流動。……在現代小說中用來獲得空間形式的方法還有:主題重復、章節交替、多重故事……?”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細致分析了作者如何通過重復手法營造輪回的世界,空間的構建也隨之開始,與碎片化的、流動的時間同一存在的空間顯示出固定的、可追溯的性質,兩者之間的張力使構造出的輪回世界更具特色。固定的空間基準點在迷霧般的世界中勾勒出人物游蕩的路程:“雷伊林蔭路73號,與蒙蘇里公園毗鄰”,“凱勒曼林蔭大道65號,舉目便是讓蒂伊公寓”,“車開到克萊芒馬羅街5號警察分局門前停下”。作者給出的地址如此清楚,從街道名稱到門牌號碼、公寓名稱,這一切仿佛真實存在著。此外,還有一系列“物的譜系”,例如《青春咖啡館》中記錄每一個客人出入的名單和記錄,《暗店街》中不斷出現卻不知所云的姓名、老照片、電話號碼本、社交名人錄等等。偵探式的寫作將空間構建得如此清晰。空間相對于時間是更加固定可靠的存在,莫迪亞諾經常通過身邊的地址條、電話號碼、黃頁等等信息中構建空間。在記憶的閃回中,“確定的”空間存在與“不確定”的回憶相對比,形成了獨特的記憶藝術。
這里我們很容易發現時間與空間之間的對立:在碎片化的時間中,人物只能通過固定的空間點試圖抓住已逝的過去。人物在巴黎街道上游蕩,一邊行走一邊回憶,那些精確的空間點不斷變化,也與人物的行走相一致。在《環城大道》里,當主人公獨自一人在巴黎尋覓著父親的蹤跡,縱街頭繁華卻只看見了孑然一身的自己時,“歌劇院林蔭路在我面前展開,并宣告其他林蔭路、其他街道;它們就要把我們投向各個方位基點。我的心跳加速。種種情況捉摸不定,而我為一個基準點,唯一堅實的場地,就是這座城市的十字街頭和人行道;毫無疑問,我最終還要在這里踽踽獨行。”莫迪亞諾筆下的人物都處于一種“疏離的”、“出離于現實”的游魂狀態,自己能夠抓住的,好像只剩堅實的腳下。面對縱橫交錯的道路,他感覺到了“最終的”未來,不斷游蕩,從此刻的空間走向輪回,因為最終“還要在這里踽踽獨行”。
第三,“形”與“神”的對立與和解。中國的輪回轉世文化提出了“形”與“神”的概念,兩者相互對立又統一于變化之中。佛教經典《牟子理惑論》中談到輪回主體“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谷之根葉,魂神如五谷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許多志怪小說中,人物總是不斷幻化著外形,例如《聊齋志異》中鬼魂狐仙投胎轉世,《紅樓夢》中報恩還淚的絳珠仙草等,都是在不同的外形下保留了同樣的“神”,前生后世的命運緊密相連。形式上,人物發生了許多變化,或人形或鬼怪,但本質上并未發生根本變化,若前世是為了追債,或被人冤枉致死,那么死后轉世的目的也同樣是為了完成前世的夙愿,即“神不滅”。
莫式永恒輪回也表現出同樣的對立與統一。不論是過去和未來的再一次重現,還是主人公一次次地拋棄過去擁抱未來,期待某種重生,都是為了通過輪回來追尋自我存在的意義。即使父親再一次缺席,即使主人公再一次陷入“照片上的人原來不是我”的困境當中,即使一切看似都回歸到了原點,人物的輪回并不是簡單的出走與回歸,因為一成不變地回到原點是不可能的,人物總是在圓形結構的時空中有所經歷、有所變化。人物并未陷入永久的虛無和自我否定之中,因為尋找的旅途就已是意義本身。但同時,永恒輪回也意味著恒定的、不變的、持續重復的部分,無論是失去祖國的猶太人,還是失去父親的兒子,在故事的結尾,他們都將繼續尋找,繼續又一次輪回。縱觀莫迪亞諾的作品,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讀者也能感受到隱藏著的相同的、穩定的內在本質,而這也是不同作品之間構成圓形結構的原因。
一次次的輪回和時空的變換下,人物必然再也不是原點出發的那個人,他們改變了形式上的存在方式,卻難以抵抗對自我追尋的命運。但每一次出走與歸來,主人公們也在不斷追尋中尋找著自己的存在意義,或失敗,或留有希望的余地。每一次追尋都更靠近一分,每一次失敗也都預示著新的開始。生命的本質這樣鋪展開來,而永恒輪回在這里成為了必然結果,正是“形”與“神”的對立與和解使人物在命定的際遇中行走,永遠追尋變化,但同時永遠面對來自心底的疑問。
五、莫式永恒輪回的意涵
第一,生命之輕與存在之重。一個“大都市的無名者”如何在世界上標注自己的位置并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他們的生活都毫無根基可言。沒有家庭,沒有依靠。是兩個可憐蟲。”(地平線:61)舉目望去,他們未曾擁有身處世界的參照點——朋友、家庭、種族、國籍。他們不僅無從選擇,更是被每一個歸屬地摒棄。“我什么也不是。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個淡淡的身影。”(暗店街:1)失憶或半失憶的狀態也是人物失去坐標點的外在表現,“失憶導致主人公身份的喪失,身份的缺失導致對已成為空白的前半生記憶的追尋,這種循環恰恰呈現出一種悖論性的狀態,即對主體真正自我的探知永遠不可能有答案。?”失憶是對迷惘的一種隱喻。在這個時刻,如何相信薩特那句看似自我安慰的話——“存在先于本質,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生命如此之輕,但存在意義的重擔依舊,當隱秘而沉重的焦慮從心底蔓延開來:這個城市最終會將他們遺忘,而抵抗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所有這些細節都記錄下來,它們常常是一個人在人世間走過一遭的唯一證明。”(青春咖啡館:34)人物不遺余力地穿梭在街道里,仿佛不停地在道路上來回行走就可以在時空中銘刻自己的軌跡,希望一次次相遇和行走都可以成為他們曾經存在于世界的證明。“他絕不會忘記那些大樓所在的街名和門牌號碼。這是他跟大城市的冷漠和千篇一律斗爭的方法,可能也是跟游移不定的生活斗爭的方法。”(地平線:17)
人物不僅在巴黎街道上刻畫出行走的路線,也試圖在不同時空留下他們的生命足跡。存在的重量使人物毫不停歇地追尋生命的意義,但生命的輕盈使個體無法在“此在”獲得生命的意義,他就只能在未來或過去尋根,來認定自我、確認自我。最終兩者將主人公們推向永恒輪回的魔咒:只有一次次的回到過去尋找記憶,或是擺脫過去跳向未來再一次重生,穿梭在永恒的輪回中,渴望尋找生命的存在證明。然而過去被遺忘籠罩了一層陰影,未來又不斷推向更遠的未來,它們像是海市蜃樓可見而不可及。人物的尋根之路均以失敗告終,并且這種失敗并不是一蹴即成的,而是人物在不同身份中輾轉后得到的結果,每一次的失敗都不是徹底的或毫無余地的,人物依舊留有希望,似乎再一次的追尋將會得到回報,他們又奮不顧身地開始下一次的尋根旅程。永恒輪回像是一個悖論但也是唯一的出口:主人公們真的可能在虛無縹緲的過去或未來尋求得到生命的意義嗎?但這是世界留給他們的唯一選擇——只能抱有一絲希望地不斷追尋,不斷留下足跡。
第二,超越另一種死亡——遺忘。基本上所有的輪回觀念都與死亡密不可分,以一種無限循環的方式對抗有限的肉體存在,是一種對死亡的幻想性超越,一種對有限生命的抗爭。當我們談及死亡,會對于它給予許多不同的定義,或是肉體的殞滅,或是靈魂的消逝,或是生命不再具有繼續堅持的意義。而莫迪亞諾作品中展現的死亡則是“被世界遺忘”。作品中的人物看似與人群遠離,對周圍事物不抱有太多熱情,但面對世界,他們無一不流露出深切的焦慮與擔憂,他們害怕再一次被遺忘和拋棄,從未在世上留下絲毫痕跡,仿佛他們根本不具有存在的意義。“我感到一陣恐懼,這種恐懼常常在夜里把我攫住,比害怕的感覺要強烈得多——我感覺從今往后要獨自一人面對人生,無依無靠,沒有人來幫我。”(青春咖啡館:65)
因為遺忘不是不為所動或冷漠無情,而是在時間的磨損下不知不覺地被替代、被忽略、被拋棄,同肉體的殞滅相比,這種死亡更為徹底。“然后,那些人在某一天消失了,人們才發現對他們一無所知,連他們的真實身份都不知道。”(青春咖啡館:123)所以,他們緊拽著最后一絲希望,期待永恒輪回可以跨越遺忘的鴻溝,再一次經歷,再一次回憶,戰勝最后的“死亡”。時光慢慢將記憶腐蝕,只剩永恒輪回將生命線變成循壞的圓形。過去可以被再次找回,生命可以通過輪回再一次重生。那些遺落的片段和不期而遇而交叉的生命線還給予他們一絲光亮。在一次次輪回中再次確認存在的意義,再次試圖揭開霧蒙蒙的過去,再次試圖抓住迷失在黑夜中的未來。如同《地平線》中的主人公那樣,到故事最后,“他看到那里六樓的一個窗口亮著燈光,也許有個人早已在等候他的到來,他感到自己患有遺忘癥。他對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已忘得一干二凈。”(地平線:74)他們永恒輪回中自我治愈,苦痛的過去將要過去,而他們也終于有勇氣擁抱追尋的“燈光”,尋回走過的街道,與暗物質作最后的抗爭。
正如莫迪亞諾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發表的演講中所說:“如今,我感覺到記憶遠不如它本身那么確定,必須不停地與健忘和遺忘斗爭。由于這一層、這一大堆遺忘覆蓋了一切,我們僅僅能截取一些過去的碎片、不連貫的痕跡、稍縱即逝且幾乎無法理解的人類命運。”那些散落在遺忘深處,丟失在未知世界中的部分,作者渴望將它們拾起來,試圖抓住生活中無意義的、徒勞的部分,通過完成一項普魯斯特式的工作,不僅僅想要回憶起已逝去的時光,更要尋回逝水年華。
第三,西西弗式幸福。在悲戚的生命底色下,永恒輪回是唯一的人生的口。然而在無數次輪回當中,他們最終能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幸福嗎?那些虛無縹緲的意義和活下去的動機真的是可追尋的嗎?如果在無數次輪回中,尋根無數次的失敗,他們一再被遺忘在巴黎的街道上,苦痛再一次降臨,希望再一次破滅,痛苦作為生命的一種基本體驗,通過永恒輪回,將反復地降臨在個體身上。更要緊的是,在這種反復的痛苦體驗中,生命似乎難以確立其積極的意義,因而也難以為生命自身而辯護。面對生命的深刻窘境,我們如何坦然直面這一境地?
或許西西弗給出了答案。他陷入永恒的輪回當中,必將回歸原點并再次從原點出發,徒勞無止境的勞作似乎消解了行動的意義。每一次的推石都暗含了已預見的無意義,西西弗卻必須將石頭推至山頂并眼看石頭再次滾落,人生的荒誕便由此而起。在絕望與荒誕的廢墟中努力抗爭著,加繆卻說“應當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莫迪亞諾筆下的人物是否也在永恒輪回中體會到了西西弗式的幸福呢?
可以說,莫迪亞諾筆下的主人公都是加繆所定義的荒誕人。“雖然確信他的自由已到盡頭,他的造反沒有前途,他的意識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時間內繼續冒險,這就是他的能力范圍,就是他的行動,他審視自己的行動,而排除一切評判。?”在接近于零的可能性中,主人公們還是在期待下一次輪回,是的,他們期待在永恒輪回中找尋到存在的意義,最后,在無數次被損耗的信心下繼續冒險,那么永恒輪回本身就已成為了意義本身。
在無休無止的輪回當中,我們發現,加繆筆下的西西弗并不是莫然消極地接受諸神的懲罰。“他對諸神的蔑視,對死亡的憎恨,對生命的熱愛,使他吃盡苦頭……這是熱戀此岸鄉土必須付出的代價。”(西西弗神話:130)而莫迪亞諾筆下的人物也同樣如此,位于城市邊緣的他們內心卻是藏著最深沉的感情,在永恒輪回中,“經受住世界的荒誕性(感受到)一種形而上的幸福。”(西西弗神話:101)
他們在一次次的失敗中一次次義無反顧地重新開始,這一次的無奈失敗變成了下一次偉大嘗試的悲壯序曲。生存在荒誕之中,唯有反抗才能證明自己真實地生活著,永不退卻的抗爭激情也點燃了灰暗的人生。每一次在塞納河邊的行走,每一次跳向未來的斷裂,每一次的身份找尋,“那巖石的每個細粒,那黑暗籠罩的大山每道礦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組成部分。攀登山頂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實一顆人心。”(西西弗神話:133)應當想象他們獲得了西西弗式的幸福。
六、結語
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里,莫迪亞諾都未曾繞開永恒輪回這一命題。不論是前期作品中主人公持續性的身份變換和尋根失敗等內容,還是后期小說中越來越頻繁提及到的尼采的“永恒輪回”,或是獨樹一幟的小說風格,相似的主題、人物、情節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表明了永恒輪回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意義。
莫迪亞諾獨特的時間書寫方式,讓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在一起。通過回憶,失憶的人不斷尋找著過去,而遺忘又讓背負過去傷痕的人努力將自己套上一個個新的身份,一切都在輪回中永恒流轉。在作品結構上,莫迪亞諾所有的作品都不是單一的、隔離的,而是共同構成了莫式小說世界。在其中一部作品中出現的相似意象、情節或人物都可以延伸到另一個作品,作品之間相互指涉,在互文中完成其含義。圓形的行文結構和回歸原點的行文趨勢,也構成了文學意義上的永恒輪回,例如尋根失敗的怪圈,具有母體意義的女性形象等。
在每一次的輪回中,人物從原點出發再一次回到原點,看似跌入永恒虛無之中,但起點并不等于終點,在一次次虛妄的追尋與回憶之后,主人公仍舊在恒定的、永久的輪回之下感受著變化,追尋著幸福。在變與不變之間,尋找本身已成為一種意義,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并不能將莫迪亞諾的作品給予一個全然悲觀基調的重要原因。
當生命的意義回歸到最初的原點,我們只是想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并且期待遺忘——即最終的死亡——將我們悄悄抹殺。莫迪亞諾筆下的主人公們像候鳥一樣不斷追尋虛無縹緲的過去、父親或幸福,心中卻帶著深深的疑問:如何抵抗被遺忘的既定命運?幸福真的是可能的嗎?答案可能并不樂觀。他們依舊努力飛翔著、尋找著,即使在無數個命運里反復失敗,即使生命像是“輕”到毫無意義,但每一次的找尋都是西西弗斯對命運的一次戰勝,對石頭的一次唾棄。應當認為,在永恒輪回里,他們也能獲得幸福。
①[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星形廣場》,李玉民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74頁。
②[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金龍格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118頁。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做注。
③[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夜半撞車》,譚立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53頁。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做注。
④[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地平線》,徐和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85頁。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做注。
⑤[美]希利斯·米勒:《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王宏圖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5頁。
⑥Akane Kawakami.,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⑦[奧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賀愛軍、于應機譯。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337頁。
⑧[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暗店街》,王文融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92頁。
⑨耿占春:《敘事美學:探索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2,203頁。
⑩[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夜的草》,金龍格譯。合肥:黃山書社,2015,70頁。
?[美]約瑟夫?弗蘭克:《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秦林芳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3頁。
?楊曉青:《論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小說中的“身份”主題》[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06,19頁。
?[法]阿貝爾·加繆:《西西弗神話》,沈志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71頁。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做注。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于尋根視角下的莫迪亞諾小說研究(項目批準號:14CWW016)階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費用資助。
(責任編輯:許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