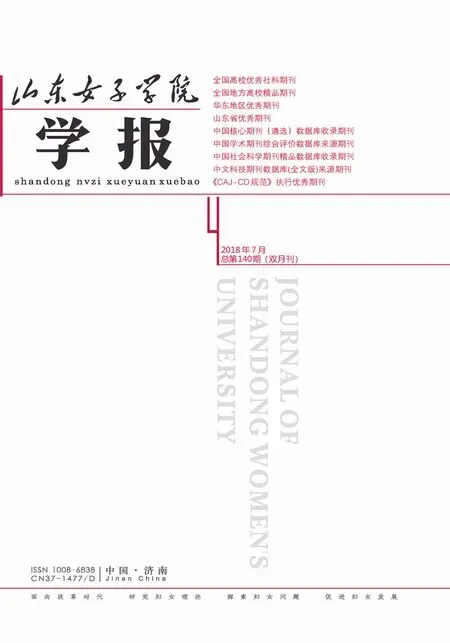護士形象的再現
——對《人民日報》1949年以來文本的分析
馬冬玲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婦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護理作為一項職業出現在1910年代。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到2016年,中國注冊護士人數達到350.72萬[1],占全部衛生人員的31.4%,占全部衛生技術人員的41.5%①。2008年我國頒布的《護士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護士,是指經執業注冊取得護士執業證書,依照本條例規定從事護理活動,履行保護生命、減輕痛苦、增進健康職責的衛生技術人員。”從該定義以及國家其他有關人口、勞動等統計中的定義來看,護士在國家的職業體系中均被界定為“專業技術人員”。
護士一直被看作是“白衣天使”,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因素的影響,護士職業地位出現了下沉現象,特別是職業聲望下降。在北京,1997~2009年間,護士聲望排名下降了21個位次,成為下降幅度最大的三個職業之一(另兩個職業是保險公司業務員和電腦經銷商)[2]。職業聲望即社會形象,這就表明,護士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發生了不利的改變。
一個形象產生的時候,它就包括了社會文化中的價值觀和規范②。社會文化對護士形象的理解與想象,不僅塑造了社會對護士的認知和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響護士自身對職業的認同,從而影響其工作投入和職業表現,因為文本的生產和閱讀也是由生產者和接受者共同參與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會參與到日常生活的主體性構建中,影響其自我認同③④。同時,護士作為一個專業/職業群體,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女性化。2016年,中國注冊護士中女性占97.9%[1]。對護士形象認知的改變,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女性形象認知的改變。因此,有必要了解社會大眾文化是如何再現護士形象的。對這些問題的初步探索,既有助于增進對護士群體的理解,也可為我們探討護理職業的特征提供一個性別化的觀照維度。
二、文獻綜述
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1963年出版的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st Mystique)中研究了女性雜志和導致女性形象改變的政治經濟因素,并認為形象對女性主義運動具有重要意義⑤。自此之后,形象研究成為女性主義大眾文化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許多著作開始關注媒體和其他大眾文化對女性和男性的各種文本再現形式。總體來說,全球各種各樣的主流大眾文化形式都是以“象征性滅絕”的方式對待女性的,即對女性表現不夠,即便在有限的再現中,女性往往也是以被貶低、被排斥、被迫害和被嘲笑的形象出現的,是以刻板的女性形象或者具有明顯性意味的形象出現的②。
在中國,女性形象的相關研究也是一個熱點。以中國知網為例,用“女性形象”為題名進行搜索,有近9000篇文章,且從1980年的1篇,增加到2017年的453篇。研究涉及到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關注到不同群體和職業身份的女性,采用了不同的女性主義視角。從女性職業群體形象來看,民國時期女店員、女記者等的形象塑造和建構都得到了關注[3][4]。總體來說,諸多學者指出當代傳媒中存在將女性形象刻板化的問題,但也有一定程度上對社會性別認知的轉變[5]。
護士的形象是隨著護理工作的出現而產生的,是護士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護理工作質量的外在表現。護士的形象也由于社會的發展、醫學的進步以及護理工作范圍的擴大和任務的不同而相應地有所變化[6]。國外關于護士形象的研究中,早期研究認為護士在媒體中是被排斥、忽視和貶低的[7];近期研究更關注護士的多元形象[8][9][10]。
國內關于護士形象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刊發于醫學和文學、影視等相關的期刊,這些文章有的采用問卷調查等形式進行研究,后者多以個別具體文本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這些護士形象研究為我們了解這一職業群體積累了豐富的資料,提供了多樣的研究角度。不過,以往有關護士形象的研究對媒體中的護士形象關注較少;從研究內容來看,對護士形象的多樣性、變化性方面關注相對較少。本研究主要選擇1949年至2017年間《人民日報》中的護士形象作為研究對象,因《人民日報》是權威黨報,對護士的報道既能反映出官方的態度,對護士在現實生活中生存狀態的書寫也有一定代表性。以關鍵詞“護士”搜索文章標題或主題,一共發現158篇報道。筆者采用內容分析方法,分析這些報道中護士的職業形象和性別形象。
三、護士形象的再現
對《人民日報》文本的分析研究發現,對護士的再現主要包括知識分子形象、勞動者形象、仆人形象和性別形象幾類。
(一)護士的知識分子形象
護士的工作是否有專業性、是否有技術含量是影響其職業形象的重要維度。
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由于人均受教育程度較低,科教文衛工作人員匱乏,政府著重強調護理的技術性。例如,1957年4月3日,衛生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廳、局和各高等醫學院校及其他有關單位發布了“關于改進護士工作的指示”,指出:“應明確護理工作是科學技術工作”[11](P58)。1957年拍攝的電影《護士日記》被認為是有關“知識分子”的電影:“隨著‘雙百’方針與‘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提出,電影創作又顯生機,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也得到重視,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影片再度出現,《護士日記》就是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影片“熱情頌揚了青年知識分子把青春獻給祖國建設的精神風貌。”[12]1984年的慶祝國際護士節大會上,全國政協主席、中華護理學會名譽理事長鄧穎超給大會寫了賀信,指出護理工作不是一般的簡單的勞動,而是“一門醫學科學的帶有綜合性的學科”,應該“一貫地成為醫療、健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衛生部時任部長崔月梨在講話中指出:“護士是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其中主任護師、副主任護師是高級知識分子。”[11](P76)對護士作為科學技術人員的形象塑造是這一時期媒體的主流取向。
一是從意識形態層面明確護士屬于知識分子,護理是科學技術工作。《人民日報》1956年11月23日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提出要關心護士,做好護理工作:“護士是一支很大的知識分子隊伍,是婦女參加社會建設的一項重要職業。”1980年2月2日發表的文章《從不愿報考護士學校談起》指出:“護理工作是一門專業學科,一個護士不僅要具備廣泛的護理基礎知識,還要具備相當的醫學基礎知識。”1981年5月7日發表的社論《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論全社會都要尊重護士愛護護士》中指出:“護理學是一門專門的學科。……是一門精湛的藝術。……護理工作大有學問。”市場化以來,也有個別文章提到護理學的學科性,如1997年5月9日王瑩在《她有一顆平常心——獻給國際護士節》中提到,護理學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護校學生要學習很多專業課和基礎課,在醫院工作中也需要了解病情特征和具有操作現代化醫護儀器的能力。
二是關于提高護理工作質量與護理技術的探討。如1956年12月18日發表的《中華護士學會召開會議,討論提高護理工作質量問題》;1958年5月14日發表的《大膽的想,大膽的干——杭州第一醫院護士改革鋪床方法》;1961年11月12日發表的《提高臨床護理工作質量,天津醫學院附屬第一中心醫院婦產科青年護士認真學習醫學理論》;1962年11月3日發表的《進一步提高護理質量,交流學術研究成果——中華護士學會召開首次學術會議》等,這些標題即顯示出其關注的是護士的技術問題。
三是關注護理人員的培養和發展問題。有的報道涉及護理人員的理論和思想建設,如1964年8月6日發表的《中華護士學會舉行學術年會和代表大會,研究基礎護理理論和護理人員思想革命化問題》。有的報道涉及護士的技能培養,如1960年8月26日發表的《醫師是教員,病房當課堂,邊教邊學,邊學邊用——武漢第二醫院加速培養護士》,1970年9月10日發表的《上海市楊浦區中心醫院深入批判修正主義醫療衛生路線,培養“一專多能”的醫護人員醫生以醫療為主,兼學護理;護士以護理為主,兼學醫療》。有的報道涉及對護士的提拔問題,如1960年3月21日發表的《工農群眾迅速知識化——吉林省、玉門、長沙提拔一批工程師和技師,北京提拔二十八名優秀的護士擔任領導工作》等。
改革開放和市場化之前,《人民日報》較多地強調護士勞動知識性的一面,將其視為知識分子,關注其技術方面的進步。但市場化轉型以來,《人民日報》除個別報道在內文中提到護理技術外,類似的話語基本消失了,特別是在標題上不再出現了。
(二)護士的勞動者形象
護士作為具有腦力和體力內涵的社會職業的從業者,對其的報道既有正面強調其勞動價值和個體主觀能動性的一面,也有關注其勞動權益的一面。
一是強調護理工作和護士的重要性。例如,《人民日報》1962年3月13日傅連暲的《“紅色護士”贊》一文在談到醫護關系的時候指出:“醫生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一個病要治好,就須診斷清楚,治療得法,調護有方。因此,要由醫務、護理、各種檢驗、藥房、營養室等許多部門的工作人員共同勞動來完成。他們的重要性,幾乎是無所軒輊的。”1981年12月13日的《上海隆重表彰優秀護士,〈文匯報〉發表社論要求尊重愛護護士》一文認為,護士的勞動是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勞動,將護士工作與工人、農民、教師、演員、機關干部所從事的各項工作相類比,認為“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社會的需要,都是光榮的”。同時將優秀護士定義為社會主義衛生事業方面的“專門家”。
二是報道護士作為不斷進取的勞動者形象。對護士典型的報道傾向于強調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不斷追求技術進步的一面。例如,1961年2月15日對福建某衛生所護士莊麗花的報道《好護士》中就有相關內容:莊麗花雖然在國外當過兩年護士,但是除了簡單地分藥、量體溫、測血壓等以外,并沒有學到多少護理技術。因此,她回國后工作中碰到了不少困難。為了做好工作,更好地服務于群眾、解除病人疾苦,她如饑似渴地學習,為記藥名“下班后還反復默讀,直到記熟為止”。兩個月以后,她不僅對衛生所里的全部藥品都了如指掌了,還學會了醫治一般疾病,并經常到場員中去宣傳衛生常識。這種作為職業主體的責任感在市場化壞境下的護士身上依然存在。例如,2003年8月25日的《我會把護士日記寫下去!》中這樣描寫護士張積慧的心理活動:“女性天生具有一種堅韌不拔、甘于奉獻的精神。但在今天,光有奉獻還不夠,終身學習,永不停步,才能真正擔起新時代女性的責任”。
三是討論護士作為勞動者的權益問題。改革開放前的報道主要從勞動保護的角度談對護士的照顧,關注護理勞動本身帶來的身體壓力和損害。例如,1956年11月23日的一篇題為《關心護士,做好護理工作》的評論員文章指出,由于護士大部分是青年婦女,“醫療衛生部門要注意照顧護士的工作特點和生理特點,在生活上關心她們,在工作上給以各種方便條件”。但是,并非所有醫療衛生部門都能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很多部門做得很不到位,對護士們既缺乏教育,又缺乏照顧,還為她們規定了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如哺乳時間要在工作時間以外補足,有的醫院甚至要求懷孕的護士參與抬病人,對她們的身心需求和現實問題考慮不夠。據1956年9月8日《關心護士的生活和學習,上海著手改進護士工作》報道,8個醫院在這一年中曾經有46個護士流產、早產。1987年5月13日艾笑的《在護士節這一天》報道,一位病房護士一個班里需要走多達55里路。2013年5月10日李紅梅的一篇《護士流失令人憂》的文章介紹到,一半護士每天工作超過9個小時,甚至連喝水、上廁所、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至于不能按時下班更是家常便飯。2015年5月12日姚友明等人的報道《床護比達標還需幾個37年?》指出,有的夜班護士須照顧80名患者。
改革開放后的報道更關注護士職業發展面臨的困境。例如,1980年2月2日的《從不愿報考護士學校談起》中,將問題歸因為領導思想認識上的偏差,以及對護士培養、晉升、福利待遇不合理等方面的不足。2008年9月4日李曉宏在《護士為什么這樣少》的報道中指出,護士職業發展中面臨工作強度大、報酬待遇低、編制控制嚴等挑戰;2013年5月10日李紅梅的報道《護士流失令人憂》指出,超半數護士對目前收入感到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5月17日她的另外一篇報道《護士勞動太廉價》指出,常規的靜脈輸液操作過程最少包括5個步驟,但這樣一個需要嚴格訓練的復雜勞動,收費一次僅2元,“還不值一個煎餅的錢”。住院一級護理每天也僅9元。她在報道中還指出,在推行優質護理服務工程過程中,一些醫院加大了護士的工作量,但并沒有相應地提高護理服務的價格和護士的報酬,不能不影響到護士工作的積極性和護理隊伍的穩定性。即使如此,多數護士仍堅守崗位,默默奉獻。2015年5月12日,姚友明等人在《床護比達標還需幾個37年?》一文中指出,護士群體仍未擺脫工作繁重、收入偏低、職業認同感差的怪圈。2016年5月20日王君平的《莫讓護士被“忽視”》一文,報道了護士收入待遇差、工作超負荷,導致護士招不到、留不住的“護士荒”的現象,認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護士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5‰,而我國只有1‰左右,護士尚缺幾百萬人。2011年5月24日白劍峰的《把護士還給病人》一文和2013年7月29日朱虹的《護士兼護理如何可持續》,則從經驗分享的角度,分別介紹了北京和天津醫院采取措施提高護士職業滿意度的實踐。
總體而言,護士作為普通的勞動者形象,媒體既再現了其積極進取、樂于奉獻的一面,也再現了其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現實。市場化以來,后一種再現更為集中和突出。
(三)護士的仆人形象
近百年來,盡管護理人員在醫療體系中的地位由無技術的勞工提升至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團隊中的一員,但護士的民俗形象(the folk image,又稱“母親形象”)、宗教形象(the religious image)和仆人形象(the servant image)[13]至今依然存在于社會大眾意識中,影響了護士的社會形象。實際上,病人似乎很難將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與較少受訓的同樣照顧病人的女性區別開來。護士與其他在家庭中進行照顧的婦女分享對常用器具和工具的使用時,護士因看起來是“沒有對科學化技能的壟斷性定義的通用式的女性服務工作者”,其專業形象一開始就受限制了⑥。
在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精英運動中,官方的意識形態認為,把觸碰人的身體的臟活看成低等工作是一種封建遺毒,“大眾被再教育,要相信所有的工作都是值得尊敬的,只要這個人的目的是全身心地服務大眾。很多手段被用于工作場所來減少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距”[14]。1966年以前,“由于當時的觀念是各行各業均需相互服務,大多數人對護士無輕視思想,社會地位比以前提高”[15]。
盡管官方力圖強化護士勞動的專業性,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存在對體力勞動者的輕視。1956年上映的電影《上甘嶺》中有一幕廣為人知:女主角護士王蘭用嘴吸住導尿管給異性傷員排出尿液。這一場景雖然描寫的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場景,被官方當作一種英雄主義和奉獻精神而正面宣揚,但在實際上起到了強化護理與人身體接觸的尷尬一面,強化了護理是(女性)伺候人的社會看法。這種描繪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以關愛為專業特性的護士與將關愛看作家庭責任的家人之間的界限。2008年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仍有25.5%的患者認為護士是保姆形象,8.0%的患者認為護士是仆人形象,多數人認為護士職業是純粹的服務性工作[16]。
在《人民日報》塑造護理專業形象的同時,也顯示了社會和文化中對護士與護理勞動的看法,以及護士的心聲。
一是病人對護士勞動不尊重。如1956年9月10日的一篇題為《尊重護士的高尚勞動》的社論文章指出,在很多人甚至衛生部門有些人的心目中,依然存在“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對護士工作的不正確的看法”,個別病人甚至認為自己是“花錢來治病”的,因此“對于護士的勞動很不尊重”。同年10月11日一篇題為《尊重護士勞動,做好護理工作》的文章認為,仍有不少病人對護士的勞動表示輕蔑,并進一步描述了這些不尊重的具體表現,如有些病人認為護士鋪床、送便器是他們用錢買來的享受,有的病人喝令護士給他們作招待員,為來看望的親友送開水,一旦遭到拒絕就臭罵護士:“你為誰服務”“你干什么!”有些病人把護士叫來說自己身體不舒服:“你這個小護士又不能解決什么問題,你給我找醫師來,快去!”
二是護士自身的不滿與呼聲。早在1987年6月16日馮軍軍在《三位老護士手捧南丁格爾獎發出呼吁:護士人少質差亟待加強,社會應該尊重護理工作》的報道中指出,三位當年獲得第三十一屆南丁格爾獎章的中國優秀護理工作者認為,新聞、宣傳部門對社會上存在的不尊重護理工作者勞動的現象負有一定責任,因為媒體報道中存在護理專業性突出不足的情況:“不能一報道就是喂飯、喂水”,實際上護理中還有很多技術性非常強的工作,都應該有所反映,“那才是護理人員的真正形象”。
總體來看,由于社會上長期潛在的對護理作為“伺候人”工作的貶低、輕視,護士的仆人形象也一定程度存在,并在官方媒體的批判性文章中隱現出來。
(四)護士的女性形象
從性別的角度來看,由于絕大多數護士是女性,加之傳統性別分工導致發生在家庭中的身體照顧勞動主要由女性承擔,對家庭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女性的態度往往也延伸到對醫院護士的態度中來,影響了對護理專業的看法。
一是強調護士勞動過程中的愛心而非技術。長期以來,對護理勞動的描繪存在用“親人”稱呼病人的情況,例如1959年3月8日婦女節,海稜發表了一首題為《護士的心》的詩:“常把病人當親人,病人心疼我心疼,千呼萬喚不厭倦,但愿病人得康寧。晝夜侍候多殷勤,病房冷暖時在心,年年月月如一日,永把青春獻人民”。
改革開放后,《人民日報》對護士的描寫也延續了“親人”的概念,媒體中強調將“愛”等情感性話語而非技術性話語與護士聯系在一起的現象日益普遍。例如,1981年5月28日發表的《他待病人勝親人——記撫順礦務局醫院外科護士肖淑芬》、1989年5月27日發表的《守護生命的“女神”——記獲得南丁格爾獎章的四位中國護士》、1991年3月9日發表的《女護士李亞賢——“奉獻愛的人”》、1997年5月12日發表的《愛,灑向顛倒的世界——記南京市腦科醫院的護士們》、同年9月16日發表的《充滿愛心的護士全雪明——一片愛心獻病人》等報道均為這類報道。2003年,由于“非典”的流行和護士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凸顯,《人民日報》共有18篇題目中包含“護士”的報道,是歷年最多的,且多用“天使”來形容護士。2006年4月17日白劍峰、云桂芳在報道《“洗腸護士”的仁心熱腸》中,用“白衣天使”稱呼護士,導語則是“干這種活,就要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在2006年7月18日趙鵬、徐志南寫了一篇題為《播種善良收獲美麗——記福建省屏南縣醫院護士包著瓊》的專題報道,盡管主人公包著瓊工作成果顯著,但在報道中作為要點提示的三個小標題“護士包著瓊的‘吝嗇’與慷慨,在屏南縣幾乎家喻戶曉”“熱心的包護士”“愛哭的‘包媽媽’”,無一涉及到其專業技術表現。2007年11月3日發表的郅振璞的《像仙子一樣的護士》,文章第一句話便是“眼前的澤仁娜姆,就像一株格桑花,外表馨香、美麗,內在質樸、善良”。重點表現其思想品質,較少提到其專業技能方面的表現。同年5月17日白劍峰的另一篇文章《陽光燦爛的微笑》同樣強調護士的“微笑”。
二是將護士與家庭責任聯系乃至對立起來。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人民日報》幾篇有關護士典型的報告較多地強調護士作為女性承擔的工作與家庭責任的沖突和對立。例如1997年5月9日王瑩的《她有一顆平常心——獻給國際護士節》對典型事跡(護士郭川華)的報道與1961年對莊麗花的報道有了顯著差異。報道用了很大篇幅講述她如何為了工作缺席家庭責任,說她多年忙于護理工作,“照料自己女兒的時間很少”。由于其丈夫忙且常年派駐在國外,孩子半歲就被送進幼兒園,小學六年級就學會了自己買菜、洗衣服,有時還得跟著值夜班的媽媽到病房的值班室湊合過一夜。同時,在她的老父親因病臥床期間,她也沒能盡心照顧,還錯過了父親去世的那一刻。2004年3月2日發表的蘇銀成等人的《軍旅模范護士——岑愛萍》中,使用了同樣的敘事模式,在講述了該護士對病人的盡心盡力之后,用了不少篇幅詳述其對家人的虧欠,如父親病危期間她還堅持值完班,等她趕回老家時,“見到的竟是父親的靈堂”。于是“她失聲痛哭,跪在父親的靈前,請求九泉之下的父親能原諒女兒的‘不孝’”。同時,由于工作繁忙,她也沒有時間照顧女兒,導致女兒在作文中寫道:“我的媽媽是白衣天使,但她是一位懶惰的天使”。
三是討論男護士的加入及其優勢。2016年關于男護士的研究發現,社會性別秩序是男護生身份認同主要參照的社會框架。由于性別身份和職業身份的沖突,男護生不能獲得對護士身份的認同,只能在現實的壓力下,通過大學生的身份緩沖兩種身份之間的沖突,獲得暫時的平衡,他們會同時運用“創造相同”和“維護差異”策略來管理自身承擔的多重身份[17]。作為主流媒體的《人民日報》則相對較少關注到這一面,更強調積極的一面。例如,2005年9月6日關悅在《北京首批高學歷男護士全部簽約三級醫院》的報道中,就工作環境、強度、社會反應等采訪了其中一名男護士,得出男護士適應良好、家人支持、科室歡迎等積極結論。2010年5月12日白劍峰的報道《“護士先生”多起來了》則介紹了10年來男護士的發展情況,指出過去男人當護士被認為是低賤和恥辱的,如今我國男護士人數增多了,而且男護士就業率高、流失率低,這些現象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和觀念的開放。報道還認為,男護士在臨床上具有體力精力、應急能力、管理能力和同性護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同樣可以在護理事業上有所建樹。
總體來看,關于護士的性別形象的再現依然將護士默認為女性,并較多與女性的關懷特質聯系起來。同時,雖然男護士依舊鳳毛麟角,但報道中的“重男輕女”現象還一定程度上存在。
四、小結與討論
本文以《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為文本,對護士的職業形象進行了梳理。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再現了護士的知識分子形象、勞動者形象、仆人形象和性別形象。一方面,護士的這些多元形象貫穿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個歷史時期,顯示了這一職業群體多種面貌并存情況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另一方面,不同時期對護士形象的再現也有差異,在市場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護士的職業形象摻雜了從知識分子、普通勞動者到仆人的等級化的形象,而對護士作為知識分子形象的再現日益讓位于對護士作為女性形象的再現。由于《人民日報》作為黨報的權威性,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社會對護士群體和護理職業的認知。
大眾文化不僅僅只反映整體文化,同時也通過復雜的方式向整體文化傳達信息。再現的概念清楚地說明,大眾文化的生產是一個調解的過程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官方話語中這四種護士形象的隱顯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會對女性職業身份與性別身份、職業角色與性別角色認識的穩定與演變并存的現象,體現了力圖打造一個無階級差異和男女平等的政府與民間根深蒂固的對照顧性勞動的社會位置的沖突。此外,從報道數量來看,護士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特別是市場化以來,相關報道往往出現在護士節前后,更多地是一種符號性意義,甚至這種符號性的再現也日漸稀少。
受限于文本本身的特點等原因,本文沒有就護士的女性形象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如在新媒體中被呈現較多的性化的一面。對影響這些多元形象存在的社會因素、對導致這些形象變遷的因素的探討也不足,需要留待今后研究加以深入研究。
注釋:
① 參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占比數據由此處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② 參見安格哈拉德·N·瓦爾迪維亞(Angharad N. Valdivia)著,朱悅平譯, Images of Women: Overview(《女性形象:概述》)詞條,載于[美]謝麗斯·克拉馬雷,[澳]戴爾·斯彭德主編的《路特里奇國際婦女百科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③ 見安妮·巴爾塞莫(Anne Balsamo)著,陳娜靜譯,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詞條,載于[美]謝麗斯·克拉馬雷、[澳]戴爾·斯彭德主編的《路特里奇國際婦女百科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④ 見凱蒂·迪普威爾(Katy Deepwell)著,朱悅平譯, Art Practice: Feminist(《藝術實踐:女性主義》)詞條,載于[美]謝麗斯·克拉馬雷,[澳]戴爾·斯彭德主編的《路特里奇國際婦女百科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⑤ 參見Friedan B.的The Feminine Mystique, Dell,1963年版。
⑥ 參見Margarete Sandelowski 的Devices and Desires:Gender,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Nursing,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年版。
參考文獻:
[ 1 ]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Z].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7:30.
[ 2 ] 李強,劉海洋.變遷中的職業聲望——2009年北京職業聲望調查淺析[J].學術研究,2009,(12):34-42.
[ 3 ] 連玲玲. “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J].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6,(14):1-50.
[ 4 ] 馮劍俠.“無冕皇后”還是“交際花”:民國女記者的媒介形象與自我認同[J].婦女研究論叢,2012,(6):59-64.
[ 5 ] 張娜.人民日報(2001~2015)話語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新聞界,2017,(3):70-74,82.
[ 6 ] 王三虎.護士形象簡史[J].中華護理雜志,1992,(11):518-519.
[ 7 ] Buresh B.TheNurseWhodoesn’tExist:Omission,NeglectandDebasementofNursesintheMedia[J]. The Journal of Nurse Empowerment,1992:10-16.
[ 8 ] Morris-Thompson T, Shepherd J, Plata R, et al. Diversity, Fulfillment and Privilege: the Image of Nursing[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2011,(19):683-692.
[ 9 ] Aber CS, Hawkins JW.PortrayalofNursesinAdvertisementsinMedicalandNursingJournals[J]. IM J Nurs Schol,1992,24(4):289-293.
[10] Bridges J.LiteratureReviewontheImageoftheNurseandNursingintheMedia[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1990,15(7):850-854.
[11] 李秀華,郭燕紅.中華護理學會百年史話(1909-2009)[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12] 朱安平.《護士日記》禮贊青春[J].大眾電影,
2009,(5):40-42.
[13] 孫慕義.醫學倫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1.
[14] Samantha ,Mei-che Pang.NursingEthicsinModernChina:ConflictingValuesandCompetingRoleRequirements[M].Amasterdam-New York,NY.,Rodopi: 30-31.
[15] 林菊英.我國護理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作用與地位[J].護理學雜志,2003,(1):3-4.
[16] 曹祝萍.醫護關系研究——歷史、現狀、存在問題及形成因素分析[D].石河子:石河子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12.
[17] 高修娟,何圣紅.青年男護生身份認同困境解讀[J].青年研究,2016,(2):68-7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