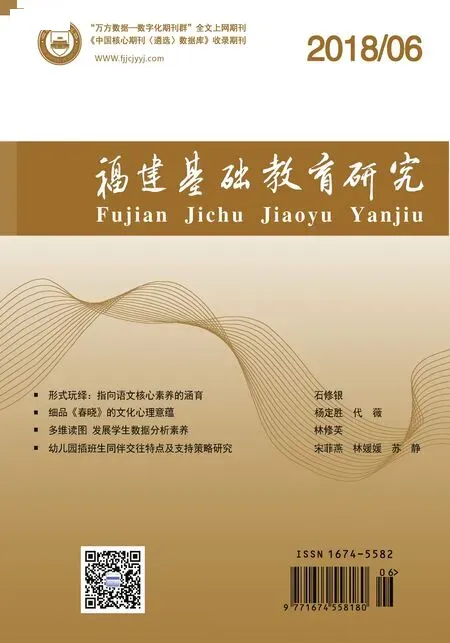細品《春曉》的文化心理意蘊
楊定勝代薇
(1.云南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 0;2.云南昆明市盤龍區新迎第一小學,云南 昆明 650 2 33)
《春曉》出現在幾代人所學的小學語文教材里,是家喻戶曉的經典名篇,為什么能夠流傳千古備受鐘愛?其藝術魅力究竟何在?王富仁認為其藝術魅力源于這幾個方面:“在醒覺過程的精微表現中創造了一個獨立而又有意味的精神境界;創造了一個與人的心靈世界相呼應的自然世界;復雜的簡單,哲理的意蘊。”[1]有研究者關注到其情感表達的復雜性,認為此詩既有面對和諧美好之景的歡欣、喜悅之情,也有惜春、嘆春之情,還有孤單冷清之意;[2]有的關注詩歌主旨的多元性,認為這首詩的主旨是“表現詩人的擺脫、超變的心境、一種東方式的禪悟”。[3]有的認為,“它絕非單純的傷春惜春之作,而是他晚年臥疾時候的無奈悲嘆,隱約傳達出他久病在身懷才不遇而終于布衣的人生體味”。[4]研究者對詩歌主旨的解讀出現了“喜春”和“傷春、傷時、傷己”這樣相互矛盾沖突的結論,然而各自都能從詩歌的語言文字中找到合理的解釋依據,讓表面看來簡單的詩歌充滿了神秘感。
從現有資料來看,《春曉》并沒有具體的寫作年代,多數研究者推測此詩是唐代詩人孟浩然隱居在鹿門山時所作。因此解讀《春曉》時,要避免一種錯誤傾向:即用作者的生平經歷和所處的時代背景去套解詩歌,這會帶來文本解讀的模式化、標簽化、空泛化問題。有效的解讀方式應該是直面詩歌本身進行合理的文本細讀,既要注意詩歌多義的空間,也要避免主觀強制性解讀的混亂,要在文本自身的規定性里進行有理有據、合情合理的解讀。部分《春曉》的研究者會產生這樣的閱讀體驗:感知到此詩很有情趣,也能品出它的部分美點所在,但是總覺得還有微妙的趣味潛藏在語言文字背后,能感覺到卻又難以說清楚。這是因為他們只關注到同一個層面的幾個美點,卻不知道《春曉》有豐富的文化心理意蘊。
一、慵懶閑適的休閑文化:勾連讀者的審美心理
《春曉》除了節奏感和韻律感比較強外,還傳達出某種與讀者生活經驗相聯系的審美心理傾向。“春眠不覺曉”把“春天”和“早晨”兩種時間疊加在一起,“春”是一年之始,給讀者帶來“花紅柳綠”“生機勃勃”的詩意想象,“曉”是一天之始,充滿朝氣和希望。這兩種時間都含有生命勃發之意,也象征著美好生活的開始。“處處聞啼鳥”的“處處”,是用方位詞來描寫聽覺效果,突出鳥啼聲“熱鬧感”的強烈,傳遞了充滿生機的氣息。“不覺曉”寫出“睡到自然醒”的生活狀態,是一種愜意、慵懶、自由閑適的生活,是一種無憂無慮、不用承擔任何生活壓力的“任性”行為。心理的閑適、輕松與慵懶,排解心理壓力,是休閑文化的應有之意。這種看似沒有任何負擔和憂慮的生活讓經歷過人生疾苦、承擔生活壓力與責任的成年人產生強烈的向往之情,能激發他們對慵懶閑適的理想生活狀態的詩意想象。此詩蘊含的休閑文化對處于困境中的人具有“心理補償”作用。
二、意識復蘇與心理推理:激活詩歌文本的動態意蘊
(一)意識之變:沉睡、半醒與復蘇
“不覺曉”描寫的是“濃睡”狀態,其特點是對任何事物的感知都是處在“覺”與“不覺”之間,半睡半醒之間。整首詩呈現出作者的三種意識狀態:首先,“意識的沉睡”狀態,因為夜里的風雨聲都不能把作者喚醒,天亮了也不知道;其次,“意識的半醒”狀態,體現在他感知到了風雨聲,雖然沒有醒來,但是卻在潛意識中知道事件的發生;最后,“意識的復蘇”狀態,是鳥的啼叫聲讓作者從沉睡中漸漸醒來,意識到天亮了。這三種意識狀態按照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應該是“沉睡”和“半醒”狀態在前,“復蘇”狀態在后。但是詩歌結構的邏輯調整了這種發展順序,作者的意識先在啼鳥聲中“復蘇”,然后再對半夜的沉睡和半醒狀態進行“追憶”。三種意識狀態交織起來隱藏在詩中,讓詩歌傳達出朦朧、模糊而又迷離的氛圍,增強了詩歌的審美趣味,也讓詩歌具有一種流動性。
(二)心理推理活動:客觀推理與主觀推理
當意識復蘇后作者便開始了對外界事物的認知,這種認知不是用直觀視覺的眼睛去看,而是在聽覺的基礎上通過心理推理活動來展開。
1.客觀推理。詩的前兩句“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表達出一種因果關系:啼鳥聲攪擾了作者的清夢,讓作者從濃睡中醒來并意識到天亮了,“啼鳥”是“因”,“覺曉”是“果”。前一句雖說“不覺曉”,然而其表達的真正意義并非“不知道天亮”,而是在意識處于沉睡到復蘇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天亮了,從沉睡中逐漸醒來。作者是怎么知道天亮的呢?是打開窗戶看到的嗎?是走出房間看到的嗎?他不是通過視覺觀察直接看到天亮,而是根據群鳥熱鬧的啼叫聲推理出來的。這里有一種詩趣:“曉”與“鳥”不僅押韻,而且兩者在語意上還有聯系——通過“啼鳥”這一事物來表達“曉”之意,用“物”來傳達“時間”概念,建立了推理關系。這種源于客觀事物,根據客觀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系進行的推理就是客觀推理。這種判斷與推理恰好說明作者意識的復蘇,讓詩歌從聽覺轉向視覺(通過想象將鳥啼聲還原成群鳥啼叫的畫面),作者牽引讀者的感知從屋內轉向層外,認知范圍在物理空間上向外擴展。
2.主觀推理。“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也表達了一種因果關系,因為作者聽到風雨聲,所以他猜測屋外應該是花落滿地的景象。“風雨”是“因”,“花落”是“果”,然而刮風下雨必然導致花落滿地嗎?這種因果關系有必然性嗎?“風雨聲”是作者親耳聽到的、確實在夜里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他并沒有親眼看見“花落”現象,或者說“花落”并不是作者親眼所見的客觀事實,而是他內心的一種猜測,是根據“風雨聲”所做出的主觀推理。《春曉》前兩句構成“前果后因”關系,潛藏著客觀推理型內心活動,后兩句構成“前因后果”關系,潛藏著主觀推理型心理活動,在結構和語意上都呈現出“由淺入深”的遞進關系,讓詩歌因蘊有復雜的心理活動而拓展了品讀空間,更增審美情趣。詩歌文本本來是“靜態呈現”的,但是語句中體現的意識之變和心理推理活動讓詩歌“動態化”。
三、生命的文化屬性:增強了詩歌文本的厚重感
人是一個復雜的生命體,作為大自然的存在物,有自然屬性;作為社會存在物,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表現出社會屬性;人又是在歷史中存在的,個體的生命歷程和時代發展是融為一體的,因此有歷史屬性;人又是文化與文明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具有文化屬性。對于熟知寫作背景和具有豐富人生閱歷的讀者來說,除了閑適的生活情趣之外,《春曉》的另一層韻味是體現了作者對生命自然屬性、歷史屬性、文化屬性的模糊感知。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描繪的是一種無羈絆的、超脫世俗責任的、怡然自得的、平淡安逸的生命狀態,體現的是慵懶自由的自然生命。“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風雨”雖然處在“春天”的語境中,然而并不是和煦輕柔的春風,而是“摧殘者”的象征,和陸游在《卜算子·詠梅》里的“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里的“風雨”意象有著相似的隱喻。“花落”不是傳統文化意象里女孩面容逐漸憔悴的比喻,也不是“青春易逝”的象征,而是多少人才在“風雨”的摧殘下隕落的隱喻,暗含著坎坷、爭斗、兇險的人生體驗。通過對意象的文化象征意味、文化內涵的選擇、組合來表達情意,本身就是作者生命的文化屬性的體現。有人根據孟浩然早年隱居、中年入世求仕、晚年歸隱的生平經歷,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去解讀詩歌,認為“‘花落知多少’恰到好處地傾吐了身世飄零之感和政治壓抑之痛,或者借落花感嘆人事變遷、友朋零落的悲涼。”[5]本來只是某個清晨醒來的短暫的思緒活動,卻通過對夜里風雨的追憶拉長了詩歌的時間維度,還在“風雨”“落花”的象征文化中融入了一生的體驗,延展了生命長度,讓個體生命充滿歷史感。此詩的后兩句間接烘托和映射了被歷史和文化浸染的生命形態。生命的自然形態、歷史與文化形態潛藏于短短的四句詩中,加大了詩歌的內容含量和可闡釋空間,增加了詩歌的厚度。
四、意象心理化與詩歌結構形式變化:傳達作者瞬間細膩的心靈變奏
(一)意象的心理化特征
《春曉》景物描寫有一個獨特之處常常被眾多讀者所忽視:詩里的花、風雨、鳥意象沒有顏色、形狀等具體的形貌特征,作者只抓住這幾個意象的某一種存在狀態來傳達意義。“啼鳥”是什么種類的鳥?不是“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中表達愛情的比翼鳥,不是抒發遠大理想的鴻鵠,也不是傳達思鄉之情的大雁。其叫聲有何特點?不是“鳥鳴嚶嚶”的和鳴之聲,也不是“杜鵑啼血”的哀號之音,僅僅是熱鬧或者略顯嘈雜的散叫聲。讀者無法從品詩中得知“鳥”的種類和叫聲特點,說明作者營造鳥意象不是為了比喻和象征,不是用來直接抒情,而是要傳達“曉”的時間概念,完成由“鳥啼聲”判斷“天亮了”的客觀推理過程,突顯當時剎那間的心理活動。“夜來風雨聲”,雨下得多大?風刮得多猛烈?也沒有具體描繪,作者只是通過對“風雨聲”的追憶來傳達夜里曾經刮風下雨的事實,主要為下一句“花落知多少”作鋪墊。“花”更是泛指,什么品種什么顏色?開在哪里?開得稀落還是熱烈?這些具體特征也沒有描繪。“花落”不是眼前實景,而是想象中花朵被風吹雨打而掉落的狀態。為了表情達意的需要,作者只用聽覺來描寫事物,用主觀的心靈把這些意象的其他具體特征全部過濾了,目的是要直接觸及和突顯當時剎那間內心的真實體驗或感受。
(二)以詩歌結構形式之變來傳達主觀心靈變奏
此詩最妙的是作者用詩歌結構形式的變化來傳達心靈的變奏,使詩歌結構形式的改變和作者內心體驗的變化有機交融,實現了情感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統一。作者的心靈體驗在意識蘇醒的瞬間發生了轉變,從剛醒來時“不覺曉”的舒心和悠閑剎那間變成了“花落知多少”的哀傷,這種內心感受的轉變是通過詩歌“絕句”結構的變化來實現的。絕句一共四句,每句音節相等,主要有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兩種。它雖然押韻,但是不需要像律詩那樣嚴格要求對仗,有的第一、二句對仗,有的第三、四句對仗,也可以全篇都不對仗。“絕句的藝術結構不同于律詩之處是有種隱秘的,不容易被人們輕易認識的靈活性。”[6]《春曉》是一首有押韻而無對仗的五言絕句,體現了絕句靈活自由和富于變化的結構特點,突出表現在其“不容易被人輕易認知的”“隱秘的”靈活性上——句子語氣性質的變化。此詩第一句就不同凡響,直接以“不覺曉”的否定語氣給讀者帶來異樣的感覺,它在“覺”還是“不覺”的多義性增加了詩歌的可闡釋空間。第二、三句是陳述語氣,第四句是疑問或感嘆語氣,短短四個句子就有否定、陳述、疑問、感嘆四種語氣,極具變化性。古代詩人創作絕句時注重在第三句體現變化。楊載在《詩法家數·絕句》中說:“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7]絕句的第三句做出變化時,語意或者情感也隨之變化,這就是“轉”的作用。而《春曉》第三句還是在重復第二句的陳述語氣,句法上沒有變化,但是語意和情感卻開始轉變,因為它引出了第四句“花落知多少”(沒有第三句,第四句便沒有依托)。“花落知多少”從第三句的陳述語氣變成疑問或感嘆,讓整首詩再增一層變化。“知”還是“不知”呢?是在問人還是問己?作者主觀推測有花朵在風雨中凋落了,但是并非要問凋落的“量”,更多的是感嘆意味。詩歌前兩句體現的是“喜春”,而后兩句卻充滿傷感和擔憂,心境瞬間的轉換和詩歌結構形式的變化有機結合起來,讓詩歌充滿張力。
《春曉》以春天為題材,但是作者并不是用眼睛去看春,而是用心靈去感知春,蘊于其中的情感是多元的:有灑脫、有惆悵;有喜悅,有失落。簡單的四句詩勾出他的心靈變奏軌跡:初醒時的閑適,追憶時的傷感,最后是“花落知多少”的哀嘆。此詩有時間的變化,意識的變化,更有心靈感覺的變化,透過簡單的詩句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潛藏在語言文字背后的那顆敏感細膩的心。
古詩語言洗煉,每字每句都是作者精心推敲的結果,所以才有“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說法。因此古詩鑒賞要避免“似是而非”的淺表化闡釋,要對每個字詞進行仔細的玩賞,在涵泳體味中品出豐厚的文化內涵和作者的心靈,品出古詩的溫度與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