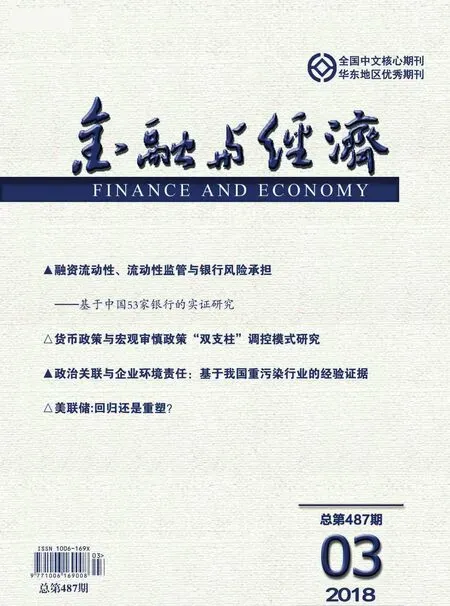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基于我國重污染行業的經驗證據
■聶嘉琪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劇。隨著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學術界開始逐漸重視企業環境責任的問題。現有文獻主要集中在從內部企業自身因素(張川等,2014)、管理者特征(李虹和張希源,2016)、企業外部環境壓力(Dasgupta et al.,2001)等角度探究了影響企業環境責任的顯性因素,而對企業與政府之間隱性因素的考察較少。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環境構成企業重要的外部生存環境,政治關聯已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近年來一些學者嘗試研究了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姚圣和程娜,2014),而關聯層級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卻少有關注。
轉型時期的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有著等級和相對自治的關系,激勵機制的錯配導致了不同層級政府之間政治目標的差異,從而其對企業行為產生的影響也不相同(李健等,2012)。分權的治理結構和以GDP為核心的晉升機制下,地方政府過度的關注經濟增長導致其偏離了中央政府的環境保護目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待環境保護的態度存在差異。因此,不同層級的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履行的影響也會不同。中央政府對環境保護問題高度關注,強化了與中央層級政治關聯企業對環境責任履行的認識,由于對中央政府資源的依賴,企業會通過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來為了維護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然而地方政府更多地關注本地區的經濟增長,與逃避環境責任的企業存在一定的利益共融性,因此企業能夠得到政府庇護,履行較少的環境責任。
本文以我國2010~2015年滬深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中央、地方層級政府目標的差異,分析不同層級政治關聯下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發現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能夠迎合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且在高環境規制地區由于較大的外部壓力加大了中央關聯對企業的重要性,其迎合的效果更顯著;對于地方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低環境規制下較低的懲處風險促成了其與地方政府的共謀關系,幫助企業逃避環境責任的履行。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基于中央、地方不同層級政府目標差異的框架下,進一步考察了不同層級的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從制度環境層面闡釋了我國各級政府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豐富了環境責任領域內的相關研究;(2)考察了不同環境規制對政治關聯層級與企業環境責任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了地區制度差異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企業環境責任
關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的影響因素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分別包含了企業自身特征和面臨的外部壓力兩方面的證據。
其中,企業自身特征決定了其履行環境責任的能力和意愿。首先,企業遵守環境規制需要付出成本,只有財務狀況良好、規模較大的企業才有相應的支付能力,張川等(2014)發現,企業財務績效的提升確實促進了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同時,以現金流為征收基礎的違反環境規制的罰金也會使得規模較大的企業積極承擔環境責任(Zhang et al.,2008)。其次,因為不同行業面臨著管制程度方面的差異,對違規成本的考量使得企業的環境責任履行存在行業層面的差異,相較于服務行業的企業,從事自然資源領域的企業更有可能制定環境保護方案(Henriques&Sadorsky,1996)。最后,作為企業重要經營決策的內容,對環境規制的遵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管理層自身理念,比如其對自身聲譽的追求。李虹和張希源(2016)研究發現,能力越高的管理層會因注重自身聲譽而將經營目標由“利潤至上”轉變為“以人為本”進而提升企業環境責任履行①關于管理層能力越高越注重自身聲譽的證據,詳見(Tadelis,2002)。。
企業面臨的外部壓力包括來自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其促使企業在可能的懲罰和潛在激勵間進行權衡。環境立法是企業首要面臨的制度壓力,目前學術界關于其有效性持兩種相佐觀點,Palmer et al.(1995)認為對環境立法的嚴格執行因成本太高而有損企業競爭力和生產效率;與之相反,“波特假說”則主張環境立法會激勵企業進行創新從而實現環保和生產率提升的雙贏局面(Porter&Claas,1995)。后續研究分別給出了支撐兩種觀點的證據:Cohen(1998)關于環境政策監督和執行的綜述類文章發現,多數實證研究表明美國的環境措施干預無關宏旨。然而,Dasgupta et al.(2001)卻發現,環境檢查大大減少了中國工業的空氣和水污染。隨著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諸如社區壓力、媒體報導和消費者、投資者市場等正在成為發達國家中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力量(Chen&Soyez,2003)。Zhang et al.(2008)、發現,利益相關者(客戶、股東、社區)的壓力能夠促進企業履行環境責任。Chen et al.(2015)發現企業的市場定位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的環境責任決策。
(二)政治關聯
政治關聯文獻的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都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Faccio,2006)。關于政治關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關聯對企業資源配置和企業價值的影響。Faccio(2006)發現,政治關聯有助于企業獲得政府資源,得到更多的銀行貸款、稅收優惠,也更容易進入政府管制行業,提升了企業價值。然而,另一些學者則發現了政治關聯對企業價值的負面影響。政治關聯企業在面臨危機時,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救助,但是企業的長期績效并沒有得到提升。田利輝和張偉(2013)發現政治關聯與國有企業業績負相關,與民營企業業績正相關。
關系是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重要制度,而作為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政治關聯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不容忽視(Allen et al.,2005)。政治關聯現象在我國企業中普遍存在,現有關于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履行的研究相對較少,且也未涉及到政治關聯層級的問題。本文將結合我國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的目標差異,重點研究不同關聯層級對企業環境責任履行的影響。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
“財政分權,行政集權”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某些政治目標上存在分歧,因此層級因素的影響在有關政治關聯的討論中不容忽視(Chen&Maggie,2009)。李健等(2012)發現了不同層級的政治關聯方式對提升企業價值的具體路徑選擇、企業CSR報告披露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即政治關聯在給企業帶來資源的同時,也為政府提供了傳達其偏好的途徑(林潤輝等,2015)。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由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價值和政府對環境責任的重視程度共同決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環境利益與經濟目標的差異,決定了其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會有所不同,因此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履行的影響應基于不同的政治關聯層級討論分析。
對于具有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來說,企業會積極主動的開展環境治理,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環境問題,其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傳達著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訴求。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經濟與環境兩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政府已將重心從高速的經濟增長轉移到更長期、平衡的中高速經濟增長和環境的協調發展。中央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應環保補貼、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的環境保護進行引導,鼓勵企業使用綠色技術,進行綠色生產。具有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能夠直接受到中央政府的引導,強化環境責任的履行;同時,中央政府為其關聯公司給予了支持,在環境責任履行方面也需要企業的回報,會對其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Oliver&Holzinger(2008)觀察到,為贏得政府的認可和相關的資源利益,企業可能會以一種典范的方式遵守政府的政策。由于對中央政府資源的依賴,企業為了維持與中央政府的長期關系,獲取關鍵資源,具有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會積極迎合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作為“回報”。同時,中央政治背景的高管具有的政治聲譽和社會影響力更大,其關聯的企業更容易被大眾媒體、政府所關注。一旦企業發生環境事故或者環境污染行為被曝光,將會損害此類高管的政治聲譽甚至危及其政治地位,也會對企業的形象造成很大損害。再者,較高政治地位的高管一般具有較高的素質和能力,較強的社會責任使命感,能夠和中央目標保持高度一致性,積極響應中央政府對環境污染治理的號召。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1: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為迎合中央政府,會積極的開展環境治理,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
相對于以公共福利為目標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動機導致其在環境治理方面存在執法困境,執行較為寬松的環境管制。對于具有地方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其更容易與地方政府達成共謀協議,在環境保護方面得到政府的庇護,較少的履行環境責任。李勝蘭等(2014)指出,分權治理結構和唯“GDP指揮棒”的激勵機制導致地方政府癡迷于經濟增長,而對環境保護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財政分權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夠從地方經濟增長中獲益,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會追求高經濟增長。同時地方政府也會通過做大GDP來取得政治上的升遷。在有限的資源和政府關注下,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重視往往會導致其忽視社會目標和環境保護。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會降低環境管制的標準(張華,2016)、縱容企業采用不環保或違規的生產方式、甚至會選擇與企業合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短期經濟增長(聶輝華和張雨瀟,2015)。同時,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高度關注也為企業的尋租提供了彈性空間,規避環境責任履行帶來的利潤損失。具有地方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可以憑借其與地方政府密切的關系,更容易與地方政府建立共謀關系,獲得地方政府的庇護,在環境監管方面獲得地方政府的“優待”。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2:地方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容易俘獲政府,在環境管制中獲得政府庇護,履行較少的環境責任。
四、數據與變量
(一)樣本說明
參考頡茂華等(2014)對重污染行業的分類標準,本文選取2010~2015年間在滬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業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同時,我們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1)剔除ST、*ST公司;(2)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3)為避免異常值對分析的影響,按照1%和99%的取值范圍對企業層面的連續變量進行了Winsorize縮尾處理,最終得到4286個樣本數據。
本文研究所需企業層面數據涉及企業財務和治理、最終控制人和高管政治關聯信息等四個方面。其中,財務和治理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最終控制人數據來自CCER數據庫,高管政治關聯數據根據CSMAR數據庫披露的高管簡歷手工整理得到。涉及外部環境等省級層面的數據分別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二)變量定義
1.企業環境責任。參照盧洪友等(2017)的做法,使用和訊網發布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評測體系中的環境責任評分作為企業環境責任的衡量指標,其主要由企業環保意識、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環保投入金額、排污種類數、節約能源種類數五個模塊組成。
2.政治關聯。政治關聯(PC)為虛擬變量,用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是否為現任或曾任政府官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進行衡量。進一步地,借鑒吳文峰等(2008)的做法對企業政治關聯進行中央政治關聯(CenPol)和地方政治關聯(LocPol)的區分。當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現在或曾經在地方政府部門工作、擔任過地方“兩會代表”、政協委員時,LocPol為1,否則為0;當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現在或曾經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或擔任過全國“兩會代表”、政協委員時,CenPol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并結合本文研究目的,我們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公司特征變量包括財務杠桿(Lev)、盈利能力(Roa)、企業規模(Size)、最終控制人性質(State)。公司治理特征變量包括股權集中度(Share)、CEO兩職合一(Dual)。變量的具體定義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本文的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ER表示企業環境責任,以和訊網發布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的環境責任評分進行衡量;PC表示政治關聯,具體而言,分別包含政治關聯總體PC、中央政治關聯CenPol及地方政治關聯LocPol。Controls為一組控制變量,分別包括企業自身特征方面的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最終控制人性質(State)和治理機制方面的股權集中度(Share)、兩職合一情況(Dual)以及行業(Industry)、年份(Year)控制變量。ε為模型干擾項。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
表2列示了單變量分析結果。我們將全樣本分為無政治關聯組、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組、地方層級關聯組進行對比分析。由結果可知,全樣本中企業環境責任的均值為3.3404,標準差為6.7389,表明不同企業間存在環境責任履行情況的差異。無政治關聯組中,企業環境責任均值為3.1619,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組中,企業環境責任的均值為5.2340,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在1%水平上顯著。而地方層級政治關聯組中企業環境責任的均值為3.2042,相對于無政治關聯組,兩者之間的差異不顯著。

表2 單變量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對主要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進行分析可知,企業環境責任與政治關聯顯著正相關。企業環境責任與中央層級政治關聯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地方層級政治關聯負相關且不顯著。政治關聯PC與地方政治關聯LocPol相關系數為0.835,說明企業大多建立地方層級的政治關聯,因兩者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后續回歸,故不會引起方程內部的多重共線問題。其他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均小于0.5,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股權集中度、兩者合一等控制變量符號同預期基本保持一致。
(三)回歸分析
表3考察了不同層級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第1列中,首先用全樣本檢驗了政治關聯(PC)與企業環境責任(ER)兩者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顯示被解釋變量企業環境責任(ER)與解釋變量政治關聯(PC)在1%顯著水平上正相關,系數為0.5032。即相對而言,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履行了更多的環境責任。第2~4列是中央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當期、未來一期及未來兩期環境責任間的回歸,我們發現中央層級政治關聯(CenPol)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中央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成正相關關系,說明具有中央層級政治關聯的企業,為維護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會積極迎合而履行了更多環境責任,且企業的迎合行為具有一慣性,假設H1得到驗證。第5-7列則展示了地方層級政治關聯對企業當期、未來一期及未來兩期環境責任的回歸結果,地方層級政治關聯(LocPol)系數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長這一經濟目標而與地方層級政治關聯企業進行共謀所致,從而致使地方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的不顯著。
從控制變量來看,企業資產負債率(Lev)與環境責任(ER)顯著負相關,企業負債水平越高,企業環境表現越差,可能的原因是負債水平高的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較大,企業會減少環保方面的資金投入,減少環境責任的履行。企業規模(Size)、盈利能力(Roa)與環境責任(ER)顯著正相關,表明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高的企業往往承擔更多的環境責任,這也與現有研究成果保持一致。企業產權性質(State)與環境責任(ER)顯著負相關,說明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履行了較少的環境責任。這可能一方面源于國有企業天然的政治任務和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則因為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受到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的歧視,使其資源獲取能力較弱,從而導致民營企業環保投入動力較弱。
(四)穩健性檢驗

表3 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不同關聯層級的影響
一是PSM配對檢驗。不同企業間自身的異質性可能會導致企業間政治關聯的差異性,引起不同企業之間環境責任履行情況的不同。有鑒于此,我們選用傾向匹配得分法來解決因企業間自身差異所帶來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根據PSM配對后的回歸結果,加入控制變量后,政治關聯(PC)的系數為0.4748,且在5%水平上顯著。CenPol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1.0992,表明中央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正相關,H1得到驗證。LcoPol的系數為0.1525但不顯著,表明地方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之間的關系尚不確定,H2未得到驗證。綜上所述,檢驗結果基本與前文回歸一致。二是改變樣本。由于國有企業天然政治關系,為了排除干擾,以民營企業為樣本檢驗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回歸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①由于文章篇幅受限,具體的檢驗結果未列出,留存備索。。
(五)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環境規制的影響
環境責任的履行不僅難以為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而且需要其投入巨額資金進行環保設備的購置或環保技術的革新,這使得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沒有積極履行環境責任的意愿(Orsato,2006),實際上,若沒有政府的環境管制政策與激勵措施,排污企業通常不會主動進行污染治理(原毅軍和耿殿賀,2010)。加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資源稟賦、環境污染程度、環境容量和生態狀況等還存在差異(唐國平等,2013),企業面臨的環境規制不同。同時地區間差異,也意味著政府將面臨不同的外部壓力,承擔不同的政治成本,政治關系所發揮的作用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不同的環境規制下,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
相對于環境規制低的地區,環境規制高的地區,環境監管力度較強,公眾具有較高的環保訴求,企業面臨較大的外部環境壓力、競爭壓力,這樣的環境下政治關系對于企業的發展十分重要。因此,在高環境規制地區,具有中央政治關聯的企業為了樹立良好聲譽、維護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會更加積極的迎合政府承擔環境責任;而對于地方政治關聯的企業,較大的外界壓力帶來的高政治成本切斷了企業與地方政府間的共謀,抑制了地方政府對其關
聯企業的庇護,被迫履行環境責任。鑒于制度環境可能存在的影響,我們進一步將樣本按照所處地區環境規制的程度不同進行了分組回歸,具體而言,借鑒李勝蘭等(2014)的方法,采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完成額與工業增加值的比值作為環境規制強度的衡量指標。根據均值大小,將樣本分為高環境規制樣本組和低環境規制樣本組,分組檢驗不同環境規制下,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環境規制的影響
如表4,第1、2列分別為高環境規制和低環境規制下中央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的回歸結果。在高環境規制樣本組,中央層級政治關聯(CenPol)的系數為1.7699且在1%水平上顯著;低環境規制樣本組,中央層級政治關聯(CenPol)的系數為0.7018但不顯著,表明在高環境規制下,中央政府面臨較高的外界壓力,其對關聯企業的環境責任履行會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加之政治關系對其發展的重要作用,企業會積極的迎合以實際行動來向中央政府表“忠心”,履行更多的環境責任。因此,在高環境規制下,中央層級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承擔的影響更明顯。第3、4列為不同環境規制下地方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的回歸結果。在高環境規制樣本組中,地方層級政治關聯(LocPol)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值為0.9437;在低環境規制樣本組中,地方層級政治關聯(LocPol)的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值為-0.5107,說明在環境規制高的地區,隨著外界環境壓力的增大,地方政府面臨的政治成本增大,阻礙了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共謀,抑制了地方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庇護作用,迫使企業積極的承擔環境責任,而在低環境規制下,地方政府面臨的外界環境壓力較小、政治成本較低,促進了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共謀,為地方政治關聯的企業實行寬松的環境管制,幫助其逃避環境責任。
六、結論與建議
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激勵機制的錯配導致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環境目標上的差異,本文以中國滬深A股2010~2015年的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不同層級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發現中央層級政治關聯與企業環境責任正相關,且在高環境規制地區正向作用更顯著,地方層級政治關聯對企業環境責任沒有顯著影響,但在高環境規制地區兩者之間顯著正相關,在低環境規制地區兩者之間顯著負相關。結果表明,在中國復雜的制度背景下,片面的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導致了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目標上的偏離,影響我國環境政策的有效發揮。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環境治理不僅需要完善的環境法律、法規,更需要提高環保執法力度,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2)調整干部考核指標,設計符合我國環境治理特征的多元激勵機制,轉變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觀念,引導地方政府重視環境問題;(3)環境治理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政府應該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業開展環境治理的動力,促使其積極的履行環境責任;(4)在環境規制相對較低的地區,中央政府應加強對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行為的監督。
[參考文獻]
[1]頡茂華,王瑾,劉冬梅.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企業經營績效[J].南開管理評論,2014,17(6):106~113.
[2]李虹,張希源.管理層能力與企業環境責任關系研究——基于模仿壓力和強制壓力調節作用視角[J].華東經濟管理,2016,30(08):139~146.
[3]李健,陳傳明,孫俊華.企業家政治關聯、競爭戰略選擇與企業價值——基于上市公司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2,15(6):147~157.
[4]李勝蘭,初善冰,申晨.地方政府競爭、環境規制與區域生態效率[J].世界經濟,2014,37(4):88~110.
[5]林潤輝,謝宗曉等.政治關聯、政府補助與環境信息披露——資源依賴理論視角[J].公共管理學報,2015,(2):154~155.
[6]盧洪友,唐飛,許文立.稅收政策能增強企業的環境責任嗎——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財貿研究,2017(1):85~91.
[7]聶輝華,張雨瀟.分權、集權與政企合謀[J].世界經濟,2015,38(6):3~21.
[8]唐國平,李龍會,吳德軍.環境管制、行業屬性與企業環保投資[J].會計研究,2013,(6):83~89.
[9]田利輝,張偉.政治關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長期績效的三大效應[J].經濟研究,2013,48(11):71~86.
[10]姚圣,程娜.政治關聯影響企業上交的排污費嗎——基于重點環境監控企業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2014,236(1):56~61.
[11]原毅軍,耿殿賀.環境政策傳導機制與中國環保產業發展——基于政府、排污企業與環保企業的博弈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10):65~74.
[12]張川,婁祝坤,詹丹碧.政治關聯、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來自中國化工行業上市公司的證據[J].管理評論,2014,26(1):130~139.
[13]張華.地區間環境規制的策略互動研究——對環境規制非完全執行普遍性的解釋[J].中國工業經濟,2016,(7):74~90.
[14]Allen F,Qian J,Qian M.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1):57~116.
[15]Chen W,Soyez D.The greening of industry:A research approach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geography[J].Geographical Research,2003,22(5):601~608.
[16]ChenY,Tang Get al..Linking Market Orientation and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Employee’s EnvironmentalInvolvement,andEnvironmental Product Qua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127(2):479~500.
[17]Chen,MaggieXY.TheMatching of HeterogeneousFirms andPoliticians[J].Economic Inquiry,2009,51(2):1502~1522.
[18]Cohen M A.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Policy[J].SocialScienceElectronic Publishing,1998,3.
[19]Dasgupta S,Laplante B,et al..Inspections,pollution prices,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6(3):487~498.
[20]Faccio 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21]Henriques I,Sadorsky P.The Determinants of a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Firm:An Empirical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Management,1996,30(3):381~395.
[22]Oliver C,Holzinger I.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cPoliticalManagement:ADynamic Capabilities Frame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33(2):496~520.
[23]OrsatoRJ.CompetitiveEnvironmental Strategies:WhenDoes It Pay to beGree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6,48(2):127~143.
[24]Palmer K,Oates W E,Portney P R.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The Benefit-Cost or the No-Cost Paradigm?[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119~132.
[25]Porter M E,Claas V D L.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4):97~118.
[26]Zhang B,Bi J et al.Why do firms engag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8,16(10):1036~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