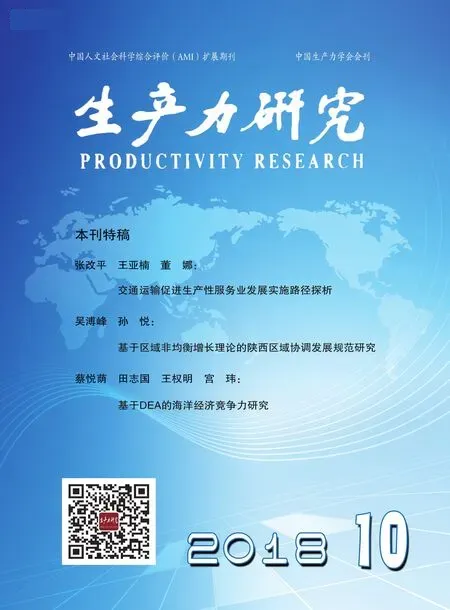中國傳統視域下森林可持續經營文化
王興文
(中共定西市委黨校,甘肅 定西 743000)
中國傳統森林可持續經營文化是我國人民在長期的林業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于森林利用、培育、經營和開發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根本目的就在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為子孫后代造福。
一、“以時禁發”的森林利用傳統
中國古人一直懂得人類與森林的關系密切。主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透過陰陽、五行、天人關系學說,以及圖騰崇拜、生態倫理等自然保護思想,就足以看得出來。翻閱大量古文獻,我們就會發現有很多合理利用森林的真知灼見。西周時期文王和武王就頒布政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1]春秋時期管仲提出“以時禁發”的森林思想,即順應樹木生長季節,封山林,以養育為主,冬天再開采利用或者在樹木成熟后采伐。秦代有一部法律叫《田律》,嚴禁春天樹木生長發芽的時候砍樹木,也不能堵住流水影響對森林的灌溉。不到夏天,嚴禁燒鮮草做草木灰,也不能摘取植物嫩芽等。唐朝的法律除了嚴格要求而且還要重重處罰。比如:盜取園林內花草樹木的,服刑兩年半。到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將古人的智慧概括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2]。
“取之有時”就是不違農時,按照二十四節氣,春種、夏長、秋收、冬藏。還是孟子說的好,“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人池,魚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用之有節”意思是對于可以開發的山林,開采利用的時候也要適時適度,也不能放任自由,掠奪式開采,否則,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正如《呂氏春秋·義賞》所言:“竭澤而漁,豈不獲得了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今雖偷可,后將無復,非常術也。”[3]后世歷代都在謹慎遵守老祖宗的教誨。
二、“任地養材”的森林培育傳統
(一)我國人工植樹造林的傳統由來久遠
《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播百谷草木”[4],帝顓頊則“養材以任地”[5]。周文王主張“潤濕不谷,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谷,樹之葛木,以為然絎,以為材用”[6]。
縱觀歷史,除了古人的思想及傳統,人工植樹造林大量實施并且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曾經沿長城邊有兩條蜿蜒茂密的榆樹林帶就是著名的“榆溪塞”。《周禮·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管子·度地》:“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明代治理黃河專家劉天和所著《問水集》總結了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6種栽植方法。“列樹表道”為中國古代的傳統之一。清代總督左宗棠在修筑通往新疆大道的同時,東起潼關,西迄烏魯木齊,沿途種植柳樹,成為史傳佳話。
(二)作品中有許多樹木名稱
中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匯集了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的許多詩篇,其中提到的樹木名稱有50余種。表明當時已能識別很多種樹木,并分類命名。西漢問世的《爾雅》是中國最早的詞典,已經有專門的單元篇目《釋草》和《釋木》。明代的《本草綱目》收錄果類104種,木類138種,禽類76種,獸類78種。清代《康熙字典》收錄果樹43種,樹木 394種,竹子 210種,獸類 236種,鳥類 439種。兩書所收樹木和野生動物種類比以前任何書籍更為齊全,幾乎包括了中國樹木和鳥獸的全部重要種類。
三、“種樹農桑”的森林經營傳統
古代具有農林牧復合經營的傳統。中國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農、林、牧、漁有機結合,使自然資源充分利用的大農業觀,這也是較早的生態農業思想。如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種谷篇》中有“瓜——豆”模式,明代鄺璠的《便民圖纂》中記載了“草——芝麻——谷”模式等。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所撰《農政全書》記述“若于園中開池,以便養魚灌園”,描繪出一幅生機勃勃全面發展的農、林、牧、副、漁的生態大農業景象。
森林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可以為人民生產出源源不斷的木材、山竹、果實、桑蠶等等。古代對森林效益的認識主要集中在經濟效益方面,在這方面有比較多的論述。《管子》:“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7]。孟軻說“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還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8]。《戰國策》記載“北有棗栗之利,民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實于民”[9]。這說明棗、栗等果實很早就被人們作為補助糧食不足的食物,可以解救貧困。
清雍正皇帝有政令:“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曠野,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供炊爨……”[10]
清乾隆帝也有政令:“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日三農生九谷,一日園圃毓草木,三日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日藪牧養蕃鳥獸。其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使山林川澤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澤丘陵之利。”[11]簡而言之,就是重視三農、園圃、虞衡、藪牧。
楊屾,清代著名農學家,在一本著作叫做《南風廣義》中有這樣的觀點:“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他的觀點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大農業”思想,森林是屬于大農業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四、“周而復始,永世無窮”的森林開發傳統
在長期的林業實踐中,我國古代形成了豐富的森林開發思想,而且,這些思想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逐漸地被具體化為徑級擇伐法和森林輪伐法。據《莊子》記載樹木不能“中道之大于斧斤”,應該“終其天年”。《禮記·王制》載:“木不中伐,不鬻于市”。這一規定可以理解為不達工藝成熟齡的樹木不許砍伐,伐下了也不許出售。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首次提出了輪伐法,即“周而復始,永世無窮”。
(一)中國古代注重對森林資源的綜合利用
隨著農業、手工業和文化的發展,人們對森林的認識日益深化,除木材外,又認識到漆、松脂等許多其他森林產物的作用,并目、逐步摸索出了比較完善的加工、利用方法。
除了用木材制作家具和器皿、建造房屋和宮廷樓閣、打車造船、建筑橋梁,以及從果樹上收獲果品外,還有許多用途,如木炭、造紙、油漆、松脂、樟腦。油料、藥物、燃料、香料、蠶絲、竹材、茶葉等,不僅歷史悠久,其加工水平也達到了相當發達的程度。
(二)重點開發森林的生態功能
1.積極利用森林的保持水土功能。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管子》一書,已認識到森林的保持水土作用。為了對水旱災害做到有備無患,管仲主張合理興修水利,“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同時,管仲是一個很有科學思想的政治家,他認識到樹木的根系,可以防砂固土,防止水土流失。他綜合運用水土保持理論,種植大量林木尤其是在堤岸周圍,《管子·度地》是這樣記載的:“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漢代的時候,人民已經認識到了森林系統的重要性,森林可以基本穩定某一小區域的氣候環境,保持好森林體系可以免受水災旱災,知道了破壞森林會導致自然災害。到了明朝,除了統治者,老百姓對森林的認識都到了一個高度,自覺認識到森林的重要性,森林可以涵養水源,老百姓都自發地植樹造林,保護森林,尤其是水源林。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書中有過這樣的記載,描寫這樣的實際圖景:“流溪地方(今廣東從化流溪河),深山綿亙,林木翳茂,居民以為潤水山場,二百年斧斤不入。”[12]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西寧(今廣東郁南)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于多林木也。凡水生于木,有木之所,其水為木所引,則溪澗長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還說“川竭由于山童,林木暢茂,斯可以言水利”[13]。這是對森林水源涵養效益的深刻認識。
2.利用森林防護農田。這個優勢和特點到清代許多仁人志士已經認識的很清楚。他們都意識到不能過度地開墾山林,并且提出了怎樣來防止和治理的意見和措施。趙仁基(1834)已經正確地認識到長江“水溢”與山林被開墾的密切關系:“水溢由于沙積,沙積由于山墾。”[14]同時,清代江西散文家、陽明學說的積極實踐者魯仕驥也認識到“必也使民樵采以時,而廣蓄巨木郁為茂林,則上承雨露,下滋泉脈,雨潦時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15]。
可是在清代中期,出現了很不好的現實和現象。由于人口激增,許多人開始開墾山林,引發多地水土流失。后果是嚴重的,教訓是慘痛的。梅曾亮在其《柏枧山房文集·卷10》中記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砂石隨下,奔流注壑,……畢至畦田中乃止”[16]。
3.利用森林保護生態環境,可以增加生物多樣性。荀子的《勸學》中說到:“草木疇生,禽獸群焉。”荀子《致士》中又說:“川測深而魚鱉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并且古人雖然沒有提到“生態”這個詞,但確實已經對森林所具有的多種生態功能有了深刻認識,已經懂得了可持續發展。這種認識是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呂氏春秋》云:“竭澤而漁,豈不獲得了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17]這些著作和言論都為日后重視、培育、保護、發展森林資源及其它的可持續經營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充分延展并開發人與森林和諧共生的關系
人們在長期與森林樹木相依共生的實踐中,逐漸形成豐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有關森林的美學文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詞、書法和畫作。比如孔子登臨泰山、莊子御風而行逍遙游與山林皋壤、屈原《山鬼》篇、陶淵明《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明代著名的地理旅行家徐霞客也留下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記》……春夏秋冬、大好河山、風光不同,物候交替、鳥語花香、桃紅柳綠,無時無刻不體現出一種生命的魅力,讓人情不自禁陶醉其中,藍天白云、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古人愛森林、游山林、享清風白云,希望健康長壽。每每將寺院廟宇建造在水草豐茂的幽深密林中,意為“草木郁茂,生氣相隨”“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古人還經常在自家宅院園林中種植大量花果樹木,比如在甘肅蘭州的仁壽山就有百年桃樹,至今還在舉行每年一度的桃花會;甘肅什川就有千年的古梨樹群;平涼靈臺就有一棵千年槐樹,至今人有很多人去瞻仰膜拜……祁連山脈是中華水塔,甘肅重要的深林水源涵養地,是一座屏障,更是一座寶庫,孕育并承載了五彩繽紛的祁連山森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