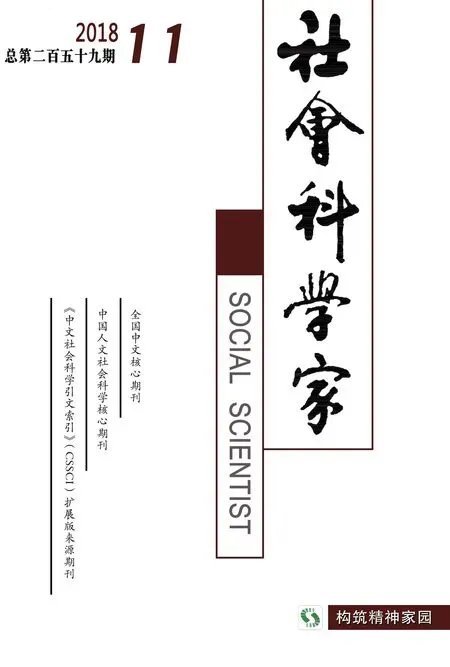文學旅游視域下的審美資源開發與利用
吳英文
(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都勻 558000)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對現實世界和作家心靈世界藝術性的審美再現,旅游是以游覽觀光為手段,以達到旅游者休閑娛樂或充實情感世界目的的審美追求。二者的共通之處在于,都是滿足人類精神需要的審美活動。因此,文學與旅游的結合并非偶然,而是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成功的審美互動形式。自先秦以來,由旅游活動生發而來的文學作品源源不斷,文學作品也將其人文內涵和精神內核轉化為旅游資源注入相關的旅游環境中,對旅游者形成獨特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經濟迅速發展、交通方便快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當代,“文學資源被視為一項經濟持久的旅游資源得到廣泛的開發和利用”[1]“文學旅游”也逐漸成為旅游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眾多針對文學旅游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研究者在對文學旅游的概念、特征、現狀、價值、保護措施、開發策略等問題進行論述時,其研究對象或所援引例證絕大多數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旅游資源開發的案例,也可以說是文學遺產旅游案例,如《論文學旅游》(兆康,劉德艷)中提到的四川三國蜀漢遺跡、北京與上海的紅樓夢大觀園,《論文學旅游的價值》(盤曉愚)中列舉的湖南桃源縣的桃花源、長江北岸的白帝城,《文學旅游地的遺產保護與開發》(張維亞)中研究的南京夫子廟李香君故居和王謝古居等等,不勝枚舉。而當代文學資源應用于旅游開發的案例屈指可數。筆者在知網數據庫中以“文學旅游”為關鍵字進行檢索,選取檢索結果中的前20篇期刊論文為調查對象,其中3篇涉及到當代文學旅游地,僅占總數的15%。雖然這個數據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能夠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代文學資源的旅游開發現狀不甚理想。
從理論上講,當代文學作品是當代作家審美經驗外化的產物,此審美經驗不僅取決于作家個人的智識情感水平,同樣來源于作家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與意識形態環境。與作家處于同一時空環境下的旅游者應該對當代文學更容易產生審美共鳴,那么,何以以當代文學為藍本的旅游活動明顯弱勢于文學遺產旅游?當代文學是否存在旅游價值?應如何開展當代文學資源的旅游開發?要回答上述問題,首先須明確什么是當代文學旅游。本文擬從當代文學旅游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對上述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
一、文學旅游相關基本范疇與內涵
了解當代文學旅游,首先必須確定兩個概念:一是“當代文學”,二是“文學旅游”。
一般來講,“當代文學”指的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文學創作。社會性質與意識形態的改變影響著人的情感意識與人生體驗,文學創作的結構也因此產生變革。當代文學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文學在現代化、市場化、科技化等種種因素的摻入下發展成與封閉含蓄的古代文學和身負社會重責的現代文學截然不同的,充溢著自由化和個性化的生態結構,足以為文學旅游提供豐富的人文資源。
而對于文學旅游這個相對年輕的課題,國內外學者根據各自研究的側重點,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國外學者往往把文學旅游直接劃入遺產旅游的范疇。如波利亞(Yaniv Poria)等學者的觀點“文學旅游地是一種文化遺產,其價值建立于作為文化遺產的文學價值上”[2]與赫爾伯特(Herbert)的觀點“文學旅游地……與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緊密相連,作為一種遺產景觀吸引旅游者”[3]均顯示出此種論點。
國內學者則往往以旅游者的旅游動機為著重點,強調文學旅游實現的基礎在于旅游主體對文學資源的情感需求。例如,兆康等(1993)認為文學旅游須“以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為依托,利用其知名度和各地區、各階層的人對文學作品的認同感和各自的審美趣味”[4],從而借助物質手段再現文學作品中的審美情境,使旅游主體得到“全方位”的物質文化享受。王洋(2010)在定義旅游文學時也指出文學旅游的基礎是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前往與作品相關的(包括與作者相關)目的地而度過一種短暫的綜合經歷。”[5]
對于文學旅游資源,研究者們的定義一般以描述為主,認為其應具備如下特征:(1)對旅游者構成一定的吸引力,能夠促使其產生旅游動機;(2)“在物質基礎上產生并依附于物質而存在”[6];(3)與文學(包括作家、作品以及作品內真實或虛構的形象或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可見,對旅游者的“吸引力”是文學作品得以物化為旅游資源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說,只有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吸引力足以催動大規模的受眾生發出對作品相關的背景環境身臨其境的情感需求時,它才具備旅游開發的可能性。
綜合當代文學旅游的客觀限制與主觀特性,筆者將其定義為:人們被當代(1949年至今)文學作品中的審美世界所吸引,從而進入與審美世界相互印證的相關現實世界中,以切身體驗獲得情感需求或審美需求上的滿足的行為過程。文學旅游資源的意義就在于有文學作品、文學作者或文學范式與旅游資源產生了某種聯系,使得該旅游資源擁有了文學旅游附加值。由于文學附加值的引入,文學旅游資源可定義為:因擁有文學旅游附加值而對旅游者產生旅游吸引力的旅游資源。[7]當代文學旅游資源則是與當代文學作品相關聯的,具備旅游開發潛力的文學景觀、自然景觀與社會景觀。
二、作為旅游新業態的文學旅游特色表征
從旅游業態的發展視角來看,需要注意的是,文學旅游資源并不是一種新的旅游資源類型,而是從獲取旅游體驗的角度對旅游資源內涵的豐富。從理論上講,任何旅游資源都有成為文學旅游資源的可能性。不同的文學旅游者,因為他們各自文學修養與素質存在著差異,對某旅游資源文學旅游附加值的認識存在差異是許可的。而對非文學旅游者來說,雖然文學旅游附加值可能并不是產生旅游動機與獲得旅游體驗的主要因素,但這并不影響該旅游資源的其他附加值對游客旅游需求的滿足。[8]而由當代文學旅游的概念可知: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一樣,都可以為旅游活動提供廣泛的人文資源,是文學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成分和生力軍。例如,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其家鄉山東省高密市東北鄉掀起了“紅高粱文化旅游”熱;古華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芙蓉鎮》經謝晉導演進行電影改編后,湖南省湘西州的芙蓉鎮(原名王村)成為聞名遐邇的旅游景點;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帶動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的桃花島旅游風靡一時等等。然而,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典例外,當代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應用似乎稍顯弱勢。這與當代文學旅游的特征密切相關。
1.依賴于現代傳媒的資源“本體性”
國家標準旅游資源(Tourism Resources)的定義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均稱為旅游資源。”[9]因此,文學作品成為旅游資源的前提是必須具有開發的潛力,也就是被大多數潛在旅游者所認同并接受,并與旅游主體建立起具有“相當的共同性”的文學觀念,從而產生令潛在旅游者前來造訪并獲得效益的“吸引力”。這要求待轉化開發的文學資源本身除了審美價值之外,必須擁有廣泛的受眾規模。受眾規模代表了文學資源吸引力的強度,也預示了其所能創造的效益規模。
古代文學作品絕大多數由于千百年來的歷史層累性,早已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和認同,部分現代文學作品也在時間的洗禮下或學校教育的著意宣傳中獲得了知名度與影響力,為二者轉化為旅游資源提供了豐厚的客源基礎。如古代文學中《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滕王閣序》、《岳陽樓記》對應的江南三大名樓,現代文學中沈從文的《邊城》對應的湖南鳳凰古城等均屬此列。
當代文學作品產生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當今社會,首先,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可以讓它們自然而然地淫浸人們生活的字里行間,其次,高強度的生活壓力與越發物質化的價值觀念使人們越來越遠離文學。這導致了當代文學資源的接受規模愈發狹窄,同時也是當代文學旅游相對勢微的原因之一。
當前,大眾對于當代文學的了解與認同主要來源于影視媒介與網絡媒介,當代先進的媒介技術成為決定文學受眾規模的首要因素。我們往往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一些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和審美價值的作品不為人知,而一旦與影視媒介相結合,立刻成為人們爭相追捧的對象。例如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版于1986年12月出版,1991年3月獲得中國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然而,這并沒有給路遙的故鄉陜西榆林清澗縣或故事的發生地“原西縣”帶來任何的旅游效益,直到2015年由其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熱播,陜西神木縣高家堡古鎮作為電視劇中“原西縣”的取景地一夜成名,僅2015年清明節期間,該景點便接納游客約4.5萬人次。這充分顯示出對媒介的高度依賴成為當代文學資源得以向旅游資源轉化的關鍵。此外,一些在藝術水平或審美價值上不占優勢、但誕生并傳播于網絡媒介的作品,其受眾規模遠遠超過以其他媒介形式存在傳播的文學作品,因而成為了豐厚的文學旅游資源。因此可以說,當代媒介技術是決定當代文學資源受眾規模以及對潛在旅游主體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當代文學資源進行旅游開發的重要助力。
2.解構與重構中獲得的“意義”與“真實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文化的多樣性也正在一點一滴被侵蝕,逐漸呈現出世界趨同或融合的趨勢。當人們身處北京、上海、紐約、東京、巴黎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往往會出現一種“迷路”的錯覺,同樣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川流如潮的街道、五色斑斕的廣告標語,城市規劃與社會文化的趨同性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產生一種迷失在浮躁中的虛無感。這正是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的初衷,他們渴望通過對異質文化的體驗與平常生活感受的碰撞與反差尋求自身存在的真實感。陶淵明塑造的桃花源、魯迅筆下的魯鎮與咸亨酒店、陳忠實文中的白鹿原,這些文學作品中虛實結合而遺世獨立形象世界則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探索空間,吸引著游客在同與異、真與幻之間獲得移動的存在感與探究的真實性。因此有學者說:“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現代旅游者希望在旅行中尋求日常生活里所缺乏的‘真實性’”。[10]
在旅游學理論中,關于“真實性”的理論主要存在著4種,分別為:“客觀主義真實性(強調旅游對象的真實性)、建構主義真實性(強調旅游對象的真實性與旅游體驗的真實性的相互作用)、后現代主義真實性(強調旅游的表層性、娛樂性與非真實性)和存在主義真實性(強調旅游體驗的真實性)”[11]。當代文學旅游所追求的真實性不同于以上任何一種。
首先,由于文類的進化演變,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小說地位大大提升,已經取代了詩歌散文,成為受眾群體最廣的文學樣式,并由此在當代文學旅游資源中占據主體位置。而由于小說本身存在的虛構性,導致絕大多數文學形象世界都不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到相對應的實體,需要旅游開發者的著意塑造去建構“虛擬”的審美實體,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旅游對象的客觀主義真實性,而這也成為當代文學資源開發滯后于具備“客觀主義真實性”的古代文學資源的原因之一。
其次,當代文學旅游者往往是帶著“朝圣”的心理進行旅游活動的。正因為當代文學的傳播并不像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那樣普及,使得當代文學旅游的潛在主體具有高度的純粹性,他們必然對作品或作者懷有深切的情感,并為此種情感吸引支配進而產生切身體驗故事的發生場所或與作者相關的場所的欲望。這種旅游活動帶著獨一無二的目的性,與普羅大眾懷著休閑放松的心態游覽“三大名樓”或西湖斷橋等行為所指示的情感追求完全不同,因而也從主體情感需求上推翻了存在主義真實性。
第三,由文學旅游資源的概念可知,文學旅游必須依附于與文學作品或作者相關的物質而存在,當代文學旅游自然也不例外,否則旅游者的“朝圣”地將不復存在,后現代主義真實性所追求的娛樂化的非真實顯然也并不符合當代文學旅游。
第四,與其說當代文學旅游者在旅游中追求的是對文學形象世界身臨其境的審美體驗,不如說其追求的是一種情懷,蘊含著“愛與歸屬感”和“自我實現”的宗教式的情懷。建構主義真實性的理念中,作為旅游對象的現實需要文學作品進行審美提升,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世界也需要通過有形的現實進行審美定型。與建構主義真實性所強調的旅游客體的真實性與旅游主體體驗的真實性的相互作用不同,當代文學旅游者更側重自身對于文學作品的審美情感的皈依,現實世界在這里或許僅僅是一個地標,一個情感符號。例如,2015年8月由網絡小說《盜墓筆記》中的“十年之約”所引發的長白山旅游熱潮,有媒體報道稱,當地景區游客量飆升50%,即使景區與小說作者南派三叔分別在微博上予以警示,依然沒有阻擋住旅游者們的腳步,導致景區不堪重負。在這場突如其來的近乎“瘋狂”的超大規模文學旅游party中,作為旅游對象的長白山景區不曾也沒有時間去建構文中所描寫的“云頂天宮”或“青銅門”,但這并不妨礙旅游者們把這里當作他們的“圣地”,去印證他們情感皈依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正是解構了傳統真實性理論,在當代文學旅游資源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另類的“宗教主義”真實性。
3.審美體驗式消費的即時性與在場感
謝有順對我們當前的時代評價為:“這是一個大時代,也是一個靈魂受苦的時代……眾人的生命多悶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來,心思散亂,文筆浮華,開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這樣,在我們身邊站起來的不過是一堆物質。”[12]正因如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愛的歸屬感”與“自我實現”,都需要尋求情感的釋放與皈依。這樣迫切的情感需求使我們更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對某個文學形象的審美沖動,而時代的焦慮所帶來的靈魂的喧囂也導致對這種審美沖動不能沉淀到骨骼,而會隨著新事物的干擾或時間的推移迅速流逝。短暫的審美沖動有可能在機緣巧合之下轉化為旅游動力,但這樣形成的潛在客源群體似乎并不牢靠。《平凡的世界》電視劇熱度退卻后,高家堡古鎮的旅游熱亦隨之冷卻;《盜墓筆記》“十年之約”所締造的“擠爆”長白山旅游現象也僅僅是恰逢其會的曇花一現,其后長白山景區的資源建設中心依然要放在自然旅游資源上。由此可見,在當前的社會文化環境下,當代文學資源的吸引力所能構成的旅游沖動大多是短暫而盲目的,帶有并不穩固的即時性,因而要把這樣的旅游資源最終轉化為旅游產品仍具有一定的風險。這也是當代文學旅游開發受到局限的第三個原因。
盡管當代文學作品作為旅游資源的潛力尚存在不確定性,仍有不少旅游開發者選擇對其進行策劃開發。如網絡小說《瑯琊榜》改編同名電視劇播出并網羅了大量受眾之后,安徽滁州瑯琊山景區將景點“會峰閣”更名為“瑯琊閣”,以期契合作為文本受眾的旅游者的“瑯琊”朝圣情結,從而帶動瑯琊山旅游業的發展;著名的旅游地江西婺源也因小說《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廣泛傳播及同名電影的熱映,打起“重溫青春”的旗號,為本就具備豐富自然旅游資源的美麗古鎮又附加了一層“見證愛情的圣地”的浪漫深意。以上兩個案例都是通過文學資源的融入對旅游資源進行人文再建構,從而達到旅游效益最大化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并不是完全以作家或文學作品作為開發的母本,而是在原有的自然旅游資源的基礎上載入文學附加值,從而達到建設人文屬性,增強旅游地吸引力的效果。文學資源的融入所需投資不大,其存在與否對旅游客體本身不構成決定性的影響,這是當地文學旅游得以實現的根本原因。旅游管理者在進行文學旅游開發的過程中,文學資源提供的旅游附加值與其投入值的比例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三、基于旅游業態文化轉型的文學旅游資源開發與利用
文學旅游區別于一般旅游活動的本質在于,旅游者始終懷抱著來源于文學深處的“尋根”情懷。何謂“尋根”?當前社會中,按部就班地行走在嘈雜與焦慮中人們在生活的重壓下變得越發機械化,越發遠離自己的靈魂。而文學作為心靈世界的話語,代表的是人類精神存活的證據。人們從文學中獲得感動,并在這種感動的支配下去探尋審美藝術的源頭,從而獲得自我靈魂的真實。當代文學與當代人們有著天然的血緣聯系,因其生存的社會環境存在著共通性。它是人們生活的一面鏡子,人們更容易在其中獲得“尋根”的滿足。因此,當代文學是滿足人們“尋根”情懷的重要資源,當代文學資源的旅游轉化開發應該得到重視。而文學旅游資源中,因古代、現代、當代文學各自的時代特性賦予了文學資源不同的特征,這也決定了在對不同的文學資源進行旅游開發時應“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策略。筆者針對當代文學旅游的特征及發展局限的原因特提出以下建議:
1.開放與利用應進一步嵌入全新媒體技術并高效利用其網絡化效應
影視媒介、互聯網媒介目前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首要渠道。人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對作者的了解、對故事情節可能發生地點的判斷、對文學旅游行程的規劃、對旅游效果的預判等絕大多數信息均來源于當代媒介。一般情況下,潛在旅游主體所掌握的信息量越多,其最終決策出行成為真正游客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無論是旅游開發者還是旅游管理者都應伸出敏銳的觸角,對媒介信息交流引起高度重視。
作為旅游開發者應在媒介中獲取前沿信息,及時掌握當代文學發展動態及受眾規模的變化,并隨之對開發對象作出調整。吉林省青年商務國際旅行社總經理由杰在接受采訪時就曾經表示:“這些年,大眾旅游和流行文化已經緊密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還是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如果能夠跟時下流行文化元素結合起來,就能收到意料之外的效果。”[13]這“意料之外的效果”正是來源于旅游開發者對媒介信息的密切關注,從而能夠為游客提供普遍興趣內容的旅游活動。如攜程集團推出的“南寧+德天瀑布+通靈峽谷2日1晚私家團·訪花千骨拍攝地私人定制”、“長春+長白山5日4晚跟團游盜墓筆記-話劇版云頂天宮獨家”都是與媒介高度結合的成功的旅游開發案例。作為旅游管理者應利用媒介發揮好廣告、宣傳、解說的作用,給旅游者或潛在旅游者提供準確的信息,提高文學旅游地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同樣,影視業作為現代大眾傳媒的集中反映類型,它對文學資源所承載的巨大的甚至決定性的輻射作用已成為基本事實,因而影視業與旅游業之間的互動已成為各自發展模式中的題中之意而理所當然。作為中國最具特色的影視中心,浙江橫店影視城憑借其宏大的基地規模、豐富的拍攝場景以及良好的配套服務,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號稱“中國好萊塢”,截至2017年底,已有超過2500部中外影視作品在此拍攝,約占全國古裝劇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接待劇組近500個,20年年均復合增長速度24.2%1。2010年4月18日,國家旅游局正式授予橫店影視城為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據橫店影視集團數據顯示,橫店影視城2017年旅游人次超過1800萬人次,2018年更是超過了2000萬人次,已超過故宮、西塘、峨眉山等旅游名勝景區,成為國內影視旅游行業最具標桿性的影視基地和影視文化旅游基地。而影視劇作為當代文學最受歡迎和消費號召力的資源形態,自然也成為拉動當地旅游消費的重要營銷手段。而浙江橫店拉動旅游業高速增長的營銷策略即是:以影視拍攝基地為基本依托,以影視文學為基本內容,以旅游觀光為主要業態,以體驗娛樂為基本目的。浙江橫店這條影視旅游的營銷策略,可以說給當前國內影視文學旅游提供可資借鑒的啟示參考:通過免費提供拍攝場景,從而吸引劇組前來拍攝,然后再通過影片拍攝的市場號召力和影響力,來擴大橫店影視城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從而打造橫店影視文學旅游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前來影視城旅游的人數達到連年遞增。正如英國文化學者約翰·尤瑞(John Urry)在其代表作《游客的凝視》中發人深省的指出,電影中的場景會促進現實旅游業發展的萌芽趨勢,即“你只要拍攝它,游客就會到來”。
2.精準把握審美體驗及其物質載體之間的情境維度張力
從本質上來講,旅游活動的目的在于尋求陌生化的美感體驗,然而,當代文學旅游“情感皈依”的真實性要求文學旅游地必須獲得旅游者源于文學作品的情感認同。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悖論,既要尋求觀感上的“陌生化”,又要滿足精神上的“同一化”。實際上二者是可以調和的。
這種基于“移情作用”的體驗式消費邏輯的互動模式,往往表現出的特點是具有較高的文學附加值的文學旅游資源,同時也能夠聚合和傳達出相應的品牌效益和符號營銷效應,而非文學旅游附加值也表現出較高的水準和質量,而且二者關系也保持著相對均衡的對比度。這種關聯互動模式往往在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上往往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文學旅游附加值與非文學旅游附加值這兩種價值形態,在開發和利用的過程中一般都是作為雙重點加以盤活,互為襯托,聯動互助。應用這種模式開發的文學旅游產品與其他旅游產品,都必須依靠對方來鞏固提升自己的地位。當然,這種模式對挖掘文學旅游資源的“文學性”要求相對較高,如許多經典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耳熟能詳、婦孺皆知的知名作品,如《水滸傳》《三國演義》《濟公傳》等,由于受眾度極高,如果所對應的文學旅游資源同時也擁有其他較高的旅游體驗附加值,采用該開發模式,一般都能收到較好的效果。
其實,文學旅游本身就是一個虛實結合的審美體驗過程,在旅游活動尚未開始之前,旅游者就會根據文學形象形成對文學旅游地的主觀想象,想象中的虛幻世界與現實中的實體世界相互印證的過程也是旅游者獲得真實感的體驗過程。當代文學旅游者對“真實性”的要求更偏重于情感的自我實現,而非文學旅游地的客觀形象的真實。因此,旅游開發過程中對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世界過度的復制,使原本虛構的世界一板一眼地呈現出來,反而會給游客造成一種對現實的抽離感,無法實現靈魂的“尋根”。比如,文學巨著《白鹿原》有著廣泛的知名度,而其成功的電影化更為這部史詩巨著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群眾共識空間。而以此為基礎于2013年建立的白鹿原影視城,其成功運營則體現出文學資源與旅游開發的有機結合所能產生的巨大綜合效益。首先,白鹿原影視城將小說中的經典場景進行了的精準復原,如白鹿村、祠堂、牌坊、田小娥窯洞等,讓游客通過這些場景再現而與小說中的場景意象發生符號聯想,觸景生情,從而更加直觀的感受到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特定的意境和氛圍。同時,為配合這種意象聯想和審美體驗,影視城還組織推出了多種多場關中民俗文化演出節目,以動態的行為文化讓游客獲得更加形象、真切和靈動的文化體驗,而且在演出中還會根據劇情需要和特定內容場景邀請游客觀眾互動甚至參演,使其能夠通過角色扮演和實景演出進一步強化自身在小說中初步形成的審美體驗,從而促動他們在直觀、形象和真實的文化氛圍中強化文學審美體驗,并增加文學審美趣味的品位高度。2017、2018白鹿原影視城連續舉辦兩屆關中民俗文化節,安排諸如社火、高蹺、鑼鼓、折子戲等關中特色的民俗活動供游客游玩。這種通過真實的體驗來感受文學作品中虛擬想象場景的方式,既是通過具體的活動來感受關中文化,又能通過整體把握關中文化而更好的體會小說所傳達出的文化氛圍。
因此,掌握好文學旅游地“虛與實”、“真與幻”之間的度是十分必要的,既要讓旅游者認識到這里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圣地”,又要顧及到旅游者情感印證與實現的需求,這需要旅游開發者長期的揣摩實踐,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3.應立足復合式的運作平臺和多元化的發展趨向
當代文學資源對人們構成的吸引力往往是強烈而短暫的,這種審美的即時性決定了旅游開發者不應對某一旅游地進行單純的文學旅游開發,而應慎重地綜合作家、評論家、旅游者的意見,將觀光、科考、度假、娛樂等多個開發方向納入考慮范圍之內進行專業科學的景區設計。一旦文學旅游地的“文學資源”吸引力下降或消失,對當地的旅游產業不會造成毀滅性的傷害。此外,文學旅游資源與非文學旅游資源在作為旅游產品開發時同時作為重點,互為依托、互重并行,有利于二者相互鞏固,共同提升旅游產品的品質,令旅游者獲得更佳效果的旅游體驗。
綜上所述,當代文學作為旅游資源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強勁的生命力,但由于自身特征導致當前發展狀況受到局限,因此,針對當代文學旅游資源的特征尋求其發展之道是文學旅游研究的當務之急。筆者所提出的幾點不成熟的建議僅作拋磚引玉之用,相信在旅游開發者與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當代文學旅游的發展前景將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