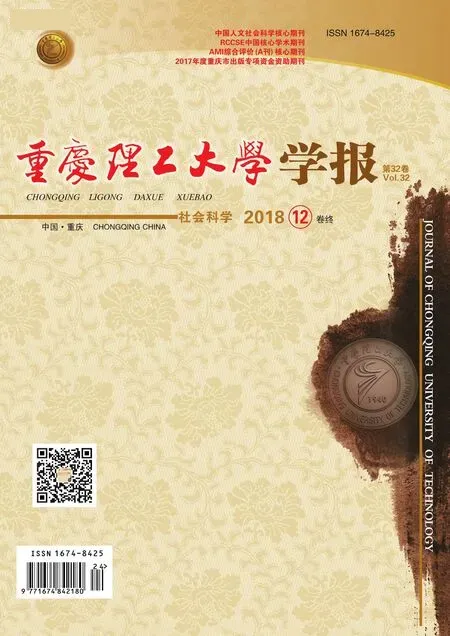規范行為:生物本能vs.社會實踐
——兼論維特根斯坦的“遵守規則”理論
樊岳紅
(山西大學 哲學社會學學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一、規范行為的兩種解釋
當哲學家們對感官知覺進行反思時,他們通常把焦點放在我們的經驗信念和知識是如何由經驗事實來合理辯護的問題上。神經生理學家通常是通過分析發生在我們神經系統中的因果關系,來最終闡明感性經驗。與神經生理學家不同的是,哲學家通常所追問的是對感性經驗的辯護理由。而還原論者又試圖通過把感知的哲學理論還原為科學事實,但還原論者的這種方法面臨兩方面的難題:一方面,對經驗事實及其關系的辯護包含一種內在規范性因素,但這種內在規范性因素又無法由科學語言來解釋。科學的終極目標是要形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理論,因此我們會期望科學理論至少在原則上能夠解釋我們的心理事件,正如能夠用科學來解釋物理上的黑洞、分子或電場一樣。另一方面,還原論者還要解釋心理規范是從何而來的問題。畢竟,人們對感知經驗和信念的把握也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但還原論者認為,人們的心理事件可以看作是他們的大腦功能,而大腦的運作又是通過神經生理學來解釋的[1]。
人們對還原論的期望是,它能夠從科學視角來解釋人們的規范行動,并且還能闡明這種規范行為是如何從因果層次產生的。或者說,人們期望還原論者能提供一種純粹物理規范來解釋規范行為與因果理論之間的關系,亦即用物理論來解釋人們遵守規則行為的原因或理由。通常來說,自然科學所關注的是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而非關注人類的理性。但自然科學的這種方法所存在的潛在問題是,它忽略了如何用人類理性來說明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
在討論了自然主義者和還原論者的觀點之后,那么維特根斯坦又是如何來思考規范行為與外在原因之間的關系呢?事實上,后期維特根斯坦更加關注的是具體事例,如孩子(兒童)是如何被同化到受規則(規范)支配的社會實踐之中的。基于此,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所關注的主要內容是,他首先對“教學”和“訓練”進行了鮮明的區分,如新生兒被訓練得以特定的方式對外在刺激做出反應,然后獲得概念,進而學習如何遵循規則或規范;其次,維特根斯坦主張通過訓練使孩子們成為特定共同體的成員,該共同體的規范又是由群體成員的社會實踐所形成的,外在的社會實踐又進一步受規則或規范支配。
當然,維特根斯坦不是要為因果層次與規范行為之間的關系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而是想要改變我們的常識觀念。“這就像是我們的生活形式。”[2]559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我們的哲學不是發展理論,而是為了解釋規范領域是如何從原因領域發展而來的,并且他也承認理由和原因都是我們日常世界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二、社會規范行為來自于訓練
后期維特根斯坦使用了語言習得的事例來說明他的立場,但他并沒有形成關于語言學習的系統性理論。有人主張維特根斯坦所用的這些事例只具啟發性,如威廉姆斯(Meredith Williams)所指出的,研究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大部分二手文獻只是把學習作為一種啟發式的工具,因而往往忽略了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學習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威廉姆斯還指出,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理論中,他把培訓過程視為“在創造邏輯空間時的關鍵區分是語法和經驗,而學習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闡明規范性的本質”[3]。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習得的評論表明了我們是如何從本能模式支配的行為轉向了自覺遵守規則的行為。從《哲學研究》的評論可以看出,維特根斯坦在教學和訓練之間進行了明確的區分。維特根斯坦寫道:“當小孩學習說話時,他們便開始運用這樣的原始語言。在此,語言教學絕不是一種解釋,而是一種訓練。”[4]5
維特根斯坦在談到學習者建立刺激-反應模式過程時并不涉及任何一種智力活動。人們在建立刺激-反應模式時并不是基于語言教學,而僅僅是基于行為的加強模式。在“訓練”一詞首次出現時,他解釋道:“雖然我是以一種嚴格類似的方式來使用‘訓練’一詞,類似于我們所說的動物被訓練去做某些事情,但訓練是通過各種實例來說明的,如獎勵、懲罰以及諸如此類的。”[5]因此,當維特根斯坦強調語言教學過程是一種訓練而不是一種解釋時,他所堅持的是語言習得最初是通過建立刺激-反應模式來解釋的;而刺激-反應模式發生在本能模式支配的行為層次中,而非發生在自發遵守規則的行為中。在語言游戲中,我們讓孩子們從成人的言說方式出發,而不是從孩子自身的觀點出發,因此這包含著一種規范性因素。
維特根斯坦提醒我們注意這種差異性,即“我已經被訓練得以一個特定的方式對這個標志作出反應,而現在我就對它作出如此反應。但那只是給出一種因果關系;它告訴我們現在只是根據路標走,而不是說明這路標是由什么構成的。相反,我還表明,只有這存在著路標的習慣用法、存在著習俗時,人們才能按路標的指示前行”[4]198。只有當共同體中的其他成人都以特定方式對路標作出回應時,那么他們才是在遵守規則,如果孩子們都只是以這種方式來行事,那么他們是被訓練得如此行事。因此,訓練過程中的因果關系只能解釋孩子的行為,而不能解釋成人的行為,因為成人會作出不同的反應。然而,孩子也是由已經參與社會實踐的成人來訓練的。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詳細討論如何把孩子的行為理解為在“遵守規則”的,以區別于孩子們條件反射式的行為。“老師不能說:‘當學生在說這句話時,也許學生已經學會如何閱讀。’因為學生所說的話是確定的,但學生何時才開始真正的閱讀,正如說這是學生閱讀的第一個字詞,這樣的表述是沒有意義的。”[4]157這也是我們判斷孩子們在遵守規則的方式,但這并不能清楚地說明孩子們最初是在哪一次開始真正遵守規則的。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開篇以奧古斯丁圖像論為例進行了詳細說明。
維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學中突出強調了語言習得的方式,尤其介紹了奧古斯丁式的語言習得圖景。根據維特根斯坦的描述:奧古斯丁認為孩子們通過傾聽成年人說話的方式來習得語言。兒童通過觀察成人的肢體動作、面部表情或眼部表情、觀察到字詞與對象之間的直接關系等來習得語言,因此孩子們通過這樣的方式學會了如何理解字詞的意義。
但維特根斯坦對奧古斯丁的這種觀點進行了三點批判:
首先,他對奧古斯丁式的意義原子論進行了批判,意義原子論認為意義可以基于單個字詞與單個對象之間的指稱關系來加以解釋。如我們可以孤立地學習諸如“紅色”“黑暗”“甜蜜”這樣的字詞,這些字詞是獨立于其他語言的。事實上,后期維特根斯坦用意義整體論來取代了奧古斯丁式的意義原子論。意義整體論是說一個詞的意義取決于語言使用者在整體環境中是如何使用它的。
其次,維特根斯坦不僅批判了意義原子論,而且他也反對奧古斯丁式的語言習得圖景。維特根斯坦認為,奧古斯丁沒有解釋兒童是如何習得第一語言的,而只是解釋了兒童如何習得第二語言。換句話說,孩子必須在已經掌握了一門語言的情況下,他們才能獨立思考對象,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已經擁有概念了,他們才能來學習第二語言。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闡釋:“現在,我想我們可以說:奧古斯丁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描述了人類學習語言的過程,語言學習就好像一個孩子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她不懂這個國家的語言;但好像她已經掌握了一門語言,但不是這個國家的語言。或者,又如孩子已經會思考,但只是還不會講話一樣。并且在這里,‘思考’意指像‘與自己說話’一樣。”[4]32
再者,維特根斯坦認為,奧古斯丁沒有區分孩子們的行為是由模式支配的還是在遵守規則的。如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會大哭,從而向她父母發出了饑餓的信號。成人可以對這個信號作出不同的回應,因為孩子父母不清楚孩子哭的原因,他們只能通過試圖滿足孩子的需求來進行猜測。生物學機制在新生兒的這些行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機制保證了孩子的生存,但這種生物學機制并不包含一種規范因素,例如一個10歲大的孩子與新生兒表示“她餓了”的方式是不同的,而且10歲大的孩子在被社會同化的過程中,他對這種推理方式是開放的,孩子可以從渴求過渡到想要吃飯,從而表明孩子的行為是遵守了規范的,而這種遵守規范的行為同時也構成了我們社會實踐的生活形式。
綜上所述,維特根斯坦認為,當奧古斯丁主張孩子們是在成人話語和環境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直接聯系時,他預設了太多的事情:(1)他必須堅持孩子們已經明白一個詞的指示定義是什么,也已經知道該詞在我們語言游戲中起什么作用;(2)在孩子們成為一種語言游戲的玩家之前,他們必須已經了解了語言的指稱功能;(3)他們已經處于某種立場中來感知對象,例如感知椅子是椅子。維特根斯坦認為從第三點來看,奧古斯丁把孩子看成是好像能夠思考的,“‘思考’在這兒意味著像‘與自己交談’的事物”[4]32。
為了分清物體,孩子必須能夠將對象劃歸為某一范疇。為了辨認面前的事物是綠蘋果,孩子們必須能夠在蘋果的概念下對它進行分類。
因此,在奧古斯丁的語言習得圖景中,孩子在學習語言之前,似乎已經擁有或掌握了一門語言概念。因為,如果孩子在學習一門語言之前,還沒有掌握任何這方面的內容,那么我們就無法通過解釋字詞意義的方式來教給他們言語,我們也無法通過非口語的實指定義方式來教會他們語言,我們的語文老師也不能用中文中的“痛”來表達英文中的“pain”。因此,在奧古斯丁的語言習得圖景中,這就意味著孩子們必須已經擁有了一門語言,掌握了一定的概念;或者至少他們已經掌握了非語言解釋的能力。但奧古斯丁的這種方法并不是通過訓練來使孩子們習得語言的。
通常在學習語言之前,孩子們的行為是由自然神經脈沖導向的,但這并不包含外在規范因素。當然,在本能模式支配的行為和自發遵守規則的行為之間的界線并非那么嚴苛。因為有人會說,新生兒的行為也可以被描述為遵守規則的行為,正如新生兒用哭來發出饑餓信號來保證他們的生存一樣,新生兒所遵循的規則可以表述如下,“如果你覺得你餓了,那么應該大哭”。甚至規則也允許出現誤差:我們可以想象孩子以這種哭的信號來表達饑餓,但是這種信號卻失敗了,這樣一來所產生的直接后果是大大降低了嬰兒的生存能力。這也表明新生兒的本能引導行為包含了一種規范因素,它遵循某些我們進化生物學中的規范。
我們是從科學機制中知道這些生物學規范的,但科學中的生物規范在許多方面不同于由社會實踐所構成的規范。在科學規范和社會規范中必須有一種獨立的標準來進行評判。然而,這些標準在科學理論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于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的,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適合方向”(direction-of-fit)上的明顯差異:一方面,物理論致力于真理這一理想,如果物理論不能滿足這一理想的話,或者說如果世界不是按物理論預測的方式來運行的話,那么我們必須改變理論,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實踐致力于遵照共同體的規范,如果某個人不能滿足這些社會規范的話,那么他必須改變自己的行為,而不是改變他所遵守的社會規范。
進化生物學的規范起到了一種綜合作用:一方面,就物種來說,雖然進化生物學理論無法全面反映人們的行為,但人們的行為在描述層次是規范的;因此,如果人們只根據進化生物學來行事的話,那么就大大降低了其生存能力。規則對生存沒有例外,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并重新制定規范理論。另一方面,如果就我們自己物種的生存能力而言,我們可以考慮改變我們的行為,例如我們可以考慮停止建造原子電站等行為,以增加我們物種的生存能力。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將生物學標準轉化為道德標準。但這種轉換破壞了還原論者的觀點,還原論者想要把由我們社會實踐支配的規范行為還原為由進化生物學支配的規范行為。因此,進化生物學理論表明了新生兒本能引導的行為,這種行為可能會增加他們的生存能力,但卻不能被描述為擁有一種規范性,也就是說,無法說明他們的行為是在真正遵守規則。
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學理論在描述層次是規范性的,它們遵循如真理般的認識論標準,而我們的社會規范包含了一種外在規范性因素。當世界無法以理論預測的方式來運行時,我們不僅可以選擇修正理論,而且也可以拒絕觀察陳述。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中,我們會改變或拒絕語言實體,但不會改變或拒絕所描述的事態。同樣,當我們指出某人違反了規范時,他可以改正自己的行為,當然他也可以挑戰規范或標準[1]。維特根斯坦認為,只有在訓練的過程中,孩子們才能成為語言游戲的玩家,而語言游戲本身又是受規則支配的。當孩子們的行為從自然神經脈沖過渡到遵守外在規范域時,他們就成為共同體成員所完全接受的成員了。孩子們的行為不再是靠自己的直覺來引導,而是受外在社會規范的指導,此時,孩子們可以通過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的行為來矯正自己的行為。
三、生物規范行為來自于本能
維特根斯坦的“訓練”概念表明,孩子們是如何按照成人共同體所提出的規則來行事的。然而,這并沒有解釋兒童自己是如何進入規范領域的,換句話說,這并沒有解釋孩子們自己是如何應用概念和遵循規則的。根據維特根斯坦的思路,為了理解如何從本能模式支配的行為轉化為遵守規則的行為,我們必須首先闡明概念和能力之間的關系。在《論確定性》中,維特根斯坦主張學習一門語言并不要求孩子事先具有一定的知識,而是要求孩子們擁有一定的能力:“但是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即‘一個已經掌握了一門語言游戲的孩子,他必定知道某些東西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必須擁有做某些事情的能力’,那這將是一種重復,而這正是我想反對第一句話的地方。”[2]534
為掌握一門語言游戲,一個孩子必須擁有什么樣的能力呢?很明顯,這會涉及各種不同的能力。掌握一門語言需要孩子有天賦的能力或與生俱來的能力,如果孩子們不能夠對刺激做出類似成人的反應或不能模仿成人行為的話,那么我們無法訓練他們。維特根斯坦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試想警犬飼養員做出一些手勢和動作來讓警犬執行搜救任務,但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對這些手勢做出如警犬般的反應,如貓就不會做出如此反應甚至貓會錯解這些手勢。正如孩子們如果不會對我們的鼓勵做出正面回應的話,那就如同人們想教一只貓來執行搜救任務一樣,孩子們也無法對成人的話語做出正確的回應。
這說明訓練預設了受訓者必須具有先天的能力,也就是說,由于受訓者的生物結構而先天擁有這些能力。除了這些與生俱來的能力,孩子們也必須擁有向社會共同體中其他成員學習的能力。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通過模仿成人的行為來學習,這是孩子們與環境中的對象互動所產生的行為。通過模仿成人的行為,孩子們學會如何行事,正如維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這是我們的行動,它位于語言游戲的底部”[2]204。在《對數學基礎的評論》一書中,維特根斯坦指出在“概念”(concept)和“領會”(grasping)之間有一種相似性:“概念幫助我們領會事物。它們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的情況。”[6]16
兒童通過學習如何在世界中行動,并且通過學習如何操控世界中的一些對象來習得一門語言,他們通過這樣的方式也學會了如何認識世界中的某些結構。維特根斯坦給出了一些啟發性的事例:“孩子不知道書的存在、扶手椅的存在,等等,但他們學會了如何去取書、如何坐在扶手椅上,等等。”[2]476因此,孩子在習得諸如“扶手椅”“杯子”等詞匯之前,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坐在椅子上、喝著杯子中的牛奶。基于這些能力,孩子習得了諸如椅子和杯子等概念,而這些概念又成為了習得其他單詞的前提。
由于概念和能力之間的密切聯系,維特根斯坦勾畫出了一幅世界和語言之間的圖景。我們只能通過控制世界中的對象來習得語言。此外,如果世界是不同的,或者說從根本上它會改變,那么我們不會甚至不能使用相同的概念來描述它。“某些事件會把我們置于某一立場,因此,我不能繼續進行舊的語言游戲,如此我們就失去了游戲的確定性。事實上,難道語言游戲的可能性不是由一定的事實來制約的嗎?”[2]617
因此,維特根斯坦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語言和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鴻溝,而這種鴻溝又只能由意義或意向性以某種神秘方式來彌合。維特根斯坦寧愿堅持,語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生活形式是由世界中的事物和事實通過實踐所構成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世界中的相關事實是我們語言的一部分。如“氣溫在零度以下時,水會結冰”這是一種事實,維特根斯坦明確指出,“這一事實融合為我們語言游戲的基礎”[2]558。
但是,到目前為止,維特根斯坦并沒將概念等同于能力。因為這正是維特根斯坦所告誡的一種簡化。他后期哲學的特點是研究語法,并反對還原論者的理論。他指出:“‘概念’是一個模糊的概念。”[6]70當孩子們第一次受訓從事某種行為時,他們還沒有完全擁有這個概念。在《哲學研究》§2中,維特根斯坦介紹了所謂的語言游戲,但在語言游戲中所發生的每一種事情,不能都稱為一種概念,那在§2的語言游戲中有概念嗎?如“板”“磚”“柱”等概念。當然,在參與語言游戲的這些概念與其他概念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線。“更為重要的是,‘概念’是指在語言游戲機制中的一種權宜之計。”[6]71
在§2的語言游戲中只涉及2個玩家和4個詞:“磚”“柱”“板”和“梁”。當玩家張三喊出其中一個詞時,他的助手李四就會遞給他相應的對象,這些對象是李四在對話過程中學會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孩子們也是被訓練得做出此類行為。在§2的語言游戲中,李四還沒有說出一門語言或擁有一種概念。因為這只有4個字詞可以使用,李四也只能按張三給出的命令行事,他沒有辦法來反思他們的語言游戲。只有當語言游戲得到擴展,達到了某種復雜程度時,才能使李四反思語言游戲中某種語詞的用法,從而指出其錯誤,此時才能說李四擁有了該概念。
維特根斯坦并沒有解釋語言游戲是如何擴展或者由誰來擴展的。是由玩家張三和李四他們來擴展語言游戲的嗎?或者是由掌握了更復雜、更豐富語言的言說者來擴展的嗎?對維特根斯坦而言,這種語言游戲的擴展既不是由張三和李四,也不是由受過訓練的孩子來完成的,而是由他們的教練、成人言說者來完成的,因為成人已經開始了解規范領域,而且他們也已經掌握了一門語言。維特根斯坦認為,孩子通過這種訓練參與到社會實踐之中,并且這種訓練是由已經掌握一門語言的成人來進行的。
此外,維特根斯坦還認為像真理、知識這樣的規范概念,從來不是從因果領域發展而來的,但它們已經深深地扎根于社會實踐之中,在實踐中孩子被訓練如何來玩語言游戲。當他們第一次在語言游戲中學會某些概念時,他們還不能做出超越訓練立場的行為。例如,兒童不會懷疑與語言游戲相關的對象。“孩子學會相信成人,懷疑是在有了信念之后。”[2]160懷疑意味著孩子在語言游戲中尚未習得相關立場。例如,在§2的語言游戲中,玩家張三只能給出命令,但不能提出疑問或做出諷刺性的評論等。維特根斯坦說:“我們教孩子說‘這是你的手’,而不是說‘這也許是或可能是你的手’。這就是孩子如何學習關于他自己的手的無數語言游戲。這里的問題是,一方面,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是否真有一只手’;而另一方面,他并沒有學習,他知道這是一只手。”[2]374
在§2的語言游戲中,只有當李四或孩子們習得并掌握了語言游戲時,才允許他們談論命題的真值,或者說允許他們知道這個或這個是那個時,他們才有能力在理性的邏輯空間里做出更復雜的行動。當成人言說者認為時機適當時,他們可以將知識歸因給兒童。只有當“知道”“真理”或“與現實一致”這些詞是屬于語言游戲的一部分時,它們才是有意義的。在這里,“與現實一致”一詞似乎并沒有任何明確的應用。兒童習得像“知識”“真理”這樣的概念,與他們習得其他語言的方式是一樣的,他們是通過訓練來參與到復雜的社會實踐之中。只有達到這種復雜程度時,他們才有能力去反思。如果我們認為有必要的話,那就可以改變我們的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認為,就整體語言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語言代替另一種語言,當我們試圖這樣做時,我們就失去了做出修改所需的工具。如果我想把門打開,鉸鏈必須不動。
總之,維特根斯坦認為,在解釋語言習得的過程中,能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兒童需要具備一定的先天能力來成為一名合格的受訓者。然后,他們開始模仿成人的行為,通過這一過程開始構建自己的世界形式,并開始應用相關概念。成人對兒童的持續培養,不僅豐富了孩子們的能力,使孩子們擁有越來越多的詞匯,而且使他們能在語言游戲中做出相應回應,直到可以把他們稱為合格的語言言說者。
四、遵守規則行為來自實踐
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他發展了一種以自主性為特征的語言習得圖景。在§2中,維特根斯坦對訓練的評論已經表明孩子是被成人同化,從而參與到受規則支配的復雜社會實踐之中。但維特根斯坦幾乎沒有討論過這樣的社會實踐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說,他沒有討論人類最初是如何形成一個社會群體,并且是如何參與社會實踐的。他也沒有討論規范領域是如何從原因領域演變而來的,而僅僅說明了孩子最初是如何進入規范領域的。維特根斯坦設想在語言概念和能力之間有密切聯系,那二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
當然,維特根斯坦反對將真理和指稱當成是語言習得圖景的基本概念,“他反對這一觀點,即語法規則鏡像了實在的本質”[7]。然而,維特根斯坦對概念和能力之間關系的討論表明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至少是由我們的生活形式來確定的,也就是由我們所參與的社會實踐來確定的。維特根斯坦在《論確定性》中,把規則支配的行為與原始本能引導的行為進行了類比:“我想把這里的人類當作一種動物;正如原始人類擁有的是本能,而不是推理能力。正如在原始狀態下的生物。任何邏輯能力足夠好的原始人則不需要類似于我們的溝通方式。語言并不是從某種推理中產生的。”[2]475
原始人類包括新生兒,他們只是受本能驅使而行動,而不是出于某種原因或推理。因此,人類所從事的第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并不是來自推理的結果,它們只不過是被動產生的。“這種游戲被證明是有價值的,這是人們玩游戲的原因,而不是推理驅動人們玩游戲。”[2]474這些評論表明,人類通過實踐發展了語言,這是合乎理性的,但還沒有涉及因果規范方面。世界所施加的約束限制了我們能參與哪些實踐。只有在證明這種實踐是成功的情況下,才能培養孩子參與實踐之中。在其他文化中,他人所發展的實踐不同于我們的實踐是有可能的,但所有這些實踐活動必須要適應這個世界。世界并沒有強迫我們進入一種特定的實踐,它排除了某些來自可能領域中的實踐。
根據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語言習得是自主性的,原因在于:(1)它獨立于心理事件和心理表征;(2)詞和對象之間具有指稱關系;(3)語言習得過程是自主的;(4)實用的目的。對于這種語言習得圖景,維特根斯坦反對用還原論者的方法對規則進行解釋,即反對用我們物理世界的因果律來支配我們的語言游戲。對于維特根斯坦來說,語言是獨立于心理世界與物理世界的。無論是個體發生還是整合到目標導向的人類實踐中,語言對規則的構成都產生了影響。維特根斯坦在《論確定性》中指出,我們語言游戲的具體形式是沒有理由的,“你必須記住的是,語言游戲就是說不可預知的事物。我的意思是說:語言游戲是不合理性的。它就如我們的生命”[2]559。
語言自主性的論題決不能被誤解為是完全脫離物理世界和我們生活形式的。我們的社會實踐,包括我們的語言游戲是深深植根于物理世界的。此外,我們規則支配的行為同時也是基于本能引導的行為,這一點與動物無異。因此,世界通過對實踐的限制來塑造我們的生活形式,包括我們的語言,但這并不能證明它們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我們想解釋為什么我們的祖先最初在發展一門語言時,是采用這種規則集,而不是另一種規則集時,我們只能引出原因,因為沒有理由來說明這一過程。如果我們試圖來解釋語言的復雜實踐,那么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從因果律得出規則,而因果律是支配物理世界的規律,我們的語言規則是自主的,它們屬于規范領域,不屬于原因領域。
維特根斯坦的理論圖景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我們可以清楚地區分原因和規范。他認為,在兩者之間可以畫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因為兩個不同的領域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他堅持認為兩者都是我們天性中的一部分。“指揮、提問、講述、聊天,就像我們散步、吃、喝、玩一樣,都自然歷史的一部分。”[4]25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維特根斯坦的立場稱為自然主義。然而,關鍵是要看維特根斯坦的這種自然主義是如何不同于還原論者的自然主義,并且還原論者的自然主義立場在當代心靈哲學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如果概念的形成可以用自然事實來解釋的話,那么概念和一般事實之間應有某種對應關系。但“我們并不討論這些概念形成的原因;我們也不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研究自然史,因為我們可以為我們的目的而發明虛構的自然史”[4]230。
在后期哲學中,維特根斯坦還闡明了世界中的規范問題。他認為,科學所描述的世界和根據規范來解釋的心理現象與生活世界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用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話來說,科學和顯象(manifest image)之間是有區別的。維特根斯坦告誡說,我們處在世界和共同體之中,我們在世界和共同體中是受理性和原因支配的。科學圖景是從理性層面抽象出來的,目的是為了在這個世界上形成一個全面的因果律形式,如果沒有這些科學圖景的話,那么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科學就不會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然而,盡管科學取得了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忽視科學只能是基于抽象的顯象而發展起來的。根據塞拉斯的觀點,顯象是“一種框架,這種顯象使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世界中的人”。“這是一個所謂精細化或復雜的‘原始形象’。”[8]另一方面,科學圖景是通過科學理論來推斷出“不可觀察物體和事件,目的是為了解釋可被感知事物之間的關聯”[8]。塞拉斯清楚地表明,盡管顯象是直接的,但更應優先考慮科學圖景,并且我們不應該完全消除顯象,而是應該把科學圖景和顯象都囊括在內。此外,塞拉斯還根據顯像的不可還原特性發展出一種人類的概念框架,但這種概念框架需要使用科學圖景來解釋,從而獲得解釋上的優勢。
當代心靈哲學中的主要立場是采用塞拉斯的觀點,即把顯像與科學圖景之間的區分作為他們研究的出發點。也有一些還原論者追隨塞拉斯的腳步,通過科學語言所提供的方法來解釋規范性。但還原論者所設想的這個策略可能是行不通的,因為只有當科學理論的假設成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圖景時,這才是有效的,而且還原論者的選擇完全取消了顯像。科學的運作不可能獲得關于人及其在世界立場中的全部理解。科學圖景忽視了人類自身的形式,當用科學圖景來理解人類生活形式時,我們要退回到現象層次來解釋相關現象。
五、結論
維特根斯坦不是要將人類的框架與科學圖景進行調和,而是認為我們錯誤地將諸事實看作為一個原型現象。科學圖景表明我們專注于特定的、明確定義的現象是卓有成效的,但當科學涉及到建構一個更全面的抽象規范圖景時,就會有太多的局限性。維特根斯坦認為,我們處在一個人與物交織的因果關系網之中,生活在一個由各種原因和規范所支配的世界和共同體之中。世界對我們來說是開放的,用抽象的理論無法來把握世界全貌,但是我們可以更詳盡地分析和描述它。當然,維特根斯坦并沒有試圖把規范還原為原因,他也不認為科學理論可以證明規則的合理性,而我們的實踐和語言游戲正是由規則所支配的。雖然維特根斯坦把原因和規范設想為一個實體的兩個方面,但他并沒有討論理論如何描述不同層次的實在,他想要做的是把物理學和心理學的問題都可以統一到一個包羅萬象的通用理論中,即發展一個完整的、連貫的世界圖景。這樣,我們通過由規則支配的社會實踐就可以獲得對語言更全面的理解并獲得一種生活形式,從而獲得規范概念來指導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