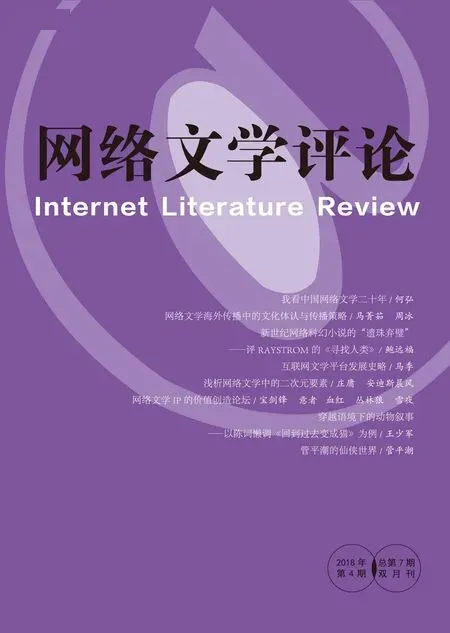刀劍馥郁,沙場如歌
——評蘇歌小說《最危險的時候》
《最危險的時候》是蘇歌的首部長篇軍事小說,也是網絡抗戰小說中的精品之作。作家花費二十余年搜集資料,不惜辭去工作,在家專司創作,嘔心瀝血五年方才完成。小說在鳳凰網非虛構版塊頭條橫空出世,2015年正式在鐵血讀書網連載,引起了大量軍事愛好者爭相傳閱,掀起了新一輪抗戰小說的閱讀熱潮。
小說三部共八十萬字,似一幅緩緩鋪開的抗戰畫卷,把歷次重大戰役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讓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躍然紙上。整部作品涵蓋中華民國成立前后近四十年的歷史,涉及中、越、美、蘇、日等多個國家,“多線條反映了正面戰場、敵后戰場及投降派,突出中日雙方的策略、戰略、戰術”[1],著力表現毛澤東、蔣中正、張學良、汪精衛等歷史人物的風云際會。《最危險的時候》囊括浩如煙海的近現代史料,復經漫長的創作周期構思打磨,“是個人創作成熟的標志”[2],達到了同類抗戰小說的新高度,取得了當代網絡軍事文學的新突破。
在當代網絡軍事小說中,《最危險的時候》是一顆耀眼的明珠。作家用近乎嶙峋的筆墨,還原戰爭的全息影像。“出于揚長避短的策略,網絡軍事小說中,大多偏重于武器裝備、戰斗場面、戰略戰術等技術性因素的展示,而疏于軍人形象的塑造”[3],但正是在人物塑造這一網絡軍事小說最為薄弱的環節,這部小說大放異彩,關于毛澤東、蔣中正、張學良等主要人物的論述可以編入抗戰人物傳記。作家沒有虛構社會體系和沖突集團,沒有引入新的人物來延展抗戰的歷史情境,放棄主觀假想推演的同時,杜絕個人英雄主義泛濫,在四大網絡軍事文學類型外另辟蹊徑[4]]。小說披著網絡軍事小說的華服,傾向回歸傳統敘事,在史料鑄就的高閣上肆意獨舞,氤氳英雄香氣,頌唱沙場戰歌。因此,《最危險的時候》是一部特殊的網絡軍事小說,也是一部足以納入當代戰爭文學史的英雄史詩。
一、戰爭模型化:宏大敘事與戰場溫度操控
如何將眾多大小戰役按照戰爭規模、戰況發展和人物活動進行邏輯熔鑄,反映了作家的空間構筑能力和敘事能力,直接決定了網絡軍事小說的成敗。《最危險的時候》對抗戰歷史進行詳備刻寫和重構,重現了無數戰爭現場,涉及近百場不同規模的戰役。作為一部長篇軍事小說,千篇一律的描寫,只會讓讀者對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殘酷戰場產生強烈的排斥感和嚴重的審美疲勞。因此,這部小說省略重復無意義的戰場刻畫,以模型化處理予以替代。
在自然科學中,模型是以某種方式對所研究事物的某個性質或者組成事物各部分之間關系的復制或者抽象[5]。我們把這個概念引入到文學創作中來,產出一個小說模型的概念:用文學處理方法對小說中的對象或者對象各部分關系的復制或者抽象。軍事小說運用的模型具有顯著特點,即戰爭規模、戰場特點的類型化和敘述語言的簡明化。戰場的中心地位無需小說對每一次戰斗的流程都進行機械化地描述,作家用自己的語言體系簡要闡明即可達成目標。因此,這部小說對戰場的模型化處理是可行的、必要的,它減輕作者的創作負擔并使小說的空間結構更趨合理化。
宏大敘事是其中一種模型化的處理方法。這部小說在塑造戰場時,著眼大的戰場,進行宏觀敘述,不涉細節,給予戰場一種壯闊的觀感。它的宏大敘事與部分中國現代戰爭文學作品“千篇一律、萬人同腔地去證明一個、圖解一個已經存在的政治概念或前衛觀念”不同[6],它注重考據,嚴謹真實地對戰場展開鋪陳,消解現實社會中的政治關系。因此,宏大敘事的重啟不是當代網絡軍事文學向現代戰爭文學的倒退,而是網絡文學充分尊重歷史、發揮作家主體性的進步表現。
小說將傳統宏大敘事聚焦在文戰和武戰兩個部分,力圖讓讀者明了整個抗戰的軍事和社會輿論狀況。文戰陣地集中在報刊,其中以對國共兩黨批駁汪精衛投降的記敘最為精彩。“重慶中共《新華日報》更是刊發一針見血的社論《汪精衛賣國》,還天天旗幟鮮明地呼吁: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7]作家對重慶國民政府的批駁雖持貶斥態度,認為重慶筆桿子的文章空洞無實、千篇一律,但也如實描述:“腔調高亢豪邁、節奏鏗鏘有力,尤其是氣勢上來后咄咄逼人,極具大家風范(第2部,第24章)。”小說中的武戰場景數不勝數,以喜峰口戰斗最為典型。“敵我主力趕到,展開新一輪血戰,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整整廝殺兩天兩夜,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第1部,第9章)。”寥寥數語,喜峰口戰役烽火狼煙、相持不下的戰況躍然紙上。作家還將武戰的筆觸伸及出征緬甸的中國遠征軍,“陳納德飛虎隊出動中緬兩地全部戰機,為之空中掩護,頓時山搖地動,遠征將士更精神抖擻,威風凜凜,陣容盛極一時(第3部,第3章)。”針對這次中華民族在世界大戰中罕見的出征,作家定格空軍掩護這一意味悠長的鏡頭,與炮火紛飛的前線戰場相得益彰,留下無盡的戰場想象空間,乃神來之筆。蘇歌橫向構筑的宏大敘事并不妨礙讀者對抗戰歷史真相的追尋,相反,完整客觀的宏大敘事能使讀者更加清晰立體地認知歷史。他用這種模型醫治長篇軍事小說千人一面的痼疾,表明重建宏大敘事在網絡軍事小說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戰場溫度操控是小說使用的另一種處理模型。溫度是表示物體冷熱程度的物理量,這里的戰場溫度不是物理溫度,而是依據讀者收到戰場刺激后情感反饋強弱設置的人文矢量。蘇歌受過嚴格系統的思維和寫作訓練,能敏銳捕捉血雨腥風在強度不同的戰爭中帶給讀者的刺激反應。他謹慎地接收著讀者的情感反饋,像一位操控溫度的魔法師,設置高溫戰場、中溫戰場和零度戰場三個戰場溫度模型,按照相應比例應用到整部小說中去。戰場的紛飛炮火不會灼傷讀者的心,因為這部小說是溫柔敦厚的,是冷暖交融的。
焦灼與持久是高溫戰場模型的主要特點,戰斗雙方互有來回,你來我往,難分勝負。單是古北口戰役,東北軍和日軍纏斗整整三個晝夜,第三天時“炮空齊鳴,陣地上處處開花,戴安瀾團及增援團飽受轟炸死傷累累,已無完整建制(第1部,第9章)”,慘烈程度可見一斑;中國遠征軍主力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機械化英雄部隊,入緬作戰本應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未能粉碎任何一路日寇的進攻,反而弄得丟盔棄甲徒步上山(第3部,第10章)”,出乎國內外軍民的意料,反映了抗日持久戰的漫長與焦灼。中溫戰場模型的處理則相對多樣,作家在瓦礫堆中發掘人性,或用挪揄的口吻,或制造場景色差,減輕戰爭的沖擊感。日軍的飛機轟炸南京,大地在顫抖呻吟。面對末日的來臨和死神的召喚,防空洞內“共同的感受拉近了人們的距離,抹平了不小的分歧(第1部,第41章)”。當人類共同面臨死亡的威脅時,他們終于回歸了人性本有的和諧狀態。談到胡博士求證蘇聯與日寇間是否存在瓜分中國的密約時,作家調侃“東北的大豆高粱早收了,華北的小麥正打場,江南的水稻也青了又黃準備開鐮,淪陷區用人耕地也要收割了(第2部,第30章)”,而胡博士在各國使節中的求證還是無果。對胡博士“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調侃,間接削弱了戰爭敘述的冷酷性,冷卻戰場的熱度,別是一道風景。蔣中正從武漢撤退前夕,“深情地遙望著武漢深秋的夜空,明月如鏡,照得江漢大地一片朦朧(第2部,第15章)”,城中人棄城撤守的既視感與明月映江的絕美畫面形成強烈的冷熱色差,凄美卻不絕望,宛如一幅水墨畫卷。讀者因此磨隕了對戰場的關注度,轉而變為無盡的感慨。零度戰場是作家運用最多的戰場模型,他曝光最殘酷的場景,進行冰冷的零度敘述,有意煮鶴焚琴,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小說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敘是零度戰場的典例,“昔日美麗的金陵成了死氣沉沉的石頭城,晦暗無比,端莊雄偉的國民政府大樓如今橫臥在雜草叢中,成了一堆堆瓦礫(第2部,第37章)”,還原了南京保衛戰失敗后的慘象:死者暴尸荒野,活者膽顫心驚。更有黃河掘堤放水、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衡陽保衛戰等事件的白描,將戰場溫度降至冰點。此外,作家會跳出文本進行評論和諷刺,推動戰場對讀者的感官沖擊。作家諷刺日寇“將其茹毛飲血的文化精髓在實際的現代戰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發出悲鳴與號召:“不奮起反抗日寇,消滅這世上最慘無人道的侵略者,就沒有自己的活路!(第1部,第56章)”相對高溫和中溫戰場,零度戰場引導讀者直面戰爭,達到與創作者的情感共鳴,它的刻畫更為直接簡單,但情感最為飽滿充實。
這是一部抗日戰爭的冰與火之歌,冷熱交錯的戰場應接不暇,讀者既可感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馬革裹尸的殘酷凄涼,又能深味人物心底的離愁別緒、兒女情長。三種溫度戰場模型的熟練使用,支撐了龐大的戰爭空間結構,避免了戰場塑造的重復與簡單化。
創作主體的自由與思維活動的不可還原性,保證了小說創作運用模型時的獨立性。因此,建構相應的模型進行文學創作是合理的,作家要敢于進行文學模型化書寫的嘗試。蘇歌的模型書寫為網絡軍事小說的創作指引了新路徑。
二、人物圖卷:抗戰眾生的“清明上河圖”
目前,主流網絡軍事小說對紛繁復雜的登場人物多做如下處理:一是注重歷史人物的功能性,描寫戰爭是首要的,人物塑造是次要的,人物的去留均為推動情節的發展服務,“全部注意力的目標在于行為,而行為者僅僅是使情節分布的形式表現成為可能的一張紙牌。”[8]人物僅充當縫制小說的絲線,既干癟又沒有活力。二是添設虛構人物,創造虛構人物與真實對象的互動機會,通過虛構人物的眼睛再現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使軍事文學中的人物飽滿化。這的確解決了軍事小說塑造人物同質化的難題,但虛設的對象占據了大量文字資源,降低了小說人物的歷史可信度。并且,虛擬人物是為了達到謳歌或者抨擊某一戰爭陣營而設置的,《最危險的時候》對二戰的各方勢力均有著筆,相關的戰爭陣營遠不止一個,虛設人物顯然不合適。因此,怎樣在緊密的戰爭敘述節奏中穿插豐富的人物描寫,是蘇歌面臨的嚴峻考驗。
與各類戰役、戰場的書寫部分相比,小說的人物刻繪占據了很小的篇幅。在不設虛擬人物的前提下,作家將毛澤東、張學良、蔣中正、汪精衛等三十個重要人物引入到烽火狼煙里來,塑造的大小角色近一百個。相關人物性格豐富多樣,覆蓋了抗戰全局,部分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但依然活靈活現。在同類網絡軍事文學中,《最危險的時候》人物處理最具難度,但也最為成功。
小說用環扣的方式安排人物出場,筑建“四角寶塔”式的人物陣營。寶塔的四端各司其職,圖卷中的人物依次登臺表演。圍繞毛澤東、蔣中正、張學良、汪精衛四個塔角,各色人物以之為頂點向下建構分屬的人物陣營。每個人物的登臺有條不紊,各個陣營的活動井然有序。作家懷著嚴謹恭敬的態度與書法不隱的勇氣,把人物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如實描繪,賦予這些歷史人物鮮活的面容與個性,而不是直接采用史學家已做定論的評價。所以,讀者伸手可及的是血肉豐盈的人物,而不是紅色文學閹割的典型。在這方面,小說中有許多神來之筆——在毛氏陣營中,毛澤東善于軍事指揮,運籌帷幄、目光如炬,千軍萬馬只等閑,但亦會有書生意氣,忍無可忍時只能選擇揭竿反抗,是一個先人后己、先禮后兵的軍事天才;周恩來縝密周到,果敢堅毅,談判桌上叱咤風云,善與各方周旋,為八路軍的利益據理力爭,為國家和民族鞠躬盡瘁;林彪生性幽默、血氣方剛,懷有杰出的軍事才能,對敵人不留絲毫情面,卻似孩童般天真無邪,會在勝利后跨上東洋馬過鬼子癮。在張氏陣營中,張學良意志堅定、鐵心抗日,因為蔣氏的幽囚走向自我回避與否定,猶豫不決、頹廢不前,有江湖義氣,也有兒女情長,最終久居山林,獨釣寒江雪。他是因不完滿而完美的英雄,是作家頗費心血著力塑造的民族英雄,“當時空倒轉,現實成為歷史,能有不止一人復述一個罪人的初衷,足以證明他的偉大!”[9]在蔣氏陣營中,蔣中正既是把控戰局、調兵遣將的抗戰總指揮,又是霸道獨裁、堅決反共的軍閥和資本家;既是當機立斷、視野獨到的作戰指揮者和大英雄,又是愛護妻子、護犢情深的小男人;既是飽讀詩書、口若懸河的領袖,又是唯利是圖、沾染流氓習氣的無賴。他的決策牽動著抗日戰爭的走向,關系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因此小說對其著墨最多,將其塑造得生動完整。此外,張治中廝殺戰場,步步為營;張自忠忍痛割愛、以死報恩;李宗仁、何應欽、陳誠、湯恩伯等形象也各有獨到之處。在汪氏陣營中,汪精衛自詡正統,羨慕并妒忌著蔣中正的地位與權力,從抗日到反抗日,從愛國到叛國,從謀真正的和平到甘做侵略者的幫兇,他偶有“為什么要到上海來?為什么要與日寇謀和平?(第2部,第34章)”之類的懊惱,卻最終在曲線救國的自我麻痹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是自我毀滅、惡吞噬善的代表。還有一些游離在塔角之間的人物,例如樂善好施、決策英明的羅斯福,莊嚴肅穆、令人生畏的斯大林,中蘇不同文化煉鑄的蔣中正之子蔣經國,他們不是小說塑造的中心形象,但豐富了人物版圖,支撐了小說的敘事結構,使讀者印象極深。
小說圖卷展現的眾多人物中,史迪威極為特殊。他作為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和蔣中正之間有著微妙復雜的關系,兩者本應在軍事和政治上通力合作,一拍即合,但史迪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因此與蔣氏總是摩擦不斷。他拒絕了蔣氏提供的安逸辦公環境,并訓斥副官們貪圖享樂,是與中華民族同生死、共進退的國際友人。他有與生俱來的傲氣與狂氣,直言蔣氏派給自己的軍隊是叫花子,將營長以上的軍官直接塞進運輸機退回。他質疑蔣中正對美援物資的處理方式,公開頂撞蔣氏,直言“我有的是東西,今后給共產黨也不給你!(第3部,第29章)”,最終在蔣氏的壓力下離開了中國戰區,離開了中美盟軍。沒有勝利者的榮耀與光環,沒有英雄鑄就的傳奇,他好像古代征戰疆場的劍士,在黎明前夕孤獨離去,離開他的“孩兒們”,留下“廉頗老矣”的感慨與不甘。他不從屬于國內的任一軍事陣營,和張學良一樣都是作家用力刻畫的悲劇人物,只是前者白日放歌、縱酒還鄉,后者田園垂釣、了卻殘生,結束的方式不同罷了。
除了直接的人物描摹,蘇歌移花接木,將傳統長篇小說的人物塑造技巧嫁接到網絡軍事小說的人物建構中來。傳統長篇小說關注感情線索的作用,擅長用深情的悲歡離合展示人物微妙的心理變化,間接把人物形象揉捏成形。這種做法對軍事小說的書寫是存在風險的,風花雪月、愛恨情仇的過多攝入,會削減軍事小說的嚴肅性,甚至會使軍事小說變成情感小說,戰場退變成人物傾訴情感的舞臺。因此,蘇歌壓縮無關戰爭的章節,由男性角色拓展文本的空間結構,讓女性角色處于從屬地位,以求保留人物鮮活性。盡管削減了女性的活動空間,我們依然看到了那些飄浮于瓦礫上空的片片落英:天生麗質、舌燦蓮花的宋美齡,為了營救親愛的“打令”,深夜拿著纖纖細筆伏案寫信,深情款款,“最后落款時還不忘將自己的英文昵稱勾了兩下,仿佛那天使的雙翼(第1部,第19章)。”張學良身旁的兩位女子則更加鮮活——潑辣強勢的于鳳至雖然有些爭風吃醋,但和張學良伉儷情深,幫助張氏進行決斷,身患重病亦無怨無悔,是一個亦妻亦友亦師的角色;忠厚善良、自愿追隨張氏的趙綺霞沒有名分,卻是他的一生所愛。當她收到張漢卿的召喚,“止不住的眼淚,淌不完的心酸呀(第2部,第39章)”,再次回到那被囚禁的懷抱。汪氏陣營中的陳璧君心思細密,為了自己的愛人不惜刁蠻耍潑,隔三差五跑到中央黨部哭鬧,要為丈夫的遇刺討說法。當汪精衛昏倒時,她“掄起兩只巴掌左右開弓,噼里啪啦一通猛扇(第2部,第34章)”,和溫婉賢淑的大家閨秀相去甚遠,顯示了陳璧君在小說中的獨特地位。但她也有柔弱的一面,當她想起闊別兩載的家,忍不住又哭又鬧,內心的軟弱暴露無遺。
當然,小說的感情線索不單指愛情,英雄的友情與絕情也是重要的構成元素。它們主要表現在蔣中正和張學良身上,對二者形象的立體化尤為重要。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中正對著張學良以手拭淚,“我現在這個樣子,你看著辦吧(第1部,第20章)”……追憶二人深厚情誼的同時,暗示二者多年的情誼終到盡頭。囚禁張氏后,蔣中正堅決否決日寇索要張氏的和談條件,“他對我不仁但我不能無義呀。(第1部,第52章)”二人雖然分道揚鑣,但兄弟情誼仍在,只是不復當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氏平安返回南京。他拒絕和張氏一同下機,面對熙熙攘攘的歡迎者,歪曲事實,說是自己用高尚的日記和正確的輿論使張學良觸及自己卑污的靈魂,以此夸大自己的領袖人格,借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待張學良到達時,“偌大的機場已冷冷清清,只有幾輛警車在遠遠地游蕩(第1部,第25章)”,凄涼如此。生死之交逐漸形同陌路,令人唏噓不已。在軍事小說中,為了表現男性角色的高尚人格,有關兄弟情誼的記敘并不少見,但對兄弟之間的絕情描述不多,多作為情感線索的終端一筆帶過。小說表現了蔣氏的絕情,將它和二人的情誼并列雙線敘述,提升了文本的真實性。
小說不僅塑造了英雄和大人物,也為普通人留了一片天地。蘇歌的目光穿透層層硝煙與炮火,落在火焰與灰燼底部的小人物身上,這是網絡軍事小說向反映社會現實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現實主義作家一直呼吁和提倡的。“在一部小說中不能無視這些普通人物的存在,因為在小說情節進展中,他們大都是不能缺少的角色;沒有他們的存在,小說的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10]小說展示的普通人中既有官,也有民,他們鮮明地展示了作家的褒貶傾向。
對民國官員這一地位較高的社會群體,蘇歌時有辛辣的諷刺。通過章太炎調查張學良棄守錦州一事,他批判“大師”們的治學陋習:無事不過問,凡事管三分,并美其為“學問”;張學良公款出國旅游,作家揭露了民國官員心安理得地把公款當家款的丑相,直言“失意政客出國考察無非是拿國家的外匯出氣,在國內都無所作為了去國外還能有所事事?變相旅游、公款購物、吃喝嫖賭什么都干,人生得意須盡歡,難道失意就不歡了(第1部,第12章)?”在批判民國貪腐風氣的同時,敲響當下反貪治貪的警鐘。
活在底層的民眾是創作者窺探抗戰全局的有力工具,也是反映民國社會現實的萬花筒。這個廣闊龐大的社會群體是可愛的,也是可憎的;是聰明的,也是愚昧的。他們看到渾身披掛但全無豪氣的汪精衛,嘴上猛喊萬歲,心里卻罵其無帝王之相、必定短命,外和內的強烈反差讓人忍俊不禁。但這個善良的群體會被日寇和汪偽政府利用而變得愚昧,他們認為自己刀槍不入,以血肉之軀直面冰冷的子彈,既可悲又可嘆。此外,蘇歌創作的思辨力與深刻程度在當代網絡作家中是數一數二的,他把“戲劇的看客”融入這部小說,塑造的大眾形象頗有魯迅筆下的看客色彩。抗日愛國團體的刺客喪命,“聰明”的民眾紛紛感慨:“外面放著好好的事不做,家里放著好好的老婆不愛,去干那些勾當,連年都沒過成,真個傻鳥(第1部,第14章)!”這和魯迅筆下“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的看客何其相似![11]作家嘗試撥開全民抗戰表象下的迷霧,觀摩民眾生活的原生態,不幸的是,他捕獲的是他們依然未得根除的看客習性。伸長脖子、張大嘴巴的看客形象整體提升了小說寫實的深刻性,震撼讀者心靈,引導人們再度深入思考國民性。
這部小說不僅直接刻畫英雄人物,用感情的絲線編織鮮活的女性形象,也用小人物訴說抗戰的大時代,在黑暗的角落管中窺豹。它讓眾生紛紛登上戰爭舞臺,勾勒自己的臉譜,是一幅由抗戰人物構成的“清明上河圖”。
三、回歸傳統:宗教救贖與古典傳承
《最危險的時候》多處借用傳統戰爭文學的寫法,顯示出一種復歸傳統文學的傾向。如果說傳統紙媒小說是位歷經千年風霜的老者,那么網絡小說就是文學與網絡平臺合力誕下的天之驕子。這部小說正是網絡文學與傳統寫作直接碰撞的衍生物,是網絡軍事小說回歸傳統戰爭史詩的杰作。蘇歌直言自己是活躍在網上的傳統作家[12],他借用新體裁破舊小說的制約,雄心勃勃地讓耳目一新的戰爭史詩與傳統戰爭文學一較高下。這部小說披上了網絡長篇軍事小說的外衣,實質上從精神內核到創作手法都是傳統的。它融入了宗教救贖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學一脈相承,是傳統創作邁入網絡平臺的嘗試。
作家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潛意識里伴隨著強烈的宗教傾向。文學在誕生之初便和宗教儀式緊密相連,宗教一直是傳統小說不可回避的主題之一,在《西游記》、《封神演義》等中國古代小說中甚至占據主導地位。這類小說大多突出某一宗教對主要人物造成的精神影響,《最危險的時候》在此基礎上引入了耶佛二教作為深化表述的對象,抓住二者共通的內涵點——救贖,實現傳統文學創作主題的回歸。
基督教認為,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導致人一出生便帶有原罪,難以逃脫懲罰與審判,“但上帝是恩慈的,他并沒有棄絕人類,而是努力救贖他們”[13]。救贖與災難共存,被救者常常經歷劫后余生,因此多心懷感恩。蔣中正被張學良囚禁后,他在見到宋美玲時的第一句話是:“打令,上帝派你來救我么(第1部,第23章)?”這是一個基督的忠實信徒在遭遇危險時的真實想法。前期因拒絕抗日被囚禁,后期各方通力合作而獲釋,這段曲折的人生經歷正是上帝對蔣中正的“罪與罰”。得到救贖的蔣中正是感恩的,在虎口脫險后,他和宋美齡一同慶祝了耶穌的誕辰。此外,救贖常駐于正義與善良之中。中國遠征軍在緬甸面臨絕境,孫立人質問忘恩負義的英軍司令亞歷山大:“我們不過是自救,你們的上帝也是不拒絕的(第3部,第14章)!”借上帝之名對背信棄義的英軍進行審判。此時,幾個美國修女是黑夜中的一道燭光,為遠征軍找到了回家的路。修女是西方現代文學中的經典形象,作家借這群“尋光者”闡明了福音的核心信息:上帝的救贖永不缺席,為善者終將被拯救。“救贖既在歷史中展開,又是上帝已經完稿的書卷。一切文化變遷與國族興衰,都無法改寫此事實。”[14]作品從西方神學的角度重新詮釋歷史,一部抗戰史也是一部救贖史,抗戰的勝利標志著上帝救贖的完成。
在佛教中,這種救贖表現得更加明顯。與上帝這一全知全能的救贖主體不同,佛教主張自救勝于他救。“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他教之解脫言他力,而佛教則言自力,這一切皆系于因果論。”[15]所以,小說中的人多是憑借一己之力涉險度關,化險為夷。并且,佛教主張兼善而非獨善,“有一眾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16]因而通過拯救惡人來弘揚善心是救贖的主要目的。汪精衛叛國出逃,在南海的暴風雨中首先想到的是大慈大悲的南海觀世音;陳璧君在丈夫靈魂出竅、“第一夫人”美夢成真的時候,或是安放觀音的神位,或是“滿心歡喜,一回家就給娘娘上了兩柱印度香(第2部,第36章)”。有求于神,故而敬神、拜神、還愿,這一套功利性極強的信教儀式在封建中國的廣闊大地極為流行。汪陳二人并非真正的佛教徒,他們不能通過修身養性實現自我約束,反而在災難降臨時病急亂投醫,去和觀世音菩薩“做買賣”,令人啼笑皆非。在作家看來,汪氏賣國求榮是可恨的,但他誤把曲線救國當作振興中國之路的執念是可憐的,所以汪陳二人可以自救進而得救。佛教“對中國鬼文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地獄觀’上,與中國固有的冥界觀念相比,佛教的地獄觀突出‘獄’的特點”[17]。佛教的救贖有時會通過適當懲罰來實現,比較突出的就是“夢入地獄”的審判模式。蔣在珍為了抗戰大局鑿河放水淹死數萬無辜百姓,雖是不得已為之,但已然鑄成大錯。他夢到閻王和鐘馗拿著“從未見過的、比最新版辭海還要厚百倍的”生死簿向他討債,醒后“變了個樣,凡事已不再毛遂自薦,自然也不能太落后,整個灰不溜秋的(第2部,第11章)”。從積極為之到碌碌無為,既是佛教對蔣在珍激進處世的刑罰,也是使其懸崖勒馬的救贖之法。
需要注意的是,蘇歌始終對宗教救贖存疑,所以他并未完全肯定耶佛二教的救贖觀。岡村寧次為非作歹卻逃脫懲罰,并為浪跡日本的湯恩伯送終。他是否該被宗教審判?又該如何實現救贖?歷史和宗教給出的答案截然相反。宗教掌握了半部人類史,卻無法改變其中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創作形式,網絡小說一直被看作外來科技文化的衍生品,它與古典文學傳統分離、斷裂,甚至是毫不相干的。蘇歌用這部網絡軍事小說為當代網絡文學發聲,證明網絡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書寫傳統一脈血緣。“這種繼承不是亦步亦趨的墨守成規的效仿,而是在橫向移植的外來參照之下的現代創造性轉換。”[18]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巨大,佛教救贖觀的引入正是網絡小說與傳統古典文學一脈相傳的表現。當然,這種傳承性不僅局限于此,酒與俠、詩性畫面的引入,更加彰顯了網絡小說對古典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酒與俠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創造。古代文人墨客每遇美酒便會俠氣迸射,進而詩興大發、文思泉涌。“酒有興近乎俠,俠生情近乎詩,詩呈美近乎酒。”[19]酒是俠唯一的飲料,酒與俠難以分離,酒與俠一同融入詩中去。有的俠像“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的杜甫,喝了酒是理性的、靜態的,是獨立清醒的;而有的俠喝了酒后變為“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的李白,是感性的、動態的、傾注生命的,是放蕩不羈的。這部小說不乏此類俠形象,尤以張學良最為突出。張氏是介于李杜之間的“時李時杜型”俠客,“酒前和和氣氣,一旦迸發,怒指千夫。廟堂為之震撼。”[20]張氏在喝酒前沉穩內斂、謹慎隱忍,一旦酒入愁腸,便化身“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的李白。他“整個兒陰天邀太陽,黑夜拉月亮,對影成六人(第2部,第32章)”,如此放浪形骸,不就是舉杯邀月、對影雙人的詩仙太白么?他讓衛兵稱自己“酒中仙”,要與其同銷萬古愁,不正是“將進酒,杯莫停”的俠客太白么?讀者在這俠氣四射、酒香絪缊的世界中恍惚迷離:是太白再世化為漢卿,還是漢卿飛升成為詩仙?遭囚禁的張學良看透了人世的生死富貴,在他看來,斗轉星移,不過杯中須臾,且須一盡杯中酒,萬事皆付笑談中。俠形象的完成標志著這部小說達成了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續承。作家若非真正的飲者與俠客,則不能為之;非對二者見解獨到,則不能達成這般渾然天成的嫁接。蘇歌在戰爭敘事中穿插酒與俠兩個古典意象,完成了小說對古典文學的傳承與回歸,古今貫通,一以續之。
中文系出身的蘇歌在創作中直引和化用的古典詩詞不可數計,他運用詩歌塑造詩性畫面,既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守望,也是選擇這種創作方式回歸傳統。西安事變發生,汪精衛的宿敵蔣中正被扣押。作家套用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改出一首《聞雜牌軍西安倒蔣》,將汪氏幸災樂禍、揚眉吐氣的丑態生動地刻畫出來,頗有四兩撥千斤之效;汪氏在南海死里逃生后寫了一首《北宮丸上作》,作家尊重客觀歷史,將其如實收入小說,表明汪氏曲線救國的心路歷程。作家除了給人物要素植入傳統詩詞,還把小說中的環境描寫當作低吟淺唱的舞臺,塑造了詩意盎然的畫面:作者筆下的江南鶯飛草長,春陽普照,春風拂面,滿目蔥蘢,正是白居易筆下“江南好,風景舊曾諳”的縮影;妙高臺好似瓊樓玉宇,宛如人間仙境,令讀者發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追問;黃昏時分,黃河上空“天幕低垂,暗云浮動,飄起了瀝瀝細雨(第2部,第10章)”,與李白《古風》中的“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一句遙相呼應;敵軍將至,長沙城的夕陽褪去金色,云霞像凌空懸掛的巨石。黑云與敵兵在同一時空出現,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觀感……蘇歌用接近詩詞的語言進行場景描述,只用兩句話便涵蓋了文工團冒雨獻藝的場景:“歌聲裊裊入云端、舞步依依收眼底(第2部,第10章)”。他化用古典詩詞塑造美輪美奐的詩性畫面,戰場硝煙彌漫,刀光劍影中流動著殺戮與死亡,但流動著古色古香的詩詞,既增一分凄涼,又添幾許唯美,別是一番滋味。
這部作品在思想上通過救贖向佛耶二教靠攏,在創作中引入酒與俠這兩大古典文學意象,借用古代詩詞精致刻畫戰場,讓紛飛的炮火也變得古風古韻。通過宗教救贖和古典接續,它打通了網絡軍事小說借鑒傳統書寫方式的筋脈。網絡文學不再與傳統文學處于割裂狀態,網絡文學可以借鑒傳統書寫方式,傳統文學也能夠與網絡文學積極互動合作,吸收其中的創新點。這種雙向的流動將不同媒介平臺的文學創作統一在大的文學理論中,對開發更加廣闊的評論資源、引導新的創作和評論方向大有裨益。
結 語
當史料的堆積與創作的欲望一同掀起頭腦風暴,蘇歌不得不面臨夢想與生活的抉擇,他毅然選擇了前者。面對生活的磨難和考驗,溫潤平和的他不予計較,“要當作家,要出類拔萃”的信念堅如磐石。幸運的是,《最危險的時候》這部五年磨一劍的佳作迅速收獲了如潮的好評,無愧蘇歌付出的艱辛努力,也足以告慰對他恩重如山的裴先生。
盡管蘇歌在跋文中稱這部小說僅僅寫了一些“普通不過的常識(第3部,第51章)”,但我們不可忽視這部浩瀚的戰爭史詩在當代網絡軍事小說中的重要性。這部小說“幽默風趣、史料可信、政治正確”[21],完整地保留歷史的真實性,讓我們能夠觸摸炙熱的戰場,傾聽英雄們的心跳并與之一同吶喊。出色的戰爭模型化敘述和涵蓋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物圖繪,使這部小說不僅具備歷史的厚度,也擁有情感的溫度。小說回歸傳統創作的傾向則賦予了自身文學史意義,成就了這部視角新穎的抗戰史詩。
抗日戰爭是華夏民族斗爭史中的至暗時刻,催生了無數血與淚之花在華夏大地盛放。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飽經風霜的中華民族距離“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八十一年。炮火已經熄滅,但輝煌的傳奇已然鑄就,流淌的熱血永不冷卻。憶昔思今,當代網絡抗戰小說之于現代社會尤為重要,我們亟需正視網絡軍事文學在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引導正確的創作和評論方向,這對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建設意義重大。如此,我們不妨重溫抗日戰場的刀光劍影,看那位作家煮一壺濁酒,以《最危險的時候》作筆,蘸墨為畫,以血題詩。
注釋:
[1]引自鐵血讀書網對《最危險的時候》的簡介,參見http://book.tiexue.net/Book24751/。
[2]引自蘇歌與筆者的對話。原文為:“這部抗戰作品費時較長,讓我懂得了許多軍事常識和歷史作用,是個人成熟的標志。”
[3]蘇曉芳:《網絡小說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
[4]同上,參看此書136-140頁。網絡軍事小說可以分為虛擬架空小說、歷史架空小說、戰爭推演小說和新英雄小說四種類型。
[5]潘天群:《博弈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6]孫科偉:《中國藝術學文庫 尋真問美集 藝術長短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頁。
[7]蘇歌:《最危險的時候》,鐵血讀書網,第2部,第23章。下文出自該作品的引用均標明章碼,不再單獨列出。
[8][俄]車爾尼雪夫斯基:《故事和小說的結構》,朱立元主編、張德興卷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 第1卷 世紀初的新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
[9]引自蘇歌對《最危險的時候》的評論,參見h t t p://p i n g l u n.b o o k.t i e x u e.n e t/post_1576965_1.html。
[1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普通人》,黃忠晶、阮媛媛編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頁。
[11]魯迅:《藥》,《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頁。
[12]引自蘇歌與筆者的對話。原文為:“我其實是在網上的傳統作家,讀書人不容易全腦洞。”
[13]閻國忠:《美是上帝的名字 中世紀神學美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頁。
[14]危舟:《與永恒有關的30個觀念 信仰尋求理解》,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74頁。
[15]李小艷:《梁啟超經世佛學思想研究》,佛山市博物館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頁。
[16]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鄢曉霞選編:《梁啟超散文》,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17]靳鳳林:《窺視生死線 中國死亡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
[18]楊景龍:《古典詩詞曲與現當代新詩》,河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9]鄭愁予:《酒·俠·詩》,黃苗子、鄭愁予等主編:《明報·茶酒共和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20]同上,第20頁。
[21]引自網友對《最危險的時候》的評論,參見http://pinglun.book.tiexue.net/post_1606924_1.html。